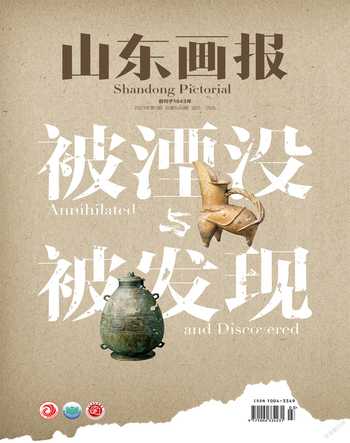直擊現場 圍觀考古
蘇煜軒 李瀟雨



在真正身臨、深入考古現場之前,我們對﹃考古﹄充滿了萬千種想象,層層黃土覆蓋的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又會是怎樣的一段歷史?能稱之為﹃世界﹄,那它一定規模夠大、布局功能夠完善;能喚作『歷史』,那它一定歷經滄桑,卻依然堅定且清晰地記載過去。
但當我們真正立于遺址發掘區的邊緣向四周望去,周邊盡是尚在進行的地產項目,和為符合環保要求覆蓋的嚴絲合縫的防塵網。它們的規模不小,但絕算不上大。墓葬與考古坑道赤裸于天地間,與想象中的威嚴、厚重、神秘確有出入。可就是在這里,入選二〇二二年度山東省五大考古新發現的臨淄趙家徐姚遺址和臨淄區南馬坊戰國大墓雙雙出土。也正是在這里,我們遇見了兩位對考古事業赤誠、熱情的﹃九〇后﹄考古人,他們是普通觀者與考古之間的橋梁,在他們的講述之中,那段被湮沒的﹃歷史﹄和那沉睡中的『世界』終現模樣,且愈發清晰……
現實與想象
本該是三月微涼,但采訪當天的光照與溫度,讓趙家徐姚遺址的副領隊孫倩倩不得不換上薄衫,戴起遮陽帽。在這周邊,建設工程不曾間斷,機械轟鳴聲不絕于耳。躲避深坑與溝壑,攀上爬下,發掘區近在眼前。它看似不大,但對于考古人員手中最長不過一尺的手鏟、刮鏟來說,無疑是一個浩大的工程。若你是小說《盜墓筆記》的忠實讀者或是影視劇《鬼吹燈》的忠實觀眾,那趙家徐姚也許完全不符合你對考古、大墓的想象。但南馬坊戰國大墓不同,這座大墓是目前山東地區正式發掘的規模最大的商周時期大墓。墓道、墓室、二層臺、槨室、陪葬坑……大墓在前,空氣似乎都變得陰涼,讓人確有肅穆之感。
近幾年,“先考古,后出讓”的條幅掛滿了臨淄城,于是,為配合城市建設而啟動的“被動發掘”成了張恒和孫倩倩的“家常便飯”,這次也不例外。2021年5月的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五星頤家所屬地塊開工建設前的考古勘探讓南馬坊大墓初現輪廓,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任命張恒作為執行領隊集結人馬奔赴現場,發掘工作于當年6月底正式啟動。數月后,在南馬坊大墓東南方向約兩公里的地方,趙家徐姚遺址的考古工作在孫倩倩和團隊的發掘、解剖中有序展開。
截至目前,兩處遺址的考古工作仍在持續進行中,但與起初的被動發掘不同,南馬坊大墓“經過近兩年的發掘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獲得了一些新的認識”。張恒介紹說:“2023年,我們通過了國家文物局的審批,將對大墓開展主動性考古發掘。”這為更加精細化的發掘工作爭取了時間和有利條件。“今年的發掘將更注重以學術研究為導向,借助多學科分析檢測技術,讓有關大墓的信息盡可能豐富地展現出來。”而在趙家徐姚,無意中被發現的距今1.3萬年左右的“紅燒土”,被認為蘊藏著近百年來“第一次”發現、可以改寫山東考古史的重要信息,這足以讓整個考古界興奮驕傲。
微小與宏大
“土”能有多重要?這是作為外行人的我們無論如何都想象不到的。但在趙家徐姚,地層剖面上一條條看似彎曲實則相對筆直的“長線”為我們揭示著答案。
紅燒土,多以燃燒產生的灰燼層與著火后略帶紅色的泥土層組成,而所謂長線,是考古人員以一層粉砂一層黏土為規律劃出的地層序列。通過系統研究及初步測年,共計17層的地層序列中,4至16層的砂黏互層年代范圍應為距今1到1.5萬年。其中,有大面積紅燒土堆積的地層貫穿8到13層。
令孫倩倩和團隊十分不解的是,第8到13層中雖存有紅燒土痕跡,但卻未發掘出任何人類遺物與遺跡。火從何來?又是為何會產生如此大面積自然態的紅燒土堆積?“我們做了實驗,也查閱了很多資料,確認這可能與火對景觀的改造有關。”孫倩倩說:“用火來進行景觀管理,是人類改造自然方式的巨大進步。靠火清理地塊,可以使資源富集,也可以掃清障礙、便于活動,獲取更好的視野。”可以說,第8到13層中紅燒土的存在,是這一階段人類用火改造自然的最直接證據,也足以證明,人類正在改變舊石器時代攫取式的生產方式,向新石器時代主動改造自然邁進。
與紅燒土一同被發現的,還有第10層,距今1.32萬年左右保存完整的古人活動營地,以及出土的千余件遺物。其中的200余件陶片是目前中國北方地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陶片。“這些陶片展現的制陶工藝好到超乎想象。跟距今1萬年至9000年的上山文化陶器有些相似,都是夾炭陶。”孫倩倩興奮地描述道:“陶器的口沿有圓唇的,有方唇的,還有花邊的。陶片厚度約0.7厘米,質地均勻,器型規整且豐富,與此同時,已被證實出現在新石器階段的磨光工藝,在這些陶片上也有應用。這就意味著,成熟制陶工藝在山東地區的出現時間一下被提前了4000多年。”
比起趙家徐姚這幾捧極其容易被人忽視的“土”,“南馬坊大墓附屬車馬坑內的車和馬基本上保持了下葬時的姿態,車子的構件都十分清楚,還發現了規格較高的一車四馬”。更值得一提的是,兩個殉馬坑都在距大墓25米之處,“從位置關系、排列方式上看,都能確認其與大墓的歸屬關系”。“甲”字形墓葬在臨淄雖不稀缺,但“有明確主墓和殉馬坑,布局完整、結構清晰、規模龐大的大墓并不多見”。張恒解釋說。
過往與未來
如此規整的狀貌,如此高等級的墓葬形制,我們自然好奇,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誰?問及此,張恒避而不答:“一是沒有一錘定音的考古線索,二是這并不是考古追求的唯一目標。”
近幾年,考古的理念、目標都在轉變。“墓主身份、墓的體量,甚至出土的文物的大小、多少,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遺跡現象所蘊含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價值,就好比,哪怕只是一個陶片它也是有溫度的,它的背后是制造它和使用它的人,是歷史的無窮智慧。”張恒飽含深情地說。“墓室填土中清理出的木結構帷帳以及大量安裝木柲的青銅兵器和工具,是研究齊國喪葬儀節、建筑形態以及手工業生產技術的重要實物資料。車和馬作為戰國時期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此次發掘出土也是齊國綜合國力和造車工藝的生動體現,甚至可以為我們進一步了解齊國馬匹的種屬、飼養、管理等信息提供幫助。”張恒稍作停頓,“這座墓規模宏大、建造考究、裝飾華美,基本可以確定,墓主身份是不低于上卿一級的齊國高級貴族!”這樣的答復“四舍五入”也算是為我們揭秘了!
而對于將史前作為研究方向,對史前考古工作有著更高熱情的孫倩倩來說,“史前更有意思,因為它是人類未知的!這段歷史、這些信息是靠我們史前考古人書寫,是我們親手發掘的啊”!孫倩倩是我們公認的、這些天接觸過的考古人中最活潑的一位,講出這些話時,她神采飛揚的樣子,深深地感染了我們。趙家徐姚遺址是華北地區乃至東北亞舊新過渡階段的重大考古發現,填補了山東地區史前考古的關鍵缺環,被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稱為“打開了一扇門,開啟了新天地”。
3月28日上午,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臨淄趙家徐姚遺址經過層層篩選最終入圍。細看名單,我們不難發現,如今評選的考古新發現不再以出土多少器物為獲評標準,而是更注重遺址的文化價值和學術價值,這就意味著國家對考古工作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
工作當中,張恒和孫倩倩平和沉穩、嚴謹細致,甚至不茍言笑。工作之余,兩位年齡相仿的年輕考古人也會到彼此負責的發掘區轉轉,聊聊最近的新進展,交流發掘困惑與心得。正如他們所說:考古工作永不重復,每個現場都有它獨特的價值與魅力,重要的不是“它是誰”,而是“怎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