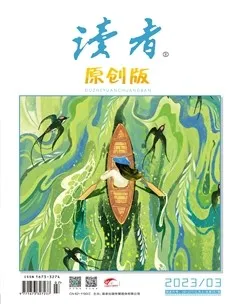一個年輕人躲去南極
吳向娟
一
來南極之前,我從不知道海能幻化出這么多種顏色。我看見晚霞從天邊傾瀉而下,把海染成金色;我也見過綠色的海,像是在白色荒漠里淬出的一塊翡翠;當船隊漂浮在翻滾著黑色浪花的海上,則有種在末日里狂奔的感覺。
每當遙遠的海岸線上浮起看上去松松軟軟、形狀不一的雪白“糕點”,我就知道要靠近島嶼了。這時候,我會站在窗前,沉浸在獨屬于南極的浪漫時刻中。
春節期間,漁船要深入南極洲內部,船上會徹底斷網,并將持續4個月。此前,大家都忙著給家人發消息報平安,我卻感到無盡的自由正朝自己走來。
初到南極,眼前的一切都令我興奮。有時是十幾米長的鯨浮上水面噴水換氣,在遠處濺起兩米高的水花;有時是成群的企鵝站在冰山上眺望船隊,用嘶啞的叫聲向入侵者發出警告;我們還遇到過被塑料袋、繩子纏住的海豹靠近漁船向人類求救;當誤捕到帶有劇毒的章魚時,船員們就慌慌張張地將其往海里放生。
搭上去南極的船,對我來說是一場逃離。畢業后的3年里,我一直沒找到想從事的工作,對未來的生活也是滿心迷茫。陷在渾渾噩噩的日子里,我如同一艘下沉的船,逃離是一場迫在眉睫的自救。
然而,上船不到10天,我的皮膚就開始瘙癢、皸裂,被船上的醫生診斷為海水過敏,給我開了些涂抹的藥。冰山折射的光穿透玻璃,將我的鼻尖照成藍紫色,映襯出我潰爛的紫紅色臉頰,新舊交疊的疤痕層次分明。
傷口難愈,一遇風就灼痛,嚴重時人還會發燒。過敏的人一般不會在船上久留,而我已經待了一年。我喜歡南極的偏遠和冷清,這兒離我的家鄉和不如意的生活足夠遠。
我所在的漁船負責在南極海域捕蝦,常年往返于南極和舟山之間,出行一趟需要20個月。應聘需要考取船員證,再交一筆3000元的中介費。我以高分通過考試,最終獲得這份工作。出發前兩天,我告訴父母我要去南極了,一個月工資一萬多。父母很滿意,覺得我終于找了一份正經事做。

曾經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和父母一直處于拉鋸狀態。高考結束后,他們就替我規劃好了未來。但這周密的安排卻成為束縛我的繩索,越掙扎,越疲憊。
因為高考成績不理想,我只能去讀大專。從那時起,父母對我的前途不再抱有希望。他們咨詢了開連鎖餐館的親戚,認為做廚師是理想、務實的選擇。17歲的我只好聽從父母的安排,進入了一年花費高達10萬元的廚師學校。
為了不辜負父母的苦心,學廚過程中,我絲毫不敢懈怠,學不好還自己躲起來偷偷練習。但日子久了,我發現自己并不快樂,只是在被動完成任務。這不是我未來想從事的職業。
抵觸的情緒總是不自覺地流露。做菜時,我頻繁走神,有時還會頭暈眼花,喘不上氣。我計劃著如何跟父母開口,從這個自己厭惡的專業中解脫。一次寒假,我在父母的要求下準備飯菜。我故意表現得技術生疏,母親忍不住質問我原因,我趁機表達了內心的痛苦。“花了這么多錢,你說不上就不上了,你以為家里很有錢嗎?”沒等我說完,母親就打斷了我,父親則在一旁保持沉默。
無法掙脫被規定的生活軌跡,我只能回校完成大專最后一年的學習。畢業后,我先后輾轉廈門、蘭州和杭州,換過3家餐館。我討厭鍋里濺出的油、冒起來的煙、高溫的空氣和狹小的廚房。廚房里來來往往,腳步急促,所有人都神經緊繃。困在廚房的日子讓我感到絕望。磕磕絆絆干了 一年半后,我再也堅持不下去,最終決定辭職。
與其說我逃離的是一份不喜歡的工作,不如說是逃離父母無處不在的掌控欲。從小到大,父母一直對我要求嚴格。上學時,成績是他們評判我的唯一標準。工作后,這個標準換成了薪水。稍偏離預期,他們就會強制干預,連工作都要替我安排。默默服從了20多年后,我迫切地想改變現狀。
2021年8月,我無意間在手機上刷到一則船員招聘廣告,密密麻麻的文字中,“南極”兩個字瞬間抓住我的眼球,令我生出遠離家鄉的沖動。我想象著把自己丟進海里,在一片湛藍中縮成一個無人在意的黑點,這讓我感到無比放松。我決定去南極,逃離這令人泄氣的生活。
當漁船在一片轟鳴聲中緩緩駛離岸邊,眼看城市的建筑群逐漸變小,最后被拉成一條直線。我發現自己對陸地毫不眷戀,甚至還享受這種與現實生活失聯的感覺。
二
能逃離現實,首先得益于忙碌的工作節奏。
在船上,我先是被分配到廚房,后來又去冷凍室做搬運,忙碌時也參與綁船、掛包、編纜、捕網等工作。大家累得從不失眠,船翻了都能睡著。每到休息時間,我都累得睜不開眼,跌跌撞撞摸回宿舍,倒頭就睡。我感激這份辛苦的工作,讓我沒時間再去想那些陸地上的煩心事。
漁船在幾百平方米的海域來回作業,我們把漁網撒下去,固定好,幾小時后再用機器打撈上來,一次能撈40噸蝦,然后打包、裝箱,搬往冷凍室。漁船實行6小時工作制,每工作6小時可以休息6小時。這是一份體力消耗極大的工作,半年下來,我從170斤瘦到了125斤。
在高強度的壓力下,與我同期上船的3個船員工作了半個月就吵著要回家,3個月后才等來一艘貨船,將他們捎回去。
一艘小小的漁船,仿佛一個真空環境,很多社會規則都不復存在。船上人際關系簡單,大家上船的目的都很明確,有人是為了躲避債務,有人只是想撈一筆快錢,我們很少關心、討論彼此的過去。我在這里肆意解放天性,這是我在陸地上從來不敢做的事情。
在南極,我有了與家人切斷聯系的正當借口—沒網。很多次,我站在甲板上,望著南極海域,恍惚間覺得天地之間只有自己一個人,逐漸感到心胸開闊、呼吸順暢,心情也好了起來。時間一久,我產生了一種錯覺:仿佛自己一出生就在這艘船上,而陸地上的一切不過是一場夢。
我厭倦在鋼筋水泥的城市與嘈雜的人群中穿梭,按部就班的工作令我興趣索然,復雜的職場關系對我是一種折磨。我不具備在社交場合游刃有余的能力,比如健談、幽默、察言觀色。從前去一些應酬的飯局,我總是張不開嘴說一些漂亮的恭維話,徒增尷尬。在陸地上,我需要費力地扮演一個能被社會接納的人,這令我感到疲憊至極。
為了掙脫內心的枷鎖,我不止一次沖破社會規訓,放任自己去做一些不符合社會期望的事情,仿佛這樣才能感受到活著的樂趣。
放棄成為一名廚師后,我曾獨自前往新疆旅游,這種反叛給我帶來了自由的快感。我盡可能去體驗,滑雪、騎馬、射箭、跳傘、徒步……僅一個月,我就花光了一年的積蓄,連買火車票的錢都沒留下。但我沒打算返程,而是在當地果園打零工,摘了3個月蘋果,一天200元。
父母在電話里責怪我不務正業,這進一步刺激了我脫離“正軌”的沖動。我發現,只要不聯系家人,就能獲得短暫的寧靜和自由,擺脫畏畏縮縮的狀態。我嘗到了失聯的甜頭。
從新疆回來后,一份去貴州六盤水山區支教的工作打動了我,父母知道后,毫不掩飾對我的諷刺:“自己都掙不到幾個錢,還想幫別人?哪個學生需要你這樣的老師?”父母的態度反倒令我產生了一絲叛逆的快感:一定要去!
與之前的幾次反叛不同,南極的工作因為有不低的報酬,所以并未遭到父母的反對。但我在意的并不是這份薪水,而是這遙遠的無人之境能讓我暫時擺脫控制。父母遠在萬里之外,即使再想伸手,最多也只能打個電話。
三
然而,即使逃到再遠的地方,“桃花源”仿佛也僅存在于想象之中。在漁船上工作的辛勞和身處南極的孤獨感,時間一長也很難抵御。
漁船順著太平洋西岸一路向南,抵達南極,單程耗時兩個月。前往南極的興奮很快被生理的不適沖淡了。我沒料到自己會嚴重暈船。漁船一旦撞上大浪,房間里的東西就會紛紛掉落,在地板上來回滾動,人更是站不穩,只感到頭昏眼花,胃里翻江倒海,持續幾天后體力就變得極差。
2022年10月末,南極迎來極晝。兩個月里,我所在的海域每天白晝長達20小時,太陽終日掛在頭頂,白色的日光像火焰一樣燎得人焦躁難安。我們的作息也變得紊亂,只能困了就睡,但睡覺時總會被門外的腳步聲吵醒,晝夜和虛實都失去了界限。
為了遵守《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每年漁船只能在2月至7月作業,剩下的6個月,我們待在船上無事可做。2022年7月,我第一次經歷極夜,每天中黑夜長達20小時,這是漁船最清閑的一段時期,時間變得無限漫長。
無工可做的時候,我們強迫自己睡覺,一睡就是十幾小時,醒來總是頭疼。我整天躺在宿舍里讀小說、看電影,直到把船長拷貝的50部電影看完了,自己帶的小說也翻遍了。
極晝時白天還能拉上簾子,極夜是真讓人著急。漁船被黑夜和涌動的海水吞沒,透出點點微光,夜長得令人心慌。我站在甲板上,生怕海里出現龐然大物把自己拽下去,恐懼黯然滋長。
我曾渴望把自己拋向虛無,最終發現徹底的孤獨令人難以忍受。在條件有限的南極,漁船漸漸成為一座與外界失聯的孤島,這對有社交需求的人來說很難適應。
整艘船只有食堂有網絡,網費一個月100元,網速很慢,發消息總是延遲,一張圖片需要5分鐘才能上傳成功。打電話則需要衛星通話,100分鐘200元。除了個別熱戀中的船員,船上大多數人都不會使用這個功能。
我不愿和熟悉的親人朋友聯系,但無法完全做到切斷與社會的連接,于是轉而去社交平臺上結識陌生人。坦白講,誰不希望獲得理解和認同呢?我幾乎每天都在網上更新南極的見聞,異域的風景引來一些網友圍觀,但我們的交談僅止于聊一些新奇的經歷,沒人關心我的內心世界。我好像更孤獨了。
一年過去了,南極對我已經不再具備最初的吸引力。現在的我,不再總去甲板上望著遠方發呆。再新奇的事物,天天看也就那樣。最極致的體驗擁有一次就夠了。在日復一日的單調中,我對陸地的向往又回來了。
一次,漁船遭遇了一年里最猛烈的風暴,船在狂風巨浪中搖搖晃晃,物品在房間里飛來飛去。那一刻,我以為漁船要完蛋了。出于強烈的求生欲,我抓緊床邊的欄桿,腳底卻一直打滑。這種狀況持續了一整天。真到了危急時刻,我才發現還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活下去。這次事故,讓我看清了自己內心深處的欲望。
我越來越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自由、輕盈地活著。我不想像一些老船員一樣,在船上一待就是10年,被磨得毫無生氣,無論是面對震撼人心的美景,還是險些葬身大海的險境,都表現出程序化的從容。這趟南極之旅還有7個月就要結束,我知道,自己必須下船了。
在我前25年的人生中,支教是我唯一懷念的經歷。我去支教的學校建在半山腰,只有不到100個學生。這里的中年人多數外出打工,留下這些孩子。他們很少有機會讀課外書,課余時間還要割草、放牛。我自費買了30本課外書,游說各家老人讓孩子們周末來學校。
支教的一年中,我終于體會到被愛、被需要的感覺。孩子們為了答謝我,總是從家里帶來好東西,有時是10個土雞蛋,有時是一只拔了毛的公雞,也有父母外出買來的柚子、哈密瓜。結束支教后,我也總收到孩子們的問候,跟我打視頻電話聊天時,他們毫不掩飾心中簡單、熱烈的情感。在地球的一端漂泊一年后,我發現自己仍然心系那個小山村。
在漁船上工作,我攢了18萬存款,足夠我在陸地生活一兩年。我計劃回到陸地后先買一輛摩托車,環中國騎行一圈,然后見一見在社交平臺上認識的女孩,最后回山區支教。這一次,我希望自己能更堅定內心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