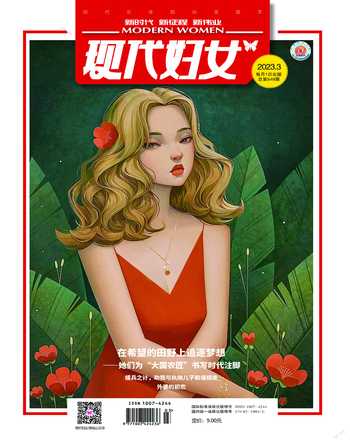《初為人母》:成為母親的獨特經歷
夏麗檸

《初為人母》(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1月版),由英國社會學家、作家,倫敦大學學院社會學和社會政策教授安·奧克利撰寫。作為英國社會學協會終身成就獎得主、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學院榮譽院士,奧克利教授長期致力于性和性別、家務、分娩、身體社會學與女性主義研究。本書通過收集整理66位母親的訪談,了解她們“生兒育女”的經歷,旨在幫助女性在“初為人母”的過程中,學習如何達到充分的自我認知。與其他同類書籍相比,本書的有趣之處在于,初版37年之后,作者及其采訪團隊對當年受訪者中的36位進行了再次訪談。
相較于初版,本書增加的內容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年人對話。受訪者不再是羞澀的20歲出頭的姑娘,而是年齡在55至70歲之間的女性。她們在經歷生死疾病、工作變更、人際變化、喬遷輾轉之后,又重新回憶起年輕時經歷的事。不論對讀者還是她們自己,重談“初為人母”的人生經歷,都具有非凡意義。
選擇成為母親,并不簡單
法國社會人類學研究者皮埃爾·克拉斯特,在《瓜亞基印第安人編年史》中,別開生面地描述了瓜亞基印第安人的分娩場景:母親皮楚基在奮力生產,而丈夫顯出了極度的焦慮與不安,因為在部落里,有妻子生產會給丈夫帶來不祥的傳統觀念。
但現代社會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思想束縛下,反而認為女性應該以生育為天職。“成為母親”,成了一種隱形“制度”。
與此同時,資本主義體制里,不分性別,人人都是重要的生產力。現代社會無法為了幾個孩子,放棄女性勞動力。奧克利在書中強調:“品鑒當今工業化社會中母性的歷史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在當前的母性歷史上具有獨特性。”如此說來,“選擇成為母親”的決定也并不容易。
書中,得知懷孕后,受訪者中有52%的人感到高興,38%的人情緒復雜,10%的人惴惴不安。這說明,超過一半的女性對生育有期待,甚至將這個過程浪漫化。奧克利對“備孕”做了耐人尋味的描述,她說,夫妻間所謂的懷孕計劃,無非就是想要孩子的一方情感占上風的委婉表達。無論如何,因懷孕導致的身體和心理變化,都標志著女性邁出了成為母親的第一步,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
就女性而言,成為母親,意味著有可能“放棄工作,待業在家,隔絕或是結交新朋友;再到婚姻、母子關系、生產時的醫療管理帶來的影響等”。由此看來,成為母親,并不僅僅是某個女人的重要事件,更是全體女性歷史上的里程碑。
從分娩到養育,帶來諸多變化
隨著現代醫學進步,借助諸多藥物與技術手段,自然分娩與女性的距離越來越遠。由此帶來的影響是,孕婦不停地奔波在去醫院做各種檢查的路上,有時感覺自己不是孕婦,更像個病人。而且,醫院為孕婦設置的所有檢查,好像只有一個目的:生一個健康的孩子。有些產婦甚至覺得自己像個生育的工具。
身邊人對孕婦的態度,同樣令其不堪重負。如果說男性同事的另眼相看,使孕婦有些許不適的話,那么丈夫對懷孕的妻子的視而不見,更令她們匪夷所思。其中一位受訪者的丈夫委屈地辯解,沒有看到孩子生出來之前,他總想不起來妻子懷孕了,仍然像平日一樣,支使她做各種各樣的事情。
分娩,意味著疼痛與危險。盡管當時開始采用“硬膜外麻醉術”緩解分娩痛苦,但仍有很多孕婦拒絕使用。而在40多年后的今天,這種麻醉術依然會由于患者體質或者有基礎病而產生副作用,甚至使產婦失去生命。
我們經常在電視劇中看到“保孩子還是保大人”的情節,它實實在在地每天發生在產房門外。由此引發的“生育權”的問題,至今難有結論。與母親和孩子生命息息相關的問題,在醫院標準化的分娩流程里,仿佛不值一提。
養育,為母親帶來了人生決定性的變化。據統計,女性患有“產后抑郁”的概率從5%至80%不等。究其原因,是產婦對不確定因素以及育兒經驗不足感到焦慮。沒有一位初為人母的女性是訓練有素的。由此,與生俱來的母性和醫學養育產生了沖突,正如至今持“母乳喂養”還是“吃奶粉長大”兩種不同觀念的人,仍然涇渭分明。就像一位丈夫抱著初生的嬰兒,激動地說:“終于看到孩子來到這個世界了。”而一旁臥在產床上的母親鄙夷地想:孩子不是早就來了嗎?從在我肚子里,孩子的生命就開始了。
生兒育女,爸爸去哪兒了
在生養這件事上,父親始終處于模糊地位。奧克利在書中寫道:“父親的作用好像局限于貢獻精子;而母親則意味著承擔拉扯的重任。”
事實上,父親也同樣承受著生兒育女的重大壓力。由于新生命的到來,父親的日常生活也被打亂了。我們的社會又常常從經濟學的角度定義父親,認為“父親是買面包的人,母親則照顧家里”。
現代女性經常用“喪偶式育兒”調侃父親。殊不知,新生爸爸與媽媽一樣,毫無經驗可談。而且,男衛生間里沒有給寶寶換尿布的設施,好像這個社會從未期待過男人做這種事。若想成為真正的爸爸,恐怕得從換尿布開始。
隨著孩子的到來,夫妻關系也會產生極大波動。懷孕時,夫妻都很興奮,因為那是雙方共同的成就。小孩出生,新生命點燃了雙方的溫情,夫妻感情達到了頂峰。然而,當照顧嬰兒成了母親的責任之后,雙方的感情也隨之惡化。
正如奧克利所說,孩子出生以后,父母劃分為不同的角色。將一個孩子帶大,是份孤獨的工作。無論女性多么想要孩子,多么想照顧孩子,由此帶來的生活中機會和選擇的減少,都需要母親進行自我考量后去長久承受。
在受訪者中,成為母親這件事被認為是困難的,僅占36%。由此可見,成為母親的經歷,依然是很多女性生命中最獨特、最值得回憶的高光時刻。
無論是否選擇成為母親,希望每位女性朋友的人生里,都能為自己自由的靈魂唱起一首歌。
(摘自《中國婦女報》)(責任編輯 王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