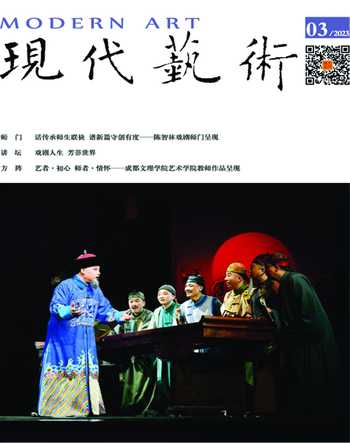縱筆揮灑皆山水
李熙斌
作畫時心中激情澎湃,其畫作表露出恣意縱橫,也精于精雕細鏤,用筆大膽凝重;善于用線勾勒,風格強悍;滿構圖的大景山水,追求層次繁富的縱深感。
曾曉滸的山水畫,著稱于湖南乃至國內畫壇。之前,在“湖南著名美術家推介工程——曾曉滸藝術展”中,其展覽的《江山臥游圖》《峽江清嵐》《粵北江山紀游圖》等山水畫,以湘、蜀、粵的山川為題材,點畫間把訪粵北之山川、涉巴蜀之峰巒、探湘山之煙霞的山水,將主觀的情境與客觀的物境熔為一爐,意境高曠,空渺清麗,在瀟湘大地上成就了可堪當代巨匠的藝術人生。
曾曉滸1938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其家是書香門第,他自幼秉承家學,少年時期輾轉求學于重慶、上海、桂林、武漢等地。寓居于上海期間,跟隨父親拜訪張大千大師,觀其作畫。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他考入廣州美院國畫系,得到嶺南畫派大師關山月、黎雄才先生的悉心指導。于廣州美院打下筆墨功底,浸潤流風余韻,幾十年來從事美術教育,筆耕硯耘,教學相長,他深切地體味到中國傳統繪畫的獨特性,以及如何純化這種獨特性。因而,他錘煉與深化他的筆墨語言、文化語義和中國文化特有的積學養氣。他始終以“真”字為自己的創作原則,提出“真情、真境、真筆墨”的藝術主張。在描繪湘、蜀、粵的自然山水時,他將個人審美和時代新風緊密結合,把嶺南畫派“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的藝術理念融入畫中。力取傳統精華,不唯一家是囿,廣覽大化神奇,卻裁自家風貌。雖為蜀人,卻具湖湘、南粵之氣。其山水畫風格,既有“北宗”之雄強,又有“南宗”之秀潤的語言特色。藝術大師黃永玉曾經說他:“曾曉滸是蜀中才子,一直為湖南奉獻,他的畫在湖南乃至全國,都是一流水平,可堪當代巨匠”。例如,他的代表作《南天獨秀》懸掛于人民大會堂湖南廳,《韶山》被毛主席紀念堂收藏。毋庸置疑,曾曉滸是湖南美術界極具代表性的山水畫大師和杰出的美術教育家。
中國山水畫的最高典范,宋元山水在筆墨趣味、審美取向和空間架構上有較大區別。北宋山水峰巒峻厚,氣勢雄壯;南宋山水清幽奇峭;元代山水則天真超逸,清雅脫俗。若以文人畫視角評價,兩宋山水甚至高矣,以平淡天真、蕭散簡遠而論,可推元人山水格高無比。正如黃賓虹大師所言:“宋畫如酒,元畫如醇,元代以下,漸如酒之加水,時代愈近,加水愈多,近日之畫已有水無酒,故淡而無味”。北派山水以荊浩、范寬、郭熙為代表,所作山水峻厚、險絕,筆墨黑焦少不渾。南派山水以董源、巨然、米氏父子為代表,多畫煙江遠嶺之景,筆墨清淡淹潤。曾曉滸在臨摹古人皴法、樹法、石法、云法等以掌握規律,通過以筆墨去認識自然、認識繪畫,得以完成從思維方式到表現方法上向山水畫傳統的真正回歸。他秉承其深厚的書法功底,以線寫形,以形謀篇,以篇成境。所作山石、樹木、亭橋、煙云無不如精詞麗句,信手拈來,為我所用,構成華美篇章。他雖然屬于學院派,但不囿于物形,渴于思慮,故無畫外妙致。
曾曉滸的畫境高遠,妙手偶得,是鐘靈毓秀,更是形似而神豐的藝術佳作。他青少年時期生活的成都,方圓幾十、百公里的青城山、峨眉山、四姑娘山等,溪山樹石,煙巒層林,鳥語蟬鳴。他知水樂山,以山為樂,以水為知,以空為悟。創作的《古柏行》《迢遞三巴路》等作品,頗有南北相融、雄秀神奇的巴山蜀水的自然審美特征。《古柏行》的筆墨豪放蒼勁,以少勝多,以簡就繁,尺幅之間,體千里之遙。幾株柏樹枝干挺拔直上,樹枝茂盛成蔭,設色清麗秀潤,氣氛寧靜幽雅,開合有度,頗得章法。構圖簡賅而意蘊深遠,層次分明而水墨淋漓,使人有云天蒼茫、遼闊無際之感。《迢遞三巴路》描寫筆法獨具,韻致清幽。山間怪石嶙峋,絕壁聳立突兀,古松參天遮日,崖間曲徑通幽,梵音繚繞于耳。一大隊人馬負重踽踽在三巴路前行,路途迢迢不知遙期。曾曉滸用小筆依山石脈絡勾出結構,勾出樹干變化豐富、層疊繁密的樹葉,又以行云流水的墨線,表現出煙云霧靄與川流不息的山泉。觀其畫,仿佛聽到瀑流的巨響,叢林的喧嘩,松風的呼嘯,似一曲醉人的交響曲,其超凡脫俗的意境扣人心扉。《峽江晴嵐》描繪的是一幅雄奇偉岸的三峽圖,兩岸懸崖絕壁疊嶂,連峰接天,峻壁屏立,煙云繚繞。峽口江水奔騰,水勢湍急。近景舟行其間,時而絕壁前阻,“山塞疑無路”,忽而峰回水轉,“灣回別有天”。一個高士佇立崖石上,若有所思,凝眸望遠。曾曉滸在畫中謀篇布局,突出了三峽的兩岸絕壁奇峭突兀的特點,筆精墨韻,氣韻天成。濃筆重彩地描繪了巴蜀峰巒偉岸的巍巍英姿和勃勃神采,以精致的筆法表達三峽煙雨迷濛之韻致,整幅畫作氣勢雄峻,嵯峨壯觀。
傳統繪畫常見的藝術符號,在曾曉滸的筆下是富有生機和活力的。松下撫琴的高士、千仞絕壁的行者、蕉葉臨池的高僧、揭竿平糶的民眾,乃至高山深壑、扁舟雅士、山石老樹等,浸潤著文化精神和古典情懷的意象,都在爽健淋漓、氤氳放逸的筆墨語言中幻化而出,成為他筆下常見的題材。千山萬壑皆入胸懷,山水風物用之不竭,體現了他的精神取向,折射出深刻的詩性內涵,是他的文化和美學品位的具象化,體現著曾曉滸對中國藝術本質韻味等藝術審美的特性,有著深刻領悟與把握。曾曉滸對中國畫的意境創作、意象造型、筆墨韻味等有著極高的造詣。他將傳統筆墨服務于真山、真水、真境的營造。《粵北江山紀游圖》是曾曉滸去粵北的韶關一帶的沿途寫生后創作的作品。畫面里他從寫實觀念進入寫意觀念,從對景寫生轉為胸中丘壑。山崖具有粵北的顯著特征,險峻的崖石上鑿出一條山路,幾個行人在匆匆趕路。曾曉滸很善于用水。以中國畫的特質而論,用筆之妙在于氣,用墨之妙在于水。氣是一個具有哲學先驗論意味的概念,在中國文化中淵源既久,影響最大。畫面中把江河的水流動表現出極具生命活力。墨因水的暈染流動作而形成豐富的層次感,借助于水將氣的流動感展現出來,賦予畫面以生生不息的鮮活感。曾曉滸把水的運用可謂得心應手,對水之多少、輕重、薄厚的適當調控,從而使得其畫氣脈通暢,松動而不散漫,緊湊而不逼仄,柔和朦朧與渾厚華滋相得益彰,而絕無心有滯礙、手迷揮運而帶來的混沌污濁,可見其筆墨描繪高超的大師級技法,把粵北的濕潤、空靈和充滿生機的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
觀賞曾曉滸在湖南美術館展出的《云淡赤崗溪路悠》《尋常蹊徑亦幽然》《江山臥游圖》《流霞光映暮秋天》等山水畫突出的特點:作畫時心中的激情澎湃,其畫作表露出恣意縱橫,也精于精雕細鏤,用筆大膽凝重;善于用線勾勒,風格強悍;滿構圖的大景山水,追求層次繁富的縱深感。畫作表現出的是樸直、精深、率意而大家的風范。中國畫講用筆、講氣韻、講格調、講境界。古人論畫:“堅質浩氣,高韻深情”,道出了質、氣、韻、情四個畫品必須具備的概念。概念要明確,堅質蘊藏于浩氣,高韻發源于深情,氣韻皆源于畫家情感所發,故以情導氣,以情行韻是毋須置疑的。筆主形,墨主象。筆墨通過畫家的審美滲透與營建,形成了自已創作的獨特審美形象。曾曉滸的這些作品,吸收諸多古代和當代大師之精華,如八大的空靈簡約,石濤的空幻多變,虛谷的高雅,黃賓虹的遒勁蒼勁等,從而使其作品達到至高的藝術境界。這種境界正如宗炳在《畫山水序》所述的藝術境界:“圣人含道映物,賢者澄懷味像……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他的上述作品的筆墨語言與藝術形象的二者體現出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就是這種境界。《尋常蹊徑亦幽然》畫面,點線面變化有致,寫形更寫意。近景是幾堆巨石崖下辟出的蹊徑上,一個牧羊人趕著羊群,另一個牧羊者停下自行車在等待羊群。山體、巨石、樹叢、枝丫用筆老辣,用中鋒提按得當,變化隨之所欲。筆力雄厚,不乏古人屋漏痕,錐畫沙,高山墜石之境界。作品用墨淋漓,運筆穩健而靈活,章法生動而傳神,以雄奇的峰巒和滾動的煙云支撐畫面。墨色濃重,線條剛勁,皴石堅硬,具體地體現出大自然巍峨壯麗與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同時體現了曾曉滸對人生世界的體悟,是當代的山水大師級的美學蘊含,并有禪意般的玄境。他以其獨有個性、獨行的審美理想和藝術語言,創造了一個典范明凈、蒼茫雄奇的山水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