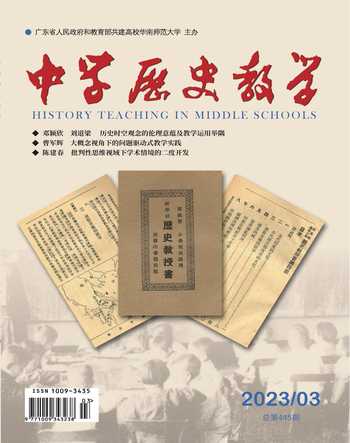將歷史學習引向深度
張兆 金曹剛
學習方式的轉變是新課程改革的起點,直接影響著教學方式和評價方式的變革。“雙新”背景下強調要讓學習深度發生,這是培育學科核心素養的重要途徑。那該如何將歷史學習引向深度呢?選擇性必修教材呈現了大量的知識、概念,相較于綱要更難駕馭,教學邊界更加模糊,并指向了更高水平層次的素養要求,對廣大教師來說無疑是一大挑戰。對此,筆者以《中國古代的法治與教化》為例,嘗試找到歷史深度學習的正確打開方式,以期實現對學科核心素養的有效培育。
一、深度學習應從揭示問題開始
就目前教學實踐來看,選擇性必修課的教學容易囿于知識的梳理,思維單一。不存在脫離了知識的能力,更不存在脫離了知識和能力的素養。[1]但如果對知識的學習不與問題解決相結合,教學是無效的。中國古代法律從先秦成文法產生到唐朝中華法系的形成,宋以后基本沿用唐朝法律體系,體現了中國古代一以貫之的法治傳統。教材選擇先秦、秦漢至隋唐、宋元至明清等重要時間節點,呈現了德治與法治在不同時期的發展狀態。對此,引導學生深入了解其發展狀況、成因是教學突破的關鍵,抓住問題至關重要。鐘啟泉教授指出,深度學習并不是從傳遞特定知識內容的教科書開始,而是從揭示問題開始的。[2]那本課要揭示的問題是什么呢?
高中新課標在“實施建議”中指出,選擇性必修課程要求教師“把握每個學習專題所涉及的范圍、重要史事和核心問題,并將這些核心問題的解決與學生歷史學科核心素養的發展聯系起來”[3]。中國古代的法治與教化是封建國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二者是對立與統一的關系。深入分析教材會發現,儒學的發展是隱性主線。因此,結合教學內容的邏輯層次,本課要揭示的問題有:一是先秦時期成文法出現后引發德治與法治思想之爭的實質是什么?二是中國古代如何通過德治與法治治理國家?三是儒學的發展是如何影響古代教化形式的?
李劍鳴認為,建構一種歷史解釋,就是要圍繞一個具體的歷史問題。[4]對于不同時期的講述,要整合綱要與選擇性必修教材相互銜接的教學內容,抓住歷史階段特征展開敘事,力求獲得通透的歷史認識。圍繞問題的揭示,重構教材順序或整合教學內容,并設計教學過程。如此,更有助于學生歷史理解,針對性會更強。
二、在真實問題情境中淬煉思維品質
思維品質是指思維能力的特點及其表現,其主要表現為思維的廣度與深度、獨立性、批判性、靈活性、敏捷性以及邏輯性等。思維起于直接經驗的情境,在真實問題情境中淬煉思維品質是進行深度學習的重要方式。核心素養下的教學最大特質在于真實性,這是核心素養的精髓所在。問題應該建立在事實間的實際聯系之上,要體現思維的廣度。通過設計教學過程中要解決的問題,為學生搭建思維的遞進階梯,這是深度學習的要義所在。
講先秦時期的德治與法治之爭,需要還原一個真實的社會情境,把當時人所處的真實境況或面對的實際問題全景呈現出來,引發學生獨立思考。從夏朝開始,中國進入早期國家發展階段。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湯刑》,周朝有《九刑》,這表明我國很早已有法律。西周建立了以宗法為核心的禮制,同時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周平王東遷后,王室衰微,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實亡,取而代之的是諸侯紛爭、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面對亂局,各諸侯國紛紛變法圖強,試圖重建社會秩序。公元前536年,鄭國子產“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
子產的行為引發了一場法治與德治之爭,晉國大夫叔向強烈反對。在叔向看來,刑罰適用于亂世,公布刑書會使百姓注重爭端,而不顧道德禮義。后來晉國也公布刑書,遭到了孔子的反對。這一情境的創設意在指向深度思維,意在促進對“德法之爭”的深度理解。為了重建秩序,除了變法外,當時人提出了不同的設想。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復周禮,將周公視為偶像,開創了儒家學說。孔子以仁、禮為核心,主張為政以德,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會秩序,重視社會道德構建。戰國時期,各國變法圖強,法律的權威地位逐漸確立,在宗法觀念和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下,深刻地影響著當時人的思想與行為。《孟子》中記載了孟子與其弟子桃應關于法律問題的一段對話。從孟子與學生的對話中,可以看出孟子的法制觀念是什么?
這一問重在培養學生思維的敏捷性,即敏銳地從史料中發現問題的癥結所在。孟子主張德治,但也不否認法制的重要性,強調權力不能干預執法。當法律與人倫沖突時,維護人倫。盡管此時儒學已成為顯學,但效果不佳,其主張并沒有被諸侯國采納。問題出在哪?公元前266年,荀子到秦國游訪。荀子看到秦國社會穩定有序,原本打算留下來輔佐秦國的,秦昭王一句“儒者無益于人之國”,令人尷尬不已。這正是秦國奉行法治帶來的效果。
問題:那為什么法家能在法治與德治之爭中脫穎而出呢?
這一問體現了思維的邏輯性,這是思維品質的核心環節。與儒家主張德治不同的是,法家主張以尊君權、尚法治,主要從君主、國家的角度出發思考問題。秦王嬴政一度癡迷于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并對其評價道:“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5]推崇法家思想,這也是秦能實現統一的重要條件之一。
問題的質量決定著思維的品質。在問題的呈現方式上要注意問題的層次性、拓展性和開放性,進而構建起問題與所學知識之間的聯系。教師作為課程的指導者、促進者,要幫助學生建構中國歷代法治與教化的知識圖譜,最終指向思維的批判性。有學者認為,深度學習與淺層次學習的最大區別是學生是否能夠對所學知識進行評判、反思、遷移,并靈活用于實際問題的解決中。[6]如西漢建立后,“約法三章”不再適應現實需要,新的法令條文不斷增加,形成《九章律》。漢武帝尊崇儒術,設立五經博士,儒學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與此同時,《九章律》之外的“旁章科條”迅速增至359章,案例匯編越編越多,《春秋》一書所記史事在判案時也用作參考。儒家提倡“以德去刑”“仁政”等主張,統治者卻奉行外儒內法的指導思想。當時身為太子的劉奭對其父漢宣帝多用文法吏、采取嚴厲鎮壓的做法頗不以為然。公元前48年,27歲的劉奭即位,是為漢元帝。
問題:漢元帝重用儒生,這又會對中國的歷史走向帶來什么影響呢?
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后,儒家經典開始影響法律實施,以禮入法。東漢時儒家學者深入影響法律條文的解釋,魏晉時期律令儒家化是最重要的變化。在教化方面,儒家學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通過對問題的揭示,凸顯出儒學在國家治理中的影響力逐漸上升,反映了學生思維隨機應變的程度。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迭,社會動蕩不安,儒家學說受到了佛教、道教的沖擊與挑戰。由于社會動蕩不安,秩序混亂,人們開始重視家訓在維護社會秩序上的重要作用。南北朝時期顏之推創作《顏氏家訓》便是代表。
隋朝在法律制度上改變了北周的嚴刑峻法,《開皇律》提高了法律的文明程度。從唐高祖頒布的《武德律》到唐太宗頒行的《貞觀律》,均受《開皇律》影響,沒有反映出新朝氣象。唐高宗頒行《永徽律》,有了很大改變。653年,律與疏合在一起,后世稱《唐律疏議》,成為中華法系得以確立的標志。那中華法系有何特點?
唐律是禮法結合的典范,對儒家倫理中的“孝”特別重視,突出成文法典、民法與刑法不分,由此構成中華法系的基本特征。唐朝提倡禮治,禮法并用,如732年頒行《大唐開元禮》,強調禮治在維護封建統治上具有重要的意義,進而又構建一個學術情境。禮教約束的對象是全社會,帝王將相亦在其中,所以它的威力較具體的法制、律典更為強大。但到底哪個作用更大?對此,統治者心知肚明,開始推廣魏晉南北朝以來重視家訓的傳統,強化對基層的道德教化。在不同問題情境與思維品質的相互交織中,深度學習便應運而生。
三、重在學生的體驗與反思
深度學習要關注學生思維的主體地位。對深度的理解要準確,不是教學內容越難越好,越深越好,而是強調學生完整的學習經歷,特別是真實情境的介入,學生的體驗與反思。[7]對此,教師要關注學生的學習過程,不能簡單灌輸結論,實現教學過程與思維過程的統一。遵循“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底層邏輯,激發學生主動思維的參與。
宋朝基本沿用唐朝的法律體系,963年頒行《宋刑統》,基本上照搬唐律。元朝對唐宋法律整體棄而不用,但在司法實踐中仍廣泛援引。明朝以唐律為藍本制定《大明律》,開創律例合編體例。清朝沿襲《大明律》,制定了《大清律例》。宋朝以降,儒學士人投身基層教化,以鄉約教化鄉里。1076年,北宋呂大鈞撰寫《呂氏鄉約》。到了南宋時,朱熹發現并推崇這個鄉約,由此聲名遠播。
鄉約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加強基層社會治理。有利于發展生產,促進了儒家文化和傳統道德的傳播。原本由儒學士人發起的教化百姓的鄉約,經政府利用和推廣而具有約束力,在宣講時引用《大明律》《大清律例》來解釋,完全由教化手段淪為了統治工具。
問題:為什么宋朝以后如此重視鄉約等道德教化?
宋朝以后,儒學開始向基層滲透,發展出理學并在社會上廣泛傳播,呈現出思辨化、世俗化的特征。以程頤、程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在南宋后期逐步確立為統治思想。理學突出個人的道德修養,強調用外在高尚的道德律令,即“三綱五常”來約束人們的行為。原本這種強制的道德要求是由士大夫自發去實踐,后來統治者將其轉化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規范,甚至以禮入法。朱熹的《家禮》和《小學》成為家庭和幼童的行為規范就是典型案例。
中國的法治與教化到了明朝表現得尤為明顯。統治者隆禮重法,禮法結合,但也清晰地向世人表明禮與法的實質是維護統治的手段。然而,在禮法并用之下,地方社會卻是另一番景象。在真實生活情境的介入下,重在突出學生的體驗與反思。如自宋明以來,江南好訟之風盛行,令地方官焦頭爛額。這是中國古代法治與教化的進步嗎?由此引發學生深度思考。深度學習還可以借助深度教學、史料研習等得以實現,值得進一步探討。當學習真正走向深度時,學科核心素養的落實將變得更加有效。
【注釋】
[1]教育部考試中心:《中國高考評價體系說明》,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5頁。
[2]鐘啟泉:《深度學習:課堂轉型的標識》,《全球教育展望》2021年第1期,第14頁。
[3]教育部:《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47頁。
[4]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第305頁。
[5][西漢]司馬遷:《史記》卷36《老子韓非子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155頁。
[6]郭彥青:《深度學習引發的深度教學是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的必由之路》,《教學研究》2018年第3期,第12頁。
[7]崔允漷:《深度教學的邏輯:超越二元之爭,走向整合取徑》,《中小學管理》2021年第5期,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