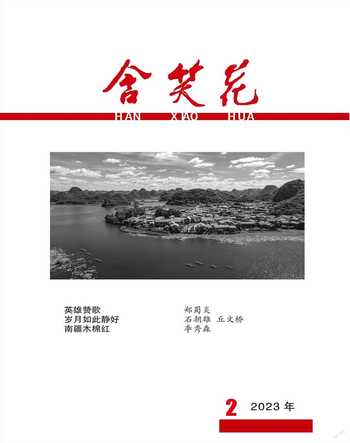膩腳落進了花的韻腳里
一
嗒、嗒、嗒、嗒……
進入膩腳,最先聽到的是如此清脆的聲音,響在大總山系的一條梁子上。不及時解答就會產生許多的疑惑,諸如:風車的轉動?花開的聲音?某機械的運轉?錯!聽到這聲音的時候,我正站在阿落白那片盡情綻放的萬壽菊地里。周邊的山頂上堆積著濃霧,與天相接,連成片,要是不仔細分辨,定會誤認為天坍塌在一座座山尖上;若隱若現的風車,在遠山,小得像超市里的玩具。山脊間的青翠鋪排著,從遠方浩浩蕩蕩流淌過來,在一片連著一片黃得濃郁、黃得明凈、黃得酣暢、黃得清脆、黃得耀眼的萬壽菊地邊來了個急剎,又悄沒聲從一朵朵萬壽菊的罅隙里一瀉而入,洋姜、雪蓮果、玉米……不同農作物或經濟作物的地塊,再順著山脊無止境地綿延向遠方。
眼里的驚嘆、心中的驚喜在無垠地擴展,綠與黃的無限對決,在這方土地,在此刻,讓我使出渾身解數,試圖把一個個熟悉的漢字,如穿珠子般串起來,可任我如何努力,每一個字,每一個詞,每一句話,都瘦得像秋后的螞蚱,無法準確表達此刻云涌的心情,無法描述眼前絢麗的景致。有些不甘心,再次把懸在半空的文字,無法抵達意向的詞或句,進行新一輪的組合,依然徒勞。
聽到這兒,你也許會說,“嗒嗒……”聲應該是心跳的韻律。這種肯定的猜測也被劃上一個大大的叉。在八月,走進膩腳,我的心幾乎是窒息的。別聯想到高原反應,膩腳位于丘北縣的西南部,最高海拔才2222米,最低海拔1511米,這樣的海拔完全在我的承受范圍內。要不是我親眼所見,也許這種錯誤的猜測會一直伴隨著我的人生,直至暮年。
順著清脆的聲音,我走進萬壽菊深處,走向那個低頭作業的女人。只見她以墑為單位,雙手靈活穿梭于每一棵萬壽菊的花間,“嗒嗒嗒……”聲更為圓潤、清脆、響亮,在這偌大的天地間,在這節奏鮮明悅耳的聲響里,我突然想到中國遠古的五音——宮、商、角、徵、羽,色澤明麗的畫面、輕輕的微風,倒有幾分貼切。
眼前突然多出幾雙眼睛,還盯著自己,倏忽間那女人的臉上生出幾分靦腆,但更多的是喜悅。這份喜悅不是因我們的出現,而是在為我們解答著萬壽菊的管理、收入時難于抑制的興奮心情。她說她家自從種植了萬壽菊,改寫了一貧如洗的面貌,蓋起房子不說,還有了微薄的存款。在她掛滿幸福的神情里,你不得不相信,在膩腳鄉,為了讓檔卡戶脫貧,邁上幸福的康莊,鄉政府走出的“信息互享、勞力互助、技術互學、銷售互帶”模式,讓萬壽菊產業在膩腳落了地,生了根。
那女人邊跟我們聊著,手間的速度也絲毫不減,這讓我想起母親插秧的情景,也如此這般嫻熟、飛快。瞧了好會兒,我陡然發覺,插秧也好,摘花也罷,講究的是手快,眼要更快,插在哪里,摘哪朵,在眼睛的牽引下,手才會順利到達。我從小插過秧,當年母親還夸贊我插秧的速度,許是多種情愫的綜合,抑或是兒時愉悅的挑逗,不自覺站到一墑萬壽菊前,開始嘗試對萬壽菊的采摘。
嗒、嗒、嗒、嗒……
從我手間冒長的聲音遠不及那女人的流暢,多了幾分生疏與笨拙,盡管如此,我還是能感受到,那一朵朵大得繡球一樣的萬壽菊,帶著晶瑩的露珠從枝頭上被摘下,鮮活的每一片花瓣,似乎都安上了一個幸福的密碼。
一朵兩朵,熟能生巧,我越摘越順手,不知是露珠的洗滌還是萬壽菊的浸染,我雙手的膚色變了,變得又嫩又白,要不是時間的緣故,也許我會一直在此,在這些花朵間,種下一串串欣喜,收藏著花朵帶給我的無限喜悅,就像那女人臉上堆積著的燦爛。
“多玩哈,這點風景還是漂亮的嘛!”
極樸實的話,極真誠的挽留,我讀出了女人的真心。瞧著滿臉燦爛的她,我想她一定有個花一樣的名字,不然也不會把這滿坡的萬壽菊種植得如此鮮艷。
膩腳的楊書記介紹著近年來膩腳種植萬壽菊的畝積,收購鮮花的總量,達到的總產值,他介紹的聲音跟那“嗒嗒”聲一樣清脆。聽著一串串驚喜的數字,我知道,膩腳的諸多貧困戶,在這盡情綻放的萬壽菊地里,如同這女人一樣,早已走出山村的沉寂,讓他們騰出足夠的心情,以純粹欣賞的視覺,讓風景歸于風景,看山是山,而不是滿腦子想的是困境、窘迫。
二
酒花,對于喝不了酒的我來說是個新詞,是膩腳之行給我陳舊人生鑲嵌的新元素。
從阿落白出來,直接進入膩腳原江酒廠,酒廠的門店是四層的樓房,店面排列著高矮、大小、形狀、容量不一的酒壺,普通得接近土氣的塑料酒壺讓我一眼呈底,從橙黃色的酒質就知道有些年代。不透明的土罐酒壺寫滿古樸,沒有滄桑,卻能讀出悠久的歲月。其實,對于大批量購買,或者遠途運輸,那些塑料酒壺倒提供了便捷與安全。塑料酒壺只是短暫的存放,時間久了,酒就會走失它原有的味道。老板介紹著一壺壺酒的年份,數字從來與我的意志相悖,再怎么努力都無法確切留在記憶里,但我能感覺到這些酒似乎都穿上了黃金夾,給人一種珍惜、名貴的感覺。
對于膩腳酒,打小就烙在我的記憶里。我們村有個小賣鋪,賣的白酒有白蘭地、方瓶裝的膩腳酒和散酒,散酒多半是剛出廠的,有膩腳酒和其他地方烤出來的玉米酒,盡管其他地方的玉米酒價格要低廉得多,但總沒有膩腳酒好賣,這就是質量決定銷售。只要家里來客人,父親總要叫我去買方瓶膩腳酒,到小賣鋪只要開口買方瓶膩腳酒,店主就會捎帶一句,家里來貴客了?這是村里一個不成文的禮節,也是最高的禮節。
穿過門臉店往里走,窄小的視覺變得空曠起來。寬闊的視野里全是低矮的以本地土瓦建蓋的小木房子,眼前的景象讓簡陋一詞在蔓延。這樣的地方能釀酒嗎?就是能釀佐不過也是些小打小鬧,有小娃玩泥巴的味兒。爬上一個小小的斜坡,我們進到一間四面通風的低矮木屋子,低矮但抹殺不了屋子的深度,整齊排列的人頭高的大瓦缸以列成隊一直向前延伸。如此氣勢,讓我想起電視里廣告的廚邦醬油大曬廠。如果不俯瞰,不說話,站到不同列隊間的間隙里,很難相互看到彼此。
醬油要曬,酒卻要窖藏。窖酒的最佳溫度一般在0℃-20℃間,膩腳屬典型的高寒山區,嚴重缺水,干燥,常年平均氣溫20℃,最酷熱的夏季也就比平常溫度高一兩度,且只有那么一兩天又回歸到常溫狀態,可以說膩腳無論是地理環境還是氣候條件,都具有窖酒所需的必備條件,不用任何的加工,不用任何的粉飾,只要雨淋不到,就可成為一個窖酒的好場所。
熱情的老板用酒提子打出酒讓我們品嘗,對于酒精過敏的體質我是絲毫不敢嘗試的,只能眼巴巴地瞧,可僅只眼觀,那黃澄澄的色澤,我瞧不出與門臉房里的酒有啥差別。見我微皺的眉頭,老板換了一個法子,用提子將酒倒在一個不銹鋼瓢里,濺起了許多大小均勻、長相飽滿、晶瑩剔透的小氣泡飄在層面,久久不肯散去。這就是酒花?我有些驚訝。老板怕我們看不懂,換了幾個年份的酒倒給我們看,年份越長的酒花存留的時間越長,且那酒線拉得又細又長,他說這是糧食純釀的關鍵所在。而膩腳鄉位于滇東南山區,氣候冷涼,大面積種植的農作物就是玉米,生長周期較長的玉米具有優質的成分,成了釀酒最佳的首選,也是唯一的選擇。再配上當地塘蓄雨雪水,經木甑蒸煮,土酒藥發酵,通過蒸餾提純而成。
雖說沒能親眼一觀釀酒的全過程,但在酒廠老板的介紹間,幾個攝友早已迫不及待地品起來,咂巴著嘴的那個脆響跟兒時飯桌上客人的一個樣,就連贊嘆聲也如此相似、一致。說到贊嘆,讓我陡然想起湖廣總督辛亥革命陸軍上將黎天才,他在1922年回丘北黎家莊省親時,席間喝了膩腳酒說過的一句話:“吾戎馬一生,喝過不少好酒,相比之下,膩腳酒堪稱佳釀,不辱彝鄉矣。”
“膩腳酒屬于小曲酒,色澤清亮透明、味甘醇,有余香,無異味”,這是1982年云南清酒評比中專家們的評語,那時膩腳酒就在云南百余種清酒中名列第五位,而顧客的評價是“小茅臺”。這稱呼不是噱頭,而是膩腳酒品質的一種實至名歸。追根溯源,膩腳酒比我們祖師爺的祖師爺年歲還要長。據記載,清乾隆五十五年,貴族的一戶鄭姓人家就在膩腳開辦酒坊,至嘉慶年間膩腳釀酒業已興盛,民國二十九年釀酒人數就有13戶。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家有了專門安排釀酒的用糧指標,由縣貿易公司分配給膩腳村釀酒,產品由貿易公司統一銷售。截至2020年底,全鄉共有釀酒個體戶51戶,年產量達120萬公斤,年產值達1300萬余元。
在膩腳喝酒不用杯子,盛酒的容器都是吃飯的小碗。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這應該就是膩腳彝族鄉人民本真的粗獷與豪邁,一碗酒下肚,開心的事情更開心了,憋悶的心情也會因這碗酒而從此和解。
三
攝影家也好,作家也罷,到膩腳必去的地方還有膩腳老寨。膩腳老寨是原膩腳鄉政府所在地,隨著七江公路的修建,鄉政府搬遷至七江公路旁,膩腳老寨村就像洶涌的浪潮,不斷涌向山頂,最后在七江公路兩旁氤氳開去,幾年的累積,也就成為今天繁茂的模樣。其實,膩腳老寨是相對于膩腳村近幾年發展而言的一種稱呼,老寨與新區沒有明顯的楚河漢界,房屋早已連成片。若要強行區分老寨與新區的話,就只能以房屋的建筑特點作依據來劃分。
走出膩腳原江酒廠大門,朝著南盤江方向徒步幾分鐘,順著左側的岔道,走過一段長長的之字形路,就能看到用本地土瓦建蓋在半坡上的清一色瓦房,這就是膩腳老寨。
寧靜而悠然是膩腳老寨給我的第一印象。走在村巷里,好會兒都見不到一個人,高大而不知名的古樹自顧自繁茂著,似乎只有不斷生長,不斷蓬勃無限的綠,才是它的終極目標。這種在寂靜與孤獨中葳蕤出的無限生機令人震撼,與青一色的瓦房相互匹配著,它們在認真抒寫一個詞——古樸。其實,最能體現古樸一詞的重要元素還要數青石砌筑的墻體。僅說青石砌筑也許不足為奇,但幾百斤重的碩大青石建筑就有些稀罕,有的房子半墻體是青石,有的整堵墻都是。不僅墻體、柱礎用青石,就是半圓形拱頂山門、天井都用青石扣砌而成。聽說這種五面石扣砌的天井,是晾曬谷物最好的佳所。
膩腳老寨的先民始于清代,在那個沒有起重機,沒有機械化工具的時代,能把這樣碩大的青石拌糯米沙灰支砌而起,實屬罕見工程。要把青石規整出這樣方正的形狀,鏨子是不可或缺或者說是必需的工具。青石上有規則的條狀,但大多是均勻的凹凸痕跡,能讓青石上每一個面的細節如此細膩,刀法如此勻實,定是當年出了個技藝高超的石匠,在此動了真情,才會讓鏨子在叮叮叮的敲打中與經年的風雨,雕刻出如此經久不衰的杰作。背陰面墻體還保持著青石本真的青色,日照稍常的當陽面已微微泛白,但不管是背陰面還是當陽面,都在訴說著時光的久遠,又為古樸增添上濃重的一筆。隨便走進一戶農家,都是四合院穿斗式木構件石材建筑,以正房、耳房(廂房)和入口門墻圍合成正方如印的外觀,這不是典型的“一顆印”民居嗎?一顆印亦稱“一口印”,是中國民間的一種建筑風俗,據說此建筑模式流行于陜西、安徽、云南等地。在書本所獲的名詞,想不到在膩腳老寨見到實體,保存如此完好的古樸建筑能成為2009年央視熱播劇《冷箭》外拍取景地之一也就不足為奇了。
考究的大青石建材,加之獨特的設計,讓膩腳老寨古樸中透著厚重,寧靜淡雅中不乏大氣奔放,要不是突然冒出的狗吠,會讓人產生穿越的恍惚。膩腳老寨的狗那真叫一個多,幾乎每一家都養著一只,都用繩子或鐵鏈拴著,還未到達門口,汪汪的一串狂吠,惡貫穿全身每一個毛孔,大家會不自覺避退開去。走在老寨的每一條巷道間,總有一種心驚膽戰的感覺。其實,你只要收起你的膽子,大膽邁出去,你就能感受到狗們的熱情。我遇到過,在一個房拐處,猛然伸出一只齜牙咧嘴的狗頭,拋出一串狂吠,我還來不及逃走,它倒先退了回去,徒留一串狂吠和一堵高大的石墻給我。我大著膽著往前走,只見縮回去的那只狗中規中矩蹲坐在門口,遇到我的目光,羞臊著把頭輕輕別朝一旁,待我走遠了,它還忠實地守著那道斑駁的木門。就是這次的遇見,刷新了我對狗的認識。
與狗相比,耳房上那只貓就顯得安靜、溫順而優雅。那貓的顏色與瓦片極為相近,稍不留神,你根本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它趴在瓦片上,似膽怯又似乖巧,頭朝著院子方向,隨著兩只耳朵一起豎著,是在聆聽我們走過巷道的蛩音,還是沉醉于那股炊煙的溫暖?炊煙沒有固定的煙囪出口,是從瓦片的縫隙間縹緲而起,輕輕淡淡地鋪在瓦片上,籠罩其間的貓就有了幾分朦朧,要不是那兩只靈動的大眼睛,我定認為是個逼真的泥塑。感觸到一只只相機鏡頭的炙熱,貓靦腆著起身,舒緩地邁上正房的瓦楞,又悄悄趴下,似乎在給我們擺著新的造型,讓一部部相機眷戀不舍,難于挪移。
這時,從灶房里走出一個老奶奶,頭上裹著彝家人特有的花頂巾,瞧見我們,臉上陡然掛起微笑,跟她臉上的皺紋一樣深厚:“回來回來,來家吃飯!”豁亮的嗓音,喊出的全是真誠。要是不了解彝家人熱情、豪爽的性格,容易誤認為我們是相識已久的熟人,其實不然,我們才第一次相見,姓啥名誰都還是陌生的概念,這就是膩腳老寨,只要走進來,管你認識不認識,他們都把你當親人。瞧著眼前的一切,在我心間暖暖地冒長起“故鄉”這個詞。從詩經算起,故鄉這個早已走過幾千年歷史,被詩人吟誦,文壇賦文的詞語,在膩腳老寨,不管人還是牲畜抑或每一物什,都在努力用自己的一顰一笑、一歲一足認真詮釋。
四
在膩腳,八月的天氣還保持著六月的心性,陰沉沉的天空,在料想不到的瞬間,陽光刺破了厚厚的云層,突然展現在眼前。
撕破的云,就像決堤的壩,陽光越泄越多,厚厚的云層一敗涂地,漸散漸逃,厚厚的灰色或黑色云層,轉眼就逃沒了影,一塊塊棉花似的云朵乘機涌來,與通透的藍天相襯,潔白得不忍用自己這雙濁眼去看。剛才還是點滴或是塊狀的局域光,此刻像草原上奔跑的駿馬,讓成林的玉米、雪蓮窠、烤煙、草葉上的露珠馱著,在膩腳這塊疆域,跑過一片片白菜、甘藍、花菜等蔬菜地,路經膩腳原江酒廠,推動著云朵和氣浪,撫摸著一頭頭即將出欄的小黃牛、一圈圈黑山羊,越過一座座山頭,在地白光伏稍做停留,一溜煙四散向大龍山、老莊科。就這氣勢,我以為氣溫會在云層的逃散間飆升到三十攝氏度以上,不料也就高了那么一點點就不再往上升,至此我才知道,這就是膩腳,再藍的天空也不會讓溫度超出我的想象。
在膩腳,陽光和風都有各自的性格,但不管哪種性格,似乎都有著共同的目標,都從不同的角落、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不同的季節奔向膩腳的大龍山、古城、飛尺角、地白、麥沖、團樹、金龍山、老莊科、火山不同片區,以風力發電、光伏發電項目來建設、繁榮著膩腳的每一個村莊,以富裕的電量燃亮每一個鄉村的夜晚,驅趕著黑夜的孤寂;將即是名詞又是形容詞的“現代化”植入每一個村莊,接替著柴火的使命。就是這些發電項目的注入,改寫了膩腳“出門一把鐮,歸家一捆柴”的生活日常,再也聽不到刀削斧劈的粗暴聲,一座座山在陽光和風的韻腳里不斷豐腴、茁壯。
不管我們去往阿落白、大鐵,還是膩革龍的路上,有翠綠、墨綠,抑或黛綠,交替刷屏了我的眼球,肥厚的綠在陽光下、在微風里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綠蔭。隨便在一個地方駐足,都能看到魔芋、雪蓮果、粉紅腰豆、烤煙,一系列的種植業與萬壽菊齊頭并進,鮮活在膩腳的村村寨寨。
不管從阿落白進去,還是從膩革龍出來,一路上都有萬壽菊的跟隨相送,特別是路邊地埂上嫩得會出水的小南瓜,與那棵熟透在地邊的桃子,總能勾出我們的饞涎。
在牛屎坡,以萬壽菊為主角的鄉村旅游開始興起,觀景臺立在花海的中央,站上去,被喧囂浸染的靈魂在這份景色里被徹底洗滌,想著今天走過的每一個點,我知道膩腳鄉間的春色已不再寂寞,它們正用自己特有的魅力改變著許多人的心電圖。就像從膩革龍出來,路邊一片片鮮紅的朝天小椒,伴隨著飛馳而過的高鐵一樣,早已掀起一串串驚喜的巨浪。
僅一天的時間,我們無法走完膩腳的村村寨寨,但快速發展的腳步給周遭空氣帶來的震動和改變,讓我們不得不承認,膩腳已不再是曾經的膩腳,滿坡的萬壽菊,經久不散的膩腳酒花,脆甜的雪蓮果,香糯的粉紅腰豆以及其他經濟作物,早已搭上現代化高速發展的這輛快車,繁茂成一朵朵致富之花。
【作者簡介】文心,原名張文慧,彝族,云南省作協會員,在《文藝報》《大家》《云南日報》《含笑花》等報刊發表散文、小說、詩歌作品。小說《碗頭的秘密》曾獲得滇東南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