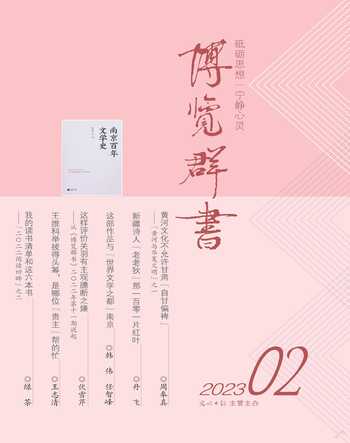這樣評價關羽有主觀臆斷之嫌
伏雪芹
《博覽群書》2022年第11期刊登了一篇名為《關羽失荊州是因為“大意”嗎》的文章,作者北塔認為關羽失荊州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傲慢的性格,直言“在相當大程度上,我們的確可以說關公死于他自己的傲慢性格”。此外,文中認為關公作為“義”的化身,是劉備集團的精神支柱和道義象征,但關羽和劉備集團不還荊州,是其在道義上的破產,所以關羽是因為“失義”而失了荊州。再者,文中很多地方對小說和關羽形象的解讀與原著存在較大的偏差,有明顯的主觀臆斷和解構之嫌。介于此,本文也想談一談關羽失荊州的原因,并就荊州的“借”與“還”及其信義問題以及當下應該如何正確認識關公形象做一討論。
關羽失荊州的根本原因
關羽失荊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簡單地歸于關羽本人的性格問題。當然,這一論調流行至今有其歷史根源。陳壽最早在《三國志》中批評關羽“剛而自矜……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自此便定下基調,后世多宗其說,認為關羽驕傲自負,擅自北伐,麻痹大意失了荊州。王夫之《讀通鑒論》也認為荊州之失在關羽的“伎吳怒吳”“激孫權之降曹”,破壞并葬送了孫劉聯盟。誠然,關羽作為鎮將,對失荊州負有直接責任,“剛而自矜”確實是他性格的一大缺點,與他后來的敗亡有直接的關系。但據此將全部責任推到關羽身上,并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
荊州的地理和戰略地位決定,孫、劉兩家對荊州勢在必爭,有荊州問題的存在,吳蜀便不能結成鞏固的聯盟。荊州“地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實乃“用武之國”,而“有識者所必爭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就劉備方而言,諸葛亮早在《隆中對策》中就確立了“跨有荊、益”,兩路北伐的戰略路線,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是占有荊州,若無荊州,焉有北伐?沒有北伐,又何談“興復漢室”。就孫權方而言,荊州“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實則東吳之門戶,而江陵之重鎮。立足江東,占有荊州,是東吳君臣策畫已久的既定國策,魯肅、甘寧、周瑜、陸遜等人都曾建議孫權圖取荊州。荊州的歸屬對雙方而言,都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孫權若得荊州,便可全據長江,與曹操抗衡,失了荊州等于失了門戶,便不能有吳國;劉備若得荊州,可藉此而居,以待天下之變,失去荊州便只能坐困益州,放棄兩路北伐。自赤壁之戰以來,吳蜀雙方在荊州問題上矛盾沖突不斷。建安二十四年,關羽興師北伐,斬將擄兵,威震華夏。關羽若北伐勝利,劉備集團更為強大,其在荊州的勢力會對東吳造成致命威脅,這是孫權集團所不能容許的。孫、劉的矛盾,在當時乃是公開的秘密,司馬懿和蔣濟給曹操獻策說:
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愿也。可遣人勸躡其后,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
(《三國志·蔣濟傳》)
孫權見時機成熟,斷然毀盟,聯結曹魏,偷渡長江,襲取江陵,關羽腹背受敵,失了荊州,敗走麥城。“這就是當時斗爭的總形勢,一紙同盟條約怎能掩蓋這生存攸關的利害沖突?”(張大可《三國史研究》)孫劉聯盟“外親內疏”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破壞孫劉聯盟的不是關羽,而是孫權。孫權的毀盟,并非關羽的刺激,而是出于對時局的把握和戰略需求的考慮。范文瀾先生曾說過:
孫權對荊州是勢所必爭的,否則便不能有吳國……劉備取得益州之后,荊州成為孫權用全力來攻,劉備不能用全力來守的局面。(《中國通史簡編》)
東吳不會允許西蜀勢力存在于荊州,即使是部分存在也不允許。所以,只要蜀漢北伐,孫權必定趁機偷襲,孫劉聯盟終將破裂。說到底蜀漢丟失荊州最根本的原因是三國鼎立形成過程中錯綜復雜的政治、軍事斗爭形勢造成的,與關羽“剛而自矜”的性格并無直接關系,三國之間的形勢與相互關系,不是任何個人所能左右的。
作為荊州守將,關羽對失荊州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一,由于他“剛而自矜”,未能處理好與孫權及東吳的關系。孫權聯姻,他不僅拒婚還辱罵其使,后來又在圍攻襄樊時,擅取吳國的“湘關米”,此二事成了孫權進兵的借口。
其二,由于他“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不能團結部下,導致內部叛變。關羽平日里就輕視麋芳和傅士仁,待及北伐二人供給軍資不及時。關羽揚言要治二人之罪,導致二人最終叛變。由于二人的叛變,呂蒙幾乎是兵不血刃奪了南郡。
其三,對東吳喪失警惕、疏于防范,是其作為荊州鎮將所犯的致命失誤。關羽當時“但務北進”,對東吳喪失警覺。輕信呂蒙稱病還建業,撤兵傾師北伐,導致后方空虛,給東吳以偷襲的機會,導致了最終的敗亡。
荊州的“借”與“還”及其信義問題
北塔在文中還從小說的題旨和關羽本人的道德形象出發,討論了失荊州的原因。指出關公作為“義”的化身,是劉備集團的精神支柱和道義象征,但關羽和劉備集團不還荊州,是其在道義上的破產,標志著劉備集團從此喪失了繼續發展的道德基礎,所以關羽是因為“失義”而失了荊州,并主張這也是小說作者羅貫中的用意所在。我們暫且不論小說的題旨和作者羅貫中的用意,先來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劉備集團不還荊州是否就是“失義”。
首先,從道義層面來講,有借就要還,但“借荊州”是一樁歷史公案,歷來爭論不斷。“借荊州”之說最早見于吳國國史《吳書》,繼而見于晉初虞溥所作《江表傳》,陳壽撰《三國志》沿用“借荊州”之說,遂使此說成為定論。《三國志》雖沿用“借荊州”之說,但僅見于《吳志》中的《魯肅傳》《程普傳》和《呂蒙傳》,而不見于《魏志》和《蜀志》,“借荊州”之說皆出自吳人語。所以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撰有“借荊州之非”專條,懷疑“借荊州之說,出自吳人事后之論,而非當日情事也”,并且反駁:“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與人也。荊州本劉表地,非孫氏故物”,既然并非孫權之物,又何來“借”一說呢?事實上,荊州七郡原為劉表所據,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劉表,得江北三郡。赤壁之戰,曹操潰敗,劉備奪得劉表舊部的江南四郡。所以,劉備所得荊州,是從劉表舊部和曹操手中所得,并非借自孫權。退一步講,即便真如《吳書》所載,東吳所借荊州者,也只是南郡部分土地,并非劉備所得荊州之全部。赤壁之戰后,周瑜率兵占據江陵,為南郡太守,劉備率軍回師江濱,屯兵公安,與周瑜隔江相望,雙方共據南郡。劉備以劉表吏士多來投奔,所占地狹小不足以安民為由,從權借荊州數郡,孫權聽取魯肅的建議,從南郡撤兵,承認劉備為荊州牧這一既成事實。所以,“所謂借荊州一事,實則僅僅涉及南郡一郡之地,其余諸郡都是劉備在戎馬征戰中從曹操和劉表舊部手中奪來的”(杜建民《劉備實未“借荊州”》),但東吳將其夸大演繹為“借荊州”,不符合歷史事實。
其次,荊州的歸屬,本來就是吳蜀雙方之間的博弈與較量,并不關涉信義的問題。自赤壁之戰以來,孫、劉兩家在荊州問題上矛盾沖突不斷,前后引發了借荊州、分荊州、索荊州、還荊州等一系列紛爭。吳蜀對荊州的爭奪和分割,其實是雙方實力的較量與利益權衡的結果。第一次荊州之爭發生在赤壁之戰結束不久,劉備經赤壁之戰實力大增,向孫權提出“借荊州”的要求,孫權采取妥協政策,答應從南郡撤兵,允許劉備都督荊州。孫權從南郡撤兵,雖名之曰“借荊州”,實則是以聯合抗曹為目的,在權衡雙方實力與利弊得失之后做出的選擇;建安二十年,東吳以“還荊州”為由,討要荊州不成,便派呂蒙武力奪取,雙方兵戎相見,戰爭一觸即發。后來迫于曹魏的壓力,劉備主動求和,吳蜀協商以湘水為界中分荊州而治;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北伐,東吳擔心北伐勝利,會對其造成威脅,所以聯結曹魏,兩面夾擊關羽,關羽敗走麥城,蜀漢由此退出荊州。回顧吳蜀荊州之爭,雙方因“利”而離合,荊州的“借”與“還”其實是雙方為了爭奪荊州的博弈與較量。再者,地域的占有,實則是強權的產物,所謂“借荊州”不過是雙方勢力之間的一種妥協平衡,“借”與“還”都只是說辭和權宜之計,以“借”得之,以“還”奪之,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因此這種“借”,就不會輕意“還”(朱紹侯《吳蜀荊州之爭與三國鼎力的形成》)。借荊州的實質和要義,并不在于這一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通過“借”與“還”的糾紛展現孫、劉之間的矛盾與斗爭。
最后,在荊州問題上,吳蜀雙方是對立的,還荊州一事,在談信義之前,需要明確立場問題。從東吳的立場出發,有借就要還,還了荊州是為信守承諾,不還則是失了信義,所以魯肅曾斥責劉備集團和關羽“貪而背義”。但從蜀漢的立場出發,還與不還,實則是“小義”與“大義”的取舍與抉擇。歸還荊州意味著蜀漢勢力全部退出荊州,劉備集團便只能坐困益州,被迫放棄隆中路線,于劉備集團而言是為“小義”;不還荊州,雖然會失信于東吳,但能守住荊州,繼續兩路北伐,最大限度地維護集團自身的利益,是為“大義”。從集團利益出發,蜀漢只能舍“小義”而取“大義”。同樣,作為荊州守將,關羽代表和維護的是劉備集團的利益,面對東吳的索要,如果答應讓地,于東吳而言當然是“義”,但對劉備集團而言,將荊州拱手讓人,不僅是鎮守失職,更是對集團利益的嚴重損害。作為劉備集團的成員,他的立場和身份決定了他只能守荊州,而不能還荊州。所以,不區分立場問題單純從信義的角度,說關羽不還荊州是“貪而背義”,甚至說是關羽在道義上的破產,實屬不當。
關羽形象不可輕易否定
北塔文中很多地方對小說和關羽形象的解讀與原著存在較大的偏差,如文中論及關羽性格,說關羽“傲慢僭越,傲慢無禮,傲慢得目中無人”,看不起有才無德的曹操,所以在性命攸關的情況下“降漢不降曹”;說關羽只是“侯”,而孫權是“君”,但在關羽看來“君侯”是“君”+“侯”,比一國之君還牛。還說關羽不還荊州是耍賴耍狠、強詞奪理,既失信義又失情義,文中諸如此類的解讀不勝枚舉,這種帶有明顯主觀臆斷的曲解,對關羽形象無疑是一種解構。關羽作為“忠義”的代表,受到人們的普遍崇拜,民間稱其為“關公”,或敬稱為“關老爺”“關圣人”“關圣帝君”。宋以后,由于統治階級的追封表彰,關羽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先后有16位皇帝,23次為關羽頒旨加封,尊號愈來愈高,清朝加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圣帝君”,僅頭銜就長達26字,且與孔子并祀,稱文武二圣。關羽的地位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由圣而神,關羽崇拜一度出現“儒稱圣,釋稱佛,道稱天尊,三教盡皈依”,“萬古祠堂遍九州”的景象,對關羽的崇拜和信仰超越了宗教、歷史和階級的限制,有些本來不容易統一的東西卻神話般地在關羽身上得到了統一(王齊洲《論關羽崇拜》),在我國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
關羽崇拜的形成,除歷史氛圍的特殊需要外,關羽身上的忠義精神,是后世關羽崇拜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原始基因。陳壽《三國志》評價歷史上的關羽“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有國士之風”,宋以后的詩文、戲劇、小說,增飾演繹了關羽的各類忠勇事跡,塑造了“精忠貫日月,大義薄云天”的關公形象。但真正成功塑造關羽“忠義”形象的作品,當屬羅貫中的長篇歷史小說《三國演義》。小說約有十八回寫到關羽,內容多與“義”相關:“桃源三結義”是其與劉、張二人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的兄弟“情義”;“屯土山約三事,降漢不降曹”,是其對漢室的“忠義”;“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是其對舊主劉備的“忠義”;黃忠馬失前蹄,不乘人之危,是其濟困扶危的“俠義”;“白馬解圍”“義拜華容”,是其知恩必報的“仁義”,“秉燭達旦”,又是其對嫂夫人的“禮義”。毛宗崗《讀三國志法》評價關羽“是古今來名將第一奇人”,堪稱“義絕”。關羽的“義絕”正是他被社會不同階層、不同集團和各方人士所崇拜的根本原因所在,關羽身上體現了“義”的全部豐富性和生動性,涉及社會倫理道德的方方面面,滿足人們對“義”的不同需求,為人們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樹立了道德理想標準。隨著歷史的不斷積累,關羽已經成為了“義”的化身,代表了中華民族的理想人格,寄托著萬千民眾的道德精神。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關羽的“義絕”,使上層精英文化(大傳統)與下層民間文化(小傳統)在關羽身上能夠達成共識,他既可以是士大夫心中“春秋大義”的代表和綱常倫理的化身,也可以是普通百姓的財神爺和守護神,關羽已然成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寄托。此外,關羽文化自身蘊含的道德意蘊決定了關羽精神具有歷久彌新的人文價值,關公的道德品行和人格氣質滿足不同時代價值信仰重構的精神需求(靳鳳林《歷史上的關公文化及其現代性轉型》),隨著時代的發展可以不斷賦予其新意,其“忠義仁智勇”的文化內核依然是當今構建中國特色人文價值體系的精神實質,這是關公文化的顯著特質。時至今日,這一文化現象也仍然沒有完全成為歷史,其蘊含的深層道德意蘊和核心內涵,值得我們持續思考和發掘。
(作者系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