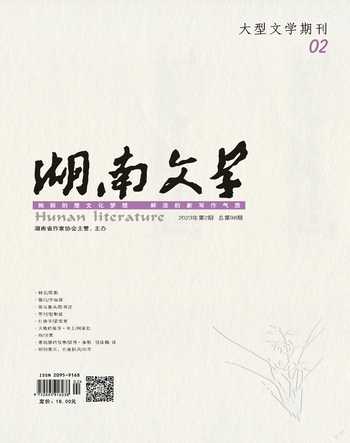季節之書
錢紅莉
雨水帖
雨水過后,陽光變得明亮起來,眼前仿佛晃動著無數錫箔。風也起了變化,吹在臉上細細茸茸,宛如溫柔撫摸,不比寒風那么急切掃臉。
眼界里,一切都是澄明的……
枝頭鳥雀喧喧,唯有斑鳩的鳴叫喑啞低徊,如若中提琴的音質,傷感荒寂,聽得久了,叫人起了遠意,總會想起空山淡薄,古寺傾圮……
洗菜時,自來水不再寒涼,水流嘩啦嘩啦,如一路小跑著唱歌,一切都欣欣然的。連冷藏于冰箱的青菜,也顯出生命無窮的蓬勃來,它們悄悄躲在食品袋里抽薹,掰開層層葉片,菜心鵝黃粉嫩。每一棵青菜皆舉著一稈細小的薹,頂端是珍珠一樣的花骨朵,細如魚子。這些青菜,縱然脫離了泥土,卻也不愿枯萎,這份銳意進取的好強之心,想必是基因自帶的——窗外春光無限,它們當真感應到了呢,就算被囚禁于逼仄漆黑的冰箱,也要加入到抽薹的起義之中……
誰都不辜負這明晃晃的早春。
露臺上一株月季,是一夜間冒出的芽尖尖,烏紫紫的,在風里抖動著,仿佛可以掐來吃。
喜歡在小區里逡巡,查看黑鐵一般的各樣果樹有無萌發。
杏,李,桃,星辰一樣密集的花骨朵,同樣是一夜間生發出來的,令人驚奇,仿佛一場暴動。
櫻桃樹上,遍布花蕾,一日日地鼓脹起來了。
碧桃,永遠是矮壯的樹種,滿枝蓓蕾大如黃豆,吹彈欲破——昨夜略微一場微雨,今晨仿佛“砰砰砰”一聲聲,所有花苞齊簇簇就把自己敞開來了。碧桃開起花來,向來一股癡氣,好比一個胖子睡得太沉而鼾聲四起,一聲迭一聲蓋過黑夜,連春天也都招架不住了。確乎沒有哪樣花像碧桃開得如此高歌猛進,簡直萬花怒綻,隔著幾里,似可聽聞聲響。由深紅而淺紅,似初盛的春潮,一波一波涌動,也像過年時爆竹被點燃,噼噼啪啪,滿地碎屑……一年年周而復始,有亙古如斯的熱鬧。
同樣一場微雨,辛夷頂破毛茸茸的外殼,舉出一小群白花來,浮在春夜里,像一盞盞靜謐的河燈。
辛夷開在深山,開在水邊,俱好。
每日騎車經過一片湖的西岸。每一年春上,湖畔那幾株玉蘭,最先開出淺粉的花,細細淡淡的,于水波的一送一遞間,恍如中國山水畫的皴皺技法,倒映著淺粉花影,惹人流連,這里面深藏一份急速飛逝的美。
春水曾被稱為桃花水,并非蕩漾,也非瀲滟,倒比較接近日本古寺門前的枯山水意境——春風柔細如發,一點點爬梳著湛藍的湖面,縱然逼窄,卻也叫人望見了海洋的浩渺無垠。
早春的風,始終蕭蕭霏霏的,一刻不停地吹,湖面隨著風勢,變幻萬端,一忽兒雨點皴,一忽兒披麻皴,一忽兒又是卷云皴了。
一個人在早春的湖邊,可以坐很久很久,獨自欣賞風行湖面的畫意。這眼前一切,似乎來自舊時代的畫,是馬遠、夏圭的,也是黃公望、陳洪綬的,也可能是沈周、石濤的。
偶爾,春風吹得急些,湖面呈現的便是大斧皴、小斧皴了,一如八大的山勢,似可將春天的一切席卷了去。慢慢地,春風漸止,湖面有了平疇野畈的廣闊,春水一如和田玉般碧綠,仿佛新生。
總歸是到了春天,自然萬物一齊活泛過來,板結了一冬的泥土,漸已蘇醒,兀自松散;人的筋骨,也不再僵硬,總喜歡出去走走,宛若初生,眼界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
距家不遠,有一小河,河畔無數春梅。年年早春,云蒸霞蔚……整座城市的人,似乎一齊擁來了,頗為喧鬧。我不太喜歡。
看花,最好一個人。
白梅最美,美在雅淡。
元人胡奎有一句詩:分明一片黃昏月,留向禪床伴寂寥。
對,白梅美就美在寂寥上,避開人世喧鬧,與黃昏的月一起沉入深夜之中。
春夜的月,同樣寂寥,像波格萊里奇彈奏的鋼琴小品,孤清無匹。
春夜的月,也似龔賢的畫,一人一石一樹,眼前的山河流云,俱為蕭瑟。
春夜的月,望得久了,到底是寒涼的,偶爾裹一層光暈,并非松花黃,而是枯黃。王維寫: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詩人所真正表達的,并非鳥的心境,而是指一個深山久居的人太過孤獨,忽為月光所驚。
人只有寂寥之時,方能覺知四時節候的變化。人只有孤獨之時,才能眺望繁星孤月,領略星挪辰移的奧秘……
去荒坡,閑走,一片枯草地上,匍匐三兩蒲公英。隔幾日,再去,忽然撐起一把把小黃傘,頗似幼童調皮的眼,骨碌碌于風里轉。
開成一片寶石藍的,永遠是阿拉伯婆婆納。野豌豆、菟絲子們始終收斂著腰身開花,一如沉思,一如低吟……
小區池塘邊,柳樹七八株。前陣,明明一派暗淡的褐灰。近日,春風細拂,柳泛酥色,一霎時生動起來了,是楊萬里的詩——柳條百尺拂銀塘,且莫深青只淺黃。
早春的柳色,適宜遠看,那一縷縷深青淺黃,如霧如煙,如一冊紙頁泛黃的《金剛經》,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世間芳菲萬種,我獨喜杏花。喜歡它“濃綠萬枝紅一點”的素淡,不比“高燒銀燭照紅妝”的海棠那般濃烈。
杏花,蓓蕾絳紅,花開而白,像故人——他一顆心,被風雨洗禮,慢慢淡下來了。
三年前,在河北太行山中偶遇一位大姐,她與我說起,北方杏花四月才開,到時還會下雪。說著,大姐將手機屏保滑開,給我品賞自己私藏的十余幅“雪中杏花圖卷”——是茫茫白雪中那一點點紅,當真是“一汀煙雨杏花寒”。
如此,一直難忘。
驚蟄帖
驚蟄后,氣溫驟升,攝氏二十五度,可穿短袖。這樣的高溫,讓人一時適應不了。地球是否被什么神秘的星系吸引著稍微脫離了既定軌道?予人轉速加劇的錯覺。
往年三月,氣溫爬升緩慢,可以讓人從容感受自然萬物的細微變化,不比今年如此猝不及防。
自雨水以來,我每日都要對小區的一株杏樹進行一番體察:從枝條僵硬,到慢慢柔軟,再到花芽一夜萌出,只小米粒那么點兒大,漸而大米粒,漸而黃豆般……昨日晨,積蓄至一個節點,一樹七分之一蓓蕾敞開花朵。今晨,再看,竟然花開滿樹了。叫人且喜又嘆——太快了,花要慢慢開啊,將春光拖長些,再長些。
我沒什么事情做,兀自坐在杏樹對面柳蔭下,靜對一樹杏花發呆。天湛藍,過了無數遍濾鏡一般地失真。近旁,干涸池塘底部,石上生草,蒲公英自水泥夾縫間躥出,舉一朵七瓣黃花。沉沉垂墜的柳枝,被風細細梳過,風吹得人幾欲昏睡……柳芽愈盛,斑鳩聲聲,如在深山。
凌晨五點,第一聲鳥鳴劃破春夜寂靜。前后窗洞開,可分辨林間各樣鳥鳴,畫眉婉轉,云雀急速,麻雀始終一驚一乍的——趁人不備,忽然“嘰”一聲,你要問它什么事吧,它又說不出所以然,末了,又趁勢“嘰”一聲,聽得久了,也頗無趣。
喜鵲偏愛正午陽光,拖著巨大尾羽俯沖而下,一邊喳喳叫,一邊大步流星,停駐于枯草叢中,啄食草籽,忽而扶搖直上了……
比起杏樹來,李樹性子憨些,只零星開三兩朵花,害羞似的,開一朵,靜一靜,再偷瞄一眼四周,等春風暫歇,再綻開一朵。三三兩兩渺小細淡的花朵,湊近了聞,沁香馥郁。上弦月掛在西天。
沿屋后步道,騎車緩行,順便查看溝渠蘆葦、香蒲、千屈菜是否萌芽。清晨濕漉漉的空氣,裹挾不知名的花香、青草香,叫人一霎時將整個身心融入到自然之中了。
荒坡遍布鉆天楊、法國梧桐以及水杉和楊柳。三月的柳,當真好看,有遠意,與俗世隔了一層的,柔柔糯糯的,叫人迷離沉醉,同林風眠筆下的江南如出一轍,那份淺綠鵝黃,蕭蕭逸逸的,如畫如夢,令人頹廢,不能奮發進取。
一路走一路看,有些不知身在何處的茫然。如此,春天相當置人失智。
合肥是一座干燥粗啞的城市。
這個時候的江南,又該是別一番情境了——江水渙渙,菜花明黃,薺麥青青,群山嵯峨……小雞雛、小鴨、小鵝茸茸出殼來,用胡蘭成的話講,天地都是這樣的貞親。
一路走,一路想著不可抵達的江南,到底無法遠行,就更加迷茫些。
一走,又到了小河邊。
大量年輕人跑步,那一張張因運動而紅撲撲的臉,可真是令人羨慕的啊。那年輕的身軀,起伏的線條,靈動的馬尾,跳脫地從我旁邊飛逝而過了,而河畔春梅尚未凋敝,一樣地如夢如煙。
我的身體大不如前了,幾乎急速衰落,連跑步也殊難,但我喜歡坐在河畔看年輕人奔跑,他們的身體里仿佛擱著我的靈魂,帶著我一起飛。
坐在河邊,隨便拔一根青草聞嗅,也是香的,根須帶著泥土的簇新,這份簇新里也雜糅著一份腥氣,濕漉漉的,像一個人的來處,深藏自然的奧秘。
春陽融融,曬得后背酥麻麻的,也還不早了。起身,往菜市去。
馬蘭頭一夜間登場,順便帶來自然的氣息,那紫紅的莖青綠的葉。水芹瘦高纖細,苜蓿青翠粉嫩,春筍胖壯乳黃……各樣植物生得可歌可泣的,簡直可以對著它們畫出一張張素描,隨便一張,堪比《詩經名物新證》中的插圖。
前陣,有人約寫“詩經風物”,頗無興趣。早已摒棄掉這種文藝腔的以虛見虛的創作手法,我們要回到自然中去,世間萬物,可看可觸可感,俯拾皆是,帶著體溫,有著活氣的。
迷茫地在菜市打轉轉,水芹的藥香,馬蘭頭的清香,香椿的濃香,依次將鼻腔洗禮一番。末了,買點兒黃鱔、蒜薹、鴨血、豬肝、肉糜、雞毛菜。慢騰騰回家,將這些什物往廚房一撂……忽然不想做飯了。
不行,得出去轉轉。
并非耐不住寂寞,而是萬物起身的召喚更能吸引人。
將小區的杏花、李花、玉蘭依次拍了一遍。山墻轉角處,幾叢芭蕉,老樁枯萎,新芽初綻,年年如此,新舊交迭,不曾更改。茶梅開花,有一些奮不顧身的頑強。一株灌木,百朵之眾,猩紅繁復奢靡,永遠開不敗,與生俱來地強悍。若是白花茶梅,則清雅得多,甚或比白牡丹、白芍藥,都美。素色花朵,一貫予人接納感,是敞開的懷抱,永無攻擊力,也是一直往里收著的綻放。這里的“里”,指代精神領域,缺乏直觀感,頗有千人各面的歧義。
掐兩枝李花回來插瓶。李樹枝條繁密,該疏疏了——酒斟半滿,樹得蕭疏,方好。
回家取出一只冰紋陶瓶,古拙憨直,儲滿水,插上花枝,隨便擱于鞋柜,都是美的。
蓓蕾未放,有含蓄收斂的低沉,配著陶瓶汝窯的淡青,看得人說不出來地好。這樣的好,是什么呢?沒有雕飾,原生態,純天然,大道至簡,大智若愚?你就是把中國所有的哲學書搬出來,都找不到一個詞來形容這李花的好。它的好,好在自然,一如亙古即在的星月。
也是這樣的春夜,好比你一人戶外散步,漆黑的蒼穹深處,忽現一彎新月,你什么也說不出,唯有與美同在,低頭走路……
黃昏,沿天鵝湖東岸騎行,夕陽穿林而來,三分橙黃七分暖黃,湖水粼粼……人行其中,如置身畫里。
沿岸一株株玉蘭,花開葳蕤:望春玉蘭,紅里氤氳著一點紫,天然的舊色;白玉蘭整個樹冠匯聚了無數白鴿,星光一樣圣潔繁密。
漸晚,暮色四合,花朵愈發潔白,有黑夜飛行的懸浮幻覺,似乎一年都開不敗的,永生永世。
一個年輕人邊騎行邊將手機開著錄抖音,嘴中念念有詞……是真快樂,一如嬰兒初涉人世的純粹,將我這個一貫頹唐厭世的人都感染了。
深夜,閑翻惲壽平畫冊,是花卉系列。尤喜他筆下杏花,有種形容不出的淡雅,唯有默默感受,看了又看,是舍不得放手的珍惜。設色淺灰,大片留白,只略略橫出一枝,斜斜地,將倒欲倒,看著心疼,本能地想去扶,又怕造次,還是縮回了手。末了,還又總是擔心她。是虛無里橫空出世的,流淌著靜氣……看舊畫,如見故人,人始終惘惘的,如讀李商隱無題詩,就是那種“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的悵惘之情。
心有起伏,何以如此喜愛杏花呢?你看陳洪綬的老樹病梅何等地有風骨,一派凜寒獨自,自成宇宙。然而,杏花既靜且鬧,始終有一口活氣在,總是給予我這個頹喪之人蓬勃的生命力。
一樹杏花,開在一日里的昏暝時刻,最美,有一點點舊氣,亦如故人,親切又疏離,伸手可觸,卻到底不能了。惲壽平筆下杏花,氤氳了文人的氣質,同樣又雜糅些人間的熱氣,叫人看了一遍又一遍,是值得珍惜的。
何止杏花呢?整個春天都值得我們珍惜。
活在春天里的人們,被花包圍,被風吹拂,似乎一切都是混沌的,猶如天地初開。
大暑帖
被高溫連續炙烤數日,終于有了一場雨。
黃昏時分,騎行于湖畔,迎面而來的風,一陣攆一陣,忽有深山溪水的涼潤,讓人精神為之一振,一霎時有了秋天的幻覺。
每一十字路口,兩兩相對,分別植有十數株一人高的木本月季,就都一齊開了紅的花,粉的花,白的花,黃的花……一派拂綠穿紅麗日長的盛景。這一朵朵大而綺麗的花,實在可觀。實則,這些齊頭并進的繁復之花,前幾日早開了的,我們不過是被太陽的烈焰曬傻了,一個個低頭急急趕路,不曾注意到它們罷了。
每年最為酷熱的大暑時節,當所有綠樹的葉子逐漸委頓而耷拉下來時,唯有紫薇開得最為熱烈濃艷。路上,小區里,公園湖畔,均見紫薇花影。似乎天氣越熱,它們開得越好——玫紅、深紫、淺紫、淺粉、純白,開著開著,便開成了瀑布狀態,簡直要飛流直下了。一拗一拗的花球,直將枝條壓彎,宛如菩薩低眉,又好比石濤的山水,有高山墜石的氣勢。
我家門前一叢紫茉莉,整個白日始終懨懨耷耷的,但,每至薄暮時分,便格棱棱活泛過來了,無盡的綠葉捧出濃紫小花,如珍如惜,小喇叭一樣滴滴滴吹著,吹亮了天上幾粒星子。
吳其濬在《植物名實圖考》中說紫茉莉“處處有之,極易繁衍”。陳淏子在《花鏡》里說它“清晨放花,午后即斂,其艷不久,而香亦不及茉莉,故不為世重”。
陳淏子的說法不甚確切。紫茉莉不僅清晨開花,黃昏時亦開。在民間,它還另有一個更形象的小名——“洗澡花”,晚飯過后人們洗澡時,正是紫茉莉開花時分。汪曾祺在《晚飯花集》里寫它:因為是在黃昏時開花,晚飯前后開得最為熱鬧,故又名晚飯花。
《紅樓夢》里,婦女之友賈寶玉也曾安慰平兒,并拈了一根棒兒遞與她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兌上料制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撲在面上也容易勻凈,且能潤澤,不像別的粉澀滯。
雖說紫茉莉的香氣似有若無,但暑熱中走出家門,一見著它們,原本一顆煩躁囂嚷的心,忽然變得靜謐。
心一靜,世間便起了涼意。
小區底樓人家,均植有幾叢紫茉莉,大多紫花品種,間有黃花、白花色系——每當暗夜來臨,就著路燈的微光,白花茉莉的那一點點白,沁著玉一樣的溫潤色澤,到底是迷人的。
不怕暑熱的花,想必天生有著韌勁,花期久長——除了紫茉莉,金銀花也在綿綿不絕地開,原本沁人的香氣一經高溫籠罩,逐漸地變得清淡起來了,淡淡淺淺,絲絲縷縷,又飄飄忽忽,如若一個剛剛學步的幼童,盤旋著,遲疑著,延宕著,一直不肯走遠。
暑氣漸盛,花氣必然清淡,不比春花那么濃烈襲人了。
所有酷暑中的花,都在收斂著性情,白花夾竹桃尤盛,漸次是我家屋后荒坡上的一年蓬、野芫荽花……站遠了眺望,坡上猶如覆著淺淺一層雪。
溝渠里生長著各樣植物:千屈菜長得高聳,獨立一條枝,四周鋪展四五片巨大的綠葉子,共同捧出頂端一稈紫花,天堂鳥一樣展翅欲飛;香蒲愈發茂盛濃碧,即將抽棒;野蓼叢叢簇簇,近日起了米粒大花苞,到底距離秋風起不遠了。
每當黃昏,我總喜歡往荒坡溝渠間逡巡一番。水杉樹上的蟬鳴不絕于耳,草叢中紡織娘的吱吱唧唧聲響成一片,間或蘆葦叢里冒出一兩聲低沉宏厚如男中音般的蟾鳴。經仔細觀察,馬尾松原也是盛夏開花,毛茸茸的花球越滾越大,起先是綠的,不幾日,漸變至赤黃,趁人不備,結出一個個塔狀小果子,隱在深綠的針葉叢中……整個植株散發出松科樹種特有的芳香,人已遠離,那香氣卻尾隨一路,孩子樣地跟腳呢,也像童年的炊煙,平鋪直敘而沉沉低垂,為風所牽絆,裊裊繞繞的,到末了,又仿佛起了回音,絕響一樣,實在好聞。
水杉的香氣也是粘人的。盛夏所有樹種的香氣,大抵是被夜色浸染出的,一如月光,一如星空。
除了這些植物,酷暑里值得看上一看的,莫非大風走云的氣勢。黃昏,在布滿濃蔭的甬道散步,原本晴空萬里,忽聞北面的天起了隱隱雷聲,一陣旋風緊跟著閃電即起即停,烏云不知從哪里火速滾來,是積雨云,淺灰色系,火山噴發一般聚攏,壘砌,愈積愈多,越壓越低,直至快要碰到對面高樓的屋頂,實在宏大壯觀,引人駐足良久。
更多的時候,是太陽銜山而去了,暑氣漸收,玫瑰色晚霞鋪滿西天,銀河一樣橫亙天庭,有眾神駕到的肅穆莊嚴,漸漸地,寂色籠罩,夜色來臨。酷暑天的黃昏,漫而長,小號一樣吱吱吱地吹,是維瓦爾第的《四季》了,一年年地,時光漫漫渙渙,世間一切都在,什么都不曾改變過,除了濕熱和流汗。
有一年出差賀州,見識眾多釀菜,苦瓜釀、瓠子釀、秋葵釀、辣椒釀、藕釀……還有南瓜花釀,客家人的詩性無處不在。至今回味那里的芋頭夾肉釀。回家復制過,但這邊的普通芋頭,比起那里的荔浦芋頭,差得并非一個檔次。
前陣,濕熱難擋,胃口頗差,試做一道下飯菜——辣椒釀。未找教程,唯憑手感。買回露天種植的有機辣椒十余只,剪去辣椒蒂,掏空辣椒籽。瘦肉糜里打一只雞蛋,拌上姜絲、小蔥粒、淀粉,鹽、醬油適量。當空腹辣椒被肉糜塞滿,將之平鋪鍋底,微油,小火,焗至焦黃,激點開水,燜煮兩三分鐘,大火收汁,起鍋裝盤。兩三只辣椒釀,便可解決掉半盞白米飯,葷素搭配,營養均衡,且還刺激食欲。
倘若哪日遇見南瓜花,何不再做一道花釀?
小暑之后的半個月,暑氣到達極致。以中醫的理論,濕熱會“困”住人的五臟機能,有傷心氣。天熱,人易貪涼,西瓜、冷飲不絕,總是頻繁穿梭于戶外炎熱環境與室內空調房之間,心氣易損。中醫最講氣——倘若氣泄掉,人難免染病嘛。
在一個中醫公眾號看來一道養生涼菜——甜杏仁拌茴香。
甜杏仁用水煮十分鐘,茴香洗凈切碎,以2:1的比例放入醬油、醋拌勻。
甜杏仁補氣,兼有潤肺、潤腸之效。茴香的種子就是常用的調料小茴香,也是一味補腎陽的中藥。茴香菜除了補腎,也還有開胃散寒的作用。這道甜杏仁拌茴香不僅清暑,對于預防熱傷風,也有功效。
酷夏的主旨,就是盡量少動明火。我還喜歡做另一道簡單至極的涼拌菜——西芹百合。西芹斜切寸段,焯水斷生,備用。蘭州鮮百合,一瓣瓣剝開,洗凈,焯水斷生。將兩者混合一起,拌入適量鹽、芝麻油、藤椒油即可。口感參差多重,味蕾首先被藤椒油的麻香轟開,繼而是西芹的酥脆,百合的甜糯,再呷一口雪花冰啤,可喜,可悅。
一日,忽然不想繼續三菜一湯的煙熏火烤,去成品店買一坨醬牛肉,忽然被一堆閃閃發光的鹵鴨爪擄走魂魄。家務完畢,坐在藺草席上,狂啃鴨爪,辣得咝咝地倒抽涼氣,俄頃,汗出,咕嚕幾口檸檬水壓驚。
日子就這么零敲碎打地過著,再過半月余,就也立秋了。古語云:立秋分早晚。意即,再怎么熱,立秋之后的早晚,也都有了涼意。再順藤摸瓜去古詩中展望一下“寒露驚秋晚”的日子,為期不遠了。
近些年,年歲漸長,心氣漸萎,每過完一個酷暑,深覺一下蒼老十余歲。除了吃吃喝喝,還有什么可撫慰人的呢?
寒露帖
轉眼寒露。天色宛如沁了一層水墨,霧氣茫茫如馬勒《大地之歌》,詠嘆調一樣籠罩四野,天空明凈,冷月高懸……人行戶外,涼風習習,總是寒寒瑟瑟的,莫如一句古詩:空庭得秋長漫漫,寒露入暮愁衣單。
寒露驚秋晚,朝看菊漸黃。我家屋后山坡,遍布野菊,遠望,星星點點的黃。待走近了,菊叢下鋪排大片鴨跖草、芒草。迎著晨風,每一片草葉異常珍惜地將露珠抱在心尖尖上,每一滴珠露似可映照出整個宇宙乾坤。這晨間的瓔珞珠玉,一滴滴晶瑩剔透,是轉瞬即逝的美。
大片柳林,無數枝條,靜靜低垂,一齊籠于清涼的霧靄之中,枝葉間飄逸著的似有若無的氣息,想必是晨嵐了。秋天深了,木芙蓉忽然被點燃,繁花大朵砰砰有聲地怒綻于漠漠秋風中。夾竹桃將花期自春暮一直延展至秋深,紅的花,白的花,默默給生命收尾……
秋天深了,雁群南飛。荒坡草叢中,再也不聞紡織娘歌聲,徒添無數油蛉的鳴叫。白鷺不見身影,唯麻雀眾多,呼啦啦一片。松鴉也不見了,長尾喜鵲遁跡而去。溝渠內蘆葦繁盛至極,迎著秋風嘩嘩作響。香蒲一年一度,結出無數蒲棒,深咖色,像極火腿腸,仿佛聞得見肉香。無數水杉,身姿筆直,針狀葉叢散發出迷幻的藥香氣,沁人心脾。
荒草滿坡,分布著大薊、小薊、夏枯草、蒺藜、車前子……唯芒草,適合遠觀,一穗穗笤帚狀白花,沐風浴露,靜穆如儀。寒露以后,芒花雪一樣,茫茫渺渺,總是那么寂寥蒼涼,如若水邊琴聲,讓人起了遠意。這遠意里,涵容未曾獲得的夢想,也是“得未曾有”之未來。
唐代詩僧齊己有詩:
宜陽南面路,下岳又經過。
楓葉紅遮店,芒花白滿坡。
猿無山漸薄,雁眾水還多。
日落猶前去,諸村牧豎歌。
深秋適合去山中,芒花開滿坡谷,山也薄了,有“秋盡一身輕”的意思了。四季流轉到寒露,好比人至中年。無論舍得、舍不得的,幾場秋風秋雨,都也留不住了。
天空澄澈,晨星閃亮。地上紅蓼結起一穗一穗花骨朵,沉沉低垂。除了宋徽宗趙佶畫過《紅蓼白鵝圖》,宋元以來,乏人問津。至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齊白石一度喜歡畫蓼,《紅蓼蟋蟀圖》《紅蓼蜻蜓》《紅蓼螻蛄》《紅蓼彩蝶》……一幅幅,惹人憐愛,滿紙鄉野氣息。到了暮年,齊老頭又畫紅蓼圖,不見蟋蟀、蜻蜓、螻蛄、彩蝶,唯余一株獨蓼,三兩葉子,設了焦墨的,黑葉配紅花,望之心驚。
看齊老頭的畫,越到后來,越是一份“物哀”之美。如聞拉赫瑪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開篇初始,鋼琴一聲聲,如旭日初升,緊隨而來的上百小提琴,徘徊低音區,拉出森林萬頃,遠古的綠意撲面而來,青苔歷歷間,稚鹿、溪水徐徐目前……簡直奪人心魄。
無論繪畫,抑或音樂,人類何嘗不在試圖一點點還原自然,呈現自然?唯書寫,最為笨拙,總是不能精準抵達核心地帶。一份份自然之美,只適合于人心間蕩漾。
家居市郊,毗連一片菜地。我喜歡早起去菜蔬間徜徉。
有位老人起得更早,她正給一壟韭菜澆水,一瓢一瓢潑過去,有愛惜的意思。挨著韭菜地的籬笆墻上,爬滿一架綠葫蘆,伶仃幾朵白花。花葉皆有茸茸之氣。隔老遠,似也聞得著清苦之味。
葫蘆、瓠子、牽牛、木槿,一樣樣植物,皆喜愛夜間開花,當太陽初起,她們紛紛將花瓣閉合,這些植物大約皆可被稱作“朝顏”的。我站在習習涼風中,將一架葫蘆看了又看。這些自然界中一株株平凡植物,宛如一粒粒頑石,遍布青苔,簡單原始,叫人感知著時間的痕跡。這些平凡簡單的東西,都是美的。這眼前一架葫蘆花,白得貞靜,連晨風都要繞著她們走。這樣的幾朵花,太純潔了——晨曦遍布,秋風自遙遠的天邊來,仿佛帶有溪水的清甜,默默陪伴一架葫蘆靜靜開花。
葫蘆開花,也不為別的,就是純粹開花而已。
這自然中的一切,實在撫慰人。
秋日晴空,高遠遼闊,始終是瓦窯的淡青,片云也無,四海八荒,空無所有,正應了古詩——“有時空望孤云高”。
秋夜更美。用過晚餐,照常去小區木椅上坐一會兒,觀觀天象,聽聽秋聲……我就是這樣沉淀自己的。
夜氣甘冽,云蓋四野,一輪明月懸于樓縫間,大而圓,仿佛初來世間的橘黃色,除了驚奇,也說不出什么,我就望著它,一直望著它。被自然之美擊中后的漣漪,于心間起伏微漾。
深秋月色,亮而靜,有亙古的意味。咫尺處,一株無患子,整個樹冠日漸地黃下去,月色下仿佛燃燒起來了——窗里人將老,門前樹欲秋。
夜夜,天上無月,唯余大朵白云。天穹幽藍,襯得云格外白亮,望之良久。
秋天一日日深下去,像被神投入幽潭,不再憂心焦慮,人生的遠景、近景,似一夜消失,唯余一顆心。白天,坐在陽臺曬太陽,牙刷、毛巾、被褥、枕頭抱出曬曬。黃昏后,被陽光洗禮后的棉絮,像極北方老面發的饅頭,松軟而暄香。
四季里,唯秋冬兩季的太陽飽含幽香。
林間有風,天空澄澈透明,迎著光行走,秋光讓人睜不開眼。忽而秋風起,法國梧桐的黃葉忽剌忽剌往下旋落,蝶一樣輕盈。一年年里,紅蓼繁了密了,芒草黃了枯了,夏枯草堅持在秋風里開紫色小花……眼前一切,縱然蕭瑟荒涼,但,卻那么美——到底,自然的荒蕪更有審美力。深秋的蕭瑟與盛夏的葳蕤,自是別樣,皺紋皓首比之明眸皓齒,更見生命的力度與內涵。
深秋真是蘊藏深厚的一個時節,銀杏、烏桕于秋光下,如若兩個永恒的發光星體,襯著鈷藍的天,黃如赤子,紅如赤子。
每年這個時辰,特別向往回到鄉下:那里最好有一條江,或者一條河,夾岸大片稻田。丘陵山岡上,蕎麥地蜿蜒不竭。僻野的深秋氣質卓絕,更見風骨——零落的草甸,荒涼的山岡,清澈的河流……一齊平鋪于地上,連秋風也是無所牽絆的,秋霜一日濃似一日,田畈一派泠泠然。
每臨秋日心必閑。坐在鋪滿陽光的客廳,翻牧溪畫冊,到《六柿圖》,忽然感動起來……是這樣的墨色,一瓣瓣,淺淡深濃。舊氣,隔了千年遞過來的舊氣,尚有余溫,是清灰里焐過的,底層的,日常的,謙卑的……
是牧溪的平凡打動了我。除了《六柿圖》,還有《白菜圖》。每日都會買一兩斤白菜。寒露之后,菜有霜氣,異常可口。
百菜不如白菜。牧溪筆下的白菜,正是“客來一味”,何以令人心悸?
“春初新韭,秋末晚菘”,這八個漢字里,埋伏著時序節令、人間煙火,以及一顆始終跳動著的溫熱的心。
牧溪感知到的,又是什么呢?
白菜晚菘圖中那些墨色,已然舊了。舊的東西,總是珍貴的,厚重,凝練,內斂,欲言又止,留下一派清氣,以及與生活隔了一層的凜冽之氣。這所有的一切,皆源于秋氣——荒涼之氣。
我無法在盛夏的溽熱里讀懂牧溪,唯有深秋,一種無所不在的冽與寒,正是牧溪的精髓所系。他的《寒鴉圖》那么孤獨,甚至凄涼,何嘗不在表達一顆心呢?屏蔽一切傖俗熱鬧,走向內心的明月深山。如此,孤獨凄涼何以不是一份大自在?牧溪的燕子,猶如風中少年,一個獨自飛,畫幅上端稍微垂下幾條樹枝,是紅柳吧,一樣被墨色浸透了,縱是春草蔓生的三月,也是叫你守住了一份清寒。
每臨深秋,我走在菜地,走在風里,走在湖邊,不免想起牧溪《墨雁圖》里一句題詩:西風吹水浪成堆。那份不請自來的寒涼,讓人真切感知到人與自然之間的那份兩兩相照,以及秋天老了蘆花一夜白頭的無可挽回。
人們秋夜望月,何嘗不是那種物我之間的兩兩相照呢?
牧溪的僧人身份,注定了他的抽離感。到了二十世紀初葉,另一畫壇異數常玉,簡直走向了牧溪的反面。
孤寒的反面,不正是溫靜嗎?
常玉的溫靜無所不在。他的粉色系列,猶如嬰兒安睡于夏帳之中,輕輕掀開一角,乳香鋪天蓋地。這是屬于我個人的視覺上的通感了。
常玉大片未知的留白,構成了他藝術的夏帳,無數線條流暢比例失衡的馬、駱駝、鹿、象、人,猶如亙古即在的嬰兒。整個畫面,像極西方圣嬰們的受洗圖卷,溫柔,祥和,寧靜。
一幅“嬉蝶”圖,簡直神品——背景一向是常玉派系的“粉”。白貓自粉色云堆間躍出,輕輕把一只灰蝶捉住了……那一刻,仿佛叫人知道了流水惘惘的意思。視覺上無限的沖擊力,永遠那么動人心魄,過后,又默默消弭于荒蕪的時間中。
常玉的人體系列、動物系列、瓶花系列,所表達的主題,無非時間的流逝,是將人拋荒于廣漠的時間里而無能為力的消逝,流水一樣,一刻也不曾停止地消逝。
牧溪的抽離,常玉的淺淡,一遍遍體現于孤寒溫靜之中,像極這眼前的秋。
大雪帖
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四季流轉中,轉眼大雪。門前柿樹上黃葉,寥寥無幾,飄來落去,猶如一首《憶秦娥》,并非唐詩,是宋詞。宋詞的格局較唐詩小,長句連短句,仄仄平平,抑揚頓挫,確乎是關于冬日的聲聲斷斷。風中黃葉,并非字字錦,仿佛歲暮無依的孤單凋零。
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寒冬注定就是用來腌制咸菜蔬的。一堆鴿蛋般大小的圓白蘿卜,用線串起,曬制蘿卜干。做這份活,機械無聊,最好有音樂陪伴。要將巴赫一部冗長的《英國組曲》聽完,才能將所有蘿卜串好,是驚人的耐心。手工活越做越少了。長夜里,織一件毛衣,打一雙手套,縫一床被褥……漸成古老往事。
黃河以北地區,早已大面積飄雪。雪花落在魚鱗瓦,落在枯草地,落在荒坡,黑白分明,不注意,以為隔夜的一場霜。霜作為自然界中最為涼薄的存在,直如人心世態,經不起拿捏。所有北窗封起,桌上爐火正溫,栗炭正紅,鍋里燉了羊肉,裊裊如煙的熱氣中,添些粉絲、青蒜,吃在嘴里,豐腴滑嫩。有一杯黃酒更好,抿一口,一種發酵后的燙瞬間占領喉舌,如大軍壓境,直搗肺腑肝腸。窗外雪正飄,屋內飲酒人默然無聲。
或者,一只老雞,砂鍋里滾著,丟幾粒白果進去,咕嚕咕嚕一鍋好湯。涮幾片冬筍,燉一塊豆腐,燙半斤白菜,最是鮮甜甘美。民諺有:百菜不如白菜。畫僧牧溪喜畫白菜,題款總是“待客一味”四字,一如冬日,沉靜又平凡,有一直過到老的篤定在。
冬天還可用來做些什么呢?無非喝杯酒,談談天,聊聊文學也好。實則,并未有什么可以促膝深談。一二知己,下盤棋更佳。屋外雪正緊,屋內人在長考,修身,靜心。
大雪之后,白日更短。五點半光景,斜陽欲墜,如若一個燃燒未盡的球體,懸浮西天,瞬間沒入地平線,人世一忽兒暗下來。長夜是一條流淌的大河,河岸有一些樹和零星的人。
寂寥小雪閑中過,斑駁輕霜鬢上加。
算得流年無奈處,莫將詩句祝蒼華。
徐鉉詩好,點出冬日的閑,襯出流年的無奈。人忙碌時,無暇惆悵煩憂。一旦閑下來,才會關注內心的需求。作為一個典型的閑人,我主要利用冬天讀閑書。
有一夜,看一位作者寫馬勒,驚心動魄,好比古人說的“點畫萬態,骨體千姿”。好文章是一行行書法,令人沉醉忘我。好文章,也是漫天雪地里走來的,渾身揮不去的清冽,北風蕭蕭寒徹,是“陰影覆蓋下的小溪”,靜靜流淌……
古典音樂在冬天是繞不過去的。最喜歡靠在家里暖氣片上,聽圣桑《天鵝》,舒曼《童年即景》,柴可夫斯基《四季》,拉赫瑪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屋外,觸目皆靜,蒼灰的天上不見鳥影,頹唐與勃發交織的節候,默片一樣冗長。假若用四季比喻音樂——流行樂是春天,處處草長鶯飛花團錦簇,直接予人感官刺激;夏季是歌劇,一首詠嘆調唱下來,大汗淋漓,元氣大傷,需要歇至秋盡了;古典樂則是永恒的冬季,白雪皚皚,寒風凜冽,暗流涌動。這樣的季節,一開始你怎能喜歡呢?非得等到一定的年歲,方能融入。貝多芬有一首《A大調大提琴奏鳴曲》,久石讓版本,經年陪伴我。因為唯一,所以懂得。
聽貝多芬,就是將一個人關在冬日屋子里煮茶,茶葉于紫砂壺里重新復活,沁出異香,一遍又一遍。但凡在人世時苦難深重的音樂家,最后給予人類的多是精神上的微甜。久石讓的琴聲,有拯救感。
久石讓這個老頭其貌不揚,個頭矮小,穿一件灰西裝,還是舊的。可是,當他端坐琴邊彈奏貝多芬時,仿佛脫胎換骨了,波瀾壯闊,靈動飛揚。一個人的才能,足以摧毀一切,重建一切,讓人親愛,欲罷不能。
久石讓有一首鋼琴曲——《你可以在靜靜雪夜等我嗎》,彈得白雪彌漫,所有人間窗戶皆閉合,唯一的屋子里,一根煙被點燃,靈魂起舞,星光、月光以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還那么遙遠。
冬天正漫長。只要一口熱氣在,縱然平凡如我們,也有一粥一飯的光輝。
責任編輯: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