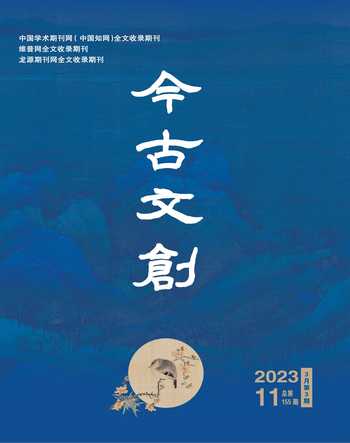淺析北宋時期岢嵐軍軍事防御戰略的形成


【摘要】 北宋時期的岢嵐軍作為宋遼邊境地區的行政區劃,扼守宋遼邊境重要地區草城川,地理上的重要性使岢嵐軍成為宋遼兩國必爭之地。景德元年,遼軍大舉入侵宋朝,宋遼戰爭爆發,而岢嵐軍作為宋遼邊境地區要沖,在整個宋遼戰場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軍根據戰場形勢靈活變化,在岢嵐軍一帶隨機應變,制定出不同的防御戰略。一方面,由于自然地理因素、人文地理因素、宋廷大戰略文化影響,宋軍在岢嵐軍一帶采取了前沿防御戰略,在景德元年宋遼戰爭初期獲得了不菲的戰果。另一方面,宋軍在景德元年宋遼戰爭中依據形勢變化制定了彈性防御戰略。在遼國大軍逼近河北地區之時,派岢嵐軍一帶軍隊發動突襲,在邊境地區取得了一定的戰略優勢。宋軍在岢嵐軍一帶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宋遼澶淵之盟的簽訂,為宋遼和平共處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 岢嵐軍;北宋;防御戰略
【中圖分類號】K244?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1-007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1.023
11世紀中期,遼國、西夏和北宋王朝構成了當時中國的主要政治格局。這一時期,地處中原的北宋王朝與遼國、西夏多次展開戰爭,雙方圍繞邊境上的一些重要戰略地點展開爭奪,宋遼邊境上的岢嵐軍就是一個典例。景德元年,遼國大舉進犯北宋,采取了圍攻岢嵐軍的戰略。由于宋廷在岢嵐軍一帶采取了防御戰略,擊退了遼軍。學者們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岢嵐軍有所關注,劉宇瑞[1]從河東路軍事地理的視角肯定了岢嵐軍在河東路軍事戰略地位重要性;胡守靜[2]則從界壕的角度剖析了岢嵐軍周圍的界壕,并對其防御作用進行了中肯的評價;徐琳[3]則從岢嵐境內的長城遺址入手,對岢嵐附近的長城進行了考證;馬繼業[4]則從河東路城池修繕的角度肯定了岢嵐軍的戰略價值。以上文章均從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岢嵐軍在整個河東路中的戰略地位,但并未單一地從岢嵐軍角度出發,以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當時宋朝形成的大戰略文化論述宋王朝在該地形成的防御戰略。因此本文將通過上述因素來論述宋廷在岢嵐軍一帶所采取的戰略防御方針,并結合宋真宗時期宋遼戰爭中宋軍在岢嵐軍一帶成功的案例來進行補充說明。
一、自然地理因素——岢嵐軍一帶防御戰略形成的天然屏障
宋代的岢嵐軍,即現在的山西省忻州市岢嵐縣。岢嵐軍在北宋初年時屬北漢管轄,不在北宋的疆域內。宋太宗即位后,發動滅亡北漢之戰,北漢在宋軍摧枯拉朽的攻勢下迅速投降,宋太宗在滅亡北漢之后,于太平興國五年,以嵐州嵐谷縣建為軍,這便是北宋時期岢嵐軍建制之始。岢嵐軍位于宋遼邊境地區,扼守遼國西京帶一部分領土。“太原則忻、代二州,寧化、岢嵐二軍,控契丹之朔云、麟府二州,守河外嵐、石、隰三州。”[5]岢嵐地勢東南高,西北低。與整個山西地區地貌環境相類似,區域內重巒疊嶂。“復山疊嶺,形險勢聳。”[10]多山的地勢使得岢嵐軍成為宋遼邊境上的一處軍事戰略重地。其一,岢嵐軍扼守河東路重鎮太原城,“扼西路之吭拊晉陽之背。”[10]而太原城得失事關洛陽、長安得失,洛陽、長安一失,開封則無險可守;其二,岢嵐軍扼守宋遼邊境之地草城川,據《武經總要》所載,其距離岢嵐軍不過短短三十里。如果宋遼之間一旦爆發戰爭,遼人很可能從草城川出兵,襲擊岢嵐軍,威脅到整個山西的安全。宋人在奏議中注意到了草城川、岢嵐軍在邊境上的重要性。“惟岢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11]“況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止隔界壕。”[6]總之,岢嵐軍一帶多山的地形因素為宋軍在這里實行戰略防御形成了天然良好的基礎。
二、人文地理因素——岢嵐軍一帶防御戰略形成的推動因子
(一)人口
一個地區的人口多寡與該地是否能在戰爭時期組織起有效的防御有著一定的關聯。筆者試結合《中國人口史宋遼金卷》[7]和《宋代河東路經濟研究》[8]對北宋時期山西的各軍戶數、人口占比及人口密度整理如下(政和三年設立的慶祚軍由于設立時間晚于列入統計的年代,缺乏人口資料,尚未歸入統計列表。之后各表不再將慶祚軍列列入統計)。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岢嵐軍人口在山西各軍中較為稀少。從人口密度來看,太平興國年間各軍人口密度相差不大,元豐元年、崇寧元年火山軍人口密度則遠遠領先于其他軍。岢嵐軍在崇寧元年的人口為2917戶,位于統計列表中第五位。從崇寧元年岢嵐軍人口密度來看,岢嵐軍位于第四位。然而,若從整個河東路人口占比來看,岢嵐軍占比就沒那么大了。岢嵐軍人口之所以如此稀少,或許是由于其地邊遠之故,“麟府州、岢嵐軍極邊之地。”[9]宋境內居民往往以安居樂業為主要目標,不愿意自冒風險遷居易發生戰爭的邊境地區。這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解釋岢嵐軍境內人口稀少的現象。
(二)商業
商業的發展與繁榮最能反映出一個地方經濟的活躍度,而商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該地貨物流通狀況與市場交易頻繁程度。筆者根據《宋會要輯稿》[10]以及《宋代河東路經濟研究》[13]將山西地區各軍商稅整理如下(小數點前單位為貫,小數點后單位為文)。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岢嵐軍在熙寧十年前商稅稅額為3894貫,相比寧化軍、火山軍還多出一部分,但是到了熙寧十年時,商稅稅額大為減少。岢嵐軍商稅稅額的減少,應當和當時宋遼劃界,宋廷失去岢嵐軍大部分領土相關聯。熙寧八年,宋廷將“南北百余里,東西五十里”[11]的土地割讓給遼國,這大大減少了商人們經商活動的空間,這就使商人從事商業活動有了一定的困難。其次,岢嵐軍商稅減少可能還和市馬貿易活動的減少有關。北宋時期,由于宋廷缺乏飼養良馬天然環境,于是采取在邊境地區設立馬市的辦法買馬。“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岢嵐軍” [12]。由于買賣馬匹獲利不菲,一部分別有用心之人便開始越邊界盜取遼人良馬,再返回宋境內出售。因岢嵐軍地處邊境,再加上宋廷在這里設立了馬市,方便就地銷贓,獲取盈利。這一系列行為引起了遼人的不滿,遼人稱“邊人多盜馬越界趨利。”[13]神宗不得不將岢嵐軍市馬機構關閉,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商稅稅額。
三、北宋初年對遼攻守大戰略文化的轉變——自太宗末期確立的對遼防御戰略
宋初,趙匡胤一方面積極整頓內政、大修武備,同時對遼國附屬國北漢采取積極經營的戰略。宋太祖開寶元年(968年),“丙寅,命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領兵屯洺州,將有事于北漢也。”[14]但是這次的征伐行動卻由于遼軍的支援、氣溫突變、軍中多疫病等原因而不得不停止。宋太宗即位后,由于宋太宗通過“斧聲燭影”事件即位,人心多有不服,宋太宗便繼承了太祖對外積極經營的戰略,“太原我必取之。”[15]由于宋太宗討伐北漢軍事布局得當,郭進在擊敗來援的遼軍軍隊后,太原城很快投降。宋太宗在討伐北漢勝利后,便有了輕視遼國之心,宋太宗并未讓軍隊休養生息,而是北上收復燕云十六州。由于軍心懈怠、人心不齊等種種因素,最終宋軍在高粱河一戰慘敗,“帝乘驢車南走。”[15]此次戰敗后,宋太宗并未放棄奪回幽云十六州的想法,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聽從大臣們建議決定再度討伐遼國,但卻在岐溝關一戰中大敗。此后,宋軍在陳家谷、君子館等戰役之中又是大敗,宋太宗甚至還在伐遼的戰爭中腿上中了兩箭。身體的傷勢、屢次伐遼的失敗、再加上軍中扶立太祖后裔趙德昭的動亂,使太宗放棄了收回燕云十六州的行動,并產生了嚴重的畏遼情緒。宋太宗開始將重心放在內治上,再也不談伐遼之事了,“上因謂近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18]太宗對遼國的軍事部署開始傾向于消極防御戰略,這影響到了真宗時期對遼國的軍事策略。
四、戰略防御運用成功的典型案例——景德元年遼伐岢嵐軍之戰
曾瑞龍曾在《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15]中指出:傳統戰爭的防御戰形態有三種,即前沿防御、縱深防御和彈性防御。中國歷代王朝多采用前沿防御戰略,宋廷也不例外,在岢嵐軍一帶采取了前沿防御戰略。這種防御戰略在宋遼戰爭初期取得了很大效果。
景德元年九月,遼國大舉入寇,“秋閏九月,帝同母蕭太后大舉攻邊,遣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軍、安順軍……契丹兵東駐陽城淀。又分兵圍岢嵐軍。”[16]當時并代鈐轄高繼勛面臨著防御遼國軍隊入侵,他認為,宋軍應當憑借當地地形優勢進行防御,待敵人出現進攻空隙時再出擊。“敵雖眾而鼓譟不成列將無人也,我領騎兵三千,雖不足與戰,侯敵南去,當臨隘出奇以要擊之。彼前不得戰,退不得還,子可悉眾左右乘之,必大亂。”[17]果然,遼軍的進攻出現了漏洞,高繼勛即刻出擊,大獲全勝。“追殺至寒光嶺,斬首及自相騰轢以死者萬余人。焚車帳獲馬牛橐駞器械蓋數萬計。”[17]
此后遼軍再度對岢嵐軍發動進攻,此時的宋廷并沒有在岢嵐軍一帶堅守前沿防御策略,而是靈活變通,將岢嵐軍放入反擊遼國的軍事大戰略中進行考慮。當時契丹主要的軍事目標是河北定州,遼軍只不過派出了一小部分部隊圍攻岢嵐軍。在擊敗遼國軍隊后,宋廷為了緩解河北一帶抗擊遼軍的壓力,在岢嵐軍一帶采取了彈性防御戰略。彈性防御戰略是在一定程度上摒棄領土概念,以軍隊為核心,將擊敗敵人軍隊作為勝利目標。景德元年十月,契丹再次圍攻岢嵐軍,宋廷得知消息后,命令麟府鈐轄韓守英率兵前往岢嵐軍,并令“岢嵐威虜軍、保州、北平寨部署等深入賊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18]宋廷對來犯的遼國軍隊采取了分割進攻的戰略,取得大勝,“保莫州、岢嵐威虜軍、北平寨并言擊敗契丹,群臣稱賀。”[18]這次戰役勝利后不久,宋真宗聽取寇準建議,親臨澶州城下,宋軍大部分主力也開始向澶州城靠攏,這時又發生遼軍主帥蕭撻覽被宋軍床子弩射死一事,“敵大挫衂,退卻不敢動。”[18]宋遼戰爭的天平明顯向宋朝傾斜,在這種不利形勢下,遼國開始與宋朝商討和平條款,在經過一系列的外交談判后,宋遼之間達成澶淵之盟,開啟了宋遼之間來之不易的和平。
參考文獻:
[1]劉宇瑞.北宋河東路軍事地理研究[D].山西大學, 2017.
[2]胡守靜.北宋西北界壕考[D].寧夏大學,2018.
[3]徐琳.岢嵐縣境內長城小考[J].晉城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7,10(5).
[4]馬繼業.宋代城池防御探究[D].山東師范大學, 2005.
[5]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6.
[6]歐陽修.歐陽修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1.
[7]吳松弟.中國人口史·遼宋金元時期[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8]賈秋瑩.宋代河東路經濟研究[D].河北大學,2012.
[9]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0.
[10]徐松.宋會要輯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1]彭山杉.封陲之守——宋遼河東熙寧劃界諸層面[D].復旦大學,2012.
[12]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4.
[13]馬端臨.文獻通考[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4]畢沅.續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99.
[15]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16]葉隆禮.契丹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4.
[17]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18]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簡介:
閆宇佳,男,山西忻州人,延安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