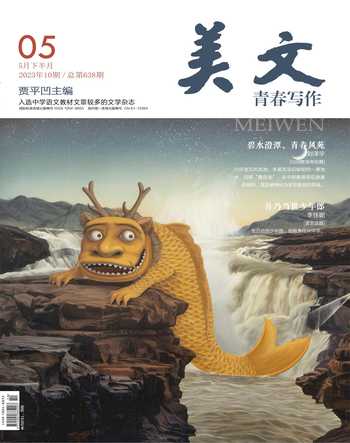青年人的路
楊晨潔
任何藝術家都不可能單獨地具有意義,我們總是要在不同的參照間,給他以評價。美學的,往往也是歷史的。作家的創作幾乎毫無例外地要與傳統構成某種關系,或是完成對傳統的建構,或是沿用傳統的因子形成對當下的講述。甚至我們可以毫不避諱地說,作為藝術家的作者,其創作背后包涵的過去有多遠,作品存在的范圍就有多大。
曾經被特別強調的“美”或“美感”,作為一種獨異、敏感的經驗,較之于社會生活日益粗鄙化的趨勢,越來越顯出它的空洞和多余。當然,仍有一些領域執守著“美”的權利,比如文學。
青年時代的審美趣味對其今后的人生,是底色般的存在。我們對未來審美方向的預判,也需要從現在青年人的傾向中找到依據。本期的美文話題提出了“以詩言遠志”,我們提倡青年人在詩歌這一傳統且經典的文體形式中,找到自己的方法。來稿中,許多經青年人之手綻放的古典審美情致,令人驚喜地共存著現代與傳統的雙重意志。《吾乃當世少年郎》寫得大氣磅礴,行文間的自信與自強,縱貫作者所了解的全部中國史,囊括現實中時代發展的大回音。竟讓人忍不住遙想至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有如此文章,我們可能無需再高度地介懷,古時之傳統如何在當下留存,焦慮當今之意義如何延續至未來。這些青年的情懷以及自我的彰顯,足以說明一切。
對古之傳統,青少年還會有更新奇的解讀和獨此一家的傳承。《愚公移山》乍看題目并無新意,走進文章才發現這是位戴著古人帽子的“新潮派”,其間對愚公移山的現代詮釋,雖會讓人想起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但在內容上卻富有青年人的樂觀,“移山”變為了對山的合理開發,不必消耗過多的人力,更不需破壞原有的平衡,山并未移走,路卻修得通暢。轉換思維,古時的許多議題,或許還有更多的解讀方向。
自由且樂觀,襲古又創新,青年人穿行在歷史傳統中,攜帶著既往的火種,沿路播撒,向前開拓著新的審美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