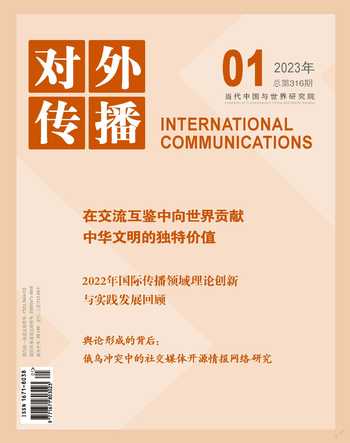2022年中國視聽領域國際傳播實踐創新與未來展望
葉琿 劉俊
【內容提要】2022年,中國視聽領域國際傳播呈現出主體多元化、渠道平臺復合化、傳播機制復雜化與去邊界化的特征。在當前較為嚴峻的國際輿論環境下,更加完善立體、靈活多樣的傳播機制具備為講好中國故事,展示可信、可愛、可敬中國形象開拓藍海的強大潛能。要實現這一點,有必要做好頂層戰略規劃,推動不同傳播主體、渠道形成傳播合力,以低語態的信息實現跨文化、跨國的信息破圈,并形成分區域的精準化傳播。
【關鍵詞】 視聽作品 國際傳播 新媒體平臺 戰略傳播 共情傳播 精準傳播
一、引言:視聽國際傳播的優勢與獨特性
伴隨著中國迅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其受關注程度以及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這為中國參與國際社會治理帶來了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中心—邊緣”格局的挑戰使得近年來我國的經濟貿易、文化交往、國際輿論等領域面臨著嚴峻的不利環境;而另一方面,中國以和平崛起的大國形象在國際社會中倡導推廣互惠互贏的新型國際交往準則,中國在相關領域已經深度嵌入國際社會的經濟文化實踐中,中國對于國際社會的影響也不是單純在民族—國家制度設計層面設置障礙可以阻擋的。
中國視聽作品國際傳播這一場域典型地體現出這種機遇與挑戰并存的特征。從整體上看,影視視聽的全球產業布局以及權力格局,與全球當下的中心—邊緣格局類似,呈現出歐美尤其是美國主導,憑借其全球文化貿易主導權及其對全球傳播、發行網絡的掌控,成為最重要的視聽產品輸出方以及游戲規則制定者。在這種整體情況下,中國視聽作品在制度層面與話語權層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掣肘。但另一方面,視聽文本的傳播作為一種文化活動,它帶有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說“整體的生活方式”①的自發性色彩,其流動與傳播帶有很強的自下而上的自發性,并不完全受制于民族國家的制度邏輯。尤其是在信息通訊技術(ICTs)的蓬勃發展下,國際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要素不斷被數字化、信息化,有學者指出,數字技術所打造的“虛擬或第三交往空間”越來越成為視聽作品對外傳播、建構中國話語、講述中國故事的新型平臺②。
視聽內容具有受眾辨識信息的門檻低,同時影響受眾情感的能力高的特質;而視聽領域的國際傳播行為則具有主體多元化、渠道平臺復合化、傳播機制復雜化與去邊界化等特征。在當前較為嚴峻的國際輿論環境下,視聽領域國際傳播的相應特質特征具備為講好中國故事,展示可信、可愛、可敬中國形象開拓藍海的強大潛能。
二、2022年中國視聽領域國際傳播實踐創新
縱然面臨著多重因素疊加的相對不利的國際輿論環境和國際傳播態勢,但2022年中國在視聽領域的國際傳播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拓展了一些有效的做法。本文對其中一些重點和創新性做法進行如下盤點。
(一)主題性劇集作品的海外傳播
近年來,以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為背景,以新農村發展為主題的劇集創作成為視聽領域的醒目現象。《山海情》作為在國內收視市場引起巨大反響的此類視聽劇集代表,在2022年也開啟了其海外傳播、展示中國脫貧攻堅歷史成果的新征程。寧夏衛視獲得了該劇在阿拉伯語地區播出授權,已與中東廣播中心(MBC)、黎巴嫩(LBC)、沙特Rotana電視臺、突尼斯國家電視臺、約旦國家電視臺、也門國家電視臺達成合作意向。經過寧夏衛視有序推進完成其阿拉伯語本土化譯配及海外平臺落地播出工作,《山海情》已于2022年12月初正式與阿拉伯地區觀眾見面。
該劇集的譯制工作經過前期針對多國的海外調研,確定采用敘利亞方言進行本土化譯制。為了更加貼近阿拉伯國家與地區觀眾的收視習慣和偏好,翻譯團隊在確保忠實原著的基礎上,盡量做到語言生動、文字流暢、通俗易懂。同時,為確保導向正確、翻譯標準,特邀埃及開羅大學青年漢學專家等擔任審校。
事實上,從當年《媳婦的美好時代》開始,劇集作品一直是官方渠道踐行文化“走出去”戰略中成果最為顯著的領域。近年來借助重大宣傳時間節點,我國視聽領域涌現了一大批觀賞性與主題性兼具的精品。這些劇集承擔起了通過官方文化出口貿易的渠道開展對外傳播的“蓄水池”。除了《山海情》之外,2022年眾多在國內收視、口碑雙豐收的劇集也積極拓展著各類海外主流視聽平臺的市場份額。比如《人世間》一開拍就被迪士尼購買了海外獨家播映權;2022年初受到收視市場熱烈追捧的懸疑劇《開端》在韓國的亞洲電視劇頻道AsiaN播出;都市劇《三十而已》上線20多個海外播出平臺,被國外廣播公司購買了翻拍權;甚至包括《甄嬛傳》這樣的老劇集也通過重新剪輯的方式在奈飛(Netflix)平臺播出。
這些劇集一方面通過版權出售、收視分賬等方式持續在國際市場盈利,為中國電視劇市場在國際舞臺開拓盈利的藍海;另一方面,較之于其他文藝形式,劇集往往更容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心靈交互的文化載體,③而且像《山海情》《人世間》這類聚焦于現實題材的視聽作品,受到海外觀眾的高度關注和共情,逐漸打破了古裝、武俠劇集在海外一枝獨秀的局面,從而為世界展現了一個更為真實、接地氣的中國形象。
(二)新媒體平臺與二次創作傳播
當下的信息傳播環境已經與“內外有別”這一我國國際傳播多年來堅守的原則有所不同。互聯網的蓬勃發展及其對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意味著視聽作品在任一網絡平臺上的播放,就代表著其全球化傳播的開始。互聯網給視聽作品帶來了“墻內開花墻外香”的可能,也給來自于第三世界國家的視聽作品與歐美發達國家影視市場同臺競爭的可能。比如,早在《山海情》通過官方渠道出海之前,該劇集就已經通過上線優兔在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播出,上線優兔熱播劇場10天后流量突破50萬人次,黃金時段播放時長突破170萬小時,線上觀眾點贊率高達96%,成為海外用戶評論最多的一部國產電視劇。④ 這提示我們,伴隨著信息傳播技術發展,信息的流動軌跡并不完全與民族國家制度邏輯所劃定的地理邊界、制度邊界相重合;因此,我們不應完全以傳播主體、傳播內容自身的屬性來判斷其國際傳播的“陣地”,視聽作品既可以通過傳統的、官方的文化走出去渠道,也可以通過互聯網視頻平臺乃至社交短視頻平臺二次創作實現新的信息社會網絡的建構。如果說中國電視劇作品上線優兔平臺只是單純的內容搬運,那么在社交媒體、短視頻平臺上近年興起的“反應視頻熱”則進一步向我們展示出二次創作帶來的巨大傳播潛力。
近年來,以來自英國的“英國杰克”、韓國的“韓國東東”等為代表的外國視頻博主,紛紛在優兔、抖音、B站、微博等平臺上以“反應視頻”(reaction video)的形式走紅。他們往往在不同平臺上均有自己的賬號,以一種跨文化他者的身份觀看來自中國的視頻,并伴隨視頻的觀看做出實時反應。這些“洋網紅”制作的反應視頻中主要圍繞的內容,以中國影視劇、綜藝節目、美食節目和音樂會現場為主,這種由“看”與“被看”的凝視行為形成了特殊的跨文化傳播機制,在“洋網紅”觀看的過程中,完成了對中國視聽作品的第一輪傳播;而這些被他們觀看的中國視聽作品又成為了他們進行自我表達、自媒體傳播的素材來源。這種具有很強互動性的傳播過程的核心推動機制是文化與知識差異所帶來的身份區隔,由此觀看的不同主體成為了跨文化互動的主體,這對中國文化的傳播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中,青年歌手周深在綜藝節目、音樂會上的現場演唱視頻是外國博主重點制作的對象。尤其是他在《聲入人心》《歌手》等音樂綜藝上演唱的《野獸》(Monster)、《告別時刻)(Time to Say Goodbye)、《回憶》(Memory)、《想念我》(Think of Me)這四首歌曲有最大的上傳、點播與點贊評論數量。究其原因,這四首歌曲在西方的大眾文化語境里,都是普通受眾耳熟能詳的國民級歌曲,外國博主往往會帶著某種思維定勢開啟視頻的觀看過程。而此時,周深自身反差感極強的聲線與精湛嫻熟的唱功天然是挑戰既有思維定勢,并給反應視頻制造戲劇沖突的絕佳文本。在這個過程中,周深在中國綜藝節目上翻唱外國觀眾耳熟能詳的歌曲,這是第一輪的跨文化傳播;而外國博主的反應視頻,以及參與反應視頻制作的外國專業音樂人在視頻中的反應與店鋪則是第二輪的跨文化傳播;而中國互聯網用戶通過視頻平臺觀看這些反應視頻成品則是第三輪的跨文化傳播。這充分說明,在新媒體平臺上,信息傳播是一個不斷持續進行的流動過程,伴隨著對某一個特定視聽文本的跨文化接觸、解讀不斷深入,新的傳播循環不斷生成并釋放出巨大的潛能。
除此之外,伴隨著TikTok平臺在國外用戶中的用戶粘性持續增長,中國非遺文化通過TikTok也有了更加具有推廣度的傳播平臺。根據Social Insider對海外社交媒體近兩年的互動率分析,TikTok的平均互動率不僅遠遠高于照片墻、臉書和推特,而且差距還在擴大;而且,只有TikTok在2021年的平均互動率較前一年有所提升(從5.11%增加到5.96%),其他幾個平臺的平均互動率都呈下降趨勢。
而根據2022年6月8日文旅產業指數實驗室發布的2022年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在海外短視頻平臺上(以TikTok為主要數據分析源)的影響力報告顯示,TikTok上中國非遺文化相關內容視頻播放總量目前逾308億次。⑤像“功夫老爹”梁長興,竹編師傅潘云峰、李年根等一批非遺文化的傳播者,也通過TikTok被更多海外觀眾所知曉,他們通過短視頻的制作發布為他們從事的非遺項目擴大了海外影響力。短視頻作品中非遺傳播通過各種方式展示出匠人精神獲得了廣大海外短視頻用戶的共鳴與認可。在網友轉發、評論留言里,都能看到相當數量的類似“中國匠人”“藝術品”“匠人精神”的詞匯出現。
(三)影視IP與產業開發傳播
在新冠疫情與世界經濟格局深刻調整變化等客觀環境持續影響下,影視作品在海外形成現象級爆款的數量下降明顯。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影視領域逐漸以更加產業化的運作方式在市場的深層機制層面展開跨國合作,甚至干脆“借船出海”,乃至“造船出海”,深化影視IP與產業開發的海外競爭力。
如由騰訊影業發起并出品主控、閱文和新麗傳媒共同出品的電視劇《人世間》創下了央視一套黃金檔收視率近8年新高,其海外播映權已授權給迪士尼。以IP版權售賣的方式開啟海外傳播的征程,已經是國內視聽內容開發平臺方較為成熟的方式。而對于國產IP的國際化開發,2022年最重磅的成果就是奈飛經過三年醞釀與制作,在2022年9月24日發布英文劇集《三體》的首個片花,并宣布該劇的第一季已經殺青,正在進行后期制作,將于2023年上線。作為影視界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奈飛給《三體》的待遇稱得上“頂配”:不僅找來了美劇《權力的游戲》《星球大戰》等國際頂級IP的主創開發團隊,并邀請原作者劉慈欣與小說英文版譯者劉宇昆共同擔任顧問。
作為近年來國內最具有國際影響力的IP之一,《三體》因其天馬行空的宏闊想象力而備受國內外科幻讀者的喜愛,同時其IP影視化后的質量也一直受到讀者群體的擔憂。《三體》交給奈飛來進行影視化制作,會是在美國的成熟工業流水線下完成的作品。雖然圍繞著《三體》,也有國產電視劇、漫畫、廣播劇的全面開發,但是奈飛開發制作《三體》電視劇的舉動無疑是視聽領域跨國合作一個值得期待的案例,也是我國影視IP與產業開發“借船出海”的一個成功案例。
同時,與借奈飛這樣的成熟海外平臺的“船”相比,自己“造船出海”無疑是更具有自我賦能意義的國際傳播行為。2022年,騰訊視頻以其2019年正式在海外落地的WeTV為依托,通過本土化運營方式,快速積累用戶,在東南亞地區逐漸形成自己的市場影響力。目前,騰訊視頻海外版下載總數超過1.5億人次,已成為東南亞市場比較有影響力的流媒體之一。從內容時長來看,騰訊視頻海外版華語內容時長超過1萬小時,配音內容主要是泰語、印尼語、英語,超過2000小時。在東南亞一些重點國家,騰訊視頻也有本地運營團隊,包括市場推廣、內容運營等環節,已經提前2-3年布局,并在2022年開始顯露出厚積薄發的勢頭。⑥
依靠文化上的接近性,中國的影視劇在東南亞地區有相當的觀眾接受基礎。過去幾年騰訊視頻主要加強了在當地的本地化自制內容的建設,吸納并穩固受眾群體,然后將他們轉化成觀看華語內容的用戶。當穩固的用戶群形成后,騰訊視頻海外平臺主要依靠與當地本土較有影響力的視頻博主、關鍵意見領袖合作的方式,對中國的影視劇內容進行二次創作,然后再在平臺上對節目內容進行傳播。依托在地化的傳播網絡,使得中國故事有了更多元化的敘事方式,更容易形成“破圈”的效果。在社交媒體矩陣包括臉書、推特等平臺,騰訊視頻的粉絲超過7000萬個,占整個東南亞人口規模的10%。騰訊視頻的內容通過社交媒體覆蓋了東南亞國家30%左右的年輕人。⑦而從事二次創作的視頻博主則無形中承擔起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把中國文化傳播給本地的功能。
三、中國視聽領域國際傳播的未來展望
展望新的一年以及未來相當一段時間的中國視聽領域國際傳播工作,除了繼續堅持已有的有效經驗,以及能形成影響力釋放的常態做法,還建議在如下一些方面有更多的創造性成就。
(一)戰略傳播理念下的視聽傳播合力
在當下的美西方仍然手握世界信息傳播秩序的主導權的客觀環境倒逼下,中國視聽領域的“出海”競爭必然要實現從單純的內容輸出到主動利用、融入游戲規則,通過深度參與國際信息傳播的全球分工,在多元傳播主體、多元傳播渠道的協同合作下,實現在全球范圍有效的資源調配,從而實現講好中國故事、建構價值共識的目的。
這要求我們亟待將視聽國際傳播工作提升至戰略傳播的高度,而不是哪幾個部門、哪幾個環節、哪幾個領域的小規模聯合。視聽領域的國際傳播在未來如能形成更大的合力,需要注意戰略傳播理念下的政策布局的頂層性、資源調配的協同性、目標群體的針對性、價值輸出的共識性、重點領域的統籌性。⑧
可以看出,在2022年的視聽領域缺少李子柒這樣的現象級案例的情況下,版權交易、IP合作開發,通過社交媒體實現文本的二次創作、二次傳播等方式成為視聽領域國際傳播的“主戰場”。順著這種趨勢,我們有必要建設、儲備更多的傳播主體、更復合的發聲平臺,以及更加熟練地打造“造船出海”的能力。對于傳播主體而言,李子柒這樣的現象級主體也許可遇不可求,但是在互聯網的場域中,任何傳播行為都具有國際傳播的潛能。國際傳播理想的狀態不應是官方的主體地位強勢與其他主體的地位弱勢,而是應由政府官方、傳媒、(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民間社團以及公民個體等,共同組成國際傳播的多元主體,⑨形成在國際化平臺如TikTok、優兔,國內平臺如B站、快手等不同的平臺上穩定的合力,從而構筑立體、多樣化的傳播網絡。
而所有這些規設和布局,都需要戰略傳播理念和措施的體系性配合,戰略傳播是一個需要全面統籌、集聚和兼顧各種資源的傳播系統和生態,強調資源的豐富性,以及調配的協同性。這些資源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外交、軍事、商業、科技、媒介、公共領域資源等。戰略傳播考驗著一個國家層面的資源協調能力與分工合理性。⑩
(二)低語態共情敘事的溫潤信息傳遞
有學者指出:“一個更具全球性、共同性、共通性的價值取向是中國國際傳播應該謀求的目標。這既是對長期以來對外單向輸出邏輯的超越,也是對當下和未來全球對中國現實關注的客觀回應,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11這就進一步要求我們在傳播話語中強化對于價值共同點和情感共鳴點的追求,繼續以共情傳播為傳播實踐的道與法,增進理解、互通情感,從發出中國聲音到“破圈”講好中國故事。12
在傳統外宣思維的模式中,國際傳播的對象是作為典型的邊界外“他者”出現的,但是如前所述,互聯網深度嵌入社會生活的事實使得“內外一體”的趨勢愈來愈明顯,媒介化力量驅使著國際傳播作為一種持續性的過程,事實上時時刻刻發生在不同主體、不同場域上。無論是互聯網巨頭的“造船出海”,還是普通互聯網用戶、草根“網紅”對于主流媒體視聽內容的二次創作與傳播,都離不開與誕生在日常生活經驗下的普通人話語實踐的勾連,按照文化研究“作為表達的接合(articulation)”13的觀點,尤其越是抽象的、宏觀的意識形態話語,就越需要在表達上與日常經驗相縫合。
共情作為人類心理活動的一種本能,共情傳播能調動主體的非理性沖動,驅使人們對一件事物更溫潤地認知、接受和理解。進入國際傳播場域的視聽作品可考慮更多訴諸人類共通的感性思維,情感是主體進行創作、傳播和接受的主要動力來源。視聽作品在國際傳播中如果能通過例如低語態、生活語境、溫潤化等方式實現共情效果,可極大地促進國際傳播各主體彼此之間文化上的交流和情感上的溝通,讓目標受眾掙脫刻板、板結思維的束縛,實現更高層次的“共情審美”。14
(三)精準傳播觀念下的分區域化傳播
不同的國家、區域與文化群體有自己在社會文化、價值理念與社會制度設計上的獨特性,這需要未來的視聽國際傳播遵循精準傳播的理念,注意針對不同國家、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城市進行精準化傳播,即“一國一策”“一域一策”甚至“一城一策”。
從區域上說,要善于定位針對不同區域的優勢與不足。比如中國文化背景的內容在東南亞地區具有更強的文化接近性,在傳播過程中會遇到較少的“文化折扣”。非洲地區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則可能是我國現實題材視聽作品的主要目標出口地。相比較而言,美西方由于受制于意識形態和文化差異的隔閡,整體的傳播阻礙較大,即便有部分接受度較高的作品卻仍然避免不了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凝視。因此,對于東南亞、非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上文提到的阿拉伯地區等,可以利用全球信息傳播秩序中的薄弱環節,采用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實現傳播。而對于歐美地區而言,則更需要借助“網紅”對于內容的二次創作與詮釋,實現分眾化的傳播效果。相關聯的,從內容層面上說,需要在創作時培養全球思維,善于抓住敘事的共情點,找尋我國立場、利益訴求基礎上與其他文明、國家之間的最大公約數,避免自說自話,做到內外傳播的相輔相成、相互轉化。
在戰略傳播思維下,精準傳播在視聽國際傳播實踐中特別需要注意儲備智能化技術、指向聚焦化群體、細分區域化目標、建設替代性渠道等做法。
四、結語
從2022年中國視聽領域國際傳播面臨的現狀看,我們可以越來越清晰地發現,誰的傳播機制更加完善、立體,誰更能利用現行的游戲規則、誰更熟練掌握當前的傳播生態,誰就能繼續在當前的國際傳播格局中占據一席之地。對于中國而言,可繼續轉變思路,思考“內外有機統一”“國際傳播不分陣地”的原則,立足于多個渠道、多元主體共同發力。同時,針對不同的分眾領域、區域特征,“一地一策”地做好頂層戰略規劃;根據不同對象特點靈活利用立體、完善的傳播機制,打出因地制宜的“組合拳”,為中國形象全球認知度、美譽度的提升作出貢獻。
本文系中國傳媒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海外華人跨國實踐的媒介物質性研究及其對中國國際傳播實踐的啟示 ”(項目編號:CUC2019C004)、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項目“我國國際傳播人才培養的現狀、問題與對策研究”(項目編號:BGA220159)的研究成果。
葉琿系中國傳媒大學國家傳播創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數字倫理研究所研究員;劉俊(通訊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學報《現代傳播》編輯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注釋」
①[英]雷蒙·威廉斯:《文化與社會:1780-1950》,高曉玲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責任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32-339頁。
②張毓強、潘璟玲:《內外彌合: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的全球價值趨向》,《對外傳播》2022年第10期,第74頁。
③劉永昶:《國產劇進階“出海”的跨文化傳播邏輯》,《人民論壇》2022年第13期,第117頁。
④《叫好又叫座,國產電視劇“出海”又“出圈”》,“南京文化產業協會”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X_LB6x6bGveEPdPqin76HQ,2022年3月4日。
⑤《TikTok助力非物質文化遺產海外走紅》,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 tech/2022-06/13/c_1128737762.htm,2022年6月13日。
⑥《騰訊視頻深耕東南亞市場的做法與經驗》,“中國聯合展臺”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1SvX7piJJihcGmzuq-vH4w,2022年12月15日。
⑦同⑥。
⑧劉俊、江瑋:《戰略傳播思維與精準傳播實踐》,《對外傳播》2022年第7期,第13-15頁。
⑨胡智鋒、劉俊:《主體·訴求·渠道·類型:四重維度論如何提高中國傳媒的國際傳播力》,《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年第4期,第9-11頁。
⑩劉俊、江瑋:《戰略傳播思維與精準傳播實踐》,《對外傳播》2022年第7期,第14頁。
11張毓強、潘璟玲:《內外彌合:新時代中國國際傳播的全球價值趨向》,《對外傳播》2022年第10期,第76頁。
12王峰、臧珈翊:《面向海外“Z世代”做好國際傳播的主流媒體新策略》,《對外傳播》2022年第10期,第48頁。
13Grossberg,L. (ed.)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Morley, D & Chen, K.-H.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141-142.
14劉俊、董傳禮:《中國影視國際傳播能力提升的理念與路徑》,《文化研究》2022年夏季卷,第160-161頁。
責編:譚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