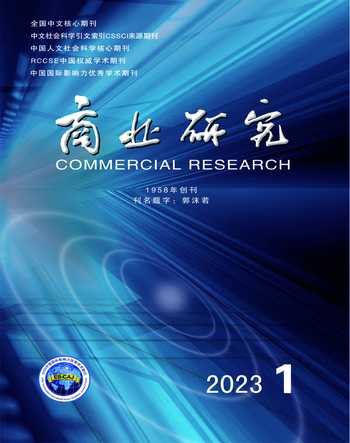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趙冉冉 韓孟孟 沈春苗



摘?要:基于2000-2015年中國海關進出口貿易數據構建地區全球價值鏈嵌入度,本文運用OLS模型和2SLS模型檢驗了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研究發現:全球價值鏈嵌入有助于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驅動力,但需要注意產業結構合理化中的“虛假產業均衡”;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全球價值鏈嵌入顯著促進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且產業結構合理化表現為“良性產業均衡”,但對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不顯著。中國除了持續深化全球價值鏈分工參與度,還應加強培育產業鏈競爭優勢,并鼓勵中西部地區尋求差異化的產業結構升級路徑。
關鍵詞:全球價值鏈嵌入;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高級化;產業結構合理化;區域異質性
中圖分類號:F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23)01-0001-10
收稿日期:2021-12-07
作者簡介:趙冉冉(1985-),女,山東濟寧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韓孟孟(1990-),女,河南安陽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沈春苗(1986-),女,安徽六安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產業經濟。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項目編號:?42101183;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重大項目,項目編號:?CYD-2020018。
隨著信息技術發展、經濟全球化加快,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成為主流。中國加入WTO以后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程度持續深化,2013年以來中國連續多年維持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地位,而且中間品和制成品貿易比重不斷上升。根據世界銀行和聯合國貿發會議共同發布的“世界綜合貿易解決方案”(WITS)數據,2019年中國貨物出口額占全球貨物出口額的比重為13.?5%,其中,中間品、資本品、消費品出口額占全球相應產品總出口額的比重分別達到10.?7%、18.?6%、15.?9%。
理論研究表明,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產業升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貿易全球化和國際分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生產效率提升、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決定因素,這主要與國際貿易分工過程中的研發溢出效應有關[1-3]。但相反的觀點認為,由于全球價值鏈低端鎖定和大型跨國公司的“俘獲效應”[4-5],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對中國企業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厘清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對于中國把握自身在國際分工中的定位、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意義重大。
一、影響機制與研究假設
(一)全球價值鏈嵌入的產業關聯效應
產業關聯是指產業之間通過產品供需而形成的相互關聯、互為基礎的內在聯系,主要表現為產品供需和技術供給兩個方面:從產品供需來看,任何產業或產品之間都可能存在雙向關系,一方面成為其他產業或產品生產的投入要素,一方面以其他產業或產品的產出為投入要素實現自身生產;從技術供給層面看,任何產業或產品的生產需要其他產業或產品技術水平的支撐,同時它的發展也推動了其他相關產業的技術進步。多數情況下,這兩種產業關聯會同時發生在同一個生產過程中,以產品內分工為特征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將產品設計研發、原材料采購運輸、中間品加工制造、產品組裝與分銷等整個生產過程進行分割和離岸生產,從而將全球范圍內的企業形成上下游產業關聯關系,當某個企業或生產環節的生產、技術、產值等發生變化時,將對其上下游企業及產業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種影響稱為產業關聯效應。
一個產業或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最典型的效應就是產業關聯效應。一國嵌入全球價值鏈的產業關聯效應主要表現為中間品關聯、技術關聯所帶來的規模擴大、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當一個國家生產的中間品作為投入要素出口給世界其他國家或者作為最終品滿足國內市場后銷往國外時,全球市場需求將通過后向關聯帶動出口國相關產業增加值擴大、就業人口增加;當一個國家通過進口世界其他國家的中間品來生產所需要的最終品時,或者通過與跨國公司合作生產最終品時,該國將通過進口中間品所產生的前向關聯來獲取國際市場信息、產品生產技術、產品質量標準以及低成本效應,或者通過與跨國公司合作獲得技術轉移外溢、管理技能與經驗以及吸引高端人才等來促進本國技術進步、效率提升和產業升級。當一個產業或企業的生產效率和利潤提升時,這必然引起社會資源從效率和收益較低的部門流向效率和收益較高的部門,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二)全球價值鏈嵌入的資源配置效應
盧鋒(2004)認為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是產品內分工的基本利益源泉:產品不同生產工序或區段的要素投入比例存在差異,而不同的國家所擁有的要素稟賦不同,因此每個國家或企業根據自身要素比較優勢選擇參與不同的產品生產環節,以獲取較高的經濟收益,或者跨國公司作為全球生產分工的主導者根據不同國家或企業的比較優勢進行生產分配,使企業利潤最大化。另外,如果給定產品的不同生產區段對應的有效規模存在差異,把對應不同有效規模的生產區段進行分離和空間布局,就可以實現成本節約和資源配置效率提升[6]。因此,全球價值鏈分工可以通過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實現全球范圍內的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
基于比較優勢理論嵌入全球價值鏈可以實現資源配置效應,進而影響產業結構升級。一個國家或企業只要擁有具有比較優勢的要素資源或生產技術,就可以利用比較優勢在全球價值鏈上參與專業化生產和分工,避開自身處于劣勢地位的生產環節,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全球價值鏈嵌入的資源配置效應有利于一個國家或企業的專業化提升,從而促進產業規模擴大、產業競爭力提升,以及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另外,隨著一個國家或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程度不斷加深,專業化水平和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提升,該國或該企業可以集中主要力量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或生產環節,把比較劣勢的產業或生產環節轉移到其他國家,從而降低自身生產成本、優化資源配置。全球價值鏈嵌入的資源配置效應有利于提升生產效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但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價值鏈嵌入的資源配置效應在加強專業化生產的同時也容易造成比較優勢固化和價值鏈低端鎖定,忽略技術創新和新興產業發展,從而導致產業結構升級延緩或受阻[7-8]。
(三)全球價值鏈嵌入的競爭效應
全球價值鏈嵌入的競爭效應包括技術水平差距較大的企業間競爭效應和技術水平相近的企業間競爭效應[9]。因此,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影響也包括兩個方面:第一,當一個國家或企業與全球價值鏈上擁有高技術、高附加值的企業差距較大時,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企業會面臨兩方面的競爭壓力,包括具有先進技術水平并占據全球價值鏈高端的發達國家企業的技術控制和產品質量要求,以及具有低成本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企業的低端市場擠壓。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企業為了應對這兩方面的競爭壓力,穩定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和國際市場,必然會主動進行研發和技術創新、加強國際分工合作[10-11]。技術研發和創新將有利于企業攀升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發展附加值較高的高新技術產業。第二,當一個國家或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程度和地位不斷上升,尤其是當技術水平與處于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的企業差距更加接近的時候,它所面臨的競爭更加激烈,包括技術遏制和市場爭奪。為了提升自身競爭能力并爭奪國際市場份額,面臨激烈競爭的企業一方面需要加強科技研發和技術創新,一方面需要通過多樣化生產實行錯位競爭,或者挖掘新的市場空間實行產業轉型升級,技術進步和多樣化生產分別從效率提升和市場拓展方面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上述理論機制表明全球價值鏈嵌入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但是部分從實證角度出發的研究發現,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也存在潛在差異性。例如,Stollinger,R.?(2016)以制造業為研究對象,研究了1995-2011年歐盟成員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與產業結構變化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參與全球價值鏈促進了中歐成員國向制造業的結構轉變,卻加速了其他歐盟成員國的工業化進程[12]。Jouanjean,M.?et?al.?(2017)研究發現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為一國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提供了機會,因為各國可以通過發揮比較優勢從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獲益,但是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與部門轉型升級之間的聯系存在差異性[13]。盛斌和趙文濤(2020)研究發現全球價值鏈嵌入對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的影響存在相反效應,并且因地區之間的開放程度、經濟規模、產業政策等不同而存在異質性:全球價值鏈嵌入對沿海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效果明顯高于內陸地區[14]。據此,本文對全球價值鏈嵌入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1:全球價值鏈嵌入總體上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但地區之間由于限定因素不同而存在異質性。
另外,從投入產出理論角度出發的研究表明要素資源配置是生產率提升和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動力。以Hoffman(1958)為代表的學者認為資本深化是工業化發展的必經階段,大多數國家的工業化發展都會經歷資本-勞動力比例持續上升的過程[15];Acemoglu和Guerrieri(2008)通過構建兩部門一般均衡模型,論證了資本深化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部門間要素密集度差異是導致產業結構變化的主要原因[16]。于澤和徐沛東(2014)利用1987-2009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考察了資本深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結果表明資本-勞動力比例上升顯著促進中國產業結構升級[17]。余東華和張維國(2018)的研究表明,要素市場扭曲導致的資本深化在長期內對制造業轉型升級存在抑制作用[18]。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2:資本深化總體上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但地區之間由于資本深化動因不同而存在異質性。
二、模型構建、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一)模型構建
根據上述理論機制和研究假設,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且存在區域差異性,本文利用2000-2015年中國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對上述研究假設1和假設2進行驗證(由于西藏自治區數據缺乏完整性,因此省級面板數據中被剔除)。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過程表現為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因此,本文模型設定為:
ISUkt=γ0+γ1GVCkt+γ2Capkt+γ3Z+μk+τt+εkt(1)
ISRkt=β0+β1GVCkt+β2Capkt+β3Z+μk+τt+εkt(2)
其中,公式(1)考察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公式(2)考察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ISU和ISR分別表示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k和t?分別表示地區和年份;GVC代表全球價值鏈嵌入度;Cap代表資本深化程度;Z表示控制變量集合;μ?和τ分別表示地區和時間固定效應;εkt表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選取及說明
1.?被解釋變量。(1)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ISU)。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的產業結構從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演進的過程。這種從低到高的產業層次演進過程通常有兩種解釋:一種是促使各個產業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升的結構演進;另一種是基于一二三產業勞動生產率依次升高的既定經驗或假設,某國或某地區產業結構重心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逐次轉移的結構演進。本文借鑒劉偉等(2008)提出的包括比例關系和勞動生產率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具體公式為:ISU=∑3iYiY×LPi,其中,i為各地區的三次產業(i=1,2,3);Yi、Y分別表示各地區第i?產業的產值和總產值;LPi表示各地區第i?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某地區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產業占比越大,產業結構越高級[19]。(2)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ISR)。產業結構合理化聚焦于要素資源在產業間的流動、配置和協調性,強調不同產業間資源配置效率的均衡化。本文借鑒韓永輝等(2017)提出的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具體計算公式為:SR=∑3iYiYLPiLP-1。其中,i?為各地區的三次產業(i=1,2,3);Yi、Y分別表示各地區第i?產業的產值和總產值;LPi、LP分別表示各地區第i?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總勞動生產率。一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越均衡的時候,各產業勞動生產率越接近于總勞動生產率,SR值越接近于0。所以SR值越小,產業結構越合理。值得說明的是,此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與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顯示出負向關系,即指數越大,表明產業結構越不合理[20]。為便于分析,在本文實證分析過程中,選取SR的倒數來衡量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即ISR=1SR。
2.?核心解釋變量。(1)全球價值鏈嵌入度(GVC)。本文參考Hummels?et?al.?(1999)對全球價值鏈嵌入度的考量方法,即使用中間品貿易數據作為替代變量的做法[21],利用來自國外的全國中間品投入乘以各地區進口額在全國總進口額中的占比來估算各地區中間品投入進口總價值,然后再計算各地區中間品投入進口總價值在地區增加值中的占比來測度全球價值鏈嵌入度,計算公式為:GVCit=IMitYit=(TIM×MitM)/Yit,其中IMit和Yit分別表示地區中間品投入進口額和地區增加值,TIM、Mit和M分別表示全國中間品投入進口額、地區進口額和全國進口額。(2)資本深化程度(Cap)。資本深化是指資本要素積累速度持續快于勞動力要素增加,從而使資本-勞動力比率持續上升的過程。因此本文選用人均資本(取對數)來衡量資本深化程度。
3.?控制變量。為減少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偏誤,選取控制變量如下:(1)技術創新(Sd)。本文借鑒沈春苗和鄭江淮(2019)所提出的國內知識資本存量(取對數)來衡量技術創新水平,主要在各年研發投入流量的基礎上,利用永續盤存法對知識存量進行估算[22]。具體計算公式為:Sdit=SIit+1-δSdit-1,其中Sdi2000=SIi2000/(f+δ),SI表示各省研發投入,f表示年均實際研發投入增長率,δ為年折舊率,取5%。(2)城鎮化率(City)。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都伴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而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尤其離不開城鎮化這一重要推動力,它從需求角度和消費升級角度帶動了中國產業結構升級,通常用城鎮常住人口占比表示城鎮化率。(3)人力資本(Edu)。人力資本是促進一國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影響因素,而人力資本的能力和質量跟受教育程度直接相關,因此本文選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的衡量指標。(4)金融集聚(Aggl_f)。資本流動和金融發展為經濟活動的開展提供了媒介,金融集聚可以通過促進要素流動、資源配置等方式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本文采用各省(市)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占GDP比重的區位熵指數來衡量金融集聚程度,具體計算公式如下:Aggl_fi=DoaniGDPi/DoanGDP,其中Doan和GDP分別表示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和國內生產總值,i?表示地區。(5)政府干預(Fisc)。本文選用各省(市)政府財政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政府規模,以及政府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干預程度。
(三)數據來源及描述性分析
根據實際情況和數據可獲得性,本文研究樣本選取2000-2015年中國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由于西藏自治區數據缺乏完整性,在此面板數據中被剔除)。其中,中間品貿易數據來自中國海關進出口統計數據,市場化指數來源于《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6)》,其他原始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歷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統計年鑒。需要說明的是,自變量數量級不一致時會存在異方差與量綱差異,取對數可消除這種數量級相差很大導致的量綱差異,所以在不影響經濟意義的情況下,模型實證分析過程通過對數量級較大的絕對值變量取自然對數進行量綱化處理,包括衡量產業結構升級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衡量資本深化的資本-勞動力比率,以及衡量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的國內知識存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表1給出了量綱化處理之后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特征。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關于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應分析,主要采用產業結構水平作為因變量,其中包括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產業結構高級化更趨向于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產業演進,從而發揮實際結構效益;產業結構合理化更趨向于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平均化。首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對模型(1)和(2)進行估計,即檢驗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中國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的影響,具體檢驗結果見表2中的(1)、(2)列和(5)、(6)列。其次,全球價值鏈嵌入與中國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內生性問題:一方面隨著中國不斷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國企業在國際分工合作過程中通過“干中學”、技術溢出、競爭倒逼等方式提高自身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促使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的生產效率提高、產品質量提升、員工素質增強也將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投資和貿易機會,促進國際產業轉移對中國的青睞。隨著中國企業生產效率和技術提高,中國產業結構漸漸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這將進一步促進中國企業攀升全球價值鏈。這都表明全球價值鏈嵌入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互為因果關系的可能性,即全球價值鏈嵌入度是內生變量。再加之遺漏變量可能導致內生性,因此為了控制和減少內生性問題引起的估計有偏性,本文借鑒連玉君等(2008)的做法,使用全球價值鏈嵌入度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進行2SLS估計[23],估計結果如表2中的(3)、(4)列和(7)、(8)列,通過Hausman內生性檢驗,結果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P=?0.?0000),弱工具變量的檢驗值?F?也大于10,表明使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內生性處理是合理有效的。
表2中(1)-(4)列顯示的是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中國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效應。其中,GVC的系數為正且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Cap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全球價值鏈嵌入和資本深化對于中國產業結構高級化起著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控制變量中,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發揮積極作用的有城鎮化率、人力資本和金融集聚,這些因素表現為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驅動力;科技創新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效應不顯著;政府干預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效應表現為消極抑制。
表2中(5)-(8)列顯示的是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中國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效應。其中,GVC的系數為正,且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Cap的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全球價值鏈嵌入和資本深化對于中國產業結構合理化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其他控制變量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類似于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城鎮化率、人力資本、金融集聚以及科技創新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都表現出正向促進作用,但科技創新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促進作用不穩定,政府干預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表現為消極抑制作用。基準回歸模型的檢驗結果表明:全球價值鏈嵌入和資本深化有利于促進中國產業結構升級,與理論假設1和假設2相一致。
值得關注和探討的是,全球價值鏈嵌入同時促進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的結論不同于盛斌和趙濤(2020),后者的研究發現:全球價值鏈嵌入促進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同時,間接導致產業結構偏離均衡化[14]。本文產生相反結論的原因在于:中國各個省(市)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與對應產值占比之間的發展趨勢出現了很大的差異,即各省市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一致呈增長趨勢,按照要素資源由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轉移的推論產業結構也隨之變化,但實際上中國各省(市)并沒有發生一致向勞動生產率高的部門轉移的現象,由此呈現出“虛假產業均衡”或“非良性產業均衡”。
2000年以來,中國產業結構變化呈現出同時趨向高級化和合理化的現象,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價值鏈嵌入、要素資源配置合理、科學技術不斷進步、人力資本素質提高等因素推動了產業效率提升和產業差距縮小以外,很大程度還在于上述提到的“虛假產業均衡”以及“次優資源配置效率”。因為正常情況下,當一國或地區產業結構同時趨于高級化和合理化時,就說明其各產業之間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并且差距縮小,而在中國的30個省(市)中,并不完全呈現這種現象。在全國30個省(市)中,有15個省(市)的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與對應產值占比之間的變化趨勢相同,主要出現在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另外15個省(市)的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與對應產值占比之間的變化趨勢存在很大差異,主要出現在西部地區和部分東部地區。當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變化趨勢和對應產值占比變化趨勢相同,且產業勞動生產率越高產值占比越大時,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會越高,表明資源配置效率越高;當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并且差異變大,產業不斷向勞動生產率高的行業轉移時,比較勞動力生產率更趨向于不均衡,從而產業結構越不合理;當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變化趨勢和對應產值占比變化趨勢不同時,例如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都不斷增長,但是勞動生產率最高的產業產值占比卻不是最大,計算出來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雖然會不斷增長,但不是最優增長路徑,同時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會更大,表現為地區產業結構更趨向于均衡,但是這并不是“正常或良性產業均衡”,而是“虛假產業均衡”。
觀察中國30省(市)的微觀數據,只有部分省份出現了良性的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而大部分趨向于產業結構合理化的省份并沒有出現勞動生產率差異縮小和產業結構向勞動生產率高的產業傾斜的現象(為不影響篇幅,具體數據省略備索)。例如,加入WTO以來,廣東省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一直位居最高位,但是2012年以前卻一直是第二產業的產值占比最高,這就會造成虛假的產業均衡現象。尤其是西部地區的11個省份,其中8個省份都出現了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和勞動生產率變化趨勢不協調、不同步的現象。這其中的原因很可能與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導向、資源要素稟賦限制等因素有關,從而導致表面上產業結構合理化,實際卻是產業內部效率不均、資源配置效率次優的情況。
(二)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驗證全球價值鏈嵌入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穩健性,分別對上文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進行指標替代。首先,根據配第-克拉克定理對產業結構演進和升級的描述:隨著經濟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提高,第一產業的相對比重逐漸下降,第二產業的相對比重上升,經過進一步發展,第三產業的相對比重也開始上升。所以本文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測度,采用徐德云(2008)的研究方法,?對一二三產業分別賦值?1、2、3,?然后進行加權平均,最終得出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具體計算公式為:ISU′=∑3i=1yi×i=Y1Y×1+Y2Y×2+Y3Y×3,其中ISU′為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yi?表示第i?產業產值占比;i?表示產業部門。ISU′越接近于1,產業結構層次越低;ISU′越接近于3,產業結構層次越高[24]。其次,根據干春暉(2011)和韓永輝(2017)的定義,產業結構合理化表現為產業間聚合和資源有效利用兩個方面,即通過要素投入合理配置促進產業結構協調發展[25]。本文利用干春暉重新定義過的泰勒指數的倒數來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具體計算公式為:ISR′=1/∑3i=1YiYln?(LPi),其中?i表示產業部門,涉及一二三產業部門;ISR′是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Yi和Y分別表示某地區第i產業的產值和總產值;LPi表示第?i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泰勒指數越趨近于0,經濟越趨近于均衡狀態,產業結構越合理,而泰勒指數與這里的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成反比。因此,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越大,產業結構越合理。
表3為全球價值鏈嵌入影響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穩健性檢驗結果,模型(1)-(8)均顯示全球價值鏈嵌入和資本深化與被解釋變量的估計值符號與基準回歸結論相吻合,并且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他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關系與基準回歸結果也基本一致,且系數均顯著。再次證明了全球價值鏈嵌入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趨向于高級化和合理化,只不過這里需要謹慎對待中國各地區產業均衡的虛假性問題。
(三)異質性分析
中國是一個由31個省(市)組成的大國,其經濟也表現出大國經濟和地區差異的特征,地區間對外開放程度、參與國際分工、資源要素稟賦、制度文化基礎以及政府干預情況等都存在很大差別,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在各省市之間也表現出很大的區域異質性。因此,本文針對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再次進行東部、中部、西部的分樣本回歸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依然按照OLS基準回歸分析、內生性處理、2SLS回歸分析三個步驟進行檢驗,內生性處理過程中選擇全球價值鏈嵌入度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內生性,弱工具變量檢驗顯示工具變量選擇有效,具體過程在此省略。異質性分析結果如表4和表5所示,表4和表5分別表示全球價值鏈嵌入影響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區域異質性結果。
首先,表4反映了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區域異質性影響。關于東部地區,模型(1)和模型(2)顯示,變量GVC和Cap的系數為正,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全球價值鏈嵌入和資本深化對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高級化具有積極促進作用,一方面東部地區確實對外開放環境較好,例如進出口貿易往來、對外直接投資、招商引資合作機會相對較多,且全球產業鏈環節上的生產合作、技術合作也比較多,這種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帶來的技術及知識的外溢和競爭激勵促進了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高級化,資本深化的促進作用表現在此階段資本-勞動力的要素配置有利于生產效率提高;關于中西部地區,模型(3)-(6)顯示,變量GVC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這表明參與全球價值分工對于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沒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甚至為負,這與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環境、全球價值鏈分工參與度以及資源要素的流動通暢度有很大關系。變量Cap的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原因類似于東部地區。控制變量方面,在東部地區對產業結構高級化起顯著促進作用的因素為技術創新、城鎮化程度和人力資本;在中部地區對產業結構高級化起顯著促進作用的因素為城鎮化程度和人力資本;在西部地區對產業結構高級化起顯著促進作用的因素為城鎮化,而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和金融集聚沒有發揮相應的驅動作用,與西部地區的技術創新不足、人力資本流失以及金融發展落后有關系。
其次,表5反映了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區域異質性影響。關于東部地區,模型(1)和模型(2)顯示變量GVC和Cap的系數為正,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全球價值鏈嵌入和資本深化對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合理化具有積極促進作用,而且是良性的產業結構均衡。一方面東部地區的省份確實對外開放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程度相對較高;另一方面,東部地區大部分省份的產業結構合理化確實呈現出良性的產業均衡,即勞動生產率最低的第一產業占比逐漸降低,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升高的過程中差距不斷縮小甚至趨同,特別典型的就是北京、上海兩個地區的第一產業逐漸降低為1%以下,而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近乎趨同;關于中部地區,模型(3)和模型(4)顯示變量GVC和Cap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全球價值鏈嵌入和資本深化對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合理化具有消極抑制作用。這種影響表現在中部地區的大部分省份出現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差距變大,而產業結構又不斷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產業傾斜的現象,這種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同時必定帶來產業結構偏離合理化,原因在于中部地區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同時,過于注重全球價值鏈嵌入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促使要素資源更多地流向高效生產部門,而忽略了三次產業之間的效率反差和兩極化。另外,資本深化對中部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為負的原因類似于要素資源流動的方向過于追逐高效益部門,而抑制了產業間效率均衡;關于西部地區,模型(5)和模型(6)顯示,變量GVC的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變量Cap的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全球價值鏈嵌入對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較小,原因可能在于西部地區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程度較低;而資本深化顯著促進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控制變量方面,模型(1)-(6)顯示,東部地區對產業結構合理化起顯著促進作用的因素為城鎮化和金融集聚;中部地區對產業結構合理化起顯著促進作用的因素為人力資本和政府干預;西部地區對產業結構合理化起顯著促進作用的因素為科技創新、人力資本、金融集聚和政府干預。
上述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中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效應存在差異性。比較明顯的差異在于,全球價值鏈嵌入顯著促進東部地區產業結構趨于高級化和合理化,而且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合理化表現為良性的產業均衡;但對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的影響效應不顯著,甚至為負。產生如此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兩方面:一方面中西部地區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程度較低,一方面中西部地區自身存在實際上的資源限制、流動限制以及內部不均衡。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理論機制和經驗事實,利用2000-2015年中國海關進出口貿易數據構建地區全球價值鏈嵌入度,并運用OLS模型和2SLS模型檢驗全球價值鏈嵌入度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及其區域異質性。研究發現:第一,全球價值鏈嵌入有助于產業結構趨于高級化和合理化,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驅動力。在實證分析中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中國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的影響效應都顯著為正,這似乎不符合常理,因為當產業結構向著勞動生產率較高的行業演進時,似乎必然造成產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偏離合理化,除非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同時推動了產業效率提升和產業差距縮小。但在此部分的微觀數據觀察中發現,中國大部分趨向于產業結構合理化的省份并沒有同時出現產業間勞動生產率差異縮小和產業結構向勞動生產率高的產業傾斜的現象,因此這里產業結構合理化現象表現出一定的“虛假產業均衡”,這可能與地區資源流動限制和政府干預政策有關。第二,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存在區域差異性。比較明顯的差異在于,全球價值鏈嵌入顯著促進東部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而且產業結構合理化表現為良性產業均衡;但對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的影響效應不顯著,甚至表現為抑制作用,其原因一方面中西部地區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程度不夠,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自身存在實際上的資源限制、流動限制以及內部不均衡。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政策啟示如下:
第一,要注意區分產業結構升級中兩種不同的產業均衡,特別要關注“虛假產業均衡”。“虛假產業均衡”表現為:在勞動生產率變化趨勢和產值結構變化趨勢不同步的情況下,產業結構仍然趨于高級化和合理化,這是一種沒有實現效率提升最大化和產業間效率差距縮小的次優升級路徑。
第二,進一步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同時培育產業鏈競爭優勢。對外開放層面,一方面通過優化市場機制、降低貿易關稅、減少貿易壁壘等方式來表明對“逆全球化”的態度,積極推進投資貿易自由化,擴大對外開放程度;另一方面通過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設、對標國際營商環境規則、減少政府干預行為等方式促進公平有序競爭,提升對外開放水平以及國際信譽與地位。融入全球價值鏈層面,一方面通過自身優勢和貿易協定等方式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并借助全球產業鏈溢出效應,提升企業生產效率、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通過吸收高端要素資源、加強自主創新培育產業鏈競爭優勢,鞏固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26]。
第三,依據全球價值鏈嵌入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異質性特征,繼續發揮東部地區嵌入全球價值鏈的虹吸效應和輻射效應,中西部地區合理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探索符合自身優勢的差異化升級道路。
參考文獻:
[1]?Gereffi?G.?Global?Production?Systems?and?Third?World?Development,?in?B.?Stallings(ed.),?Global?Change,?Regional?Response[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0-142.
[2]?Gereffi?G.?International?Trade?and?Industrial?Upgrading?in?the?Apparel?Commodity?Chain[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99a,48(1):?37-70.
[3]?David?T?C,?Helpman?E,?Hoffmaister?A?W.?North-South?R&D?Spillovers[J].?The?Economic?Journal,1997,107(1):134-149.
[4]?劉志彪,張杰.從融入全球價值鏈到構建國家價值鏈:中國產業升級的戰略思考[J].學術月刊,2009(9):59-68.
[5]?呂越,陳帥,盛斌.嵌入全球價值鏈會導致中國制造的“低端鎖定”嗎?[J].管理世界,2018(8):11-29.
[6]?盧鋒.產品內分工[J].經濟學(季刊),2004(10):55-82.
[7]?馬丹,郁霞,翁作義.中國制造“低端鎖定”破局之路:基于國內外雙循環的新視角[J].統計與信息論壇,2021,36(1):32-46.
[8]?周劍明,王鵬.新發展格局下我國產業結構升級面臨的壓力與對策[J].經濟縱橫,2021,427(6):94-99.
[9]?劉冬冬.全球價值鏈嵌入對中國產業升級的影響研究[D].重慶:重慶大學,2019.
[10]Peretto,?P.?F.?Endogenous?Market?Structure?and?the?Growth?and?Welfare?Effects?of?Economic?Integration[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3,60(1):177-201.
[11]Bloom,?N.,?M.?Draca,?and?J.?Van-Reenen.?Trade?Induced?Technical?Change??The?Impact?of?Chinese?Imports?on?Innovation,?IT?and?Productivity[J].?The?Review?of?Economic?Studies,2016,83(1):87-117.
[12]Strollinger,R.?Structural?Change?and?Global?Value?Chains?in?the?EU[J].Empirica,2016(43):801-829.
[13]Jouanjean,M.,?J.Gourdon,and?J.Korinek.?GVC?Participation?and?Economic?Transformation:?Lessons?from?Three?Sectors.?OECD?Trade?Policy?Papers?207,?OECD?Publishing.
[14]盛斌,趙文濤.地區全球價值鏈、市場分割與產業升級——基于空間溢出視角的分析[J].財貿經濟,2020(9):131-145.
[15]Hoffman?W?G.?Growth?of?Industrial?Economics[M].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58:16.
[16]Acemoglu,?D.?and?Guerrieri,?V.?Capital?Deepening?and?Nonbalanced?Economic?Growth[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8(116):467-498.
[17]于澤,徐沛東.資本深化與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基于中國1987-2009年29省數據的研究[J].經濟學家,2014(3):37-45.
[18]余東華,張維國.要素市場扭曲、資本深化與制造業轉型升級[J].當代經濟科學,2018(2):114-123.
[19]劉偉,張輝,黃澤華.中國產業結構高度與工業化進程和地區差異的考察[J].經濟學動態,2008(11):4-8.
[20]韓永輝,黃亮雄,王賢彬.產業政策推動地方產業結構升級了嗎?——基于發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論解釋與實證檢驗[J].經濟研究,2017(8):33-48.
[21]Hummels,?D.,Ishii,?J.?and?Yi,?K.?M.?The?Nature?and?Growth?of?Vertical?Specialization?in?World?Trade[J].Social?Science?Electronic?Publishing,1999,54(1):75-96.
[22]沈春苗,鄭江淮.中國企業“走出去”獲得發達國家“核心技術”了嗎?——基于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視角的分析[J].金融研究,2019(1):111-127.
[23]連玉君,蘇治,丁志國.現金-現金流敏感性能檢驗融資約束假說嗎?[J].統計研究,2008(10):92-99.
[24]徐德云.產業結構升級形態決定、測度的一個理論解釋及驗證[J].財政研究,2008(1):46-49.
[25]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1(5):4-16.
[26]凌永輝,劉志彪.橫向競爭視角下全球價值鏈治理結構變動及產業升級[J].江西社會科學,2021(2):37-48.
The?Impact?of?Global?Value?Chain?Embeddedness?on?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
——Analysis?of?Regional?Heterogeneity?Based?on?Chinas?Provincial?Panel?Data
ZHAO?Ran-ran1,HAN?Meng-meng1,SHEN?Chun-miao2
(1.?Center?for?the?Yangtze?River?Deltas?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f?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3,
China;??2.Business?School?of?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210046,China)
Abstract:??This?paper?constructs?the?regional?GVC?embeddedness?based?on?the?Chinese?customs?import?and?export?trade?data?in?2000-2015,then?tests?the?effect?of?GVC?embeddedness?on?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and?its?regional?heterogeneity?by?OLS?model?and?2SLS?model,?the?results?show?that:?First,?GVC?embeddedness?contributes?to?the?optimization?and?rational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so?that?becomes?an?important?driving?force?for?the?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However,?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phenomenon?of?“false?industrial?balance”?in?the?rational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Secondly,?there?is?regional?heterogeneity?in?the?impact?of?GVC?embeddedness?on?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GVC?embeddedness?significantly?promotes?the?upgrading?of?industrial?structure?in?eastern?China,?and?the?rational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shows?“a?benign?industrial?equilibrium”,?but?GVC?embeddedness?has?no?significant?impact?on?the?upgrading?of?industrial?structure?in?central?and?western?China.?In?view?of?this,?China?should?not?only?continue?to?deepen?the?participation?in?global?value?chain,?but?also?strengthen?the?cultivation?of?competitive?advantages?of?industrial?chain,?and?encourage?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s?to?seek?differentiated?path?of?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according?to?their?own?conditions.
Key?words:?global?value?chain?embeddedness;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optim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rational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regional?heterogeneity
(責任編輯: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