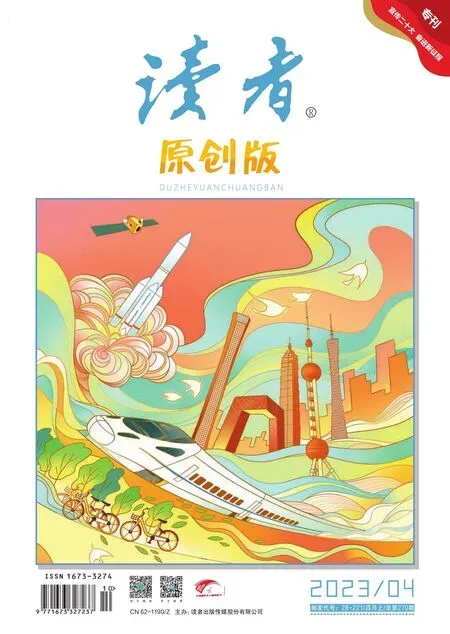把店鋪開到東京去
文|棖不戒

一
鎮上一開始是沒有裁縫鋪的。
那時候做衣服要請裁縫到家里來做活,鄉下講究禮節,要提前去師傅家里請,然后把布料、棉花都準備好。等日期排到了,師傅便來到家里做事,主人家供中午、晚上兩頓飯,每頓都要有肉有酒,還要有陪師傅喝酒的陪客。等一個工期做完,結算了工錢,再把師傅送回家,這件事才算完結。
上學前班那年冬天,一天,雪下得格外大,早上外公背我去上學,腳踩下去,雪沒到小腿,根本分不清哪兒是大路哪兒是溝渠,一不小心就會掉到溝里。
外婆請來裁縫給全家人做新棉衣。過年雖然要穿新衣,棉衣棉褲卻不是年年都做,棉衣外面套罩衣,棉褲外面套外褲,節約的人家,一件棉衣穿上七八年都是有的,每年新做的也就是外面的薄罩衣。我可不管這些,一聽說要做新衣服,就拉著正在曬新棉花的外婆去鎮上買布,美滋滋地給自己選了一塊紅底帶牡丹鳳凰圖案的花布。
請來的裁縫是個60多歲的男人,皮膚白皙,帶著一個小徒弟,徒弟肩上挎著一個大大的工具箱。外公拆了一塊舊門板放在堂屋,臨時充當裁縫的工作臺。我坐在小板凳上,看著裁縫指揮徒弟把松軟如云朵的棉絮鋪在花布上,再蓋一層藍色格紋里布,像是撫平一塊云彩般把它們平整地縫制在一起。他在上面打上粉筆印,裁裁剪剪,前身后背的形狀出來了,袖管也留出來了。這正是我的新衣服。新做的棉衣是最暖和的,棉花蓬松又有彈性,透著陽光的氣息;穿的時間久了,棉花就壓實了;等到穿舊過了水,棉胎就會板結,吸滿灰塵和螨蟲,箍在身上僵硬沉重。
請裁縫來一次不容易,我的衣服被特意做大了一些,因此穿新棉衣時要把袖子卷起來。但這并不影響我臭美,沒人的時候,我把外面的滌綸罩衣脫下來,單穿著棉衣在鏡子前來回走動,想象自己是古裝電影里的紅衣女俠。
二
我去鎮上讀小學的時候,老裁縫身體不好,已經不再去別人家里做活兒,此時鎮上有了第一家裁縫鋪,名叫曉蓮制衣。這是一家夫妻店,男人姓張,是正經學藝出來的裁縫,剪裁、制衣都是他;女人叫曉蓮,她是婚后跟丈夫學的手藝,做些絞邊、縫扣子的活兒,只能給丈夫打下手。張裁縫留了兩撇小胡子,不笑的時候看起來很嚴肅;曉蓮圓臉大眼睛,見人就笑,說起話來快人快語,十分討人喜歡。張裁縫手藝好,除了做常規的棉衣、罩衣、長褲、大擺裙,還能做新潮的西裝套裙。母親就在他家做過一件粉色珠光緞的西裝套裙,衣料在陽光下波光粼粼,把人襯得格外溫柔,像一朵顫巍巍開在春天的桃花。母親穿著它出去買菜,實在是出風頭,木材市場的女人們看見了,一窩蜂都跑去裁縫鋪,整個木材市場突然就開滿了花,大紅的、粉藍的、鵝黃的,穿著套裙的女人們配上新燙的大波浪鬈發和口紅,要多時髦有多時髦,來進貨的外地客商見了這綺麗柔媚的場景,笑稱我們鎮是“小香港”。
鎮上女人們的審美是流動的。每個月她們都會包一輛面包車去縣城購物,郵遞員也會按時把訂的雜志、報紙送過來。而張裁縫不僅訂了雜志,還買了時裝畫報和編織書籍。曉蓮做衣服是學徒,織毛衣卻很有天賦,菠蘿紋羊毛衫、鏤空白色針織長罩衫、電視劇里女主角穿的針織衫,她看了就能上手復制。
鎮上女人們雖然趕時髦,但也節約,守店時熱衷織毛衣、鉤茶巾、做鞋墊、鉤毛線拖鞋,這便少不得要向曉蓮請教手法。大家扎堆兒在裁縫鋪里學習新式的毛衣織法時,也不好白占用人家的時間,順便就請張裁縫做一兩件日常的襯衣。是以,即便在縣城百貨大樓的威脅下,裁縫鋪的生意也一直不錯。
張裁縫與時俱進,去武漢進來高檔的羊毛呢子,在冬天能做漂亮修身的呢子大衣—并不是每個人都有完美身材,商場里賣的呢子大衣往往要么肩膀過寬,要么衣長過長,這讓他的生意迎來又一個小高峰。張裁縫乘勝追擊,又買了做羽絨服的機器。縣城商場里賣羽絨服,他也定做羽絨服,價格比商場還便宜,就連附近幾個鎮的人都知道他能定做呢子大衣和羽絨服,到了年底,就專門跑到曉蓮制衣來做衣服。
一門生意只要能賺錢,立馬就會出現跟風的人。眼見張裁縫夫婦開店能賺錢,很快,老街和新街上各開了一家裁縫鋪,一家是女裁縫,另一家也是夫妻店。但他們要么是手藝比不上張裁縫,要么是進的布料不夠高檔,生意都沒有曉蓮制衣的好。因此,他們便想出些別的花招來,一家兼賣毛線,另一家開展織補衣服破洞的業務,結果另外兩家也馬上學了去。最后,三家裁縫鋪的業務完全重疊了。
三
在三家裁縫鋪上演爭奪客源的合縱連橫時,時間不知不覺流逝,鎮上的初中生已經知道愛美,開始嫌棄裁縫鋪的鄉土氣息;縣城里新開了條“女人街”,售賣的衣服款式新穎、價格低廉,學生們都以去“女人街”買衣服為榮,只有我這種身材瘦小、穿不了成人尺碼的人才會繼續光顧裁縫鋪。
但比起“女人街”里那些露出線頭、粗制濫造的成衣,張裁縫的手藝實在是好,一條舊褲子穿得縮到小腿肚,褲腰的紐扣都沒崩開過,這哪兒是衣服呀,簡直是鎧甲,穿到天荒地老都不會壞,讓人都找不出買新衣服的借口。我猜張裁縫肯定不懂經濟學,不知道縮短產品使用壽命是刺激消費的重要手段。
盡管我每年換季都在曉蓮制衣做衣服,但他們的生意還是越來越差了。母親早已不在鎮上做衣服了,她喜歡的是父親從廣州買回的中式套裝,春夏穿的是夢特嬌的真絲針織衫,冬天穿的是各種皮草大衣。不知不覺中,曾走在時尚前沿的曉蓮制衣不再時髦,那兩家跟風的裁縫鋪生意更差:女裁縫靠改衣勉強維持生計,夫妻店改做窗簾生意了。
曉蓮制衣白底紅字的招牌泛黃變舊,木門也被太陽曬得掉漆,罩著布簾的工作臺上積滿了灰,沒有生意的時候,夫妻倆搬著椅子坐在店門口曬太陽,兩人對著車水馬龍的街道嗑瓜子,倒是寵辱不驚。
認真論起來,張裁縫還是母親隔房的堂弟。他雖然長了一張嚴肅的臉,性格卻很溫和,開店以來和曉蓮從沒紅過臉,兩人頭胎生了個女兒,也沒像其他人一樣要二胎。裁縫鋪生意最差的時候,正是千禧年,他們的女兒剛上小學。兩人一合計,干脆把店鋪重新裝修,改開成衣店。白底紅字招牌換成了黑底金漆的“服裝超市”,木門換成玻璃門,天花板上裝了七八根燈管,把不銹鋼衣服展示架照得锃亮,開業時還在門口擺了兩個大花籃。
“服裝超市”走的是平價路線,衣服從武漢漢正街拿貨,每個月都有新款。鎮上女人們雖然看不上廉價的衣料,但也被其鮮艷的顏色吸引,偶爾會進去買幾件圖個新鮮。最喜歡來這里的是從村里來鎮上趕集的嬢嬢婆婆們,她們來一趟不容易,只要路過新鮮店鋪就會進去逛。透過玻璃門看,“服裝超市”里總有人影晃動,有看衣服的,也有看見熟人進去拉家常的。曉蓮脾氣好,不管買不買衣服,待人都親親熱熱的,碰見砍價的也會配合地抹掉零頭。人流量帶來了銷量,很快曉蓮就忙不過來了,從村里找來一個女孩當售貨員。
四
店鋪走上正軌后,曉蓮吸取了之前的教訓,買下隔壁的兩家店鋪,趁著正月生意清淡的時候,把三家店鋪打通重新裝修。擴大店面后,“服裝超市”十分氣派,不僅賣衣服,還賣鞋、襪、內衣,二樓專門建了個試衣間,聘了三個女售貨員,這樣一來,憑借之前積攢下的口碑和人氣,張裁縫和曉蓮輕輕松松就把全鎮的服裝行業壟斷了。
鎮上人喜歡做大事,比如賣木材,發一火車皮的貨就是上十萬的貨款;賣家具,隨便一件都是幾百幾千;賣農用車、摩托車,沒有低于四位數的成交價……誰能想到,賣幾十塊錢的衣服也能把生意做大!可張裁縫夫婦就是靠這不起眼的廉價服裝掙到了錢,他們在店鋪背后的空地建起三層樓;鎮上人互相攀比買車的時候,張裁縫不聲不響就買回了一輛豐田轎車。大家都是經過風浪、見過大錢的人,雖然見他們生意好,但并不眼紅,可是說起他們家的女兒,卻忍不住要露出嫉妒的神色。那個小時候安安靜靜在裁縫鋪寫作業的女孩已經長大成人,在高考時碾壓全鎮小孩,被上海的重點大學錄取,四年大學讀完,又去了日本留學,實打實的光宗耀祖。
張裁縫擺酒慶祝,把蓄了十幾年的胡須刮得干干凈凈,露出青色的下巴,不住地傻笑;曉蓮早已不是曾經淳樸的農婦形象,她考了駕照,在市里參加過企業家培訓班,打扮得干練又清爽,一看就是春風得意的生意人。大家笑嘻嘻朝他們敬酒,借著酒意調侃,問他們女兒畢業了想留在國外怎么辦。
“她想在哪兒,都隨她。”張裁縫說。
“反正她也不會回街上接手我這個店鋪!”曉蓮笑道,“她在哪兒都一樣。”
“那是,在上海和東京待過了,哪里還看得上我們這鄉鎮?”敬酒的人感嘆。
“鄉鎮怎么了?”曉蓮一口氣喝干杯子里的酒,“她讀書的錢不是從鄉鎮來的?咱們憑自己的本事掙錢,走到哪兒也不比別人差!”
“曉蓮,你是巾幗英雄!”大家七嘴八舌起哄,“要我說,這鎮上的人也就這么多,你要想更進一步,還得開分店,要把店鋪開到縣城去,把店鋪開到市里去。”
“那哪兒夠啊!”曉蓮哈哈大笑,“我還要把店開到上海去,開到東京去呢,那才是做大事!”
鞭炮燃放后的硫黃味和酒香、菜香混合在一起,孩子們在桌席間來回追趕,貓狗在椅子下面忙著啃骨頭,臨時搭建的舞臺上演員們還在賣力地唱跳。
陽光照在曉蓮的鬢角,黑發里突兀地摻雜著一莖白發,她的眼角也爬上了細紋,但眸子閃閃發亮,那里面盛滿了無窮的展望和熊熊野心。我突然覺得,她可能真能把店鋪開到東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