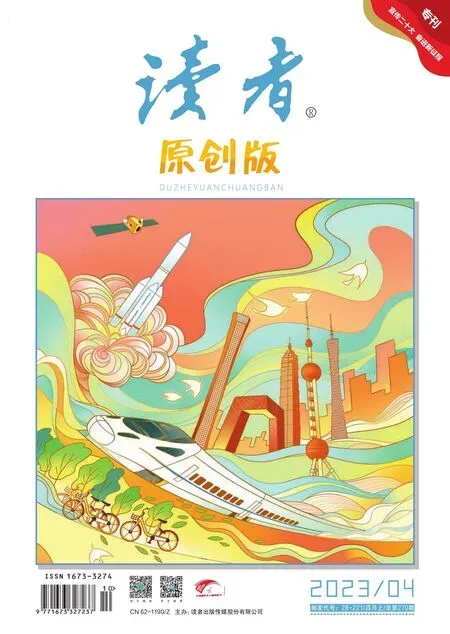回鄉偶記
文|童 鈴

袁源是一名銷售工程師,常常抱著電腦來咖啡館和客戶談工作。有一天,他等待良久,客戶卻遲遲未到,他便和我們聊了起來。
2022年12月底,我跳槽了。臨近春節,新單位大概覺得給剛入職的員工發年終獎不劃算,讓我過完年再去報到。想來想去,我決定把這空閑的一個多月時間用來陪伴父母。
想到要在家待這么長時間,我感到壓力很大。每個人選擇來北京的理由都不盡相同,有人為了謀求事業發展的機會,有人為了首都濃郁的人文氣氛,我純粹是想遠離家鄉,遠離父母,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出生于東部沿海一個經濟較為發達的小城市,家鄉不是不好,而是不夠—不夠熱烈,不夠豐富。如果用水來打比方,北京是沸騰的水,而家鄉只是溫吞的水。
北京的朋友有的開著車千里走單騎,從川藏線進藏,再走青藏線回京;有的去四姑娘山徒步,欣賞雪山美景,也忍受高原反應;有的進過無人區,近距離接觸過藏羚羊……大家玩的就是心跳,每個人都在嘗試突破自我。公園里常常傳出詩朗誦的聲音,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的跑道上永遠擠滿了跑步愛好者。在我看來,這是在熱情洋溢地表達對生活的熱愛。
我的家鄉太平靜了,大家踏踏實實地過日子,滿腦子想的都是掙錢,掙了錢干嗎呢?買大房子,換好車,再沒別的了。誰要跟旅行團去歐洲旅游一趟,這牛能吹一年。年輕人到了一定的年紀必須結婚生子,如果不按這套程序走,那就是異類。
我的父母老實本分,覺得找個好工作、拿到高工資已經是最大的幸福了。他們厭惡風險,不喜歡我折騰。有一個暑假,我突然對烹飪產生了興趣,嘗試照著菜譜燒菜,結果弄得一團糟。我爸吼我:“不會燒就不要燒!”我媽一通苦口婆心:“爸媽不指望你幫忙干家務,只盼你好好學習,將來考個好大學……”我感到很無奈。當父母的怎會不希望自家的孩子聰明能干呢?擰巴的是,他們只愿意看到結果,卻受不了我成長之路上的一地雞毛。可愛迪生發明燈泡之前不也失敗了很多次嗎?你不能說最后成功的那次才有價值,前面那些失敗都是瞎胡鬧,成功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試錯。這些道理怎么和父母講?講了他們也聽不進去。我媽的QQ個性簽名是:做普通人,過平靜的生活。
對我這樣一個生命能量旺盛的人來說,在家鄉生活太不得勁了,一輩子一眼望到頭,這不是我想要的。我期待熱氣騰騰地活著,我渴望驚心動魄的經歷,我想找一個沒有他人注視的地方去磨煉心性,我要按自己的意愿過我的一生。高考填志愿時,我不顧家里的反對,堅決報考北京的學校,畢業后又堅決留了下來。
當然,我愛我的家鄉,我常常對北京的同事和朋友夸贊家鄉的山水很美、人很務實。我當然也愛我的父母,這么多年沒有照顧和陪伴父母,我很愧疚。我只是個普通打工人,來北京這么多年,也沒能讓父母過上更高質量的生活。我常常想,父母會不會為這樣的親子關系感到遺憾?我非要跑這么遠,讓他們既缺乏陪伴,也沒有享受到孩子成功帶來的自豪。在他們眼里,我是個自私的兒子吧?
對家鄉,對父母,我有愛,也有抗拒。
回到十幾年前逃離的地方,我百感交集。家鄉大了好多,我初中時最喜歡在周六下午騎自行車出去玩,一不小心就騎到了鄉下,暖風拂面,放眼望去,是大片的油菜花。現在無論怎么騎都在城里,到處是高樓大廈,那些陌生的地名讓我無比茫然。馬路上騎自行車的少了,開車的多了,馬路雖然變寬了,卻更擁擠了。父母老了,我爸臉上長了幾個老年斑,頭發禿成了“地中海”,早已不是年輕時英姿勃發的樣子;我媽戴了假牙,爬上樓就氣喘吁吁的,還總覺得很冷,晚上不開空調就睡不著。
一切都變了,一切又似乎沒有變。
家鄉洋氣了很多,每個細節都寫滿了對大都市、國際化的向往,20層以上的建筑物會擁有“國際會議中心”“環球大廈”等大氣磅礴的名字,新蓋的小區則往往冠上“銅鑼灣”“海德堡”這樣的名稱。如果是年少的我看到這些,一定心生鄙夷,但現在我只會啞然失笑,大城市的人去小地方尋求內心的平靜,小地方的人則羨慕大城市的高端大氣上檔次,這何嘗不是一種“圍城效應”?
家鄉的人們還是不太浪漫。一個朋友郁悶地問我:“房子、車子、票子我都有了,為什么來相親的那個舞蹈老師還是看不上我?”我調侃他:“人家心里揣著詩和遠方,你只揣著人民幣,如何聊天?”他說對方喜歡三毛的文章,我說三毛長年定居撒哈拉沙漠,你不妨做個攻略,約舞蹈老師一起去摩洛哥旅游,用腳丈量三毛生活過的地方。他撓了撓頭,說那也太遠了吧。我嘿嘿一笑,不再多言。
父母也依然對未知的結果充滿焦慮和擔憂。我開車帶他們去鄰縣游玩,導航出了點兒小問題,這使得我們走了一段岔路,我媽當場崩潰,責怪我不該相信導航,她說向路人問詢就不會發生這種事。直到平安抵達終點,她才平靜下來。我忍住沒有和她爭論,但開始思索為什么我總是很淡定,而她常處于焦躁不安中。
也許是我有獨自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生活的經驗吧。
剛畢業時,不了解北京的租房市場,我吃了不少虧,遇到過黑中介,被騙了300塊錢;碰到過不講理的房東,明明還房時一切如舊,他硬是找碴兒扣我押金,我解釋半天無果,不得不屈服。那1000多塊錢押金對我來說很重要,當時我的眼淚都在眼眶里打轉。這么多年我搬過八九次家。我咬牙堅持著,是因為我自愿接受生活的捶打。在家鄉的生活當然是容易的,每天上下班兩點一線,回家看電視、刷手機,和知根知底的發小交往,心情愉悅是真的,難以獲得成長也是真的。從長遠來看,吃虧上當是好事,遇到的人和事多了,我自然就學會如何識人、如何解決問題了,所謂的社會經驗不就是在不斷成長的過程中逐漸增長的嗎?
我在北京盡可能地省吃儉用。嫌修理電器的費用太高,我便自己找視頻研究;嫌在外面吃飯太貴,我就自己動手做飯,沒有人苛責我浪費時間和材料。時間長了,我的學習能力和動手能力越來越強,對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解得也越來越多,我自認為,我至少算得上半個生活家。
我曾和朋友們騎著自行車去河北,夜晚在一片樹林里搭帳篷露營,被蚊子咬得渾身是包。第二天早上發現自行車被偷了,我們攔了一輛運磚的電動車回北京,狼狽萬分。我曾組織10人小隊去沙漠暴走3天,皮膚被曬傷,腳底起泡。那些父母認為出格的事情,只要不犯法、不傷害他人,我都盡可能地去嘗試。在嘗試的過程中,我覺得自己的力量增強了,我發現生活中的多數困難都能找到方法克服,僅有極少數問題超出我的能力邊界。心里有了底之后,我便極少著急上火。
北京這個地方人才眾多,我平時交往的合作伙伴文化水平都比較高,在互動中我也學到了不少。有句話叫“寧當雞頭,不當鳳尾”,有人愿意當雞頭,是因為當周圍的人不如他優秀時,他可以占據心理上位,得到情緒價值。而我寧當鳳尾,哪怕我是一群鳳凰里最差勁的那只,被其他鳳凰鄙視,我也不在乎,因為只有和優秀的鳳凰在一起,才能學到更多的東西。
回頭看我的父母,他們沒有上過大學,出門就能遇到熟人,很少被欺騙和傷害,不曾經歷大風大浪,也就容易把芝麻大的事兒看得比天大。成長是需要條件的,他們不具備這些條件。
臨走前我陪著我爸出去遛彎,原以為老爺子不善社交,沒想到他人緣還不錯,總有人上來打招呼,我爸也很熱情。“小張,你爺爺的腿傷怎么樣了?我家有拐杖,需要的話來我家拿。”“老李,兒子從北京帶了幾瓶酒回來,啥時候來我家嘗嘗?”這種寒喧在快節奏的大城市并不多見,大家都太忙了,自己的事兒還顧不過來呢,哪兒還有工夫去在意別人?我突然發現,熟人社會并非一無是處,也有溫馨的一面。
在家的這一個多月里,我和家鄉、和父母之間的隔閡漸漸消除,我和十幾年前內心充斥著不滿和憤怒的自己和解了,但我仍不知道丟下父母去實現自我,算不算自私。
在回北京的路上,我給我媽發了條微信:“真抱歉,我沒有攢到足夠的錢買套大房子,讓你們來北京住,我甚至沒能在家鄉給你們換套房子,有我這樣一個沒出息的孩子,你們感到很遺憾吧?”我媽回復道:“當你把你在大城市感知到的東西帶給我們時,我覺得世界一下子變得寬廣了。我去北京看你時才知道VR電影這么有趣,國家博物館包羅萬象,北方的廟會熱鬧非凡。你回家后天天做飯,我才知道菜市場里那些熟悉的食材原來有這么多做法,至于多寶魚、大龍蝦、蜘蛛蟹,我都是第一次嘗到。幸虧你去北京時我們沒有攔著,不然你怎么會懂那么多。”
我沉默了很久,正想著怎么回,她又給我發了一條:“房子不一定要在北京買,壓力太大了,北京周邊交通方便的地區也可以考慮。你的好朋友都在北京,爸媽老了,不能永遠陪著你,和好朋友在一起,也是不錯的人生。”
我的眼淚無聲地落了下來。
年少時想去遠方,想看更大的世界,想成為更好的自己,這些心愿我都實現了,或許在將來的某一天,我會回到家鄉,回到父母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