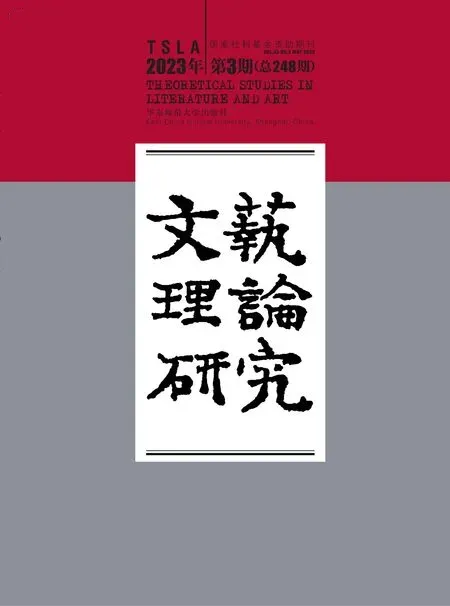電影的敘述距離:從形式到價(jià)值的考察
趙 軒
敘述距離最早由美國(guó)文藝?yán)碚摷摇⒅ゼ痈鐚W(xué)派第二代領(lǐng)軍人物韋恩·布斯(Wayne Booth)在其1961年問(wèn)世的《小說(shuō)修辭學(xué)》中提出,并被認(rèn)為是這部里程碑式著作的“統(tǒng)攝性的概念”與“布斯理論的精髓”(傅修延 108)。然而,文學(xué)研究界圍繞敘述距離的討論實(shí)則并不深入,將其納入電影敘事理論體系的嘗試則更是付之闕如。究其原因,除卻小說(shuō)文本與電影文本各自敘事體系的兼容難度,布斯敘述距離理論本身的晦澀多義與敘事學(xué)界諸多概念的不統(tǒng)一,也是造成目前研究窘境的重要誘因。基于此,本文將回到布斯原典,重新廓清小說(shuō)敘述距離牽涉之多個(gè)主體概念的原初含義,并擴(kuò)展其理論視閾,在電影敘事理論體系中為敘述距離找尋落腳點(diǎn)。在著力探討敘述距離的類(lèi)型、樣態(tài)、功用、發(fā)生場(chǎng)域與影像表現(xiàn)手段的同時(shí),本文還將沿承布斯對(duì)敘事文本道德責(zé)任的重視,論證電影敘述距離的倫理規(guī)限,以期為今后之電影理論與實(shí)踐的發(fā)展路徑提供參照。
一、 敘述距離:從文字到影像
布斯對(duì)敘述距離的最初界定是閱讀體驗(yàn)中多個(gè)主體之間的距離,亦即用以描述“作者、敘述者、其他人物、讀者四者之間含蓄的對(duì)話”中,“每一類(lèi)人就其與其他三者中每一者的關(guān)系而言,都在價(jià)值的、道德的、認(rèn)知的、審美的甚至是身體的軸心上,從同一到完全對(duì)立而變化不一”(145)。法國(guó)敘事學(xué)家熱拉爾·熱奈特(Gérard Genette)進(jìn)一步將“距離”確認(rèn)為“敘事信息數(shù)量變化范疇”(216),是可供敘事主體(作者、敘述者)調(diào)節(jié)、閱讀主體(讀者)感知的變量,其表征的是有關(guān)價(jià)值、道德、認(rèn)知、審美、身體乃至“時(shí)空的距離”“社會(huì)階級(jí)”“言談服飾習(xí)慣”(布斯 145)等方面的敘事信息。然而,以當(dāng)下眼光視之,即便站在熱奈特的“肩膀”上審視敘述距離的理論構(gòu)建,其內(nèi)涵依舊歧義叢生,運(yùn)用于電影敘事框架更是困難重重。原因一方面在于,布斯論及的閱讀體驗(yàn)主體擁有其獨(dú)特的理論背景,直接運(yùn)用于電影敘事框架將遭遇多種挑戰(zhàn);另一方面,布斯在此將價(jià)值、道德、認(rèn)知、審美甚或身體維度逐一羅列,沒(méi)有明確的分類(lèi),使得后人的研究也大多主次不分,含混不清,以致敘述距離的批評(píng)視域趨于離散化而無(wú)從把握中心。上述兩個(gè)問(wèn)題,也正為本文討論電影敘述距離預(yù)設(shè)了必須先行厘清的研究前提。
關(guān)于閱讀體驗(yàn)的四個(gè)主體,布斯在此論述的“作者”實(shí)則是“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亦即作者自己的“隱含的替身”,無(wú)論作者“如何試圖非人格化”,讀者均可由閱讀體驗(yàn)本身建構(gòu)而來(lái)的作者的“第二自我”(66—67),這也是布斯《小說(shuō)修辭學(xué)》最知名的理論創(chuàng)設(shè)之一。“隱含作者”于20世紀(jì)60年代的提出,實(shí)則是為了應(yīng)對(duì)此時(shí)形式主義批評(píng)對(duì)作者傳記式批評(píng)之理論圍剿的一種權(quán)宜之計(jì)。在“文本自足論”成為理論界寵兒的時(shí)代背景下,隱含作者“無(wú)疑是一個(gè)非常英明的概念”(申丹,《何為“隱含作者”?》 137),它實(shí)質(zhì)上創(chuàng)設(shè)了可供批評(píng)者進(jìn)行意圖歸因,卻又可以無(wú)須證明這一意圖是否真實(shí)存在的一種“人格擬制”①。
與之相類(lèi)似,法國(guó)電影理論家阿爾貝·拉費(fèi)(Albert Laffay)同樣發(fā)表于20世紀(jì)60年代初期的專(zhuān)著《電影邏輯》也提出了“大影像師”(le grand imagier)的概念,用以指稱(chēng)“操作畫(huà)面的機(jī)制”,“一個(gè)不可見(jiàn)的敘述策源地”,而非“具體的人或人物”(戈德羅 若斯特 14)。或許是基于相同的時(shí)代背景,“大影像師”的概念創(chuàng)設(shè)也極力回避了“作者”的字眼。在1954年特呂弗于《電影手冊(cè)》撰文提出“作者策略”之后,具備一定藝術(shù)表現(xiàn)能力并形成自身風(fēng)格的電影導(dǎo)演方有資格被稱(chēng)為電影之“作者”,這已然成為法國(guó)電影界的一種共識(shí)。故而,從“人格擬制”的思維范疇加以理解,大影像師與隱含作者無(wú)疑有著共通的理論預(yù)設(shè),兩者均回避了肉身化、凡俗化的作者,進(jìn)而懸置了電影特殊的創(chuàng)作機(jī)制中,單一“電影作者”之合法性的考辨(大影像師),也超克了作者傳記式批評(píng)沉浸于作者生平煩瑣考證的研究?jī)A向(隱含作者)。
另一方面,學(xué)界對(duì)電影敘事中是否存在“敘述者”,或曰是否有必要設(shè)立“敘述者”這一概念則始終爭(zhēng)執(zhí)不斷,克里斯蒂安·麥茨(Christian Metz)即認(rèn)為“陳述者就是影片,影片作為策源地而行動(dòng)、而定向”,應(yīng)從“元影片的話語(yǔ)中取消任何‘?dāng)M人的’機(jī)制,例如‘?dāng)⑹稣摺ⅰ愂稣摺ⅰ荜愓摺?以及其他同類(lèi)概念”(戈德羅 若斯特 75)。大衛(wèi)·波德維爾(David Bordwell)也明確指出,“大多數(shù)影片并未提供清楚定義的敘述者”,“若基于避免徒增無(wú)必要的理論實(shí)體的原則”,“敘述者并非我們的理論基礎(chǔ),分配給每部影片一個(gè)分身(des absconditis)是毫無(wú)意義的”(《電影敘事:劇情片中的敘述活動(dòng)》 144—145)。然而,究其本意,麥茨與波德維爾反對(duì)的均是在電影敘事中設(shè)立“作者型敘述者”(authorial narrator),亦即全知敘述中與隱含作者距離相對(duì)較小的“作者的代言人”(申丹,《敘述學(xué)與小說(shuō)文體學(xué)研究(第三版)》 222),于電影敘事而言,確定“明現(xiàn)敘述者”的位置(戈德羅 若斯特 58),則是切實(shí)而必要的。這種明確地出現(xiàn)在敘事文本的故事層,介入或并不介入故事的敘事者,被熱奈特稱(chēng)為故事內(nèi)-異故事敘述者或故事內(nèi)-同故事敘述者(175),布斯則稱(chēng)其作“戲劇化的敘述者”(145),波德維爾則稱(chēng)其作具備“敘述所在的聲音或形體”的角色敘述者或非角色敘述者(《電影敘事:劇情片中的敘述活動(dòng)》 143)。無(wú)論這一敘述者被如何命名,均是在影像文本中有著明確實(shí)體和敘述聲音的具體人物,他(她)可能介入故事甚至直接是“大影像師”的代言人,比如《陽(yáng)光燦爛的日子》(姜文,1994年)中的馬小軍;也可能只是與其他人物共處同一影像時(shí)空,幾乎不介入故事的、默默的旁觀者,比如《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張藝謀,1995年)中的鄉(xiāng)村少年唐水生。即便這類(lèi)人物型的敘述者在電影敘事中往往帶來(lái)一種不合理的“加敘”,即自身“記憶理應(yīng)有限”,卻“提供本來(lái)不該提供的信息”(戈德羅 若斯特 59),但其在影像文本中的明確在場(chǎng),為描述與其他敘事主體之間的距離,錨定了清晰的位置,故而是確定電影敘述距離研究范式的必要概念預(yù)設(shè)。
與“隱含作者”相類(lèi)似,布斯敘述距離中涉及的“讀者”,被其稱(chēng)為“假想讀者”(postulated reader),這一概念之后被美國(guó)敘事學(xué)家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發(fā)展為“隱含讀者”(implied reader),亦即完全與“隱含作者”相對(duì)應(yīng)的,“由敘事本身所預(yù)設(shè)的受眾”(134),在電影敘事中,這一“預(yù)設(shè)的受眾”可被稱(chēng)為“理想化的觀眾”。觀眾之理想化一方面是感官的健全,不會(huì)因個(gè)體的身體差異而影響到對(duì)電影文本的慣常認(rèn)知。比如講述主人公罹患閉鎖癥候群、全身癱瘓,僅有左眼可以自由活動(dòng)的法國(guó)傳記片《潛水鐘與蝴蝶》(朱利安·施納貝爾,2007年),其間人物主觀鏡頭的壓抑觀感,即建立在觀眾常規(guī)官能感知的前提之上,而個(gè)別與主人公有相同癥狀的觀眾所獲得之身體的共鳴,則并非此片敘述距離設(shè)置的原初用意。與之相類(lèi)似的還有表現(xiàn)盲人按摩師的《推拿》(婁燁,2014年),影片為了照顧盲人觀眾,片中所有字幕均有旁白講述,但盲人觀眾并非影片的“理想化觀眾”,因?yàn)樵撈挠跋癫糠质冀K無(wú)從被聲音完全表述。另一方面,觀眾的理想化還體現(xiàn)在其位置的特定性方面,無(wú)論電影鏡頭如何設(shè)置,觀眾始終是鏡頭背后的觀看者,這一“優(yōu)越的位置”被稱(chēng)作“位點(diǎn)”(locus),它代表著觀眾的抽象位置,本身并非物理位置,而是伴隨情節(jié)變動(dòng)不居,進(jìn)而給觀眾帶來(lái)“這個(gè)世界是為我而造的”錯(cuò)覺(jué)(瓦努瓦 20—21),觀眾對(duì)自身位置特定性的認(rèn)同,非但要求其應(yīng)當(dāng)在慣常的觀影環(huán)境中接收電影文本,自覺(jué)祛除來(lái)自外部的觀影噪音和情境污染(比如刻意在課堂、會(huì)議等不相宜的環(huán)境中竊自觀看影片,來(lái)謀求電影文本以外的刺激),同時(shí)還暗含著對(duì)觀眾心智、審美和道德水平的一般要求。
分析至此,布斯理論體系中的閱讀體驗(yàn)主體——作者、敘述者、其他人物、讀者,可以代換為電影敘事中的大影像師、(人物型)敘述者、其他人物和(理想化)觀眾。這也就界定了電影敘述距離的發(fā)生場(chǎng)域(見(jiàn)圖1)。其中,因?yàn)樗懻撝當(dāng)⑹稣呦抻谌宋镄蛿⑹稣?故而觀眾-人物、觀眾-敘述者各自敘述距離的作用機(jī)制并無(wú)實(shí)質(zhì)差別,兩者均主要表現(xiàn)在認(rèn)知、情感層面。大影像師-敘述者之間的敘述距離則是布斯的另一杰出理論創(chuàng)見(jiàn)——可靠/不可靠敘述(下文會(huì)專(zhuān)門(mén)論述),在可靠敘述中,敘述者-人物、大影像師-人物之間的敘述距離基本一致,除卻認(rèn)知層面的調(diào)節(jié)之外,更反映出大影像師對(duì)人物、敘述者的道德判斷,不可靠敘述則打破這一前提,使得大影像師的態(tài)度基于反諷而更趨復(fù)雜。大影像師-觀眾之間的敘述距離表現(xiàn)為大影像師對(duì)觀眾的諷刺、戲謔乃至鄙夷,往往具有冒犯性。

圖1 電影敘述距離的發(fā)生場(chǎng)域
在上述分析中,對(duì)于敘述距離發(fā)生場(chǎng)域的描述,已經(jīng)不可避免地涉及距離的認(rèn)知、情感、道德層面,這就自然引申到探討電影敘述距離必須解決的第二個(gè)前提——敘述距離的類(lèi)型。回到《小說(shuō)修辭學(xué)》,布斯在描述閱讀體驗(yàn)多個(gè)主體之間的距離之時(shí),先后使用了理智、情感、道德、身體、審美、價(jià)值、認(rèn)知等概念,著實(shí)紛繁蕪雜,但其先前在對(duì)讀者的“文學(xué)趣味”進(jìn)行分類(lèi)之時(shí),已然聲明這同時(shí)也是距離的分類(lèi)。依據(jù)布斯的論述,“文學(xué)趣味(和距離)的類(lèi)型”可分為,“認(rèn)知的或認(rèn)識(shí)的”——對(duì)事實(shí)和真實(shí)的強(qiáng)烈好奇心;“性質(zhì)的”——“看到某種完成的型式或形式的,或體驗(yàn)?zāi)撤N性質(zhì)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強(qiáng)烈愿望”,即“審美的”趣味;“實(shí)踐的”——“希望我們愛(ài)或恨、贊揚(yáng)或討厭的人們成功或失敗的強(qiáng)烈愿望”,即“人性的”趣味(116)。上述三個(gè)類(lèi)型明顯分別對(duì)應(yīng)與真、美、善,亦即認(rèn)知的、審美的和情感、道德的范疇。
明確了敘述距離的類(lèi)型,也就不難領(lǐng)悟布斯為何在描述不同距離樣態(tài)時(shí)會(huì)使用“介入”“同情”“同一”(148)等概念,針對(duì)真(認(rèn)知的)、善(情感、道德的)、美(審美的)三方面的敘述距離,可以使用如下樣態(tài)進(jìn)行描繪(見(jiàn)表1)。

表1 不同敘述距離的樣態(tài)描述
必須指出,于強(qiáng)調(diào)視聽(tīng)感官傳達(dá)的電影敘事而言,不同主體間的認(rèn)知距離最為明顯,它還可以細(xì)分為空間距離(物理上的高低遠(yuǎn)近)、時(shí)間距離(事件經(jīng)歷過(guò)程中的過(guò)去、現(xiàn)在與將來(lái))、心理距離(人物內(nèi)心活動(dòng)的顯現(xiàn)與否),并且仰仗于主觀鏡頭的普遍運(yùn)用,電影可以輕松達(dá)成不同主體認(rèn)知范圍的“同一”,亦即“絕對(duì)近”,而省略法的使用,則以對(duì)人物的“無(wú)視”達(dá)成了認(rèn)知距離的“絕對(duì)遠(yuǎn)”。情感、道德距離②也相對(duì)便于細(xì)分,由于道德判定往往并非黑白分明,惡人遭厄運(yùn)的敘事文本(比如一些黑色電影)有時(shí)未必令觀眾拍手稱(chēng)快,對(duì)于灰色人物的“同情”(即便并不“認(rèn)同”其以身試法的行徑)反而成為一種常見(jiàn)的距離樣態(tài),“鄙夷”與“對(duì)立”的存在也大致源于道德判定的多元化。審美距離或許是其中最含混的,大部分以情節(jié)取勝的電影,一般也并不重視主體間的審美距離(一些探索性的藝術(shù)片往往存在著大影像師與觀眾間的審美距離),所以其樣態(tài)也相對(duì)泛化。
仍須注明,不同類(lèi)型的敘述距離往往各行其是,其各自的樣態(tài)描述并不存在簡(jiǎn)單的正負(fù)相關(guān)。譬如認(rèn)知距離的同一或介入,并不代表情感距離的認(rèn)同或同情,《大話西游》(劉鎮(zhèn)偉,1995年)的結(jié)尾,至尊寶戴上緊箍?jī)悍艞墘m世愛(ài)情、接受取經(jīng)重任,并被他人戲謔“好像一只狗”,其不斷遠(yuǎn)去的背影(空間距離),內(nèi)心活動(dòng)的表現(xiàn)缺失(心理距離),均顯示出觀眾與人物之間認(rèn)知距離的不斷疏遠(yuǎn),但觀眾卻在這一認(rèn)知距離的疏遠(yuǎn)過(guò)程中,拉近了與人物間的情感距離,實(shí)現(xiàn)了情感上更深層次的認(rèn)同。
二、 電影敘述距離的表現(xiàn)手段
敘述距離并非靜態(tài)的,在布斯看來(lái),僅在敘述者與讀者之間,便存在“先遠(yuǎn)后近”,“由近變遠(yuǎn)而后再變近”,以及“不斷遠(yuǎn)離讀者”三種變化趨勢(shì),并且以“先遠(yuǎn)后近”為常態(tài)(147)。不同于小說(shuō)文本,電影敘事?lián)碛幸韵露喾N更為便捷的藝術(shù)手法展示并調(diào)節(jié)三類(lèi)敘述距離,并在綜合調(diào)度中顯現(xiàn)出電影敘事的獨(dú)特風(fēng)格。
(一) 鏡頭內(nèi)表現(xiàn)
1. 構(gòu)圖
電影鏡頭的構(gòu)圖體系,尤其是景深鏡頭的前中后景關(guān)系,為認(rèn)知距離的空間表現(xiàn)提供了一個(gè)頗為開(kāi)闊的舞臺(tái)。《公民凱恩》(奧遜·威爾斯,1941年)中,小凱恩的母親不顧丈夫的反對(duì),決定向銀行家撒切爾轉(zhuǎn)移撫養(yǎng)權(quán)的經(jīng)典鏡頭,位于前景的母親和銀行家、中景的父親和后景中在雪地撒歡的小凱恩,構(gòu)成了一個(gè)認(rèn)知距離與情感距離相互交織的絕佳例證。除卻縱深意義上的物理位移,構(gòu)圖上的空間距離也可體現(xiàn)在高度上,比如《用心棒》(黑澤明,1961年)的主人公三十郎就有一處巧施妙計(jì)、引誘兩派惡徒械斗,自己則坐在高處隔岸觀火的有趣鏡頭,此時(shí)觀眾與人物情感、道德距離的拉近即體現(xiàn)在空間距離(高度)的差異上,并且是成反比(認(rèn)知距離越遠(yuǎn),情感距離越近)。但正如前文所言,不同距離類(lèi)型之間并不存在簡(jiǎn)單的正負(fù)相關(guān),類(lèi)似的反例也不在少數(shù),同樣是對(duì)高度的分析,查特曼即在其《故事與話語(yǔ)》中針對(duì)《公民凱恩》的一處鏡頭得出完全相反的結(jié)論,他認(rèn)為“低角度使人物形象高聳,成為‘大于生活’的原則之象征”,但鏡頭中凱恩的“高聳”,卻可“被讀作失敗姿態(tài)”(84—85),如若聯(lián)系“革命樣板戲”電影的鏡頭美學(xué)原則,這一發(fā)現(xiàn)無(wú)疑是顛覆性的,即反面人物或許無(wú)須“遠(yuǎn)小黑”,“近大亮”的也未必就是正面人物。
鏡頭縱深距離的表現(xiàn),有時(shí)還會(huì)借助一些貼近鏡頭的“遮片”,使鏡頭的縱深感以及觀眾與人物的距離得到強(qiáng)化。希區(qū)柯克的早期電影《謀殺》(1930年)便調(diào)用舞臺(tái)道具表現(xiàn)這一縱深感,當(dāng)然,充當(dāng)“遮片”的用具此后不斷演化,《小城之春》(費(fèi)穆,1944年)中的“遮片”便是戴禮言老宅中的斷瓦頹垣。與構(gòu)圖相配合的還有色彩與光線,它們?cè)谡{(diào)節(jié)認(rèn)知距離的同時(shí)也對(duì)情感距離進(jìn)行調(diào)節(jié),影史上的相關(guān)范例不勝枚舉,此不贅述。
2. 單一鏡頭體系內(nèi)的運(yùn)動(dòng)
鏡頭內(nèi)的運(yùn)動(dòng)是對(duì)敘述距離的一種調(diào)節(jié)。它首先包括鏡頭本身的運(yùn)動(dòng)——調(diào)節(jié)縱深距離的推拉,調(diào)節(jié)高度的升降。改變縱深距離的運(yùn)動(dòng)還有一類(lèi)特例——變焦。在電影史上,“急速變焦”一度成為特定歷史時(shí)期的標(biāo)志性鏡頭語(yǔ)言,這一即刻拉近觀眾與人物的空間距離的手法,也同時(shí)衍生出特殊的敘事節(jié)奏。
如若單一視點(diǎn)的鏡頭放棄自身的運(yùn)動(dòng),演員的走位便是唯一能夠調(diào)節(jié)空間距離的方式,這即是場(chǎng)面調(diào)度帶來(lái)的“運(yùn)動(dòng)”,這種運(yùn)動(dòng)往往會(huì)帶來(lái)極大的視覺(jué)沖擊和認(rèn)知壓力,比如《公民凱恩》又一個(gè)經(jīng)典的景深鏡頭,老凱恩直接從后景走向前景,訓(xùn)斥對(duì)其第二任妻子出言不遜的聲樂(lè)老師。相較于變焦,演員的走位保證了運(yùn)動(dòng)的連貫性,亦即將空間距離的變化過(guò)程加以完整呈現(xiàn),無(wú)疑有著更為合理的節(jié)奏。故而,即便是在當(dāng)下,面向鏡頭急速而來(lái)的鬼魅之物已成為“jump scare”(或可譯作:一驚一乍)恐怖風(fēng)格的標(biāo)配,卻仍在大多數(shù)影片中屢試不爽。
可歸入鏡頭內(nèi)運(yùn)動(dòng)表現(xiàn)手法的還有升格/降格鏡頭。升格鏡頭(慢鏡頭)是通過(guò)人為拉長(zhǎng)感受時(shí)間,對(duì)人物動(dòng)作細(xì)部表現(xiàn)的一種強(qiáng)化,著力于拉近觀眾與人物的認(rèn)知距離,但這一手法自被業(yè)界開(kāi)創(chuàng)以來(lái)便有被濫用的傾向,其命運(yùn)與“變焦”相類(lèi)似,波德維爾即認(rèn)為“無(wú)休止的變焦距與慢鏡”是20世紀(jì)70年代香港功夫片淪落的標(biāo)志(《香港電影:娛樂(lè)的秘密》 253)。降格鏡頭(快鏡頭)則與之不同,它本身是以超越生活常識(shí)的節(jié)奏表現(xiàn)人物動(dòng)作,在疏遠(yuǎn)認(rèn)知距離的同時(shí),也疏遠(yuǎn)觀眾與人物的情感距離。在默片時(shí)代,有如上了發(fā)條一般的喜劇角色,即便在銀幕上鋌而走險(xiǎn)、命懸一線,也不會(huì)令觀眾產(chǎn)生認(rèn)知和道德層面的共情,這似是喜鬧劇的必需。庫(kù)布里克在《發(fā)條橙》(1971年)中即通過(guò)一段降格鏡頭表現(xiàn)主人公與兩個(gè)女性的荒唐肉體關(guān)系,這種極具間離化色彩的表現(xiàn),也是在疏遠(yuǎn)觀眾與人物認(rèn)知和道德距離的過(guò)程中,促成觀眾對(duì)人物的“鄙夷”態(tài)度。
(二) 鏡頭組合表現(xiàn)
1. 剪切
蒙太奇建立起來(lái)的全新時(shí)空關(guān)系自然是對(duì)敘述距離最為體系化的展現(xiàn)與調(diào)節(jié)。這其間的省略還涉及《小說(shuō)修辭學(xué)》對(duì)“顯示”(showing)與“講述”(telling)的兩相界分(3—8),這一區(qū)分也被法國(guó)敘事學(xué)界稱(chēng)作敘述語(yǔ)式中的“描寫(xiě)”與“敘述”,或者索性對(duì)應(yīng)于文學(xué)文本中的“故事”與“話語(yǔ)”(托多羅夫 302)。單就電影敘事而言,這兩者的區(qū)分相對(duì)更為直觀,敘述者或人物在敘述過(guò)程中是否直接使用“閃回”對(duì)敘述之內(nèi)容加以影像化展示,便是在“顯示”與“講述”中進(jìn)行的取舍。一般而言,閃回對(duì)敘述信息的“顯示”無(wú)疑會(huì)拉近觀眾對(duì)敘述者(或人物)的認(rèn)知距離,但許多影史佳作,往往省略閃回,以敘述者(或人物)的“講述”間接傳達(dá)敘事信息,影像展示的省略,實(shí)質(zhì)上達(dá)成了中國(guó)傳統(tǒng)美學(xué)意蘊(yùn)中的“留白”。比如《城南舊事》(吳貽弓,1983年)中,瘋女人秀珍向小英子講述自己凄慘經(jīng)歷,以及《沉默的羔羊》(喬納森·戴米,1991年)中作為人物出現(xiàn)的敘述者克拉麗絲,向食人教授漢尼拔講述“羔羊何以沉默”的段落,均使用了上述手法。
鏡頭間的剪切也可以單就空間距離加以調(diào)節(jié),不同的剪切方式,可以表現(xiàn)空間組合的同一、鄰接,乃至近距或遠(yuǎn)距式的分離(戈德羅 若斯特 121—133),上述手法用在人物身上,也就構(gòu)成了觀眾與人物空間距離的不同樣態(tài)。在表現(xiàn)觀眾與人物之間空間距離的剪切手法中,針對(duì)同一場(chǎng)景人物的拉近式急速剪切(即景別經(jīng)由中、近景急速剪切為特寫(xiě))也頗為值得關(guān)注,相較于急速變焦,這一手法保留了場(chǎng)景的部分細(xì)節(jié),并構(gòu)成了前文提及之鏡頭內(nèi)人物快速走位的一種反向模式,似乎鏡頭之后的觀眾伴隨著鏡頭在急速走向人物,它同時(shí)賦予了觀眾在這一認(rèn)知距離變化過(guò)程中的一種假想的主動(dòng)性,反而更具感官?zèng)_擊力。經(jīng)典恐怖片《午夜兇鈴》(中田秀夫,1998年)的高潮部分,從井中攀緣而出的山村貞子在爬出電視,緩慢走向受害者的過(guò)程中,所有觀眾便是經(jīng)由上述特殊的急速剪切手法,看到貞子的詭異面容。這一段落實(shí)際上還使用了愛(ài)森斯坦的反復(fù)剪輯(repetitious editing)手法(查特曼 57),亦即每一個(gè)鏡頭都會(huì)重復(fù)上一鏡頭的部分動(dòng)作細(xì)節(jié),拉近認(rèn)知距離的同時(shí),拉長(zhǎng)了敘事時(shí)間,延宕了感官?zèng)_擊的到來(lái),無(wú)疑是對(duì)前文提及之jump scare手法的一種超越。
正反打鏡頭(shot/reverse shot)作為鏡頭剪切的一種特例,在繁復(fù)的拍攝環(huán)境中也凸顯了被攝物(一般是交談中的人)的獨(dú)立存在,故而是對(duì)認(rèn)知距離的拉近。而相對(duì)于在前景中保留觀看者部分身體的“過(guò)肩鏡頭”(over the shoulder shot),騎軸的正反打在拉近敘述者與人物乃至觀眾與人物的情感距離方面確實(shí)存在一定的促進(jìn)作用,這種促進(jìn)作用并非僅僅源于具體某個(gè)鏡頭的主觀性,而是如麥茨所言:“感知的同化(攝影機(jī)替代主人公的眼睛)不一定導(dǎo)致象征性的認(rèn)同。確保認(rèn)同的是人物被聚焦和進(jìn)行聚焦的往復(fù)運(yùn)動(dòng)。”(瓦努瓦 163)
2. 時(shí)態(tài)和聚焦
熱奈特很早就關(guān)注到“現(xiàn)在時(shí)的使用縮短了主體間的距離”(151),影像中的此時(shí)此刻,無(wú)疑更容易激起觀眾與人物之間的認(rèn)知代入感,縮短兩者的認(rèn)知距離。相反,相對(duì)于現(xiàn)在時(shí)的預(yù)敘和倒敘,則因?yàn)檩^早地泄露了事件的結(jié)果,難以調(diào)動(dòng)觀眾對(duì)人物行為的認(rèn)知期待,故而疏遠(yuǎn)了觀眾與人物之間的認(rèn)知距離。但在有些情況下,上述做法卻有可能反過(guò)來(lái)加強(qiáng)觀眾對(duì)人物的情感認(rèn)同。比如《布拉格之戀》(菲利普·考夫曼,1988年)的結(jié)尾,經(jīng)由影片的預(yù)敘,觀眾已然先行知曉男女主人公雙雙死于車(chē)禍的結(jié)局,但當(dāng)暢飲美酒后的兩人駕車(chē)穿行于細(xì)雨中的樹(shù)林,戀人間的親密耳語(yǔ)與畫(huà)外舒緩的鋼琴曲,加上預(yù)先知曉的悲劇收尾,無(wú)疑均拉近了觀眾與人物之間的情感距離,更加強(qiáng)化了悲天憫人的觀感。近年上映的反類(lèi)型西部片《第一頭牛》(凱莉·萊卡特,2019年)的整體敘事都建立在上述結(jié)構(gòu)上,只不過(guò)由開(kāi)頭的“兩具枯骨”預(yù)先宣布死亡的是一位頗具冒險(xiǎn)精神的華人淘金者和他的生意合作伙伴——一位白人面點(diǎn)師。類(lèi)似敘事手法的屢試不爽,表現(xiàn)出電影界對(duì)于“時(shí)態(tài)”之?dāng)⑹鼍嚯x調(diào)節(jié)功用的充分認(rèn)識(shí)。
熱奈特最早選取“聚焦”這一極富視覺(jué)藝術(shù)色彩的概念去描繪小說(shuō)中的人物視角,從一開(kāi)始就預(yù)示著打通影像文本與小說(shuō)文本敘事體系的可能,而敘述者>人物(零聚焦)、敘述者=人物(內(nèi)聚焦)、敘述者<人物(外聚焦)這三個(gè)最早由法國(guó)敘事學(xué)家茲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提出的公式,經(jīng)由熱奈特的闡發(fā)和推廣,受到學(xué)界的普遍認(rèn)可(申丹,《敘述學(xué)與小說(shuō)文體學(xué)研究》 213)。電影敘事往往是通過(guò)人物在畫(huà)面中的位置,以及匹配剪輯(match-cut)來(lái)彰顯人物視角(查特曼 143),進(jìn)而達(dá)成各類(lèi)聚焦模式。大影像師在選取聚焦人物之時(shí),無(wú)論決定外察其行、內(nèi)省其心(內(nèi)聚焦)還是僅僅外察其行(外聚焦),均是對(duì)有關(guān)人物認(rèn)知距離的一種展示與調(diào)節(jié)。一般而言,因?yàn)閮?nèi)聚焦可以“內(nèi)省其心”,故而在心理距離層面拉近了觀眾與敘述者、觀眾與人物之間的認(rèn)知距離,相反,外聚焦則是對(duì)上述距離的疏遠(yuǎn),而上帝視野一般的零聚焦(這在電影中并不多見(jiàn)),觀眾自然會(huì)基于心理展示的無(wú)處不在而拉近與人物之間的認(rèn)知距離,但反而會(huì)因敘述者的無(wú)所不知(此時(shí)的敘述者已然非人物化而成為前文提及的“作者型敘述者”)疏遠(yuǎn)與敘述者的距離。
3. 主觀鏡頭組合
麥茨認(rèn)為:“主觀鏡頭要得到正確理解,仍意味著影片中必須有表現(xiàn)主人公的客觀影像,而且不能離得太遠(yuǎn)。”(瓦努瓦 162)這實(shí)質(zhì)上即視點(diǎn)鏡頭(point of view shot)與主觀鏡頭的交叉剪切。《陽(yáng)光燦爛的日子》中馬小軍用望遠(yuǎn)鏡看到米蘭臥房中的照片便是上述組合手法的體現(xiàn),其中,鏡頭的主觀性即是通過(guò)模擬望遠(yuǎn)鏡的晃動(dòng)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主觀鏡頭的使用往往在達(dá)成認(rèn)知距離的“同一”性之時(shí),也拉近了觀眾與人物的情感距離,許多表現(xiàn)主人公走向死亡的主觀鏡頭均是如此。比如《這個(gè)殺手不太冷》(呂克·貝松,1994)的主人公萊昂即將逃出升天,走出大樓的一刻,來(lái)自背后的黑槍,讓其主觀鏡頭出現(xiàn)了一剎那的閃光;而《鬼子來(lái)了》(姜文,2000年)的主人公馬大三最終被投降的日軍用軍刀正法,其滾動(dòng)的頭顱帶來(lái)的視角遷移,以及鮮血伴隨眼睛的眨動(dòng)在鏡頭前的蔓延,均渲染了人物的悲劇性和荒誕感。主觀鏡頭強(qiáng)烈的認(rèn)知同一和情感認(rèn)同效果往往容易導(dǎo)致倫理失范,這也是下文討論敘事距離倫理規(guī)限的一個(gè)關(guān)注點(diǎn)。
(三) 敘事層級(jí)表現(xiàn)
1. 畫(huà)外音
除卻影響情感、道德距離的配樂(lè)而外,畫(huà)外音對(duì)敘述距離的調(diào)節(jié)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是對(duì)敘述者內(nèi)心視閾的透視,進(jìn)而在認(rèn)知上拉近觀眾與敘述者的心理距離,比如《小城之春》的女主人公周玉紋便在與丈夫戴禮言的交談中,多次在畫(huà)外即時(shí)性地“直陳心緒”,形成“內(nèi)聚焦”模式的同時(shí),也促成觀眾走進(jìn)這一“近于冶蕩”之女子(費(fèi)穆語(yǔ))的內(nèi)心世界。羅伯特·布列松的《鄉(xiāng)村牧師日記》(1951年)明顯也使用了相同的獨(dú)白設(shè)定。另一方面,許多內(nèi)心獨(dú)白是敘述者站在當(dāng)下追憶往昔,故其在與畫(huà)面組合后,形成了第一人稱(chēng)回顧性視角(畫(huà)外音)與經(jīng)歷性視角(畫(huà)面)的共生(申丹,《敘述學(xué)與小說(shuō)文體學(xué)研究》 202),進(jìn)而達(dá)成了此時(shí)之?dāng)⑹稣邔?duì)彼時(shí)之?dāng)⑹稣叩脑僭u(píng)判。實(shí)際上,在這一特殊的時(shí)態(tài)、聚焦綜合運(yùn)用的藝術(shù)手法中,畫(huà)外音僅是輔助手段,而畫(huà)面中的敘述者已然降格為畫(huà)外音敘述中的人物。這一手法正是通過(guò)對(duì)敘事層級(jí)的跨越,拉近了敘述者與人物(畫(huà)面中正在經(jīng)歷事件的敘述者)之間的認(rèn)知距離,同時(shí)也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觀眾與敘述者的情感距離,促成其對(duì)敘述者的同情。比如《雙重賠償》(比利·懷爾德,1944年),已然中槍、即將不治的主人公,利用卷筒式錄音機(jī)回憶自己殺人越貨的勾當(dāng),慨嘆自己即將墮入黑暗、萬(wàn)劫不復(fù)。當(dāng)畫(huà)面中的敘述者伴隨著畫(huà)外音的講述,巨細(xì)無(wú)遺地展示自己如何不露痕跡地殺死了情婦的丈夫,并偽造了不在場(chǎng)證明,似乎大功告成之時(shí),畫(huà)外音忽然說(shuō)道:“我聽(tīng)不見(jiàn)自己的腳步聲,那是死人的腳步聲。”這一明顯來(lái)自當(dāng)下(重傷不治的敘述者)的評(píng)判眼光,即是一種跨越敘事層級(jí)的敘述距離調(diào)節(jié),這一句話令不同時(shí)態(tài)的兩個(gè)敘述者幾近合一,彼時(shí)的敘述者忽然具備了此時(shí)之?dāng)⑹稣叩恼J(rèn)知,而觀眾也由這句話開(kāi)始同情(即便并不應(yīng)當(dāng))眼前這個(gè)必將走向死亡的罪犯。
2. 字幕
無(wú)論是默片時(shí)代還是有聲時(shí)期,電影字幕對(duì)人物信息的交代,本身即是跨越敘事層級(jí)、拉近觀眾與人物的認(rèn)知距離的一種手段。一些字幕還會(huì)在交代人物信息的同時(shí),將扮演者的姓名也一并注明,這已經(jīng)在強(qiáng)調(diào)影片本身的虛構(gòu)性,有了“自反式敘事”的色彩。同時(shí),中國(guó)早期電影還傾向于利用字幕大發(fā)議論,對(duì)片中人物痛下針砭,這其實(shí)也是拉近大影像師與觀眾道德距離的一種嘗試,可惜效果不佳。被稱(chēng)為“鄭老夫子”的鄭正秋,即因?yàn)槔米帜贿M(jìn)行道德說(shuō)教,而被譏諷“打破世界各國(guó)影片字幕所無(wú)的例子”,其影片字幕兼具“固本培元”的功能(四通 1)。
3. 不可靠敘述
在《小說(shuō)修辭學(xué)》中,布斯用“不可靠敘述”描述敘述者與隱含作者的思想規(guī)范是否一致,倘若一致,敘述者即是可靠的,反之,則是不可靠的(148)。這實(shí)際上即是對(duì)兩者之間敘述距離的描繪,并且布斯使用了“事實(shí)/事件軸”和“價(jià)值/判斷軸”用以區(qū)分距離的類(lèi)別。很多年后,美國(guó)敘事學(xué)界權(quán)威詹姆斯·費(fèi)倫(James Phelan)在布斯的基礎(chǔ)上增加了“知識(shí)/感知軸”,并將每一類(lèi)型的不可靠敘述區(qū)分為“錯(cuò)誤報(bào)道”和“不充分報(bào)道”(申丹,《何為“不可靠敘述”?》 134)。現(xiàn)在看來(lái),費(fèi)倫增加的“知識(shí)/感知軸”仍舊沒(méi)有脫離布斯“事實(shí)/事件軸”的基本架構(gòu),始終屬于認(rèn)知范疇,而布斯區(qū)分的兩大軸依舊脫胎于其對(duì)距離的三分法,亦即前文提及的認(rèn)知、人性(情感道德)、審美,只不過(guò)敘述者與隱含作者之間的審美距離,對(duì)于敘述可靠性的影響似乎可以忽略不計(jì)。
于電影而言,“不可靠敘述”即對(duì)應(yīng)于大影像師與敘述者之間的距離。為了顯現(xiàn)敘述者的不可靠,大影像師可以通過(guò)敘述者內(nèi)心獨(dú)白與影像畫(huà)面之間的矛盾直接譏諷敘述者的“信口雌黃”,比如《雨中曲》(斯坦利·多南/吉恩·凱利,1952年),吉恩·凱利飾演的主人公向記者講述自己成名前的演藝經(jīng)歷,閃回段落中,主人公的畫(huà)外音堅(jiān)稱(chēng)自己的成名過(guò)程是“尊嚴(yán),永遠(yuǎn)是尊嚴(yán)”,但畫(huà)面講述的則是默默無(wú)聞的他,賣(mài)力表演卻飽受觀眾嘲諷,這就達(dá)成了一種聲音與畫(huà)面在真實(shí)性上的違逆;而像《陽(yáng)光燦爛的日子》中馬小軍講述自己在餐廳被劉憶苦毆打的段落,影像本身的虛構(gòu)性直接促成觀眾對(duì)影片整體敘事真實(shí)性的質(zhì)疑,一些娛樂(lè)性更強(qiáng)的電影(比如好萊塢的神經(jīng)喜劇和香港的無(wú)厘頭喜劇)甚至?xí)屟輪T直視鏡頭,用以表現(xiàn)對(duì)旁白的不滿,這均是“不可靠敘述”的反諷性功用。
如果敘述者的“不可靠”是在電影結(jié)尾之時(shí)才加以揭露,這實(shí)際上達(dá)成了情節(jié)上的“突轉(zhuǎn)”。這種“突轉(zhuǎn)”,往往是以“補(bǔ)敘”的手法,最終填充了電影整體敘事過(guò)程中的多處“留白”。基于大影像師疏遠(yuǎn)敘述者之過(guò)程的延宕性,觀眾在最后一刻方始質(zhì)疑整個(gè)故事的真實(shí)性,或是區(qū)分其中的真實(shí)和虛假的比例,這也讓整部影片保有了敘事張力。近年被認(rèn)為“重拾港味”的港產(chǎn)制作《無(wú)雙》(莊文強(qiáng),2018年)即是在結(jié)尾處揭露郭富城飾演之主人公作為“不可靠敘述者”的真實(shí)身份(一個(gè)心理病患),而后“補(bǔ)敘”整個(gè)故事的真實(shí)樣態(tài)。
值得一提的是,敘述者的“不可靠”也有可能是源自心理鏡頭的展示,比如《鳥(niǎo)人》(亞歷杭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圖,2014年)的主人公總會(huì)在無(wú)人在場(chǎng)時(shí)忽然具備臨空飛起的“超能力”,又或是《困在時(shí)間里的父親》(佛羅萊恩·澤勒,2020年)罹患艾滋海默癥的敘述者完全混亂的感知、記憶影像。“不可靠敘述”的這一運(yùn)用模式也在主觀鏡頭之外,發(fā)掘了另一種達(dá)成觀眾與敘述者情感認(rèn)同的有效路徑。
4. 自反式敘事
自反性(reflexivity,又譯“反身性”),用以指稱(chēng)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包括自我關(guān)注、評(píng)價(jià)和批判)乃至自我否定(self-refutation)等思維方式(肖瑛 11)。自反式敘事(reflexivity narrative)是在敘事過(guò)程中的自我指涉,它不惜凸顯敘事文本的虛構(gòu)性,以達(dá)成對(duì)敘事本身的自我反思乃至對(duì)抗和否定。電影中的自反式敘事手段多樣,如字幕、聲音與畫(huà)面的違逆,敘事段落相互矛盾卻并行推進(jìn),在電影敘事文本之外加上額外的敘事套層,甚至直接展現(xiàn)演員表演、劇組拍攝和后期剪輯的真實(shí)過(guò)程。除卻改編自“元小說(shuō)”的《法國(guó)中尉的女人》(卡雷爾·賴(lài)茲,1981年)和《項(xiàng)狄傳》(又譯《一個(gè)荒誕的故事》,邁克爾·溫特伯頓,2005年)外,表現(xiàn)南斯拉夫國(guó)族命運(yùn)的藝術(shù)片《地下》(又譯《沒(méi)有天空的都市》,埃米爾·庫(kù)斯圖里卡,1995年)中“戲中戲”《春天騎著白馬來(lái)》與影片本身的相互指涉,傳記片《阮玲玉》(關(guān)錦鵬,1991年)中穿插進(jìn)導(dǎo)演對(duì)主要演員的訪談和演員補(bǔ)妝過(guò)程,乃至喜劇片《大佛普拉斯》(黃信堯,2017年)中旁白將全片由“黑白”短暫地轉(zhuǎn)換為“彩色”,均是自反式敘事在當(dāng)下電影敘事實(shí)踐中的多元化運(yùn)用。
自反式敘事對(duì)敘事文本可信度的極力消解,完全打破了觀眾與敘述者乃至與大影像師之間的信任關(guān)系,故而是對(duì)認(rèn)知距離的疏遠(yuǎn),但類(lèi)似于孟子的“反求諸己”“反身而誠(chéng)”,電影文本對(duì)自我的解剖和反思,反而使觀眾不再關(guān)注敘事文本的情節(jié),而是更為關(guān)注大影像師所要傳達(dá)的情感蘊(yùn)藉或道德觀念,拉近了觀眾與敘述者、大影像師之間的情感道德距離。《地下》對(duì)南斯拉夫的復(fù)雜情感,《阮玲玉》對(duì)傳主悲苦命運(yùn)的抒情式表達(dá),《大佛普拉斯》對(duì)臺(tái)灣貧富差異的道德針砭,均是因自反式敘事得到了加強(qiáng)。
三、 切近感與優(yōu)越感:電影敘述距離的功用與倫理規(guī)限
誠(chéng)如布斯所言:“距離本身從來(lái)就不是目的;努力沿著一條軸線保持距離是為了使讀者與其他某條軸線增加聯(lián)系。”(114)電影對(duì)敘述距離的展示和調(diào)節(jié)本身也是為了達(dá)成多種敘事功用。上文就多次論及敘述距離在情感認(rèn)同上的功用,同樣地,這一調(diào)節(jié)的反向過(guò)程則是達(dá)成情感疏遠(yuǎn)甚或道德批判。
認(rèn)知距離的調(diào)節(jié)除卻其情感功用之外,更重要的是通過(guò)對(duì)敘事信息數(shù)量的掌控,為觀眾帶來(lái)懸念和驚詫。具體而言,就是保持認(rèn)知上的遠(yuǎn)距離(時(shí)間、空間或心理),以形成懸念;不期然地拉近認(rèn)知距離,以形成驚詫。這其中驚詫的達(dá)成,可以是懸念的解除;或者通過(guò)補(bǔ)敘、揭露不可靠敘述,形成既往認(rèn)知的顛覆;甚至有可能僅是認(rèn)知距離的急速拉近,以達(dá)成一種感官刺激。《火車(chē)進(jìn)站》為第一批觀眾帶來(lái)的“驚詫”即是如此,這也即是湯姆·甘寧(Tom Gunning)所言之有關(guān)電影“原初驚恐”的神話(107)。在認(rèn)知和情感道德維度還有一種始終保持適中距離的做法,類(lèi)似于福樓拜“客觀而又無(wú)動(dòng)于衷”的寫(xiě)作態(tài)度,可被稱(chēng)為影像上的冷峻風(fēng)格,許多表現(xiàn)大屠殺的作品以及科恩兄弟的黑色電影均有這一風(fēng)格的體現(xiàn)。
戲謔、反諷均是在大影像師參與之距離場(chǎng)域中達(dá)成的敘事功用,前文已然討論的“不可靠敘述”,除卻在結(jié)尾處突轉(zhuǎn)以表現(xiàn)驚詫之外,由大影像師通過(guò)對(duì)自身與敘述者距離的疏遠(yuǎn)也可以表現(xiàn)一種“反諷”,但這一反諷的主體還須進(jìn)一步厘清。費(fèi)倫通過(guò)區(qū)分“錯(cuò)誤報(bào)道”和“不充分報(bào)道”對(duì)布斯“不可靠敘述”體系的補(bǔ)充,實(shí)際上即是嘗試區(qū)分?jǐn)⑹稣咧安豢煽俊笔欠窬邆渲饔^性,這對(duì)于將“反諷”歸因于何人有重要意義。如果敘述者的不可靠是愚人的力有不逮,那么大影像師自己秉持反諷態(tài)度,此即查特曼所說(shuō)以犧牲敘述者為代價(jià),顯現(xiàn)隱含作者的反諷態(tài)度,達(dá)成其與隱含讀者的交流(213),前文提及的《雨中曲》的段落便是如此。而如果敘述者的不可靠是智者的有意為之或無(wú)奈之舉,那么反諷的便是敘述者自身,大影像師反而借此拉近了觀眾與敘述者的情感距離,前文提及的《鳥(niǎo)人》,演藝事業(yè)已然江河日下的主人公,只能不斷回想自己飾演的超級(jí)英雄——飛鳥(niǎo)俠,以達(dá)成一種積極的心理暗示,此時(shí)敘述者張開(kāi)雙翅、飛檐走壁的大量心理鏡頭,在形成“不可靠敘述”的同時(shí),實(shí)質(zhì)上顯現(xiàn)出敘述者面對(duì)人生低谷時(shí)的一種深深的無(wú)力感,觀眾很難將此歸因于敘述者的心智障礙或病患,反而是對(duì)其情感窘境的感同身受。
還有一種反諷存在于大影像師與觀眾之間,亦即大影像師直接疏遠(yuǎn)自身與觀眾的審美距離。比如《日落大道》,其敘述者——一個(gè)窮困潦倒的好萊塢編劇,所講述的故事——自己被徐娘半老的默片女演員包養(yǎng),意圖脫離這種荒唐關(guān)系之時(shí),卻被發(fā)了瘋的女演員槍殺,在真實(shí)性上并無(wú)可供指摘之處。但這一敘述的可靠性卻與影片經(jīng)典的開(kāi)頭出現(xiàn)了嚴(yán)重的違逆。開(kāi)頭處,頗具戲謔性的畫(huà)外音,在向觀眾指涉自己——一具身中數(shù)槍,漂浮于貴婦泳池中的死尸,并且這種自我指涉并不是時(shí)態(tài)上的回顧與經(jīng)歷,因?yàn)楫?huà)外音對(duì)自己死后的事件也知之頗多,甚至直接加以評(píng)論。如若了解相關(guān)影史趣聞,這一開(kāi)頭其實(shí)已然經(jīng)過(guò)導(dǎo)演的修改,原本的開(kāi)頭更為前衛(wèi),電影直接將鏡頭對(duì)準(zhǔn)停尸房,廁身其間的主人公在同身旁的伙伴(當(dāng)然全是死尸)暢談各自的死因③,如果加上這部影片本身對(duì)好萊塢制片廠模式的諷刺,這一開(kāi)頭對(duì)觀眾認(rèn)知、審美慣性的冒犯實(shí)屬昭然若揭。據(jù)說(shuō),米高梅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路易斯·梅耶在試映后對(duì)導(dǎo)演比利·懷德大罵不絕,試映時(shí)觀眾也噓聲不斷(克羅 430—431)。修改后的開(kāi)頭雖然不及停尸房場(chǎng)景的戲謔程度,但確實(shí)又保留了大影像師的反諷用意,可以說(shuō)是大影像師與觀眾審美距離的一個(gè)典型例證。
實(shí)際上,敘述距離的上述功用大都可以歸化于不同主體間“切近感”與“優(yōu)越感”之間的調(diào)控。在認(rèn)知距離上,人物或敘述者更加“切近”事實(shí)本身,則其“優(yōu)越感”超過(guò)觀眾,這就形成“懸念”,反之,當(dāng)觀眾最終或突然“切近”事實(shí),就打破了人物或敘述者的認(rèn)知優(yōu)越感,形成了“驚詫”,距離適中的“冷峻”風(fēng)格,則是在這兩者之間維系一種平衡;在情感、道德距離上,大影像師、觀眾對(duì)人物或敘述者的認(rèn)同或同情是一種“切近感”,反之,鄙夷和批判則是一種“優(yōu)越感”;在審美距離上,大影像師或敘述者的戲謔、反諷,也均是一種“優(yōu)越感”的體現(xiàn)。
布斯曾經(jīng)不無(wú)憂慮地認(rèn)為:“我們中流行的對(duì)像‘好人’和‘壞人’這樣的道德術(shù)語(yǔ)的忽視真是一種不幸。”(121)秉承《小說(shuō)修辭學(xué)》對(duì)敘事倫理的一貫關(guān)注,作為修辭手段的“敘述距離”,其道德意涵也理應(yīng)引起重視。
首先,就“切近感”而言,影片應(yīng)慎重處理極端暴力的“受難場(chǎng)景”所帶來(lái)的“驚詫”,因?yàn)椤皼](méi)有任何其他場(chǎng)面像苦難的影像一樣,能夠引起如此緊迫的倫理問(wèn)題”(唐寧 薩克斯頓 100)。具有猶太教背景的法國(guó)哲學(xué)家伊曼努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即出于對(duì)“圣像禁誡”(Bilderverbot)的闡發(fā),“認(rèn)為納粹消滅歐洲猶太人和其他族群的企圖是不可以表現(xiàn)的,斷言它不能或者不該用圖像還原,”(130)此時(shí)的“受難場(chǎng)景”已然具備了宗教神圣性,進(jìn)而成為“不可再現(xiàn)之物”,表現(xiàn)納粹猶太大屠殺的紀(jì)錄片《浩劫》(克洛德·朗茲曼,1985年)便是這一觀點(diǎn)的忠實(shí)體現(xiàn)。而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則認(rèn)為有關(guān)“受難場(chǎng)景”的影像,無(wú)論是記錄或搬演,均是“遠(yuǎn)距離觀看痛苦的一種方式”,但“我們沒(méi)有權(quán)利在無(wú)法接觸他人的原生力量的情況下,遠(yuǎn)距離體驗(yàn)他人的苦難”(108),這已然顯現(xiàn)出對(duì)距離帶來(lái)的“優(yōu)越感”與“切近感”的反思。桑塔格進(jìn)一步論證道,當(dāng)作為觀眾的我們,基于影像中的“受難場(chǎng)景”而產(chǎn)生同情之時(shí),“我們的同情宣布我們的清白,同時(shí)也宣布我們的無(wú)能”,這種同情實(shí)質(zhì)上掩蓋了觀看者的特權(quán),進(jìn)而是“不切實(shí)際的”反應(yīng)(94)。總之,依據(jù)桑塔格等理論家的意見(jiàn),“注視別人的痛苦,這種行為本身并沒(méi)有什么問(wèn)題,真正有問(wèn)題的是那些表現(xiàn)模式和反應(yīng)模式,它們將痛苦的場(chǎng)面工具化”(唐寧 薩克斯頓 106)。不難發(fā)現(xiàn),桑塔格的思路最終還是落實(shí)到影像的敘述距離層面之上。
延續(xù)敘述距離的思路,電影中的“受難場(chǎng)景”當(dāng)然不可以將觀眾設(shè)置在一個(gè)遠(yuǎn)離苦難的位置上,在認(rèn)知或情感道德距離上的刻意疏遠(yuǎn),無(wú)疑有違電影表現(xiàn)上述場(chǎng)景的本意。但另一方面,更應(yīng)當(dāng)在影像敘事中拒絕極端暴力的“切近感”,因?yàn)檫@正是“將痛苦的場(chǎng)面工具化”。《不可撤銷(xiāo)》(加斯帕·諾,2002年)中長(zhǎng)達(dá)13分鐘的性侵表現(xiàn)。《索多瑪120天》(皮埃爾·帕索里尼,1976年)中各種無(wú)所不用其極的肉體折磨游戲,無(wú)疑均超出了必要的限度,而蛻變成對(duì)低級(jí)感官趣味的變相迎合。相反,《浩劫》以講述(telling)替代顯示(showing)的做法,自然是對(duì)“切近感”較為徹底的拒斥。當(dāng)然,對(duì)敘述距離的適當(dāng)調(diào)節(jié),或許是更為變通的做法。比如日本電影《愚行錄》(石川慶,2016年)在表現(xiàn)女主人公一度被多人輪番性侵的經(jīng)歷之時(shí),既沒(méi)有用“講述”替代“顯示”,也沒(méi)有直白地記錄以致墮入低俗感官表現(xiàn),而是以一種間離化的手法——心理鏡頭中,許多雙手肆意地貼近主人公身體,巧妙地避免了“切近感”帶來(lái)的倫理失范,又給予觀眾一種感官上的震撼,進(jìn)而達(dá)成對(duì)主人公的同情。
其次,就“優(yōu)越感”而言,影片不應(yīng)當(dāng)令觀眾認(rèn)同加害者(即布斯所言之“壞人”)的優(yōu)越感。基于主觀鏡頭組合的特殊效能,觀眾與人物(加害者)認(rèn)知距離的無(wú)限拉近,實(shí)質(zhì)上是在達(dá)成對(duì)邪惡本身的“認(rèn)同”。比如近年來(lái)因真兇最終現(xiàn)身而重獲關(guān)注的韓國(guó)影片《殺人回憶》(奉俊昊,2003年),在影片敘事中段,一個(gè)過(guò)肩鏡頭穿過(guò)殺人犯的右側(cè)視野投射于行走在鄉(xiāng)間小路上的兩個(gè)女性之上,鏡頭的不斷推進(jìn),最終達(dá)成了觀眾與謀殺者的認(rèn)知合一,所有觀眾此刻享有了與謀殺者同一的主動(dòng)地位。而后,鏡頭左右搖移,似乎在從中選擇獵物,并最終對(duì)其中的女學(xué)生下手。這一僅有1分鐘的鏡頭段落,完全出離了一部驚悚片應(yīng)有的倫理預(yù)設(shè),讓觀眾共享加害者的主觀視閾,生成了“逍遙法外”的犯罪主體,無(wú)疑是對(duì)觀眾倫理訴求的虧負(fù),更有悖于一部影片擔(dān)負(fù)的社會(huì)倫理責(zé)任。與之相類(lèi)似的還有《此房是我造》(拉斯·馮·提爾,2018年),全片將敘述者選定為一個(gè)患有強(qiáng)迫癥的連環(huán)殺手,以其大段內(nèi)心獨(dú)白串聯(lián)多個(gè)極端暴力場(chǎng)面,并不惜在虐殺他人之前,奉上一段“邏輯自洽”的道德演說(shuō),在聚焦、畫(huà)外音等多個(gè)層面均是在拉近觀眾與這一邪惡敘述者之間的距離,進(jìn)而形成了一種不恰當(dāng)?shù)摹皟?yōu)越感”。
同時(shí),即便是大影像師自身的優(yōu)越感,也理應(yīng)加以限制。比如并未引起太多關(guān)注的自反式影片《吉祥如意》(董成鵬,2020年),一向以喜劇演員和導(dǎo)演身份示人的董成鵬(大鵬),此刻卻以偽紀(jì)錄片的形式講述自己的家族之痛——自己的三舅因疾病失智而被妻女拋棄,老母辭世后,成為一家人的負(fù)累。影片的高潮設(shè)定為三舅女兒的扮演者情難自已,跑出攝影棚,與真實(shí)的“女兒”同框。此刻,真正具備道德責(zé)任的倫理主體與假想性的倫理主體,構(gòu)成了同一影像時(shí)空中的并置——角色痛哭不止、角色原型在冷漠地玩手機(jī),即便在影片的采訪片段中,導(dǎo)演多次聲稱(chēng)自己無(wú)權(quán)評(píng)判三舅妻女的選擇,但這一打破敘事層級(jí)、疏遠(yuǎn)認(rèn)知距離的自反式敘事,已然彰顯出大影像師在情感道德層面的批判態(tài)度。然而,如若重新審視這一片段,無(wú)法走出角色的演員與拒絕進(jìn)入社會(huì)角色的人物原型,如此巧妙地并置于鏡頭之前,其“搬演性”實(shí)在昭然若揭。這一自反式處理,仍舊是敘述距離的倫理失范,跨層敘事背后,是大影像師對(duì)自身道德評(píng)判權(quán)利認(rèn)識(shí)的表里不一,更是其優(yōu)越感的不當(dāng)顯現(xiàn)。
余論:電影敘事倫理的研究路徑
本文從布斯《小說(shuō)修辭學(xué)》出發(fā),將小說(shuō)文本的敘述距離適用于影像文本之上,本是旨在探討一種更為便捷的觀照大影像師創(chuàng)作意圖與觀眾觀影效果的形式批評(píng)方法,但秉承布斯原典對(duì)敘事倫理的重視,本文對(duì)敘述距離調(diào)節(jié)技巧的討論很自然地延伸到技巧適用過(guò)程中的倫理規(guī)限上。這恰也從一個(gè)側(cè)面印證了電影敘事倫理的思考理路。眾所周知,在曲春景教授系統(tǒng)論證電影敘事倫理的研究方法之前(77—83),國(guó)內(nèi)學(xué)界圍繞“敘事倫理”就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理解:一是側(cè)重對(duì)敘事文本進(jìn)行倫理闡釋的“所敘之事”的倫理;二是針對(duì)敘事行為進(jìn)行倫理分析的所謂“事之所敘”的倫理。有論者將以上兩種研究理路概括為“倫理批評(píng)的新道路”與“敘事學(xué)的新發(fā)展”(劉郁琪 97),王鴻生教授認(rèn)為上述兩種界分“其實(shí)都是自設(shè)陷阱式的界定”,“緣于頑固的現(xiàn)代學(xué)科歸類(lèi)意識(shí)在作祟”(17)。然而,筆者認(rèn)為,基于影像敘事本身的特殊性,對(duì)于影像敘事行為本身的倫理分析,即“事之所敘”的倫理,確乎具有分門(mén)別類(lèi)、獨(dú)立觀照之必要。除卻影像敘事的感性特質(zhì)更容易形成倫理失范之外,思考電影敘事行為本身的倫理規(guī)限,更是關(guān)注形式的電影敘事研究最終基于倫理考量而走向價(jià)值的必由之路。在此意義上,本文對(duì)電影敘述距離的考察,便是對(duì)上述研究路徑的一種踐行。
注釋[Notes]
① “人格擬制”本是一個(gè)法律術(shù)語(yǔ),原指與自然人格相對(duì)應(yīng),被法律承認(rèn)的虛擬人格,比如“法人”。筆者在這里使用這一概念,意圖表明“隱含作者”以及下文提及的“大影像師”等術(shù)語(yǔ)的創(chuàng)設(shè),本無(wú)意還原真實(shí)存在的文本作者,而只是賦予文本一個(gè)虛擬人格,作為批評(píng)者歸納文本敘事意圖的話語(yǔ)工具。
② 筆者在這里應(yīng)當(dāng)及時(shí)對(duì)“心理距離”與“情感距離”作進(jìn)一步界分,前者用以描述“我是否能夠完全知曉你在想什么”,而后者則用以描述“你的歡樂(lè)和悲傷是否能夠打動(dòng)我”。
③ 這一設(shè)置非常類(lèi)似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的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shuō)《佩德羅·帕拉莫》(1955年)中的有關(guān)情節(jié),卻又比小說(shuō)發(fā)表早了5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韋恩·布斯:《小說(shuō)修辭學(xué)》,華明等譯。北京: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7年。
[Booth, Wayne.TheRhetoricofFiction. Trans. Hua Ming, et al.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2017.]
大衛(wèi)·波德維爾:《電影敘事:劇情片中的敘述活動(dòng)》,李顯立等譯。臺(tái)北:遠(yuǎn)流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Bordwell, David.NarrationintheFictionFilm. Trans. Li Xianli, et al. Taipei: Yuanliu Publishing Co. Ltd., 1999.]——:《香港電影的秘密:娛樂(lè)的藝術(shù)》,何慧玲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
[---.PlanetHongKong:PopularCinemaandtheArtofEntertainment. Trans. He Huiling. Haikou: Hainan Press, 2003.]
西摩·查特曼:《故事與話語(yǔ):小說(shuō)和電影的敘事結(jié)構(gòu)》,徐強(qiáng)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
[Chatman, Seymour.StoryandDiscourse:NarrativeStructureofFictionandFilm. Trans. Xu Qia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3.]
卡梅倫·克羅:《對(duì)話比利·懷爾德》,張衍譯。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
[Crowe, Cameron.ConversationwithBillyWilder. Trans. Zhang Ya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麗莎·唐寧,莉比·薩克斯頓:《電影與倫理:被取消的沖突》,劉宇清譯。重慶: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19年。
[Dowing, Lisa, and Libby Saxton.FilmandEthics:ForeclosedEncounters. Trans. Liu Yuqing.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傅修延:《文本學(xué)——文本主義文論系統(tǒng)研究》,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
[Fu, Xiuyan.Textology:ASystematicStudyofTextualistLiteraryTheory.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安德烈·戈德羅,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電影敘事學(xué)》,劉云舟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5年。
[Gaudreault, André, and Fran?ois Jost.LeRécitCinématographique.Trans. Liu Yunzho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yǔ)·新敘事話語(yǔ)》,王文融譯。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0年。
[Genette, Gérard.DiscoursNarratif,NouveauDiscoursNarratif.Trans. Wang Wenro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0.]
湯姆·甘寧:《一種驚詫美學(xué):早期電影和(不)輕信的觀眾》,李二仕譯,《電影藝術(shù)》6(2012):107—115。
[Gunning, Tom. “An Aesthetic of Astonishment: Early Film and the (In)Credulous Spectator.” Trans. Li Ershi.FilmArt6(2012):107-115.]
劉郁琪:《“敘事學(xué)新發(fā)展”還是“倫理批評(píng)新道路”——敘事倫理的提出及其理論價(jià)值》,《江漢論壇》7(2009):97—100。
[Liu, Yuqi. “‘New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Science’ or ‘New Way of Ethical Criticism’: The Presentation of Narrative Ethics and its Theoretical Value.”JianghanTribune7(2009):97-100.]
曲春景:《中國(guó)“敘事倫理批評(píng)”的電影觀及研究方法》,《同濟(j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6(2019):77—83。
[Qu, Chunjing. “The Film Concept of Chinese Narrative Ethics Criticism and the Research Method.”JournalofTongji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 6(2019):77-83.]
申丹:《敘述學(xué)與小說(shuō)文體學(xué)研究(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
[Shen, Dan.ResearchonNarratologyandFictionStylistics(ThirdEd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何為“隱含作者”?》,《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2008):136—145。
[---. “What is ‘Implied Author’?”JournalofPeking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 2(2008):136-145.]——:《何為“不可靠敘述”?》,《外國(guó)文學(xué)評(píng)論》4(2006):133—143。
[---. “What is ‘Unreliable Narration’?”ForeignLiteratureReview4(2006):133-143.]
四通:《功能固本培元的鄭正秋的字幕》,《電聲日?qǐng)?bào)》,1932年5月11日。
[Si Tong. “Consolidating Basis and Cultivate Spirit: The Function of Zheng Zhengqiu’s Subtitles.”ElectroacousticDaily11 May 1932.]
蘇珊·桑塔格:《關(guān)于他人的痛苦》,黃燦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
[Sontag, Susan.RegardingthePainofOthers. Trans. Huang Canra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茲維坦·托多羅夫:《敘事作為話語(yǔ)》,朱毅譯,《敘述學(xué)研究》,張寅德編選。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9年。
[Todorov, Tzvetan. “Narration en tant que Discours.”Trans. Zhu Yi.StudyofNarratology. Ed. Zhang Yind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9.]
弗朗索瓦·瓦努瓦:《書(shū)面敘事·電影敘事》,王文融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
[Vanoye, Francie.Récitécrit,RécitFilmique.Trans. Wang Wenro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王鴻生:《何謂敘事倫理批評(píng)?》,《文藝?yán)碚撗芯俊?(2015):14—21。
[Wang, Hongsheng. “What Is Narrative Ethic Criticism?”TheoreticalStudiesinLiteratureandArt6(2015):14-21.]
肖瑛:《“反身性”研究的若干問(wèn)題辨析》,《國(guó)外社會(huì)科學(xué)》2(2005):10—17。
[Xiao, Ying. “An Analysis of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Reflexivity.”SocialSciencesAbroad2(2005):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