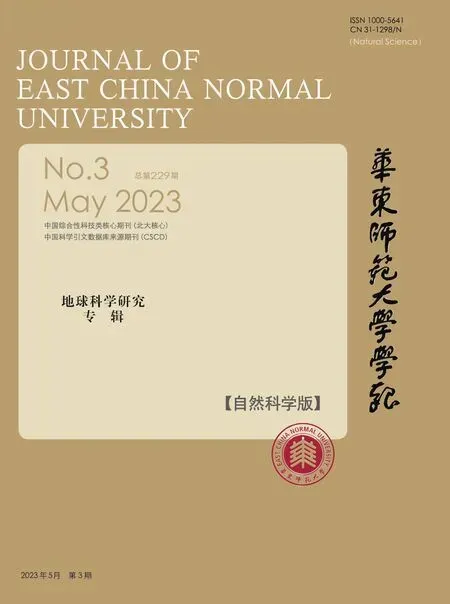濱海濕地中溶解態CH4的通量及影響因子
張 穎, 張曉慧, 劉婷婷, 楊芷璇, 唐劍武,2,3
(1. 華東師范大學 河口海岸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上海 200241; 2. 崇明生態研究院, 上海 202162;3. 長江三角洲河口濕地生態系統教育部/上海市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 上海 200241)
0 引言
在過去100年內, 甲烷 (CH4) 已經成為僅次于二氧化碳 (CO2) 的重要溫室氣體之一, 且CH4的單分子增溫潛勢大約為CO2的25倍[1]. 世界氣象組織報告顯示, 過去10年內, 大氣中CH4以5.21 ×10–3mg·m–3·a–1的速度增長, 截至2019年, 全球大氣中CH4濃度已高達(1340.71±1.43) × 10–3mg·m–3,為1750年的260%[2]. 水體沉積物中產生的CH4溶于水, 待溶解態CH4累積至飽和后, CH4進入大氣,所以水環境是大氣CH4的重要來源之一[3]. 河口區是陸地淡水和海洋的過渡區域, 特別是濱海濕地區域, 水中溶解態CH4通常表現為高飽和狀態, 是大氣中CH4的重要來源之一[4], 在CH4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中承擔重要角色.
濱海濕地中, 周期性潮汐淹水為CH4的生產提供了適宜的厭氧環境[5], 較高的初級生產力和來源豐富的土壤有機物為CH4的合成提供了豐富的底物[6]. 缺氧環境下, 土壤有機質降解的最終產物是醋酸鹽, 或是CO2和H2, 產甲烷菌利用它們作為原料生產CH4[7-8]. 適宜的溫度有利于提高產甲烷菌生產CH4的速率[9], 引起水體中溶解態CH4濃度升高. CH4的產生還會受到多種因素的抑制, 由海水攜帶進入濕地的鹽分, 主要包括硫酸根離子和硝酸根離子等電子受體, 均是抑制CH4產生的重要因素. 它們與產甲烷菌存在競爭關系, 如多種硫酸鹽還原菌會利用H2作為電子供體[10].
濱海濕地水體溶解態CH4的通量是土壤和水體CH4產生、消耗及傳輸共同作用的結果[7,11]. 目前,對濱海濕地水體CH4的研究主要集中在CH4溶存濃度、飽和度、水氣界面垂向擴散通量、產生和消耗機制等方面[12]. 濱海濕地受到的潮汐作用會改變水體中有機物和營養鹽等生源要素的水平輸送[13-14], 而且可能進一步影響水體內相應溫室氣體的橫向輸運, 但是對濱海濕地水體CH4水平輸送通量卻鮮有研究.
對水氣界面CH4的擴散通量的測定通常采用靜態箱法和擴散模型法[15]. 靜態箱法成本低、操作簡單[16]. 但是, 此方法獲得的樣品數量有限, 不適合大區域和長期觀測; 漂浮箱的規格及氣體混合方式等沒有統一規定, 會導致觀測結果的偏差[17]; 此外, 在有風和流動水體的條件下, 箱體會改變水體表面空氣的流動狀況, 箱體與表層水體的摩擦會引起水體擾動, 影響觀測結果的準確性. 而擴散模型法是一種基于CH4水氣界面擴散過程的半經驗模型方程, 通過計算水體和大氣中CH4的濃度差, 得出CH4水氣界面交換通量[18]. 因此, 該方法可以減小風速和水流對觀測結果的影響, 但是對溶解態CH4的高頻率連續觀測依然存在困難. 近年來, 對水體溶解態CH4等溫室氣體進行原位連續觀測的方法逐漸增多, 在解決儀器布設及供電問題后, 通過氣體平衡裝置連接氣體分析儀, 可以對溶解態CH4濃度進行高頻率連續觀測[19-20].
針對目前的研究現狀, 本文以長江口濱海濕地為例, 利用溶解態CH4原位連續觀測系統, 探究了溶解態CH4濃度、垂向擴散通量、水平輸送通量的時空特征及主要驅動因子. 本文的研究結果對完善濱海濕地CH4輸送過程有重要意義, 有助于探究濱海濕地CH4在全球CH4生物地球化學循環中的作用.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九段沙濕地自然保護區 (以下簡稱“九段沙”, 記作“JDS”) 位于長江口外南北槽之間的攔門沙河段 (圖1(a)), 總面積約423.2 km2[21]. 潮汐類型為非正規半日潮[22], 水文變化受到長江徑流洪枯季變化、潮汐周期性變化和風暴潮等因素的共同影響. 此區域受東亞季風氣候影響, 年平均氣溫為15.7℃. 蘆葦是九段沙上沙的優勢植被, 互花米草和海三棱藨草等植被零星分布[23]. 采樣點位于九段沙上沙碼頭東南處一條寬為11 m的潮溝入海口處 (圖1(b)), 潮溝的流域面積通過潮溝的數字高程模型計算, 為0.18 km2. 西沙濕地公園 (以下簡稱“西沙”, 記作“XS”) 位于崇明島的西南端 (圖1(a)), 處于長江口的一級分汊處, 總面積3 km2, 潮汐類型為非正規半日潮, 受長江徑流洪枯季交替影響[24]. 氣候類型為亞熱帶季風氣候, 年平均氣溫約為15℃[25]. 西沙濕地草澤區主要植被為蘆葦. 采樣點位于西沙聽潮平臺東南處一條寬為16 m的潮溝入海口處 (圖1(c)), 潮溝流域面積為0.11 km2. 兩處研究區域均安裝了通量觀測塔站, 配備有開路式渦度相關系統和生物氣象輔助系統, 探頭均距地面10 m, 可以收集長時間、連續性CH4交換通量和生物氣象數據[26].
1.2 溶解態CH4間隔樣品采樣與測定
在2020—2021年期間分別在九段沙和西沙采樣 (表1). 使用亞克力采樣器采集潮溝水體水面以下30 cm深處水樣, 采樣間隔為30 min, 每次至少采集3個潮周期. 采樣后, 緩慢釋放水樣至60 mL的棕色玻璃瓶 (提前酸洗, 超純水洗至中性后烘干) , 待水溢出后, 擰緊瓶蓋, 并確保瓶中不存在氣泡. 同時, 采集300 mL水樣于棕色PET塑料瓶, 4℃下避光保存. 采樣結束后, 采用頂空平衡法提取水樣中的CH4氣體[27]. 首先, 用氣密性好的注射器向玻璃樣品瓶緩慢注入30 mL高純氮氣, 排出多余水樣;然后, 將樣品瓶置于振蕩器中, 以180 r/s的速度震蕩40 min后, 靜置15 ~ 20 min, 使用注射器抽取15 ~20 mL頂部氣體注入氣袋, 4℃下保存. 返回實驗室后, 抽取5 ~ 10 mL氣體樣品注入氣相色譜儀 (Agilent 7890B, 安捷倫, 美國), 氣體濃度通過FID (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 檢測器進行檢測, 使用CH4氣體濃度為0和3.68 mg·m–3的標準氣體對檢測結果進行校正, 標準偏差≤2%.

表1 間隔采樣和原位連續觀測采樣信息Tab. 1 Sampling information of interval sampling and in-situ observation
棕色PET塑料瓶水樣使用孔徑為0.7 μm的GF/F濾膜過濾. 過濾后, 濾膜置于15 mL的離心管中, 用于水體中葉綠素a濃度測定. 過濾后的水樣儲存在預先經過酸洗、超純水洗至中性高密度聚乙烯塑料瓶中, 用于測定水體中營養鹽和濃度. 濾膜與水樣 –20℃保存.
葉綠素a濃度采用分光光度法測定. 采用反復凍融法處理葉綠素a樣品后, 加入10 mL 90%的丙酮溶液萃取后離心. 使用紫外可見光分光光度計 (UV-8000, METASH, 上海) 測定上清液在750、664、647和630 nm波長處的吸光值, 計算得到濾膜中葉綠素a的濃度[28-29]. 營養鹽測定使用營養鹽自動分析儀 (SAN++4通道理化分析, San plus system, 荷蘭). 測定時, 確保水樣為溶解態, 記錄整理和濃度數據, 檢出限分別為0.28和1.40 μg·L–1, 相對標準偏差為0.1% ~ 4.0%[30]. 使用鉻酸鋇分光光度法測定水體中濃度, 測定過程參考《水質 硫酸鹽的測定 鉻酸鋇分光光度法 (試行) 》(HJ/T 342—2007). 測定前, 確保水樣為溶解態, 通過濃度梯度為0.00、5.00、20.00、40.00、80.00、120.00、160.00和200.00 mg·L–1的硫酸鈉溶液標準曲線, 測定樣品的濃度.
1.3 溶解態CH4原位連續觀測
本文還對水質參數與水體溶解態CH4濃度進行了原位連續觀測, 采樣信息見表1. 原位連續觀測系統由以下3部分組成: ① 多參數水質分析儀 (YSI, EXO2, 美國), 測定鹽度、水溫、pH、濁度、溶解氧 (dissolved oxygen, DO)、葉綠素a和熒光溶解有機物 (fluorescence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FDOM) 等水質參數, 使用浮球綁定儀器, 確保始終測定水體表層30 cm處參數, 測定頻率為5 min;② 聲學多普勒流速儀 (Xylem, SonTek PLUS, 美國), 測定流速、流量和水位等水動力參數, 測定頻率與多參同步; ③ 自主搭建的溶解態溫室氣體原位連續觀測系統, CH4測定儀器為溫室氣體測定儀(LGR, UGGA, 美國), 詳細組成與運行過程見專利 (CN202011192389.6.), 測定頻率為1 s. 整個原位觀測系統在野外的安裝布放如圖1(d) 所示.
1.4 CH4氣體通量計算
本文中CH4的氣體通量包含垂直和水平方向的通量. 垂直方向通量是指CH4在水體和大氣之間的垂向擴散通量, 本文中從水體向大氣擴散為正方向; 水平方向通量是指CH4在濕地內與濕地外橫向輸送通量, 本文中從濕地內向外輸出為正方向.
1.4.1 CH4氣體溶存濃度和瞬時通量計算
CH4氣體水-氣界面擴散通量使用擴散模型法計算[31]:
式 (1) 中:Fv為單位時間內溫室氣體CH4水-氣界面氣體交換通量 (nmol·m–2·s–1);Kw為氣體在水氣界面逆濃度梯度擴散速率 (m·s–1), 是氣體施密特數 (Schmidt number,Sc) 和風速的函數;Cobs指水體中CH4的溶存濃度 (μmol·L–1);Ceq指采樣現場大氣平衡時CH4氣體濃度 (μmol·L–1), 數據來自于通量塔.
Cobs的計算公式如下:
式 (2) 中:C0指平衡后溫室氣體濃度 (μmol·L–1), 即氣相色譜儀 (gas chromatograph, GC) 所測定的氣態CH4濃度值;β為體積分數表示的氣體溶解度 (L·L–1·Pa–1), 可以根據Henry定律求得[15,32];R為理想氣體狀態常數;Tobs為平衡過程中的實際水溫 (K);V0是平衡氣室氣體體積 (mL);V1是水樣體積(mL).
氣態CH4的Sc數計算如下[33].
西沙:
九段沙:
式 (3)—(4) 中:T為水體溫度 (℃); 西沙水體CH4的Sc數計算公式為淡水條件下的計算公式; 研究顯示Sc數受鹽度影響極小[33], 所以九段沙水體CH4的Sc數計算公式使用海水條件下的計算公式.
本文所選樣地潮溝水深較淺且風速較小,Kw的計算公式[34]如下:
式 (5) 中:U10為樣地水面上方10 m處的風速 (m·s–1), 數據來自研究區的通量觀測塔.
溶解態CH4濕地內外水平輸送通量計算公式如下:
式 (6) 中:FL為單位時間內, 溶解態CH4在濕地內外交換產生的水平輸送通量 (μmol·m–2·s–1);Q為水流量 (m3·s–1);S為潮溝流域面積 (m2), 九段沙和西沙潮溝流域面積見1.1節.
1.4.2 CH4氣體平均通量計算對比
九段沙和西沙水體CH4垂向擴散和橫向輸送通量分別用3種方法計算并對比. 方法1使用間隔采樣數據計算得到的水體中CH4溶存濃度; 方法2使用CH4原位連續觀測系統測定的高頻溶解態CH4溶存濃度, 并用間隔采樣數據進行矯正; 方法3通過建立間隔采樣數據與水質參數的多元回歸模型, 獲得CH4溶存濃度的高頻率估算結果. 多元回歸模型建立的步驟如下: ① 分別計算各環境因子與間隔采樣所得CH4溶存濃度的相關性; ② 根據相關性系數由大到小的順序, 依次探究CH4溶存濃度和環境參數的擬合曲線類型, 根據擬合系數的大小確定單一環境參數的擬合形式; ③ 依次疊加環境參數個數, 建立CH4溶存濃度與環境參數相應的曲線擬合形式的多元回歸模型使用、赤池信息值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value, AIC) 和均方根誤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 確定最終回歸方程,越大, AIC和RMSE越小, 說明擬合程度越好. 按此步驟建立的不同研究區域的多元回歸模型如下.
九段沙:
式(7)中:XpH為水體pH值;XDepth為水位高度值;V為水體流速值;XDO為水體溶解氧濃度值. 九段沙中水體CH4溶存濃度估算的標準誤差為 ±0.01 μmol·L–1. 回歸方程估算所得水體CH4溶存濃度的殘差值滿足正態分布 (Shapiro-Wilk test,p>0.05), 且殘差平均值為0, 即回歸方程滿足擬合要求.
西沙:
式(8)中:XFDOM為水體熒光溶解有機物(fluorescent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FDOM)值. 西沙中水體CH4溶存濃度估算的標準誤差為 ±0.06 μmol·L–1. 回歸方程估算所得水體CH4溶存濃度的殘差值滿足正態分布 (Shapiro-Wilk test,p>0.05), 且殘差平均值為0, 回歸方程也滿足擬合要求.
水體中CH4橫向輸送通量計算公式如下:
式 (9) 中:FLat為水體中CH4日平均橫向輸送通量 (mg·m–2·d–1);M為CH4的相對分子質量 (g·mol–1);t為研究時間 (s);T為研究天數 (d).
水體中CH4垂向擴散通量計算公式如下:
式 (10) 中:FVer為水體中CH4日平均垂向擴散通量 (mg·m–2·d–1).
2 結果
2.1 水環境參數變化特征
研究期間, 九段沙和西沙的水體環境參數的時空變化如表2所示. 九段沙和西沙的水溫都有顯著的季節變化 (Kruskal-Wallis test,p<0.001), 夏季水溫最高, 平均水溫分別為 (28.63±1.25)℃和(25.90±2.22)℃; 冬季水溫最低. 九段沙和西沙水體的DO濃度也存在冬季高、夏季低的特征. 夏、秋兩季為長江流域豐水季, 九段沙受長江淡水影響增強[35], 鹽度降低. 研究期間, 秋季九段沙水體的平均鹽度最低, 為 (0.57±0.76)‰; 而冬季為長江流域的枯水期, 九段沙主要受海水控制[35], 平均鹽度為(10.36±2.97)‰. 西沙是典型的淡水潮汐濕地, 采樣期間鹽度低于0.50‰. 九段沙和西沙水體的鹽度差異與濕地的地理位置有關: 九段沙地處長江口外南北槽之間的攔門沙河段, 受海水和長江沖淡水共同影響, 西沙地處長江口的一級分汊口, 主要受長江沖淡水影響. 研究期間, 水體葉綠素a濃度在夏、秋兩季較高, 在春、冬兩季較低. 除此之外, 九段沙和西沙水體的營養鹽和濃度也存在季節差異. 九段沙水體的平均濃度冬季最高, 而西沙的平均濃度在冬季和春季都較高. 觀測期間, 九段沙和西沙水體的平均濃度不足的1%. 九段沙水體的濃度在冬季最高, 春、秋兩季降低. 西沙水體的濃度春季最高, 秋季最低. 九段沙和西沙水體的濃度均在冬季最高, 而在夏、秋兩季較低.濃度的變化一方面與海水的影響有關, 在冬季, 海水侵入九段沙和西沙引起水體濃度增加; 另一方面, 冬季植被凋零, 土壤表面的腐殖質層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分解產生大量的[36].

表2 九段沙和西沙采樣點的基礎水環境特征的平均值和標準偏差Tab. 2 Mean±standard deviation for water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in sampling sites, JDS and XS wetlands
2.2 水體CH4溶存濃度的潮周期和季節變化
研究期間, 九段沙和西沙的CH4溶存濃度變化特征如圖2所示. 潮周期內, 水體CH4溶存濃度與水位變化相反: 漲潮開始時, CH4溶存濃度較小; 水位升高, CH4溶存濃度緩慢下降; 落潮初期,CH4溶存濃度降到最低; 水位下降, CH4溶存濃度逐漸上升; 落潮結束時, 達到CH4溶存濃度的最高值. 采樣期間, 秋季的九段沙水體的CH4平均溶存濃度最高, 為 (0.30±0.19) μmol·L–1, 春季最低; 夏季的西沙水體CH4平均溶存濃度最高, 為 (1.16±1.52) μmol·L–1, 冬季最低. 九段沙和西沙水體的CH4溶存濃度在潮周期內的變化范圍也存在季節差異: 采樣期間, 九段沙和西沙的CH4溶存濃度在潮周期內的變化范圍均在夏季最大, 分別為0.06 ~ 0.91 μmol·L–1和0.19 ~ 6.17 μmol·L–1.

圖2 九段沙和西沙的水深及CH4溶存濃度的變化Fig. 2 Water depth and CH4 concentration in the JDS and XS wetlands
2.3 水體CH4溶存濃度的影響因子
九段沙和西沙濕地水體中CH4溶存濃度受到復雜的環境因子影響, 且不同的環境因子之間也存在相互作用, 所以, 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探究影響濱海濕地水體CH4溶存濃度變化的主要因子 (圖3). 在PC1方向上, 九段沙和西沙PC1得分的季節變化顯著(p<0.05), 同時, 溫度的載荷與PC1方向接近平行. 因此, PC1可能與環境因子的季節變化有關. 在PC2方向上, 水位的載荷與PC2接近平行. 因此, PC2可能與濱海濕地的潮汐作用等水動力因素有關.在PC1方向上, 九段沙得分的變化范圍 (–3.14 ~ 4.20) 大于西沙 (–2.52 ~ 0.67), 推測九段沙主要受到環境因子季節變化的影響. 而在PC2方向上, 西沙得分的變化范圍 (–0.88 ~ 4.22) 大于九段沙 (–2.31 ~0.95), 推測潮汐作用是西沙的主要影響因子. 影響水體CH4溶存濃度變化的季節因素主要包括水溫、鹽度和濃度; 與影響水體CH4溶存濃度變化的潮汐變化顯著相關的環境因子包括水位、DO濃度和pH值. 在主成分分析模型中, PC1和PC2僅占總方差的63.7%, 因此, 影響水體CH4溶存濃度變化的因子十分復雜. 在九段沙和西沙, 硝酸鹽對CH4溶存濃度的影響可能十分有限,濃度與CH4溶存濃度相關性較小 (R=–0.16,p<0.01).

圖3 九段沙和西沙的水體環境因子主成分分析圖Fig. 3 Biplot from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based on wat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JDS and XS wetlands
2.4 溶解態CH4通量潮周期和季節變化
單位時間內, 溶解態CH4通量包括CH4水氣界面交換通量 (FV) 及水平輸送通量 (FL). CH4水氣界面交換通量在九段沙和西沙濕地內有顯著的季節變化 (Kruskal-Wallis test,p<0.001) (圖4). 潮周期內, CH4氣體水氣界面交換通量與潮汐作用有關: 漲潮開始時, CH4交換通量較小, 水位升高,CH4交換通量緩慢下降; 落潮初期, CH4交換通量下降至最低, 水位下降, CH4交換通量快速上升; 落潮結束時, CH4交換通量達到最高值. 采樣期間, 九段沙和西沙濕地的CH4水氣界面平均交換通量分別在秋季和夏季最高, 水體向大氣擴散的CH4通量分別為 (0.45±0.43) 和 (3.34±5.21) nmol·m–2·s–1;九段沙和西沙濕地的CH4水氣界面平均交換通量分別在春季和冬季最低. 九段沙和西沙濕地的CH4水氣界面交換通量在潮周期內的變化范圍均在夏季最大, 分別為 –0.20 ~ 5.08 nmol·m–2·s–1和0.10 ~ 20.83 nmol·m–2·s–1, 冬季最小.

圖4 九段沙和西沙水體中CH4水氣界面交換通量、水平輸送通量及水深的變化Fig. 4 CH4 water-to-air interface exchange flux, CH4 lateral-transport flux, and water depth in JDS and XS wetlands
潮周期內, 漲潮開始時, 溶解態CH4隨著水流從濕地外向濕地內流入, 輸送通量隨水位升高先增加后減小; 落潮開始時, 溶解態CH4水平輸送變為從濕地內向濕地外輸送, 輸送通量隨水位降低先增加后減小. 采樣期間, CH4水平輸送通量也存在顯著的季節變化 (Kruskal-Wallis test,p<0.001). 秋季,九段沙濕地水體CH4平均水平輸送通量最高, 為 (2.32±9.32) nmol·m–2·s–1; 夏季, 西沙濕地水體CH4平均水平輸送通量最高, 為 (1.66±5.06) nmol·m–2·s–1. 九段沙和西沙濕地水體CH4平均水平輸送通量分別在春季 ( (0.03±0.23) nmol·m–2·s–1) 和秋季 ( (0.28±1.21) nmol·m–2·s–1) 最低.
2.5 水體溶解態CH4垂向擴散和橫向輸送通量對比
濱海濕地溶解態CH4通量包括水氣界面的垂向擴散通量 (FVer) 和濕地內外水體的橫向輸送通量(FLat), 對于估算濱海濕地CH4排放量有重要意義. 由于傳統采樣方法頻率較低, 溶解態CH4通量的估算存在較大誤差. 因此, 需要采用原位高頻率連續觀測技術提高通量的估算精度. 濱海濕地水體濁度極高, 水動力變化復雜, 給溶解態CH4濃度的長期直接觀測帶來諸多困難. 因此, 本文結合了短期直接觀測與長期間接觀測方法計算溶解態CH4的橫向輸送通量, 并進行對比分析, 最終獲得可靠的溶解態CH4濃度長期、高頻率原位觀測結果.
使用3種不同的方法 (詳見1.4.2節) 估算了采樣期間溶解態CH4橫向輸送通量的大小 (表3). 利用方法1、2和3得到的CH4溶存濃度來計算CH4橫向輸送通量, 通量分布無顯著差異 (Kruskal-Wallis test,p>0.05), 表明兩種原位觀測技術 (方法2和3) 的結果準確. 與方法1相比, 方法2也可以對CH4溶存濃度直接觀測, 但頻率顯著提升, 可以提高估算精度. 方法2和3均為CH4溶存濃度原位連續觀測技術, 盡管方法3是基于多元回歸擬合模型的CH4溶存濃度間接觀測, 但是估算結果與方法2估算結果分布無顯著差異 (Kruskal-Wallis test,p>0.05). 在九段沙和西沙濕地, 運用方法3建立的回歸方程估算精度分別為 ±0.03 μmol·L–1和 ±0.19 μmol·L–1, 同時, 方法3設備簡潔, 對布設環境要求低; 觀測過程不易受到水位和濁度等干擾, 有利于長期連續觀測, 容易推廣. 因此, 本文使用方法3獲得的CH4溶存濃度的長期連續觀測結果來探究濱海濕地溶解態CH4垂向擴散和橫向輸送通量的變化.

表3 使用不同采樣方法計算九段沙和西沙濕地水體CH4水平輸送通量結果 (僅間隔采樣期間)Tab. 3 Lateral flux of CH4 calculated by different methods in JDS and XS wetlands during the interval sampling period
利用高頻率的溶解態CH4濃度和水體流量數據, 計算得到九段沙和西沙溶解態CH4不同季節的橫向輸送通量. 九段沙和西沙溶解態CH4橫向輸送通量存在季節變化, 夏季較高, 冬季較低. 夏、秋兩季, 水體CH4溶存濃度顯上升 (圖2), 同時, 長江流域進入豐水期, 漲落潮期間濕地水流量增加. 在水平輸送方向, 九段沙為CH4的源, 但是在冬、春兩季, 西沙有少量河口內的溶解態CH4輸入. 九段沙和西沙溶解態CH4年均橫向輸送通量分別為1.46 mg·m–2·d–1和0.34 mg·m–2·d–1. 利用高頻率的溶解態CH4濃度、大氣中CH4濃度、風速和水溫數據, 估算得到九段沙和西沙溶解態CH4垂向擴散通量結果. 九段沙在夏季的CH4垂向擴散通量最高, 水體向大氣擴散的CH4通量為6.58 mg·m–2·d–1; 春季的CH4垂向擴散通量最低, 水體吸收大氣中CH4的通量為0.07 mg·m–2·d–1. 西沙水體中溶解態CH4是大氣CH4的源, 其中, 冬季的CH4垂向擴散通量最高, 為10.06 mg·m–2·d–1. 九段沙和西沙溶解態CH4年均垂向擴散通量分別為1.85 mg·m–2·d–1和2.90 mg·m–2·d–1.
3 討論與分析
3.1 濱海濕地水體中CH4溶存濃度的影響因素
濱海濕地水體CH4溶存濃度變化受多種環境因子的共同作用, 如水溫、鹽度、濃度、水位、DO濃度和葉綠素a等. 產甲烷菌合成CH4的速率對溫度變化有很大的依賴性[37-38], 水溫增加時, 微生物活動旺盛, 水體中CH4溶存濃度增加. Harley等[39]研究泰河河口水體CH4溶存濃度的季節變化時發現, 其季節變化明顯, 最大值出現在夏季, 這與本文研究區域水體CH4溶存濃度季節變化特征相近.除此之外, 產甲烷菌等生產甲烷的速率會受到鹽度[40]、硫酸鹽[41-42]的限制, 鹽度極高時, CH4的產量甚至可以忽略不計[43]. 本文中, 冬季的九段沙濕地受到鹽度較高的水體周期性淹沒, 土壤中電子受體增加, 產甲烷菌在競爭底物時處于劣勢, 影響CH4生成; 夏季的九段沙濕地受到長江沖淡水的影響, 水體中與產甲烷菌存在競爭關系的電子受體也減少, 有利于CH4產生. Bartlett等[44]對不同鹽度梯度鹽沼濕地CH4排放研究表明, 孔隙水中CH4濃度與濃度呈負相關, 產甲烷菌在與硫酸鹽競爭電子供體H2時, 處于劣勢地位, 所以抑制CH4的產生[45]. 冬季的九段沙濃度全年最高, 進一步抑制土壤中產甲烷菌合成CH4的效率.
潮汐作用也會影響濱海濕地水體中CH4溶存濃度, 與潮汐變化顯著相關的環境因子包括水位和DO濃度. 漲潮前, 潮溝暴露在空氣中, 土壤中水分含量低, 氧氣飽和量高, 抑制產甲烷菌合成CH4[46],已經合成的CH4也易氧化[47]. 仝川等[48]在對閩江口蘆葦濕地通量測定時發現, 氧化還原電位降低, 更有利于CH4的產生. 退潮時, 土壤中水分飽和, 產甲烷菌在厭氧狀態下迅速合成CH4, CH4溶存濃度上升. 賀文君等[11]在研究黃河三角洲鹽沼濕地甲烷排放時推測, 退潮時, 由于土壤所承受的靜水壓降低[12], 土壤中產生的CH4能夠快速溶解到水中, 也會引起水體CH4溶存濃度升高.
水體中浮游生物也會影響水體CH4溶存濃度. 祝棟林[49]在探究太湖和玄武湖的CH4產生、釋放及影響機制中發現, 水體中浮游植物的增加會加劇水體缺氧, 提高產甲烷菌合成CH4的速率. 與濕地水體相比, 湖泊 (尤其是富營養化比較嚴重的水體) 中CH4溶存濃度受葉綠素a的影響更大[50]. 人為活動可能也會對溶解態CH4合成有間接影響. 王東啟等[51]在對上海市河網CH4溶存濃度和排放研究中發現, 上海松江區河流CH4溶存濃度和飽和度均高于崇明區. 松江區人為影響較大, 居民用水和工業廢水排放造成水體富營養化嚴重, 藻類大量繁殖形成的厭氧環境有利于CH4的合成. 因此, 九段沙和西沙濕地水體CH4溶存濃度變化特征是多種環境因子共同作用的結果, 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3.2 水生態系統溶解態CH4垂向擴散通量對比
水生態系統溶解態CH4垂向擴散通量是大氣CH4的重要來源之一, 不同水生態系統CH4垂向擴散通量不同, 如表4所示, 水環境中溶解態CH4垂向擴散通量大小為: 開闊大洋 < 陸架區 < 河口區 <濱海濕地 < 湖泊 < 河流. 本文中的濱海濕地土壤中微生物活動旺盛, CH4來源豐富, 因此, 濕地水體CH4垂直擴散通量高于河口及沿岸海域. 在河口內, 由淡水端元到海水端元, 溶解態CH4垂向擴散通量會減少約兩個數量級[52].

表4 不同類型生態系統CH4垂向擴散通量比較Tab. 4 Comparison of CH4 vertical diffusive fluxes in different ecosystems
溶解態CH4垂向擴散通量在不同水生態系統之間的差異主要受到CH4來源的影響. 一般認為,微生物產生的CH4是開闊大洋表層水溶解態CH4的主要來源[62]. 而在陸架海中, 高飽和度CH4河水的流入也是水體溶解態CH4的重要來源[63]. 河流營養物質含量高, 且水位較淺, 大部分顆粒有機物還未分解便已經進入沉積物中, 形成富含有機物的河流底質, 產甲烷菌生產CH4的能力增強. 根據Rhee等[53]在大西洋、馬立杰和崔迎春[54]在南海中部和北部的研究, 發現開闊大洋和陸架海水體表層CH4垂向擴散通量均低于河流, 如亞德亞河[60]、亞馬遜河[61]及上海市內河網[51]等. 濱海濕地水體位于海陸交界地帶, 土壤有機物來源豐富, 產甲烷菌活動旺盛, 部分區域還會受到河流水體的影響. 因此,濱海濕地水體是大氣CH4的源[64]. 濱海濕地溶解態CH4垂向擴散通量遠高于河口、沿岸海域及開闊大洋 (表4). 但是, 受到河口區鹽度以及產甲烷菌可利用底物的限制, 濱海濕地溶解態CH4垂向擴散低于河流及湖泊. 此外, 人類活動也會增加水環境向大氣中擴散的溶解態CH4通量. 工業和生活污水含有大量有機質和營養鹽, 會促進微生物的代謝活動, 增加了湖泊與河流的CH4垂向擴散通量. 人類活動干擾強度大的水體, 如上海市內河流[51]和亞德亞河[60], CH4垂向擴散通量高于人類活動影響較小的河流, 如亞馬遜河及其支流[61]. 因此, 有效的水環境治理工程 (處理工業和生活污水、改善水體富營養化、河道清淤等) 對減緩水體中CH4的排放具有潛在的意義.
4 結論
(1) 九段沙濕地和西沙濕地水體CH4溶存濃度、水-氣界面交換通量和橫向輸送通量在潮周期和季節尺度內均有顯著的變化.
(2) 利用主成分分析發現, 濕地的季節更替與潮汐作用是引起CH4溶存濃度變化的主要影響因子, 低溫、高鹽度和富氧環境都將抑制CH4的合成.
(3) 利用水質參數與CH4溶存濃度多元擬合回歸方程獲得高頻率、連續觀測的CH4溶存濃度, 進一步計算得到九段沙和西沙濕地溶解態CH4年均橫向輸送通量分別為1.46 mg·m–2·d–1和0.34 mg·m–2·d–1,年均垂向擴散通量分別為1.85 mg·m–2·d–1和2.90 mg·m–2·d–1. 此方法有效提高了CH4通量的估算精度, 并揭示了濱海濕地溶解態CH4是大氣和沿岸水體CH4的來源之一, 為CH4排放的相關研究提供數據支持和理論依據.
致謝感謝崇明生態研究院、崇明西沙濕地研究站和上海市九段沙濕地國家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對本實驗提供的采樣和儀器布放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