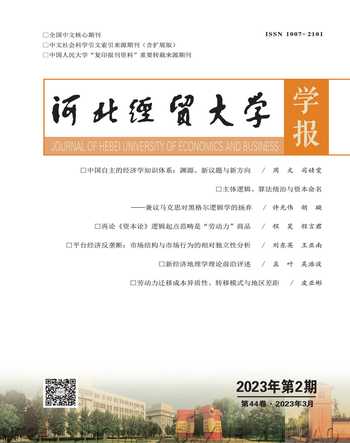勞動力遷移成本異質性、轉移模式與地區差距



摘 要:通過建立一個包含地區效率差異和勞動力遷移成本的兩部門兩地區模型,研究存在農村剩余勞動力時,產業轉移、勞動力轉移的福利效應及對地區收入差距的影響。 研究發現:縮小地區效率差異以促進產業轉移,或降低遷移成本以促進勞動力流動,都可以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并提高經濟總體產出;由于勞動力遷移成本異質性,低遷移成本勞動力偏好產業轉移,而高遷移成本勞動力偏好勞動力轉移政策,因而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兩類政策不能相互替代;當工業化水平提升或地區效率差異擴大導致勞動力流動需求增加時,如果不進一步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地區間收入差距會擴大,從而形成勞動力遷移與地區差距擴大同時發生的“謎題”。 為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流動兩類思路并不存在內在邏輯沖突,不應將二者對立,需要采取降低勞動力遷移成本和提高欠發達地區發展潛力相結合的措施。
關鍵詞:產業轉移;勞動力轉移;遷移成本;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F249. 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23)02-0078-10
收稿日期:2022-03-15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產業關聯與空間外溢雙重視角下的區域產業結構演進及機制研究”(71903072)
作者簡介:皮亞彬(1988-),男,河南太康人,廣東工業大學講師,博士。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但產業與人口空間分布不均衡的問題也日漸凸顯,城鄉間和區域間居民收入差距持續存在。 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與地區間收入差距,不僅取決于地區間生產率存在差異,也取決于勞動力在地區間遷移的成本。 在勞動力和產業分布達到空間均衡時,將產生兩種可能的結果:當勞動力在地區間自由遷移時,勞動力會向發達地區集聚,這種空間“套利”機制最終將導致自由遷移的勞動力在地區間的實際福利無差異;而當勞動力跨地區遷移存在障礙時,將導致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勞動力工資和實際福利的差異,而經濟集聚水平則低于勞動力完全自由流動的情形。 要解決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產業空間分布與人口空間分布不平衡的問題,需要從理論層面明晰決定產業和勞動力空間分布的基本經濟機制,并基于此選擇適宜的區域協調發展策略。
地區之間生產率差異,一方面來源于區位條件或資源稟賦優勢等外生因素,另一方面來源于內生的集聚效應,發達地區企業和勞動力能夠通過分享、匹配和學習機制獲得更高的效率 [1-2] 。 由于地區間效率差異,企業自發的產業轉移難以發生,而政府為了推動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所實施的一系列地區導向的政策可能是高成本、低效率的 [3] 。 勞動力的遷移決策受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的共同影響 [4-6] ,勞動力是否跨地區遷移取決于勞動力個體對地區間的工資差異和遷移成本的權衡。 我國勞動力跨地區遷移過程中仍存在較高的制度成本,從而導致勞動力難以通過跨地區轉移進行工資“套利”來縮小地區收入差距 [7-8] 。基于上述理論思路,為解決勞動力和產業空間分布不平衡以及地區收入差距問題,基本的政策思路可分為兩種:一是通過提高欠發達地區勞動生產率或優惠政策,吸引發達地區的產業資本轉移到勞動力豐富的欠發達地區,即推動產業向欠發達地區轉移;二是通過消除戶籍等限制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促進勞動力從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并獲得更高的收入,實現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即以降低勞動力跨地區遷移成本的空間中性政策 [9-12] 。 相關實證研究顯示,消除勞動力遷移摩擦會導致大規模的人口重新配置,并帶來顯著的福利增進效應 [13-15] 。 勞動力流動完全消除地區收入差距的理論前提是勞動力在地區間遷移成本為零,從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的流動所產生的套利機制將使勞動力在地區間的實際收入相等 [16] 。 但由于還存在其他類型的遷移成本,即使在最完善的制度安排下,勞動力遷移成本也不可能下降到零。 根據 Partridge 等的研究,即使勞動力流動性遠高于其他國家的美國,其勞動力轉移規模也低于空間均衡模型的預測 [11] 。
在多數空間均衡模型中,部分研究假設勞動力可以在地區間無成本地自由流動,另一部分研究則假設勞動力無法在地區間流動 [17] 。 現實中的勞動力既不是完全自由流動的,也非完全不能流動,而是介于自由流動和完全不流動的中間狀態。 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通過將異質性勞動力遷移成本作為反映勞動力流動性的關鍵參數納入空間均衡模型是一種更接近現實的建模策略。如采用“冰山”型遷移成本系數,假設勞動力在城鄉遷移過程中產生一定比例的損耗 [18-19] ; 或將勞動力轉移成本表示為消費者對不同區位偏好差異的分布 [10] ;也有學者將勞動力轉移障礙納入消費者效用函數,遷移到外地導致其損失一定比例的效用 [5-6] 。
上述研究僅僅關注勞動力在地區間的遷移或城鄉間遷移的某一個側面,本文則將地區間遷移和城鄉間遷移這兩種遷移模式放在同一框架內進行考慮,同時分析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本地非農部門就業和轉移到異地非農部門就業兩種情形。 此外,已有文獻沒有明確地將制度因素引起的遷移成本與勞動力個體偏好導致的遷移成本區分開來,在分析勞動力遷移決策的異質性時,學術界較多關注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或社會資本差異對勞動力遷移決策的影響 [20-23] ,不同個體間遷移成本的差異則鮮有文獻進行考慮。
本文建立一個包含效率差異和異質性勞動力遷移成本的空間均衡模型,為分析經濟空間分布和地區收入差距提供一個簡潔的分析框架。 首先,在對勞動力轉移成本的設定方面,本模型著重考察了勞動力轉移成本的差異,并將勞動力遷移成本區分為制度障礙和個體因素,指出哪些勞動力會選擇就地轉移到本地工業部門,哪些勞動力會選擇跨地區轉移。 其次,不同于多數文獻僅僅分析勞動力從鄉村到城市或地區間遷移的某一側面,本文在同一框架內同時考慮了勞動力城鄉流動和跨地區流動,分析勞動力就地轉移規模和跨地區轉移規模的影響因素,進一步比較勞動力轉移和產業轉移的福利效應。
二、基本模型
受到戶籍制度及附著其上的社會福利體系的制約,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跨地區遷移的成本較高。 為更好地解釋我國東部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以及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問題,本文構建如下包含勞動力轉移成本和地區效率差異的空間均衡模型。 借鑒朱希偉的做法 [18] ,為了使模型簡便并突出關鍵變量間的相互作用機制,本文不考慮商品空間運輸成本,而重點考慮勞動力空間轉移成本及地區間生產效率存在差異,并基于此探討產業轉移與勞動力轉移的變化規律。 與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在剩余勞動力假設下進行相關分析,并考慮了勞動力遷移成本的異質性。 設經濟系統中存在工業和農業兩部門、發達和欠發達兩地區。設經濟發達地區已完成工業化,地區初始勞動力數量為 θ 0 ,且所有勞動力都進入工業部門工作。欠發達地區是傳統農業區,勞動力總量為 1-θ 0 ,其中,農民數量為 L A 。 當欠發達地區農業剩余勞動力進入工業部門時,根據地區工資差異和遷移成本,勞動力選擇就地轉移或異地轉移。
(一)消費者偏好
勞動力的效用受到商品消費和遷移決策的共同影響。 根據是否遷移,代表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可表示為:
其中,M n 為代表性消費者對工業品組合的消費,A n 為對農產品的消費量,μ 為消費者對工業品消費的支出比重,μ 反映經濟系統的工業化水平。由于面臨制度、社會習俗、情感、距離等因素產生的障礙,勞動力跨地區遷移過程中存在著非經濟成本。 當消費者沒有跨地區流動時,其效用僅取決于對產品的消費量;當消費者跨地區遷移時,會產生一定的福利損失,其效用還取決于遷移自由度 γ n ≥1。 γ n 值越小,表明勞動力遷移的成本越高,當 γ n =1 時,表示勞動力可以在地區間自由遷移。 欠發達地區勞動力通過選擇就業區位來實現效用最大化,當除去遷移成本之后勞動力在發達地區獲得的效用大于其留在當地的效用,則欠發達地區勞動力選擇遷移到發達地區。
(二)工業部門
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企業效率差異反映在企業的生產成本函數上,設生產同等數量的工業品,欠發達地區消耗的勞動力數量是發達地區 ρ倍(ρ≥1)。 地區間人均產出的差異不僅來自于勞動力自身的稟賦差異,更是由所在地區的經濟社會條件所決定。 地區間的單位勞動力生產效率差異可能來自于地方資本積累、技術外部性、產業投入產出關聯、制度和社會組織方式、地區稟賦優勢等多種因素。 由于地區間的生產效率差異,盡管發達地區勞動力成本更高,企業仍會選擇發達地區進行生產。 企業生產技術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特征,代表性工業企業在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生產成本函數分別為:
其中,l ci為發達地區工業企業生產過程中所用勞動力數量,x ci為發達地區企業的工業品產出,α 表示發達地區企業的固定投入,β 為發達地區企業的邊際成本,即每增加 1 單位產出所需要增加的勞動力投入。 ρ≥1,表示欠發達地區工業生產的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欠發達地區企業生產同等數量的產品所需要投入的勞動力數量更多。 如果欠發達地區的“農民工”在本地工業中就業,則其所在企業的成本函數為 l pj ;若“農民工”流向發達地區的工業中就業,則其所在企業的成本函數為 l ci 。 ρ 值越大,表明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工業部門的生產率差異越大。
壟斷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由式(2) (3) 可知,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工業產品的出廠價格為:
其中,w c 為發達地區工人的工資水平。 在壟斷競爭市場上,廠商盈利或虧損時可自由進入或退出該行業,因而在均衡時壟斷廠商超額利潤為零。 則廠商的銷售收入等于廠商的總成本,即l ci wc=pci xci 。 根據式(3)和式(4),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廠商的生產規模為 α(σ-1) / β,則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各企業雇傭的勞動力數量分別為:
隨著產業和人口的區位調整,在工業部門空間分布達到均衡時,兩地區生產工業品價格相等,否則,企業繼續向生產成本低的地區轉移,記為p i =σβw c / (σ-1)。 則消費者面臨的工業品價格指數 P 可以簡化為:
其中,N 為工業品種類數。 由于 σ>1,則產品種類越多,P 值越小,消費者在總支出不變時獲得的福利水平越高。
(三)農業部門生產
假設農業生產只存在于經濟欠發達地區,且存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 農業部門勞動力總收入等于所有消費者對農產品總支出,則:
其中,w A 為欠發達地區農民的收入水平。 以農產品為價格標的物,設農產品價格 p A =1。 由于我國農業勞動力相對耕地資源過剩,只要農業人口大于某一門檻值,農業勞動力減少并不會導致農業總產出下降,假設耕地總量不變,則農業總產出與務農人數 L A 無關。 設農業總產出 A=1-μ,農業勞動力的平均收入為:
農業勞動力收入水平與其數量成反比,因而,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有助于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由于人地比率過高,我國農業勞動力生產率較低,轉移到工業部門就業的勞動力對留在農業部門的農民收益產生“外部性”。 在農村地區,土地流轉多是在村內親人和鄉鄰之間的非正式流轉,仍會提高留在農村的農業勞動力的人均產出和收入水平。 隨著欠發達地區農業部門勞動力流出,使勞動力流出地的人均農業資源(包括耕地、自然資源等)占有量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當土地要素不能在轉移勞動力和農民之間自由流轉時,留在農村的農民的人均耕地和收入相對更低,更接近于劉易斯模型所假設的情形。
(四)勞動力收入與就業區位選擇
設經濟發達地區當地勞動力數量為 θ 0 ,欠發達地區在農業部門就業的農民數量為 L A 。 假定從欠發達地區農業部門轉移到本地工業部門的“農民工”數量為 θ 1 ,轉移到異地工業部門的“農民工”數量為 θ 2 。 不失一般性,設全國勞動力的總量為 1,即 L A+θ0+θ1+θ2 = 1。 假設在初始時期,所有工業部門集中在發達地區,且 μ>θ 0 ,則工業部門勞動力的人均收入高于農業部門。
假設勞動力在地區內部不同部門間自由流動,則在欠發達地區內部,農業勞動力收入與工業部門收入相同:
當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同時存在時,工業企業在地區間的平均生產成本相等,由于地區之間效率差異為 ρ,欠發達地區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工資相當于發達地區的 1/ ρ,根據式(4),地區之間工業工資關系滿足:
在市場出清的前提下,工業部門勞動力獲得的總收入等于消費者對工業部門總支出,即(θ 0 +θ 2 )w c+θ1 wp =μ,則發達地區工業部門工資為:
(五)勞動力的遷移決策
假設勞動力轉移成本存在差異,流動成本最低的勞動力最先轉移,其后每一個新增的轉移勞動力的遷移成本都高于已完成遷移者。 將欠發達地區勞動力的個體轉移成本從低到高排序,為了簡便,不妨假設欠發達地區勞動力的個體遷移成本總體上服從(0,1-θ 0 )上的均勻分布。 設參數m≥1 反映了勞動力跨地區遷移的制度性成本,m值越大,表明勞動力跨地區轉移的制度障礙越大,m=1 時表示完全消除了所有勞動力遷移的制度性障礙,則在遷移次序 n 的勞動力總體遷移成本為 mθ n 。 與前文分析保持一致,設式(1)中勞動力n 的遷移自由度 γ n = 1-mθ n 。 由于異地轉移的勞動力數量為 θ 2 ,則處于轉移臨界點的勞動力轉移成本為 mθ 2 ,其遷移自由度:
轉移成本低于 mθ 2 的勞動力選擇跨地區轉移,轉移成本高于 mθ 2 的勞動力選擇在本地就業。根據 ρ 和 γ ? 的值,勞動力轉移模式有三種可能的情形:情形一:既存在就地轉移、也存在異地轉移的情形,此時 θ 1 >0 且 θ 2 >0;情形二:只存在異地轉移的情形,此時 θ 1 =0 且 θ 2 >0;情形三:只有就地轉移的情形,此時 θ 1 >0 且 θ 2 =0。 由于假設遷移成本最低的勞動力遷移成本為 0,則至少存在一個跨地區流動的勞動力,情形三不成立。 當均衡時,如果轉移臨界點的勞動力遷移自由度 γ ? >1/ ρ,則情形二成立;如果轉移臨界點的勞動力遷移自由度γ ? =1/ ρ,則情形一成立。 情形一和情形二適用于不同的空間尺度。 隨著考察的空間單元不同,ρ 和m 的值也有所不同。 比如,A 地區和 B 地區間效率差異、與 A 地區和 C 地區間的效率差異是不同的,勞動力向不同地區遷移的制度障礙也不同。情形一中,欠發達地區也存在工業部門,適用于分析區域間勞動力流動和區域間差距;而情形二中,欠發達地區工業部門完全沒有競爭力,此情形更適用于分析勞動力城鄉流動和城鄉差距。 本文下面兩節分別考慮情形一和情形二。
三、勞動力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同時存在的情形
(一)勞動力異地轉移規模及其影響因素
若 ρ 非常小,或 m 非常大時,均衡時 γ ? =1/ ρ,同時發生產業向欠發達地區轉移和勞動力跨地區轉移,勞動力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現象同時存在。按照流動成本從低到高,欠發達地區勞動力依次轉移到發達地區,直至處于轉移臨界點的勞動力在本地就業獲得的福利(w p P-μ)與其在發達地區獲得的福利(γ i w c P-μ) 相等,即 w p= γi wc 。 結合(10)式,則 γ i =1/ ρ。 當異地轉移勞動力數量為 θ 2時,可得 m 和 ρ 的關系式:
進而,將 θ 2 表示為 m 和 ρ 的形式,可得異地轉移勞動力的數量:
上式表明,異地轉移勞動力數量 θ 2 受地區間效率差異 ρ 和勞動力轉移成本系數 m 影響,易得:
勞動力跨地區遷移的制度障礙越大,異地轉移的勞動力數量越少。 而當 ρ 提高時,θ 2 隨之增加,表明當地區之間效率差異擴大時,跨地區轉移的勞動力數量增多;反之,隨著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效率差異縮小,異地轉移勞動力向欠發達地區回流。
(二)勞動力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同時存在的條件
根據(9)和(10),發達地區工業部門勞動力工資可表示為:
結合式(11)和(12),可得:
將 L A =1-θ 0-θ1-θ2 代入上式,將式(14)代入,得出就地轉移勞動力數量:
θ 1 表示在本地工業部門就業的勞動力數量,θ 1 值越大,表明產業向欠發達地區轉移的規模越大。 進一步考察分析地區間效率差異和勞動力遷移制度障礙變化對產業轉移規模和勞動力轉移規模的影響:ρ 越大,表示欠發達地區的勞動生產率越低;m 下降,表示勞動力轉移的制度性成本下降。
隨著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 m 持續下降,θ 1值隨之下降,在這一過程中,只產生勞動力和產業空間分布的變化,而地區收入差距僅受區域間工業部門生產率影響,保持不變。 θ 1 值下降為零時,達到情形一和情形二的臨界點。 令(19)式等于0,可得情形一和情形二達到臨界點時 m 取值與ρ、μ、θ 0 之間的關系:
上式說明,勞動力轉移模式和產業空間分布的具體情形取決于勞動力跨地區遷移成本、財稅政策、地區間效率差異、工業化水平和勞動力初始空間分布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響。 當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 m>m ? 時,勞動力和產業空間分布以及相應政策的效果符合情形一的分析;反之,當m0, ?m??ρ<0,表明工業化水平越高、發達地區初始勞動力數量越小、對欠發達地區的工業部門生產率越高,則 m ? 值越小,欠發達地區越容易出現工業部門,形成勞動力的就地轉移。
命題 1:當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 m>m ? 時,勞動力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同時存在,補貼欠發達地區企業的區位導向政策有利于產業向欠發達地區轉移,同時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 降低勞動力遷移的制度性障礙,只會導致勞動力和產業空間分布的變動,但不直接影響地區間收入差距。
(三)勞動力異地轉移規模及其影響因素
由于 0<μ<1,根據式(19),易得:
這表明隨著勞動力跨地區轉移的制度摩擦 m下降,異地轉移的勞動力數量增多,就地轉移的勞動力數量減少。 地區之間的效率差距越小,欠發達地區就地轉移的勞動力數量越多,異地轉移的勞動力數量越少。
命題 1:勞動力轉移規模和產業轉移規模受地區效率差異和遷移成本影響。 勞動力遷移的制度性障礙 m 越小,地區間效率差異 ρ 越小,異地轉移的勞動力人數越多;勞動力遷移的制度性障礙 m越大,地區間效率差異 ρ 越大,異地轉移的勞動力人數越少。
由于不同勞動力個體遷移成本存在差異,導致勞動力對轉移模式偏好的不一致。 只有遷移成本處于轉移臨界點的勞動力對經濟空間分布模式的偏好是無差異的。 對那些個體遷移成本高于臨界點的勞動力來說,他們傾向于選擇留在當地農業部門或就地轉移到本地區工業部門。 而對于遷移成本低于臨界點的勞動力來說,他們傾向于選擇跨地區轉移。
當 ρ 的取值不變時,降低或提高勞動力遷移的制度障礙,只影響勞動力和產業的空間分布,不影響地區間收入差距。 如果限制勞動力跨地區轉移,甚至為勞動力轉移設置障礙,固然有可能促進產業向欠發達地區轉移,實現地區間經濟總量的平衡,但并不能有效縮小地區間勞動力收入差距。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 通過限制勞動力轉移實現的地區經濟總量平衡,剝奪了欠發達地區勞動力通過跨地區遷移改善自身境遇的機會和權利,因而是不可取的。
命題 2:當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同時存在時,提高勞動力遷移的制度障礙,盡管可以縮小地區間經濟總量的差距,但并不能有效縮小地區間勞動力收入差距。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假設地區間效率差異是外生的。 事實上,如果考慮到集聚效應的存在,當更多的勞動力轉移到發達地區,發達地區的生產效率會有所提高,導致地區效率差異擴大。 此時,地區間勞動力收入差距會擴大。
(四)經濟系統總產出和社會福利分析
由于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農業總產出不變,經濟系統總產出取決于工業部門產出變化。 工業企業規模等于 α(σ-1) / β,則工業部門產出與企業數量 N 正相關。 根據式(5),當就地轉移勞動力數量為 θ 1 ,異地轉移勞動力數量為 θ 2 ,發達地區原住勞動力數量為 θ 0 時,工業部門企業總數量為:
隨著勞動力跨地區轉移的制度摩擦 m 下降,由于 ρ>1,工業企業數量變化情況滿足:
上式結果表明,隨著勞動力跨地區轉移制度摩擦的消除(m 值下降),工業企業總數量增加,根據(11)式,單位工業品的價格也隨之下降。 加之農業部門產出水平不變,這意味著通過破除束縛勞動力轉移的體制機制障礙,有利于提高經濟系統的總產出水平。 這種經濟整體效率提升來自勞動力資源在部門和空間上配置的優化,即勞動力從低收入部門向高收入部門、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的遷移。
考慮到勞動力的異質性遷移成本,當達到勞動力流動的空間均衡時,不同類型勞動力的福利水平并不相等(如圖 1 所示)。 這一結論與假設勞動力自由流動的經典空間均衡模型不同。 盡管異地轉移勞動力的工資收入與發達地區原住勞動力相等,但其實際福利水平低于發達地區原住居民。同時,由于個體轉移成本的差異,異地轉移勞動力之間的實際福利也存在差異,個體轉移成本越低的勞動力,實際福利水平越高。 而對留在農業部門和就地轉移到當地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其工資和福利水平都相當于發達地區原住勞動力的 1/ ρ(ρ>1)。 對于沒有跨地區轉移的勞動力來說,個體遷移成本的差異沒有導致未流動勞動力之間收入和福利差異。
降低勞動力跨地區遷移的制度障礙,重塑了勞動力和產業的空間分布。 這種經濟空間重塑對不同類型勞動力的福利影響如何呢? 本文從發達地區居民福利變化展開分析,并以此為基礎探討欠發達地區居民的福利變化。 發達地區居民福利變化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當存在產業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轉出時,會給發達地區勞動力的工資帶來下降的壓力,對發達地區勞動力的福利產生負向影響。 但另一方面,產業向欠發達地區轉移,欠發達地區勞動力可以就地轉移到工業部門,導致工業品種類增多,商品價格指數下降,這又對消費者福利產生正的影響。
根據式(11)和(21),發達地區原住勞動力工資可以表示為:
根據消費者面臨的工業品價格指數 P、農產品價格水平 p A ,消費者支出 Y=w c ,結合式(1)(2)(6)和(23),當滿足效用最大化條件時,發達地區勞動力的福利函數為:
由上式可得,當 μ>(σ-1) / σ 時,發達地區勞動力福利 W c 與工業企業總數量 N 成正比。 則根據公式(22)和(24),可得當 μ>(σ-1) / σ 時,?W c /?m<0,說明當消費者偏好工業品消費(或工業化水平非常高)時,降低勞動力流動障礙能夠提高發達地區勞動力福利。 當 μ<(σ-1) / σ 時,?W c / ?m>0,此時,發達地區勞動力面臨的競爭效應帶來的負面影響大于工業品價格指數下降帶來的正向效應。 當 μ>(σ-1) / σ 時,根據公式(18),農業勞動力和就地轉移勞動力的工資和福利也隨 m 下降而提高;遷移次序為 n 的異地轉移勞動力其福利水平為 γ n W c ,當 m 下降時 γ n 提高,則異地轉移勞動力福利也提高。 由此可得,當 μ>(σ-1) / σ 時,隨著勞動力跨地區遷移障礙 m 下降,所有類型勞動力的福利得到提高,產生帕累托改進。
命題 3:通過消除勞動力跨地區遷移障礙,經濟總產出增加;且當 μ>(σ-1) / σ 時,能夠實現所有類型勞動力福利的帕累托改進。
四、只存在勞動力異地轉移的情形
若 ρ 非常大,或 m 非常小時,處于臨界點的勞動力在欠發達地區組織生產工業品獲得的實際效益低于轉移到發達地區,即 γ ? >1/ ρ。 僅僅通過勞動力跨地區轉移就能達到 w A=γ? w c ,此時欠發達地區沒有工業生產活動,只存在勞動力的跨地區轉移,而沒有勞動力的就地轉移,即 θ 1 值為 0。 在這種情形下,此時的地區收入差距由 γ i 決定,γ i又由處于轉移臨界點的勞動力的遷移成本決定。
(一)跨地區轉移勞動力數量及其影響因素
由于處于轉移臨界值的工人(第 θ 2 個轉移的工人)留在家鄉務農和異地務工的實際效用相等,可得:
將工資表達式代入,并整理得 m 和 θ 2 關系式:
由上式易得:
這表明,當工業化水平提高時,跨地區轉移勞動力數量增加;當勞動力跨地區轉移制度障礙增加時,跨地區轉移勞動力數量下降。
進一步討論勞動力遷移制度障礙 m 下降對地區收入差距的影響。 結合式(25)和(26),地區間勞動力名義收入差距為:
易知,w c / w A 是 θ 2 的減函數,且?θ 2 / ?m<0,則w c / w A 隨著 m 值減少而減少。 因而,通過消除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障礙(降低 m 值),有利于地區間收入差距縮小。 保持 μ 不變,當 m 值下降時,流動成本處于臨界值附近勞動力發現流動成本下降,則轉移到發達地區的勞動力數量增加,農業勞動力工資上升為 w A ,工業部門勞動力工資下降為w c ,直到形成新的平衡 γ i w c = w A 。
命題4:當 γ ? >1/ ρ,隨著勞動力轉移制度障礙下降,勞動力異地轉移規模增加,且地區間收入差距縮小。
(二)勞動力轉移與地區收入差距關系的進一步探討
有研究指出,在一些國家存在勞動力轉移與地區收入差距擴大同時存在的“悖論”,應該如何理解這一現象呢? 本研究發現,勞動力轉移是否伴隨地區收入差距擴大,與引起勞動力轉移的因素有關。 當勞動力轉移是由于遷移制度障礙下降導致的,則地區收入差距縮小;而當勞動力轉移是由工業化水平提高等其他因素導致的,則可能伴隨著地區收入差距擴大。
當勞動力遷移的制度性障礙 m 不變時,由于?θ 2 / ?μ>0,隨著工業化水平 μ 提高,跨地區遷移勞動力數量 θ 2 隨之上升,根據式(21),這使地區間勞動力收入差距 w c / w A 擴大。 這是由于在 m 保持不變時,隨著低遷移成本的勞動力率先轉移到發達地區,轉移次序越后的勞動力個體遷移成本越高,發達地區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資來補償遷移成本。 工資的一部分是補償勞動力在農業部門的工資,另一部分則是彌補遷移成本。 出現勞動力轉移和地區收入差距擴大同時存在的情形,其原因是在一個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工業化水平的提高。 地區收入差距擴大和勞動力轉移都是工業化水平提高所引致的后果,不能將地區收入差距和勞動力轉移規模的這兩個變量相關關系視作因果關系。 不能因此而推斷勞動力轉移將帶來地區收入差距擴大,更不宜據此提出限制勞動力流動的政策。 事實上,如果工業化水平提高,如果限制勞動力跨地區轉移的話,地區間收入差距會更大。
當工業化水平提高導致地區間勞動力轉移規模和收入差距擴大時,不僅不能為了追求地區總量平衡而限制勞動力轉移,反而應該進一步消除勞動力轉移的制度障礙。 這樣才能真正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提升欠發達地區勞動力的福利。 現實中,工業化水平提高與勞動力轉移制度性障礙的清除可能是同時發生的,因而,勞動力轉移伴隨收入差距擴大還是縮小,取決于 m 值和 μ 值(反映遷移成本和工業化水平)的相對變化。 綜上,本文從一個新的視角闡明了勞動力跨地區轉移與地區收入差距變化之間的關系。
命題 5:勞動力轉移伴隨收入差距擴大還是縮小,取決于 m 值和 μ 值的變化。 當工業化水平提高時,勞動力跨地區流動規模增大,且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 在此情形下,只有進一步清除勞動力遷移的制度性障礙,才能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
(三)經濟總產出與福利分析
當異地轉移勞動力數量為 θ 2 ,發達地區原住勞動力數量為 θ 0 時,工業企業數量為:
隨著勞動力跨地區轉移的制度摩擦 m 下降,由于 ρ>1,工業企業數量變化情況滿足:
上式表明,隨著勞動力跨地區轉移制度摩擦的消除(m 值下降),工業企業總數量增加,工業品價格指數下降。 由此可得命題 6。
命題 6:在僅存在勞動力跨地區轉移的情形下,降低勞動力跨地區轉移的制度障礙,有利于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且提高經濟系統總產出,實現“均衡”與“效率”兼得。
下面討論隨著 m 下降,農業勞動力、異地轉移勞動力和發達地區原住勞動力的福利變化情況。由于農業勞動力工資 w A =(1-μ) / (1-θ 0-θ2 ),易得?w A / ?m<0。 則隨著勞動力跨地區轉移制度障礙消除,農業勞動力人數下降,農業工資上升。 又由(30)式,工業品價格指數下降,則隨著 m 下降,留在農業部門的勞動力福利提升。
根據式(24),僅存在勞動力異地轉移的情形下,發達地區勞動力的福利水平滿足:當 μ>(σ-1) / σ 時,?W c / ?m<0;當 μ<(σ-1) / σ 時,?W c / ?m>0。 因而,發達地區勞動力的福利變化取決于工業化水平和消費者對工業品多樣化的偏好情況。 μ>(σ-1) / σ 時,異地轉移勞動力的福利也隨 m 下降而提升。 在消費者對工業品支出比重較大、或非常偏好工業品多樣化的情形下,降低勞動力跨地區遷移的制度性障礙,有利于改進所有居民的福利。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在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內,根據勞動力流動制度障礙和地區間效率差異,從“公平” 和“效率”雙重視角分析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對區域協調發展的差異化作用機制。 研究發現,居民在地區間的收入差異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情況,取決于地區間生產效率差異以及勞動力在地區間的遷移成本。 當勞動力可以流動但存在遷移障礙時,勞動力通過遷移進行空間“套利”,均衡的條件是處在遷移臨界點的勞動力通過跨地區轉移獲得的福利增進等于其遷移成本。
本文將勞動力遷移的制度障礙和勞動力個體異質遷移成本同時納入模型,根據個體遷移成本的高低以及勞動力遷移的制度障礙,異質勞動力決定跨地區遷移的順序以及是否遷移。 拓展模型揭示了產業向欠發達地區轉移與勞動力跨地區遷移同時存在的經濟機理,并進一步考察了產業轉移規模和勞動力遷移規模的決定因素。 模型證明,勞動力轉移制度障礙越小,異地轉移的勞動力人數越多;地區之間效率差異越小,就地轉移的勞動力人數越多。 當勞動力遷移成本存在個體差異時,勞動力對經濟空間分布的偏好并不一致,個體遷移成本低的勞動力偏好促進勞動力轉移的政策,而個體遷移成本較高的勞動力則偏好促進產業轉移的政策。
本文的理論模型解釋了現實中觀察到的“勞動力遷移與地區差距擴大同時發生”的謎題。 隨著低遷移成本的勞動力率先流動到發達地區,遷移次序越后的勞動力個體遷移成本越高,發達地區企業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資來補償勞動力的遷移成本。 因而,企業支付給勞動力工資的一部分是補償勞動力在農業部門的工資,而另一部分則是彌補勞動力的跨地區遷移成本。 如果勞動力流動是由于遷移制度障礙下降導致的,則地區收入差距縮小;而如果勞動力流動是由工業化水平提高等其他因素導致的,則可能伴隨著地區收入差距擴大。 現實中,工業化水平提高與勞動力流動制度性障礙的清除可能是同時發生的,因而,勞動力流動伴隨收入差距擴大還是縮小,取決于遷移制度性成本和工業化水平的相對變化。
在進行區域平衡的政策分析時,不應局限于論證產業轉移與勞動力轉移哪一種情形更好,更應該將研究重點聚焦于如何通過進一步改革降低勞動力遷移的制度性障礙,以及如何縮小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技術差異。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應進一步創新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同時推動促進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措施,通過降低勞動力、技術、資本等要素在地區間和行業間轉移的制度性摩擦,優化資源空間配置效率,促進資本和信息在地區間的流通。
參考文獻:
[1]KRUGMAN P. First nature,second nature,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93,33(2): 129-144.
[2]DURANTON G,PUGA D.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M] / / HENDERSON J V,THISSE J. Handbook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Amster-dam:North Holland,2004:2063-2117.
[3]GLAESER E L,GOTTLIEB J D. The Economics of Place-Making Policies[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8(1):155-239.
[4] ZHAO Y.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9,47(4):767-782.
[5] BRYAN G, MORTEN M. The aggregate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internal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9,127(5):2229-2268.
[6]DESMET K,NAGY D K,ROSSI-HANSBERG E. The ge-ography of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8,126(3): 903-983.
[7]蔡昉. 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分析———解釋流動與差距同時擴大的悖論[J]. 經濟學動態,2005(1):35-39+112.
[8]白南生,李靖. 城市化與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問題研究[J]. 中國人口科學,2008(4):2-10+95.
[9]BARCA F,MCCANN P,RODR?GUEZ-POSE A. The case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place-based versus place-neutral approaches[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2,52(1): 134-152.
[10]KLINE P,MORETTI E. People,places,and public poli-cy: Some simple welfare economics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ams[J]. Annu. Rev. Econ. ,2014,6(1): 629-662.
[11]PARTRIDGE M D, RICKMAN D S, OLFERT M R, et al. When spatial equilibrium fails: Is place-based policy secondbest? [ J]. Regional Studies, 2015, 49 ( 8 ): 1303-1325.
[12]陸銘. 城市、區域和國家發展———空間政治經濟學的現在與未來[J]. 經濟學(季刊),2017(4):1499-1532.
[13]周文,趙方,楊飛,等. 土地流轉、戶籍制度改革與中國城市化:理論與模擬[J]. 經濟研究,2017(6):183-197.
[14]劉修巖,李松林. 房價、遷移摩擦與中國城市的規模分布———理論模型與結構式估計[J]. 經濟研究,2017(7):65-78.
[15]TOMBE T,ZHU X. Trade,migration,and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9,109(5): 1843-72.
[16] NEUMARK D, SIMPSON H. Place - based policies[M] / /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2015:1197-1287.
[17]REDDING S J. Goods trade,factor mobility and welfa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 101: 148-167.
[18]朱希偉. 偏好、技術與工業化[J]. 經濟研究,2004(11):96-106.
[19]張杰飛,李國平,柳思維. 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理論模型及政策分析:Harris-Todaro 與新經濟地理模型的綜合[J]. 世界經濟,2009(3):82-95.
[20]GANONG P,SHOAG D. Why has regional income con-vergence in the US declined?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7,102: 76-90.
[21]CARRINGTON W J,DETRAGIACHE E,VISHWANATH T. Migration with endogenous moving cos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 909-930.
[22] MORETTI E. Local labor markets[M] / /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2011: 1237 -1313.
[23]DIAMOND R. The determinants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US workers' diverging location choices by skill: 1980-2000[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6,106(3):479-524.
責任編輯:彭 青
Cost Heterogeneity, Transfer Mode and Regional Disparity of Labor Migration
Pi Yabin
(School of Econom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0, China)
Abstract:By establishing a two-sector and two-region model including regional efficiency difference and labor migration cos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welfare effect of industrial migra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regional income gap when there is rural surplus labor. It is found that narrowing the regional efficiency difference to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er, or reducing the mi-gration cost to promote labor mobility can both narrow the regional income gap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economic output. Because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labor migration costs, low-cost labor force prefers industrial migration, while high-cost labor force prefers labor migration policies, so the two policies of industrial migra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can't replace each other. When the demand for labor mobility increases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or the expansion of regional efficiency differences, if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labor mobility are not further eliminate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regions will widen, thus forming a "puzzle" in which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widening of regional gap occur simultaneously. In order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re is no inherent logical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ideas of promoting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labor mobili-ty. They should not be opposed to each other, an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the cost of labor migration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Key words:industrial transfer; labor force transfer; migration cos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