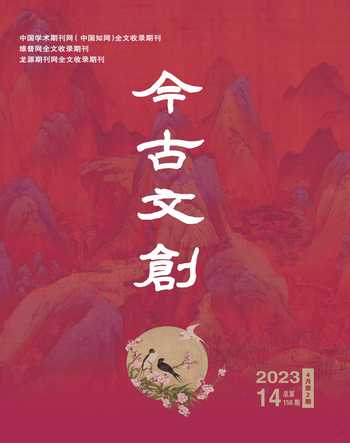“事”與“聲”:理解柳宗元村居詩之“鑰”
【摘要】 柳宗元貶謫期間的村居詩創作呈現出兩個主要特點:一方面,詩中的“人物速寫”繼承了柳宗元小品文的寫作特色,人物塑造成就突出;另一方面,詩中“聲音景觀”的運用頗為獨特,營造出五音繁會的湖湘風情“音樂會”。而“事”與“聲”背后隱藏的則是柳宗元貶謫期間孤獨苦悶而又凄涼彷徨的精神世界和心路歷程。
【關鍵詞】 柳宗元;村居詩;感事;聲音景觀;貶謫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4-001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4.003
柳宗元貶謫期間詩歌創作120余首,其中村居詩30余首。這些詩作繼承了《詩經》和陶、王、孟以來的田園詩創作傳統,在創作手法上又有創新。他將其小品文中的“感事性”融入詩歌,促進了詩歌人物形象的刻畫與敘事說理的表達,豐富的“聲音景觀”的運用也與傳統田園詩的創作迥然不同。村居詩中的“形”與“聲”,為我們打開了柳宗元謫居永州、柳州時的心靈之門。
一、感事與“速寫”
“感事”,顧名思義就是緣事而起、有感而發。柳宗元被貶永州與柳州期間,學習前人超脫世俗卻總不得,相反,卻使他對下層世俗社會與自身有了更深的了解。一方面,感事為“感他人之事”。貶謫期間,柳宗元與社會底層形形色色的人物交往甚厚,尤其對農民與官吏這一對立階級的認識頗為深刻,因此,在詩歌創作中感于二者不可調和的矛盾,通過對農民與官吏進行人物“速寫”,將其在詩歌中表現出來。另一方面,感事為“感自我之不平”。雖然遭受貶謫,使柳宗元與下層社會有了更多的接觸,但由于他的身世與經歷,他總是無法真正融入下層社會,總是像一個孤獨的旅人、過客一樣羈留于此,內心的抑郁不平之氣只有借詩歌才得以表達。
(一)鄉村人物與底層官吏的刻畫
柳宗元村居詩的語言總體呈現一種平易通俗、自然率真之感,在此基礎上的某些描寫卻又繼承了柳宗元小品文的語言特色,論說鞭辟入里、描寫深刻。在柳宗元村居詩中,著重塑造了兩種形象,一為質樸無華的農民,一為貪殘暴虐的官吏,二者又形成鮮明的對比,將作者的思想情感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柳宗元的筆下,農村生活是率性質樸的。“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 ①(《田家三首》其二),“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 ①(《田家三首》其三)。農民們白天努力勞作,男耕女織,傍晚則圍坐一起聊聊家長里短,田園純美風光與田家淳樸民風交融互輝,一派和諧融洽的社會風景。與此相反,柳宗元筆下的官吏則是殘酷不仁的。“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公門少推恕,鞭撲恣狼藉” ①(《田家三首》其二)。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柳宗元真實描繪了下層官吏貪殘暴虐、欺壓人民的丑惡嘴臉與無恥行徑。官吏肆意鞭打、恐嚇人民,以致底層人民的生活異常艱辛。所以在當時,農民只能“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 ①(《田家三首》其一),生怕延誤交租導致“鞭撲恣狼藉”“唯恐踵前跡” ①(《田家三首》其二)。柳宗元通過傳神的筆觸,慧眼獨具,通過農民與官吏這兩個對立階層,將當時的社會面貌以及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的處境直觀而又深刻地表現出來,讀來令人生悲。
(二)自我形象的刻畫
柳宗元是同情底層人民的。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農民的生活異常艱辛,對上要恭敬地侍奉殘酷不仁的官吏,對下要辛勤勞作保證一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再多苦痛只能自己承受,推己及人,柳宗元自己又何嘗不是這樣。柳宗元被貶之后,對上需要小心翼翼、謹言慎行,避免對立政治集團的打壓,對下要養活一家老小,生計艱難。一腔抑郁不平、踟躕愁苦之氣難以排遣,所以,除了在村居詩中塑造了眾多形象鮮明的下層農民與官吏之外,柳宗元更是將自己“主體客體化”,以“旅人”“孤客”的形象出現在詩中,以慰藉自己的孤獨愁思。“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聊從田父言,款曲陳此情” ②(《首春逢耕者》)。元和元年,詩人被貶到永州方一年,漫步田野,春耕就在眼前,農民都在辛勤勞作,而作者永州司馬卻是有名無實,無法在自己的事業上辛勤耕耘,就如同羈旅的囚徒一般,才情氣力不得伸展,只能向田翁訴說自我孤獨羈旅的愁懷。“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傖人不思還” ③(《聞黃鸝》),離家將近十年,歸家之途千山萬水、道路迢迢,“我”這孤獨的旅人被貶南荒,何時才能回到家鄉呢?《入黃溪聞猿》作于元和八年,柳宗元已被貶八年,他一方面探賞山水,埋頭研讀,著書立說,顯露出其平和豁達之態;另一方面始終沒有擺脫貶謫僻鄉的悲苦,內心深處總充滿著沒有得到朝廷任用的失落和怨憤,“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④借凄厲云云。“宦情羈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轉迷” ⑤(《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詩人剛剛遇赦回京,還未施展抱負便再次遭受貶謫,貶謫之地則是更為遙遠的柳州,柳州二月春天還未過半榕葉便遭受風雨摧殘以致凋落,令我感到凄迷,轉念回思,“我”這一仕途羈縻的罪臣貶謫之路也方才正半,等待“我”的也還將是榕葉全部凋零的凄寒深秋啊。孤獨之人的孤寂愁思,化主為客,將無力主宰命運、隨風浮沉的痛苦與無法直言,僅以客體代言的孤寂與悲憤宣泄出來,真切感人。
柳宗元詩歌中的“人物速寫”方法與其小品文中人物刻畫方式如出一轍,通過簡單的動作、語言、外貌、心理等描寫,寥寥幾筆就將人物形象鮮明的刻畫出來。《梓人傳》中,刻畫木匠的形象時只是描寫了他簡單的言語與動作,再加之與普通工匠的對比手法,一位技藝高超的木匠形象便躍然于紙上;《蝜蝂傳》中通過對蝜蝂行為特點的簡單刻畫傳達出對官吏貪得無厭的痛恨;《謫龍說》通過對龍女外貌、言語、神態的簡單刻畫,表現了龍女高潔的情操。在柳詩中,對農民與官吏的刻畫大多吸收柳文中動作與心理描寫。農民往往“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①(《田家三首》其一),通過速寫農民的勞作場景,刻畫農民的吃苦耐勞;“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①(《田家三首》其二),又通過速寫農民的心理狀態描寫農民對官吏的害怕與痛恨;“公門少推恕,鞭樸恣狼藉”,通過速寫官吏鞭笞人民的動作刻畫出官吏的暴虐,加之兩者之間鮮明的對比,兩個階層的人物形象便鮮活起來。而對自我形象的刻畫,則多借用柳文中心理描寫及隱喻的手法。“行人迷去住” ①(《田家三首》其三),行人長途跋涉,以致難以認路,實際隱含著的是作者對自己前途渺茫的擔憂;“眷然撫耒耜,回首煙云橫” ②(《首耕逢春者》),行人以手撫耒耜,悵然回想著平生的行跡,內心五味雜陳,誠可嘆也。旅人形象便鮮活起來,成為詩人的化身。詩文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促進,柳宗元的人物速寫法便在融文入詩中自成一格。
二、聲音景觀:元和年間的湖湘鄉村“音樂會”
相對于柳宗元的散文、游記、小品文等,其詩作尤其是村居詩這類寫景兼寫實的作品,一般不直接表現作者的思想情感,其情感往往通過獨特的聲音描寫表現出來。柳宗元的村居詩與中唐其他詩人的詩作呈現出迥異的面貌,原因之一就是聲音景觀的大量運用。聲音由物體振動而產生,是聽覺的對象。聲音景觀(簡稱“聲景”)則是人對聲音環境的感覺,是聽覺的結果,包含感知方式和聲音感受的表達方式,具有空間性和人文性。而這種景觀的運用一方面增加了作品的容量,深化了作品的內涵,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借各種聲音表達自己內心情思的獨特方式,拓展了作品的意境。柳宗元村居詩中聲音景觀的運用是對湖湘地區自然與社會的雙重深刻體驗,為我們展示了一場情感豐富的湖湘鄉村“音樂會”。
在柳宗元的村居詩中,多描寫能“發聲”的事物,如“雞鳴”“蟲鳴”“猿聲”“鳥鳴”“耒耜”聲、“烏鳶”聲、“風聲”“雨聲”“疏麻”迎風響動聲以及農民的嘆息聲、官吏的催逼聲等等,這些聲音無不向我們展示了一幅繪聲繪色的古代場景圖。在柳宗元的村居詩中,聲音景觀的運用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一)以聲景狀物
“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⑤(《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柳州的二月,一場風雨過后,百花凋零,榕葉也隨風紛紛落下,鶯聲也在枝丫間雜亂無章的響起,好像是在責怪風雨的無情。“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 ②(《首春逢耕者》),園林之中,各種鳥兒幽幽地唱個不停,林中一泓清泉徜徉而過,一片幽深靜謐的景色躍然紙上。“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 ⑥(《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半夜,輾轉反側,思鄉之情由然而起,起床出門望故鄉,遠處的泉水流過山石不斷激起清越的響聲,山谷之中還未入睡的鳥兒時不時地清啼,使人頓感山谷之清幽。
(二)以聲景寫事
不同的聲音相互串聯,使敘事更為清晰明暢。“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⑦(《夏初雨后尋愚溪》),時節入夏,一場幽幽的小雨過后,天氣已是又炎熱起來,循著彎彎曲曲的愚溪一邊聆聽清音,一邊悠然前進,路途之中歡快的歌聲由衷而出,走累了就坐下休息,暫以此來緩解夏日如火氣候帶來的不適。通過雨聲、溪聲以及歌聲將作者溪居生活的日常及對愚溪生活的自然閑適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 ①(《田家三首》其三),天就要黑了,此時的“旅客”卻還在外游蕩,與田翁親切交談,田翁笑著告訴“我”路途遙遠又崎嶇,而“我”也被田翁的笑聲感染,投宿其家。“投宿”一事在田翁的笑聲與兩人的交談聲中完成。
(三)以聲景抒情
《寄許京兆孟容書》 ⑧:“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柳宗元被貶南荒,才學氣力不得伸展,又不敢明面訴說自己的激憤以免再次被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只能借物之口來表達自己內心的一份幽怨情思,排解內心的“不平之氣”。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 ④(《入黃溪聞猿》),小溪蜿蜒曲折看不見盡頭,而猿聲卻時刻不斷地緊緊跟隨于我,叫聲凄厲,連綿不絕,猿啊你到底在哪里呢?不要再伴著“我”這孤獨寂寞之人再讓“我”獨自傷悲了。“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閉聲回翅歸務速,西林紫椹行當熟” ③(《聞黃鸝》),長時間聽子規的叫聲已使“我”倦怠,黃鸝忽然的鳴叫讓“我”倍感清新與哀婉,黃鸝的叫聲清脆悠揚,讓我再次回想到曲折不盡的楚江,再次讓我看到故園春意盎然的景色,但是,黃鸝啊,不要再無意義的鳴叫了,快快往回飛吧,紫椹就要成熟了。濃濃的思鄉與相思之情,通過聲音直達心底,觸動詩人最柔軟的一根情思。“清商激西顥,泛滟凌長空”“希聲閟大樸,聾俗何由聰” ⑨(《初秋夜坐贈吳武陵》),琴聲清越激蕩,曲調高遠,如波光閃耀,粼粼奪目,而且音質清麗,曲調流暢。琴聲雖美,可不明事理的俗人如何聽得懂呢?柳宗元用辛辣的嘲諷表達了心中無比的憤慨,為朋友,也為自己。雖然各種聲音交相混雜并不統一,但他們都是作者借以抒發內心情感的手段。借雞鳴、鳥鳴、溪聲以及蟲鳴之聲表現農村的自然靜謐和農村生活的悠然自適;借耒耜之聲、機杼之聲、疏麻之聲表現對勞動人民辛勤勞作的肯定與贊美;借普通百姓之口控訴官吏為官不仁、肆意欺壓勞動人民的罪行;借猿聲、黃鸝鳴叫聲表現自己思念故國與貶謫帶來的抑郁不平之氣。這些聲音引了作者的注意力,引發作者的思緒和感觸,多種情感交相融匯卻又互不干涉,表現了柳宗元強大的情感表現力。
三、人物形象與“聲音景觀”背后的心靈世界
柳宗元筆下的農民形象,是其借底層人民生活的艱辛、生存的不幸表現對天下廣大受苦受難的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其筆下的官吏形象則是以個別代替總體,通過對底層官吏的貪殘暴虐的刻畫,表現的是對整個官僚體制不合理的悲憤,更有對各種官員徇私枉法、中飽私囊、沆瀣一氣等丑惡行徑的揭露,通過兩個階層的對比將元和年間廣闊的社會面貌生動的刻畫出來。柳宗元對自我形象“旁觀者”的刻畫,實際是為自我情感的宣泄尋求合理的途徑,運用這一形象,不僅可以將自己的情感抒發最大化,不受現實世界的約束,還可以使表現的情感更加真實具體。另外,柳宗元通過在村居詩中大量運用聲音景觀,將自己仕途的失意、故國的愁思、相思的眷戀等細膩委婉的情思娓娓道來。這些聲音景觀不論是用于寫景狀物還是敘事,最終都成為柳宗元排解復雜思想情感的窗口,為他所熱愛的、鄙夷的、希冀的、痛心疾首的、欲言說卻又不敢言說的各種情感找到宣泄口,大大增強了作品的容量以及柳詩情感的飽和度。
柳宗元的心靈世界是復雜多樣的,其心靈世界復雜性背后隱藏的,首先有他對百姓的同情和對官吏的痛恨,這與他參與永貞革新的初衷是一致的,表現出士人拯世濟物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其次有對村居生活的喜愛,這種喜歡固然緣于他對自然山水的喜愛,與其山水小品文寫作動機一樣,但同時何嘗不是他借山水田園暫時逃避貶謫后的失意、苦悶;再次,是“回歸心切”與“歸而不得”的矛盾,即安居鄉村和不甘心安居鄉村的矛盾。種種矛盾心理復雜交織,是柳宗元復雜多樣的心靈世界的基礎。“感事”與“聲景”相互融合、交相使用,使柳詩呈現出獨特的面貌,這也是為什么柳詩中的情感總有一種異乎尋常的穿透力,能直達讀者心靈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之,雖然柳宗元的眾多村居詩表面看是描寫田園生活的詩,但卻又與傳統上描寫田園景色的詩作不同,其詩文風格和特色是他獨到的人生經歷和情感心路所決定的。他在描寫田園景物的同時更加關注社會民生,把自己憂國憂民以及仕途失意的人生百態貫穿其中,所以說,柳宗元雖然沉醉于農村的自然風光和鄉土人情,以此來排解自己內心的憂郁與被貶的無奈與辛酸,但他總是不能從心底真正將仕途放下,在仕途失意的主線之下交織著思鄉、相思之情,環繞著閑適自得、孤獨無依、隨緣自適、欲而不得等多種復雜的情感,并且在自我寬慰中愈發難以釋懷,這與柳宗元強烈的政治意識有關,無論遭遇多大的打擊,他始終相信對自己抱有希望,所以即使前途再渺茫、命運再黑暗,他都不曾屈服,而是執著于官場仕途,難以自適。柳詩的美,“發纖秾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 ⑩,田園風光里總有一個不屈的追尋者的影子在里面。
注釋:
①(唐)柳宗元:《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238頁。
②(唐)柳宗元:《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212頁。
③(唐)柳宗元:《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249頁。
④(唐)柳宗元:《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215頁。
⑤(唐)柳宗元:《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172頁。
⑥(唐)柳宗元:《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217頁。
⑦(唐)柳宗元:《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213頁。
⑧(唐)柳宗元:《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779頁。
⑨(唐)柳宗元:《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134頁。
⑩吳文治:《柳宗元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2頁。
作者簡介:
李忠營,男,漢族,山東臨沂人,西安工業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