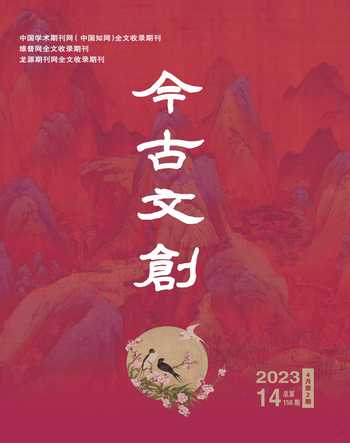從《德伯家的苔絲》看哈代筆下的役使動物
閆少勇
【摘要】 《德伯家的苔絲》是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最為讀者所熟知的作品,在這部作品中也有非常豐富的動物形象。這部小說所描述的生產生活中,役使動物的參與很明顯。本文通過分析小說中以馬和奶牛為代表的役使動物,揭示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工業文明影響下,其在生產生活中依然發揮重要作用但更加淪為工具或機器、地位進一步降低的狀況和這一狀況背后哈代本人對動物的關切。
【關鍵詞】 《德伯家的苔絲》;托馬斯·哈代;役使動物;維多利亞時代
【中圖分類號】I1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4-002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4.008
《德伯家的苔絲》是英國作家托馬斯·哈代最為讀者所熟知的作品,也是哈代最為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這部小說成功地刻畫了苔絲這一鮮活而飽滿的形象。苔絲本是一個美麗的農家姑娘,在命運的操弄下為亞雷少爺所害,失去了“貞潔”,又因此在日后遭到了心愛之人克萊的拋棄、失去了到手的幸福,在再次遇到亞雷時最終成功復仇,但也付出了失去自己生命的代價。
這部小說所描繪的鄉村生活中,動物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特別是小說中描繪的馬、奶牛等役使動物,既被描寫得十分生動形象,也十分深入地參與到了小說人物的生活勞作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而也是值得特別關注的一部分。在以往對《德伯家的苔絲》這部小說的研究中,無論小說中的動物還是役使動物都得到了一些關注,但并不充分。劉克東和張瑾(2010)注意到了小說中的馬與錦雞。他們指出,苔絲家的老馬“王子”是消亡中的小農經濟的代表,“王子”的遇難看似偶然實則必然,是舊的生產方式被新的生產方式取代的必然,也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的體現。小說中受傷的錦雞則被認為是“苔絲的化身”,錦雞與苔絲一樣都是“清白、無辜”的形象,但在弱肉強食、不和諧的環境中,成了被欺侮的犧牲品,并最終走向了消亡(47—49)。在劉克東和張瑾的分析中,這部小說中動物形象的意義更在于其象征意義而非動物本身,動物形象本身的意義、影響并沒有被充分挖掘。吳燕和馬春玉(2018)也注意到了這部小說中豐富的動物形象,但在也更偏向其象征意義,指出小說中的老馬“王子”、母馬“蒂貝”(又譯作“提伯”)以及亞雷的另一匹馬隱喻了苔絲落入深淵的整個過程,小說中的鳥則象征了苔絲的心境與處境,而麥田老鼠無處可退最終被打死的命運則象征了苔絲被整個社會圍堵、逃不出所謂“正義”審判的命運(68—69)。林曉青(2016)在分析《德伯家的苔絲》中的自然意象時也提及了其中的動物意象,重點分析了這部小說中鳥的形象,認為鳥與苔絲本人關聯最為緊密,體現了苔絲的心理狀態,也暗示了其命運走向(26—29)。吳曉峰(1999)則聚焦于馬和馬車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分析,指出馬和馬車在小說中的突出地位。他提到,馬和馬車在這部小說中并不只是一般性的點綴,而是起到了“組織安排結構、塑造人物形象、構成意義空間層次、增添風土人情”的功能的重要存在。吳曉峰認為,馬和馬車伴隨了苔絲命運起伏、變化的每個階段,或作為工具、或作為預兆、或作為人物形象、行為的象征(57—59)。從總體看,和上述提到的研究一樣,吳曉峰更關心的依然是馬和馬車在小說中象征性作用,既包括對于情節發展的預示,也包括對于人物形象的隱喻。盡管吳曉峰在論述中也提及了馬和馬車在當時英國社會生活中所處的狀況,但除了指出苔絲家庭依靠老馬“王子”作為生意上的支柱這一情節體現了社會中家境差的小販需要依靠病馬、老馬的實際情況外,并沒有結合文本對馬和馬車本身在社會的狀況做進一步分析。
上述研究普遍更偏重于小說中動物對于人物形象、情節發展的象征意義,但對于動物本身在小說中的狀況、作用挖掘仍不夠深入。在《德伯家的苔絲》中,哈代對于包括役使動物在內的動物本身的刻畫非常細致,生動地呈現了這些動物的狀態以及這些動物是如何與人進行互動的。特別是在這部小說所展現的生產生活場景中,役使動物的參與十分深入,承擔了許多任務,而哈代對此的交代也比較詳細,清晰地呈現了這些動物在生產生活中的作用。因而對于動物本身特別是役使動物本身的挖掘也應該是研究這部小說的一個重要方向。
本文聚焦于《德伯家的苔絲》這部小說中的馬與奶牛等役使動物,通過分析對這些動物本身的描寫,指出哈代筆下這些動物形象本身的情況,并分析在生產生活中這些役使動物是怎樣發揮作用的,從而揭示這部小說所反映的役使動物在維多利亞社會的狀況。哈代筆下的鄉村往往被認為是淳樸的、自然的,哈代本人也往往被認為是懷舊的,但在《德伯家的苔絲》這部小說中其實有著不少工業文明的痕跡。工業文明的發達是維多利亞社會最典型的特征之一,而小說中的役使動物也受到了工業文明影響。研究小說中的役使動物,也離不開維多利亞社會工業文明這個大背景。
馬是維多利亞社會中最為普遍的一種役使動物,在這部小說中也被廣泛提及。
在小說中人物的出行中,馬和馬車是最為普遍的選擇。苔絲每次離家遠行都乘坐馬車。苔絲第一次離家遠行、前往純瑞脊攀“本家”時所乘坐的就是有彈簧輪子的“大車”(a cart)。當時,苔絲的母親昭安·德北還有所懷疑,認為前來接本家應該用“馬車”(a carriage)(56)。從昭安·德北的話中,大家看到“馬車”(a carriage)是當時鄉村中用于更尊貴的客人的。但無論是相對普通的“大車”還是用于更尊重客人的“馬車”,都是由馬所驅使的交通工具,都是人們所說的馬車,這也體現出馬車在當時英國鄉村適用范圍之廣、地位之重要。苔絲經過在家的休養、第二次離家遠行去牛奶廠做工時乘坐的依然是馬車,分別是她自己雇來的一輛小馬車(a trap)和農夫的大馬車(a cottage)。盡管乘坐的車型并不相同,但都是馬車。在描述苔絲等待農夫的載人裝貨的大馬車的情節時,小說也提到鐵路只繞過那塊腹地的邊界,并不穿行它的內部(127—128)。這也體現出工業革命中興起的鐵路在當時仍有著明顯的局限,在很多地方覆蓋不到,因而馬車在這些地方的貨運客運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優勢,是生產生活所依仗唯一的選擇。通過這些可以看出馬在交通中的重要作用。即使伴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鐵路運輸等工業化的運輸方式進入了英國人的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維多利亞時代,馬車這種傳統的運輸方式依然在小說所描繪的鄉村、鐵路涉及不到的腹地等地區發揮著重要作用,甚至是人們出行的唯一選擇。但在小說的論述中,被提到的往往只有馬車,而沒有驅動馬車的馬,這也體現了馬本身在交通運輸中并沒有特殊意義,并沒有被人們充分關注,更被關注的只是其所驅動的馬車。
這部小說也提到了馬在農業生產中被運用的情況。在描述收割麥子的場景時哈代寫道:
“機器開始活動起來了;之間三匹馬套在一塊兒,拉著剛才提過的那輛搖搖晃晃的長身機器,在柵欄門那一面往前挪動;拉機器的那三匹馬里面,有一匹馱著一個趕馬的,機器上有一個座,坐著一個管機器的。機器全部先順著地的一邊往前一直地走……跟著看見的,是顏色鮮明的十字架,最后看得見的,才是全副的機器。”(108)
在這段描寫中,人們看到機器是很沉重的,機器上有一個高高的十字架,十字架之外還有復雜的結構,而且三匹馬拉起來都搖搖晃晃,只能往前挪動。此外,馬背上還坐著趕馬的人,機器上還坐著管機器的人。這都說明這三匹馬的負擔很重。而這三匹馬被套在一起,在人的驅趕下拉著機器一直往前走,也完全失去了自由,儼然變成了機器的一部分。
這些都體現出在機器被廣泛運用的維多利亞時代,作為傳統勞動力的馬依然在生產生活中得到了保留,甚至以全新的方式參與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馬參與勞動的過程中,他們或彌補機器的缺失與不足,或與機器相結合來共同發揮作用。但作為一種役使動物,馬在生產生活中的價值只在于其所提供的勞動力,其作為生命個體的意義是被淡化的。在小說所描繪的維多利亞時代,通過生產生活中馬的狀態,也能發現這一現象也有著變本加厲的趨勢,在與機器相結合的過程中,馬也越來越淪為機器的一部分,越來越“機器化”。
奶牛是這部小說中另一種占據較大篇幅的役使動物,也正是在牛奶廠打工的過程中,主人公苔絲與心愛的安璣·克萊相識、相熟并相愛的,牛奶廠的經歷成了苔絲命運中的另一個重要轉折。而奶牛本身也是牛奶廠很重要的一部分,也被哈代投以了許多關注。
小說中哈代對奶牛的脾性的刻畫令人印象十分深刻。“這些趕到棚子里的牛,都是不太老實的。老老實實自動靜立的那些,都是在院子中間就把奶擠了,因此那時有許多這樣更安靜的牛在那兒等待”(133-134)。在哈代筆下,站在院子里擠奶和被趕到棚子里擠奶不僅是兩種被客觀呈現的狀態,更是兩類牛脾性的生動展現。這一描寫充滿了畫面感,不太老實的奶牛不情愿地被人趕著到棚子里去擠奶,老實的奶牛在院子里就乖乖地交出了自己的奶,讀起來妙趣橫生,充滿了可愛與生氣。這些奶牛是活生生、有自己個性的生命,而不是僅僅被人類用來擠奶的工具。透過擠奶時的兩種狀態,哈代呈現出的是有自己秉性的、更為立體、豐滿的奶牛形象,他從外在寫出了奶牛的內在。這樣的描寫在小說中也不止一處。關于一些奶牛對于擠奶人的偏好的描寫也是很典型的代表。
“通常的時候,總是哪一條牛碰到誰手里,誰就擠那一條,并沒有什么愛憎厚薄、挑挑揀揀的。不過有一些牛,卻總要對于某兩只特別的手表示喜歡,有的時候,這種偏好,可以達到一種極端的程度,因此除了它們喜歡的人,它們就不肯老老實實地站著,要是有生手來擠它們,它們就一點也不客氣,干脆把牛奶桶給你踢翻了。”(153)
寥寥數筆描寫,哈代就將我行我素、個性倔強的奶牛形象躍然紙上。在這段描寫中,牛并不只是被動接受人的擠奶,也在挑選擠奶人,仿佛在挑選服務一般。這體現出在哈代的筆下牛的地位并不是低于人的,同樣作為主體在與人互動,有思維、有偏好、有性情。盡管在現實中,奶牛的舉動更被認為是源于本能沖動而非審慎思考,哈代對奶牛的行為、狀態的詮釋顯然加入了自己的主觀解讀,與客觀情況存在出入,但他非常生動、形象地描繪出了奶牛的行為,也傳遞了奶牛的生機活力 。
盡管哈代本人在描寫中對奶牛投以了很多關注,透過哈代的描述,大家也看到奶牛生機勃勃、充滿活力又風格各異的一面,但在哈代筆下的牛奶廠的老板和員工那里,牛奶才是他們更為看重的,奶牛的價值只在于產奶本身。這在老板克里克的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在他的視角下,對奶牛所采取的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只在于產奶,奶牛的脾性不是他所關注的,奶牛的區別只在于出奶是不是旺、擠奶是否容易。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描寫:
“擠牛奶的工人們,男男女女的,很夠組成一只小支隊伍,男工擠的都是奶頭硬的牛,女工擠的卻是脾氣比較柔和的……通共算起來,在克里克老板名下,差不多有一百多條乳牛,這里有六條或八條,歸老板親自動手擠,除非他不在家,才歸別人。”(136—137)
老板對于牛的分類和分工的依據都是是否容易擠奶,這是他對牛的認知的核心。而對于上文所提到的牛的脾性,因為妨礙了擠奶,老板也積極思考對策克服。
“克里克老板的規矩老叫工人們不斷地互相替換,把這種愛憎好惡的習慣盡力打破……但是女工們私下的心意,和老板的規矩卻正好相反,因為她們每天擠那八條或十條牛的時候,要是永遠挑她們擠慣了的,那么那些樂意出奶的奶頭子,擠起來的時候就非常順手、非常省勁兒了。”(153)
克里克老板絲毫沒有順應牛的脾性,而是出于擠奶方便的考慮,故意打破牛的習慣。這也再次說明了奶牛在他心中只作為工具,他行為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擠奶。女工們則不愿意順應老板的這個要求,更愿意挑她們習慣的。雖然這樣看似順應了奶牛的習慣,但其實也是為了女工們自己擠起來得心應手。所以女工們的關注點也不是奶牛而是她們自己的方便。不過她們這一行為客觀上順應了奶牛的習慣,也使得她們自己的目的更容易達到。這也體現了一種人與動物的合作,順應動物的習慣客觀上也能起到幫助人類的作用。
縱觀牛奶廠的生產模式,可以看到牛奶才是核心。雖然人工擠奶的方式依然是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但在奶牛的管理和運行上都圍繞著牛奶這一產品進行,有嚴密的組織和分工,十分追求效率。這明顯地體現了工業文明的影響。小說中提到的運輸牛奶的火車則更是工業文明的直接體現。從這個角度看,工業文明實際也是當時牛奶生產的重要依托。在這樣的環境下,奶牛作為一種役使動物,也更加淪為工具,更加抽象為牛奶的提供者。對奶牛其脾性的把握也僅僅是為了擠奶方便,甚至工廠老板為了便于生產讓員工直接與奶牛的脾性對抗。這都說明奶牛本身并不如牛奶重要。在這一過程中,擠奶工也只是生產鏈條上的一個環節,不僅奶牛被異化,工人也被異化,都淪為了牛奶工業的一部分,奶牛和人的個性都更加被忽視。基于以上對牛奶廠的分析,可以看到,維多利亞時代工業文明方便農業生產的同時也對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產生了巨大沖擊,這種沖擊下盡管役使動物和工人依然在發揮重要作用,但其地位都進一步低下。
本文主要分析了《德伯家的苔絲》中馬和奶牛這兩種役使動物的情況。在工業文明快速發展的維多利亞時代,這兩種動物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并且與工業文明的生產方式相結合,但其地位卻進一步降低。馬和馬車在鄉村以及鐵路覆蓋不到的地方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運輸作用,在農業生產中馬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勞動力,并且能與當時新出現的機器相結合。然而,馬本身的意義被進一步淡化和忽視,甚至淪為機器的一部分。在牛奶廠,奶牛的作用依然重要,但在工業文明的影響下,其個性被進一步漠視,地位進一步降低,更加淪為提供牛奶的工具。哈代這部作品生動地揭示出役使動物在維多利亞時代發揮重要作用卻享有更低下地位的現狀,體現了維多利亞時代工業文明對動物的進一步異化。哈代本人在小說中對充當勞動力的役使動物進行的細致描寫,這在維多利亞時期的作家中也并不多見。這體現了他本人對這些動物的細致觀察和對其命運的特殊關切。因而,《德伯家的苔絲》這部小說中的役使動物也傳遞出哈代本人對動物的關愛,透過對役使動物的描寫,也可以看到哈代本人的高尚情操。
參考文獻:
[1]托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絲[M].張谷若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2]劉克東,張瑾.哈代《苔絲》中的自然主義意象[J].世界文學評論,2010,(01):47-49.
[3]林曉青.《德伯家的苔絲》中之自然意象[J].安順學院學報,2016,18(01):26-29.
[4]吳曉峰.從比較文學角度談《苔絲》中的馬車和馬[J].理論與創作,1999,(06):56-59.
[5]吳燕,馬春玉.淺析《德伯家的苔絲》中的動物意象[J].安徽文學(下半月),2018,(08):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