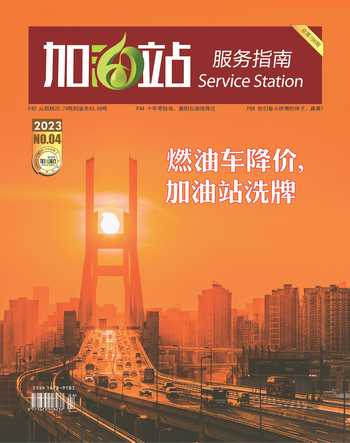融入身體的酸菜
錢雙慶

在嚴寒的陣陣催逼下,草在出生的地方枯萎了,葉子在夢圓的地方凋落了。大地變老,嚴冬駐扎,在溫暖徹底淪陷的當口就到了吃酸菜的時候了。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脾胃,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癖好。這該是一個人不同于另一個人的內因。對于我來說,酸菜對脾氣、對胃口。愛吃酸菜,我是天生的。
我的記憶硬盤里存貯有這樣一幀畫面和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深夜,肚子餓得咕咕叫,從暖烘烘的被窩里爬出來,披上棉衣,躡手躡腳地推開門,鉆進冰窖般的廚房,從腌菜缸里撈出一片帶有冰碴的酸菜來,撕成一縷一縷送進嘴里。瞬間,一種針扎般刺疼的酸香劃破我的味蕾,在肚腹掙扎、撕扯著……
為了在萬物凋敝、漫長難捱挨的冬季吃上可口的蔬菜,母親每年都要腌酸菜。她不僅腌白菜,還腌雪里蕻、青蘿卜、胡蘿卜;不僅腌大蒜、蒜薹,還腌豆角、黃瓜……母親似乎能把整個秋天的收獲都腌起來,把前一年的新鮮保存到來年。
母親用酸菜做的食物很多。紅辣子炒酸菜、酸菜面條、酸菜拌湯自不必說,還有酸菜炒粉條、酸菜炒豆腐,更有鮮香四溢的酸菜炒肉,用酸菜包包子、包餃子也都是美味,甚至怕麻煩了滴幾滴香油把酸菜涼拌上,都是下飯的珍饈。
寒露過后,水靈靈的蘿卜、圓滾滾的土豆、辣鼻子的大蔥等秋菜開始大量上市,也到了大白菜最豐美、最便宜的時節。此時,母親準備腌酸菜了。
一大早,母親借來一輛架子車,和我們一起拉著去國營大菜店。買菜的人早已排起了上百米的長龍,大家都在儲備秋菜過冬。輪到我們買時都快到下午了。進到秋菜小山般堆放的倉庫里,售貨員正指揮著兩個壯漢用杯口粗的木樁擔起大桿秤秤重。過完秤,我們把100多斤大白菜、100多斤洋芋、30多斤青蘿卜搬出倉庫,裝上架子車一趟趟往家拉。
秋菜拉回家后,母親就開始腌酸菜。她先把大白菜抱到院子里晾曬,讓每棵白菜都接受秋陽的撫慰。同時,將大白菜外面的枯黃葉子和破損的菜幫子扒掉。這些扒下來的枯葉和菜幫子,就成了母雞們的口糧。
接著,母親搬出一口跟我歲數差不多大,盆口粗、半人多高的醬油色大缸來。這口缸已經休息大半年了,今天該派上用場了。
母親把這口能腌一百斤白菜的大缸仔仔細細洗干凈。隨后,把晾曬好的大白菜收回來,切掉根,再放到開水鍋里燙一下晾涼控干,把整棵白菜底朝下地擺進缸里,再一棵棵、一層層轉圈碼好,用手按壓緊實,不留空隙。
母親碼一層白菜就撒些鹽和花椒進去,也把對生活的期待裝進了缸里。白菜碼得高出缸口后,母親在上面壓上一塊從黃河邊搬來的滾圓的、大過臉盆的石頭。幾天后,本來冒尖的白菜全部鉆進了缸里。母親往缸里倒些涼開水,水漫過白菜后再蓋上潔凈的木頭鍋蓋。
小時候,整個冬天除了土豆和酸菜外,幾乎沒有其他菜可吃。我家的酸菜要吃一個冬天和一個春天的。母親腌酸菜極其認真仔細,不僅要將自己的手洗得干干凈凈,而且要將腌菜的缸、燙菜的鍋、壓菜的大石頭洗得干干凈凈的。
在腌菜的過程中,只要涉及腌菜的器具,她一個也不放過,不讓沾一點油腥和灰塵。菜腌好取菜的時候,她也專門準備一只盆子和筷子。其間,母親都是一個人操持,不讓我們上手。
一個月后,大白菜腌好就變成酸菜了。酸菜那醇香厚實的味兒也從缸里一絲一縷地逸散出來,讓人禁不住吸鼻子,把香味收進肺腑。這時,大白菜的葉子也由碧綠變為誘人的燦黃。
一天,在我們的期盼中,母親用筷子撈起了一棵黃澄澄、酸香四溢的酸菜,洗凈、切好,又搟了一大杖子面條,做了頭頓酸菜面條。那碗面條熟悉的香味,有我說不出的溫暖氣息。紅辣子炒酸菜是絕配。
深秋時節,長辣椒大量上市。母親論堆買來一大網兜倒進洗衣盆里,把碰傷的、殘缺的、腐壞的,模樣欠周正又不鮮嫩的挑揀出來。隨后,再找來一團粗線團、一根縫被子的大針,把線紉到針上,將一大盆辣椒串好,一串串挑起來掛到院里曬,一面綠色的彩旗就在院里飄了。
童年心里不裝事,油綠的辣子什么時候變紅的已經記不得了。只見一串串紅辣子,就像一團團燃燒的火苗,溫暖了嚴冬、溫暖了我們的心。紅辣子炒酸菜真香啊,尤其是夾進薄餅子,拌上手搟面條,就是拿山珍海味也不換。
在無數個缺吃少食的嚴冬,是酸菜陪伴了我們。它讓我們嘴里有了滋味,生活有了色彩。如今,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可以吃到的美食數不勝數,酸菜早已擺不上臺面了。但對于我來說,酸菜永遠是我的最愛。因為是它滋養了我,培養了我不變的口味,讓我永遠無法割舍。
我這輩子是離不開酸菜了。因為酸菜已經進入我的基因。
責任編輯:曲紹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