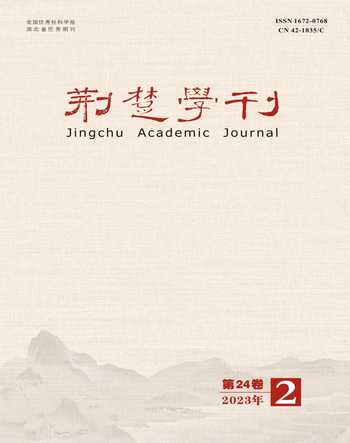對危險接受理論類型化的反思與重構
摘要:危險接受作為過失犯的違法阻卻事由,如何類型化影響著行為人的出罪與入刑。既有的以故意犯中的行為支配要素為標準的方案存在著理論的根基不當與事實缺省問題,有必要從危險接受理論的“本土資源”出發,考察被害人與行為人之間是否結成了危險接受共同體,過失結果的歸責在共同體層面得到消解,阻卻對共同體內部的個人歸責;反之,若被害人獨自接受危險。過失結果的出現意味著行為人沒有正確掌控風險,違背了被害人反對結果發生的信賴,應當承擔過失責任。
關鍵詞:危險接受;行為支配;危險接受共同體;被害人信賴
中圖分類號:D914?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2-0768(2023)02-0062-07
一、問題的提出
肇端于德國判例學說的危險接受理論,經過近一百年的發展,產出了諸多教義學成果。例如,危險接受理論的適用領域是過失犯罪,只有結果的發生才具有刑法意義;被害人的接受對象僅限于行為的風險,而未接受此種風險的現實化;危險接受的體系定位是違法阻卻事由,在與共犯理論關聯的意義上,根據何者支配了危險行為,將危險接受案件類型化為自己危險化的參與和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 1 ],前者因缺乏構成要件符合性而一律阻卻違法,后者則原則上不阻卻違法性,僅在被害人間接支配了危險行為時才例外地阻卻違法。前兩點教義學成果幾乎獲得了所有學者的認同,成為了學界探討危險接受的理論基底,但是對于危險接受理論的類型化這一點,則面臨著不同程度的質疑。有的學者批判這種類型化立場的合理性,認為正犯與共犯的理論不適用于過失犯領域,所有對過失結果具有因果關系的行為人都是過失正犯[ 2 ];有的學者從共犯從屬性與獨立性之爭出發,認為我國刑法不是共犯從屬性的立場,因而不能將之作為解決危險接受理論的前提,否則會造成理論與實踐背道而馳的局面[ 3 ];還有的學者認為“自我危險化的參與”和“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在規范上具有實質的相同性,這種區分僅僅具有將案件分類的作用,而不具有規范上的意義,應當放棄這種類型化,給予二者相同的(排除不法的)評價[ 4 ]。可見,批駁“自我危險化的參與”與“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類型化方案的觀點主要集中于對將故意犯罪的正犯與共犯理論移植到解決阻卻過失犯違法性的危險接受理論的反對。
筆者認為,從表面上看,這種移植具有巧思之處,試圖用行為支配這一要素貫通于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之間,進而達致體系的協調。但是,貿然移植難免產生“排異”,解決一個理論問題首要考慮的應是從問題本身的內涵與邏輯出發,尋找解決該問題的“本土資源”。因此,從“危險接受”這一自身要素出發,嘗試從行為人與被害人是否構成危險接受共同體的角度,對危險接受理論進行再類型化,方能圓滿化解以行為支配為標準進行類型化的理論難題。
二、“行為支配”類型化方案的理論檢視
危險接受問題誕生于德意志帝國法院的梅梅爾河案,確立于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海洛因注射器案,而最終類型化于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加速試驗案[ 4 ] 115-142。詳言之,在加速試驗案中,S和J為了拍攝下賽車的全過程,分別坐上了B和H的賽車。當兩輛賽車在兩車道公路上高速行駛時,為了超過前方正常行使的車輛,B和H同時作出了危險的超車行為,導致發生車禍,造成了J的死亡后果。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認為,作出超車決定的是B和H,具體實施超車行為的也是二人,綜合評判二人對整個事件起著完全的支配作用,因此B和H除構成危害道路交通罪外,還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否定了J的危險接受對其死亡結果的違法阻卻。據此,行為支配將海洛因注射器案確立的危險接受理論進一步劃分為被害人自己實施了危險行為的“自我危險化”和被害人參與他人實施的危險行為的“他人危險化”,并且認可了二者間在違法阻卻上的不同功能。我國學者張明楷教授也持相同的觀點,主張在與正犯論相關聯的意義上區分二者[ 1 ]。運用正犯理論來對危險接受案件進行類型化似乎是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但是也存在著諸多疑問。
(一)正犯與共犯的區分理論運用于危險接受的正當性存疑
危險接受屬于過失犯領域的子問題,要確定正犯與共犯區分的理論能否適用于危險接受,首先要經過能否適用于過失犯的檢驗。而這一檢驗實際上確定的是正犯與共犯理論本身的輻射范圍。在共犯的本質問題上,學界長久以來存在著犯罪共同說與行為共同說的爭論。前者認為,共犯要求行為人之間只能就某一具體的犯罪成立犯罪;后者認為共犯是一種不法形態,只要行為人之間就行為就各自實施的行為具有意思聯絡即可,最終成立的犯罪與行為人各自的責任有關,因此可能成立不同的犯罪。如果采犯罪共同說,當被害人“自我危險化”時,其本人無論如何也不成立犯罪,只具有參與的他人成立單獨犯罪的空間,因而不適用共犯論,這是當然的推論。問題在于如果采行為共同說,共犯論又能否適用于過失犯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即使是將共犯看作一種不法形態,也存在著故意的不法形態與過失的不法形態之分。行為無價值二元論為了發揮構成要件的類型化機能,將故意和過失作為主觀的違法要素納入了構成要件,因此故意殺人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在構成要件層面即可區分出來,而不必等到責任層面。相反,結果無價值論者則將故意和過失作為責任要素考察,認為故意犯和過失犯在構成要件和違法性層面別無二致,區別僅在于責任要素的不同,進而得出不法形態無故意過失之分的結論,為共犯論適用于過失犯開辟出道路。筆者認為,行為無價值二元論的觀點更具有合理性,符合物本邏輯,厘清了事實與認識的關系。行為人在實施某一犯罪行為時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主觀意志,例如,行為人在下出租車時順手將上個乘客遺留的財物帶走,即使不考察責任層面,僅從“取走他人財物”這一客觀要素,也能得出行為人具有盜竊罪不法的結論,而不可能認為行為人是過失。故意和過失與行為、對象和因果關系等構成要件要素的關系遠比于與責任年齡、責任能力等責任要素關系更為密切。此外,階層式的犯罪論體系是在事后立場對已定型犯罪進行的追問,但這種追問影響的是對犯罪的認識順序,本質上并無不同。換言之,在結果無價值論尚未檢討責任要素時,某個犯罪是故意犯還是過失就早已確定了,將二者的差異歸結于責任要素可能并不是事實的真實面貌,而是一種理論安排。相比之下,行為無價值二元論的理論安排更貼近現代心理學對于行為與意志的研究成果。所以,當不法形態具有故意和過失之分時,就不能認為共犯理論可以理所當然地適用于過失犯。
其次,共犯理論解決的是正犯與狹義共犯的關系問題,而狹義共犯只可能存在于故意犯罪之中。德國刑法第26、27條分別規定,故意教唆或幫助他人故意實施違法行為的,方可成立教唆犯和幫助犯[ 5 ] 13。換言之,教唆犯和幫助犯的成立需要滿足兩個故意,即正犯實施違法性的故意和共犯實施教唆或幫助行為的故意。故德國刑法理論一般不承認過失的教唆犯和幫助犯[ 6 ] 10。我國刑法的立場與之相同,在第25條共同犯罪的概念中強調了“故意犯罪”,表明了共犯理論旨在解決故意犯罪領域的多人犯罪。究其原因,相比于單人犯罪,多人參與犯罪,法益侵害結果更容易發生,行為人躲避抓捕的可能性更大[ 7 ] 312。而這種相較于單人犯罪的特殊性在于共同犯罪行為人之間的謀劃與協作,非多個過失行為競合在一起所能實現。在危險接受類型的案件中,危害結果是在行為人和被害人共同不注意的情況下出現的,只不過在被害人死亡的情況下,其自身的過失不具有刑法意義,僅追究行為人的過失責任。當二者成立共同過失( 1 )尚存疑問時,遑論成立共同故意。
最后,刑法理論一般認為過失犯領域適用的是單一正犯體系,而故意犯適用的是區分制正犯體系,不能將區分制下的共犯理論套用到過失犯上。雖然犯罪的本質是法益侵害,但是達致法益侵害的路徑有所不同,如羅克辛教授就曾建立支配犯、義務犯和親手犯的三元正犯體系[ 8 ] 584。在這一體系下,身份犯和不作為犯均是通過對義務的違反而造成法益侵害成立犯罪的。而新過失論認為,過失的本體在于違反了結果回避義務[ 7 ] 164,并且學者亦認為,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與過失犯的結果回避義務實際上是相同的義務[ 9 ] 245。在這意義上而言,作為區分制正犯體系核心概念的行為支配理論就難以說明過失犯的正犯性,過失犯罪的正犯只能是每個違反注意義務、有助于實現構成要件之人[ 10 ] 887。換言之,對于過失犯的犯罪參與體系只能是單一的正犯體系,違反了注意義務,與結果的發生具有因果力的人都是正犯。因此過失的教唆犯和幫助犯符合上述條件也能被認定為過失正犯,而不再適用共犯從屬性。與正犯理論相關聯的意義上區分“自我危險化的參與”和“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最大的問題就在于,正犯理論與故意犯罪具有高度適配性,導致套用到過失犯罪中反而根基不穩、疑竇叢生。
(二)正犯與共犯的區分理論運用于危險接受的具有事實缺陷
理論的形成,存在著建構主義和經驗主義兩條路徑,前者強調人對理論的設計,后者強調人對事實的接受[ 11 ]。毫無疑問,危險接受理論的形成路徑屬于后者,其并非是理性建構的產物,而是來自德國判例實踐的經驗升華。其判例基礎包括1923年德國帝國法院“梅梅爾河案”、1925年德國帝國法院“摩托車案”、1955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賽車案”、1962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天花醫生案”、1972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警察手槍案”、1997年杜塞爾上級法院的“車頂甩落案”和2008年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加速試驗案”。正是憑借法院和學者對上述案例進行闡明和評述,如今的危險接受理論的概念與類型才得以形成。從事實到理論的經驗升華的過程中,研究者要以充分認識經驗現象為前提,在梳理分析因果鏈條的基礎上,闡釋經驗內涵的價值,從“經驗”中“推出”理論[ 12 ]。因此,對危險接受理論既有類型化的事實考察就顯得尤為重要。筆者認為,以行為支配為標準進行類型化的理論存在如下事實缺陷。
首先,與正犯論相關聯的類型化觀點將行為支配與危害結果之間進行了不適合的綁定,最終發揮決定作用的是偶然的結果。以梅梅爾河案為例,該觀點認為,船夫實施了駕船行為,對被害人的死亡結果具有行為支配,因此屬于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應當追究其過失致人死亡的罪責。但是可以發現,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并非是一開始就能夠確定的結果,換言之,渡河行為也可能發生船夫死亡,乘客幸存的局面。根據上述觀點,此時案件的類型又變為了自我危險化的參與,乘客無責。似乎并非單是何者支配了行為起到了類型化案件,進而決定違法性阻卻與否的作用,而是當結果沒發生在行為支配者身上時,才能確定。這種綁定是不合理的。行為支配在結果發生前就能確定,而具體結果的發生卻具有極大的偶然性。當這種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疊加后不難看出,實際上是不確定的結果主導了最終的歸責。這個結論實際上推翻了上述類型化以“行為支配”的標準。
其次,正犯論相關聯的類型化觀點對危險接受案件事實的歸納不夠全面,放棄了行為支配者可能同樣具有危險接受以及行為人和被害人共同形成支配的事實情形。學界一般認為,危險接受闡述的是這樣一種事實:“明知自己實施或參與他人某種行為存在風險,但仍然自愿實施或參與”[ 13 ],并最終導致結果發生。所以危險接受首先是一個個體接受法益侵害風險的事實概念,而非一開始就具有保護傾向的價值觀念。在梅梅爾河案中,船夫在乘客的百般請求下最終決定駕船渡河,此時不僅是乘客接受了渡河的風險,船夫也同樣作出了接受風險的決定,并且這種危險接受的決定是乘客推動形成的,不能因死亡結果僅發生在乘客身上就放棄這一事實。因為,如上所述,具體結果發生在誰身上具有偶然性,倘若最終發生的是船夫死亡、乘客幸存的結果,在學界普遍承認過失犯領域采用的是單一正犯體系的理論背景下,就可能存在著要求不具有行為支配的乘客為船夫的死亡承擔過失正犯責任的空間。這種可能性彰顯著法律對于公民的平等保護,尤其是在過失犯下行為人并不具有對社會的敵視態度時尤為重要。例如,在二人互相斗毆時,在杜絕死亡結果出現的意義上,斗毆的雙方都是法律的保護對象。此外,以行為支配為標準的類型化方法正確解決危險接受案件的潛在條件是,只有其中一方具有行為支配,被害人一方只能接受這種行為支配的風險。但是在現實世界中,雙方共同支配行為的情形比比皆是,例如,甲和乙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共同采下了一叢毒蘑菇,共同烹飪然后進食,最終導致甲重傷和乙死亡的結果;又如,丙和丁為尋求刺激,在未充分檢查降落傘裝置時就進行雙人跳傘,最終導致丙重傷和丁死亡的結果。在上述兩個案例中,恐怕就不能根據行為支配將死亡結果完全歸屬于幸存者。
最后,強調行為支配對于危險接受類型化的意義,與危險接受理論的形成路徑相違背,存在以規范框定事實,而非由事實上升到規范的邏輯顛倒之嫌。危險接受理論作為經驗主義的產物,遵循的是一條由事實歸納到理論升華的生成道路。這條道路指向的是違法阻卻的終點。正如張明楷教授曾對危險接受的案件進行歸納后指出,“上述介紹給人的印象是,凡是屬于危險接受的案件,均阻卻犯罪的成立。”[ 1 ]但稍后其反駁道“事實上并非如此”。張明楷教授的上述言論反映出基于經驗主義生成的理論的共同困境,即在對已知的事實的歸納僅是部分歸納,而不能窮盡所有情形,因此基于前者升華的理論就面臨著例外的現象。要化解這個困境有兩種方案:其一是堅守理論已有的內涵與外延,謹慎對待理論形成之后的相似事實的歸結與納入;其二是以“原則—例外”的模式擴張既有理論的內涵與外沿,修正既有理論。以“行為支配”為標準的類型化方法采取的就是第二種方案,在承認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屬于危險接受的情形下,否定其違法阻卻的功能。相比之下,筆者更支持第一種方案。原因在于,第一種方案有利于保持理論的本真,減少理論的“騎墻派”,也不至于在本就紛繁復雜的理論體系上繼續疊床架屋,進一步復雜化,同時也不會影響具體案件的正確處理。例如甲明知道乙是醉酒后駕駛機動車,仍然決定坐上車兜風,后乙因駕駛失誤,導致其車越過道路中線,與它車相撞,造成甲重傷的結果。按照張明楷教授的觀點應當將本案歸納為危險接受的“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同時認為乙應當承擔過失致人重傷的責任。這個結論在筆者看來,如果堅持這種情形仍屬于危險接受,實際上就否定了危險接受阻卻違法性的基本法理,否則就必須承認,不屬于危險接受的類型。根據筆者的見解,本案并不屬于危險接受的類型。被害人危險接受的對象是對于自身法益具有侵害風險的行為,風險附著于行為而存在,因此不能籠統地認為是接受風險。既然“侵犯公法益的犯罪,不存在危險接受問題”[ 1 ],那么對具有侵犯公法益危險的行為也不能進入危險接受的領域內。乙醉酒駕駛的行為是一個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行為,甲并不具有接受的權限,因此此時并不存在危險接受,當乙駕車失誤造成甲重傷,自然應當承擔過失致人重傷的責任,這一責任已經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結果所包含。
除此之外,江溯教授根據對自我負責的同意和同意他人的危害的三個共通特征的歸納[ 4 ] 142,認為應當對這兩種類型的危險接受給予相同的規范評價,即“應當承認兩者均有排除行為人之不法的效力,并且在這一前提下探討這種排除不法的正當化根據。”換言之,取消以“行為支配”為標準的類型化,肯定其違法阻卻的功能。筆者贊同江溯教授的基本立場,進一步認為,可以根據行為人與被害人是否結成危險接受的共同體為核心標準,將部分案件排除出危險接受的范圍,進而還原危險接受阻卻違法的理論本色。
三、本文見解:以危險接受共同體作為核心標準進行類型化
在與正犯論相關聯的意義上,根據是被害人還是行為人具有行為支配為標準,將危險接受類型化為“自我危險化的參與”和“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的觀點,存在上述說理和事實上的缺陷,不能圓滿地解決危險接受理論的難題。究其原因,行為支配在故意犯罪中屬于核心要素,而對處于過失犯領域的危險接受問題則可能“橘生淮北”。因此,放棄行為支配轉而從危險接受理論中發掘“本土資源”就顯得具有合理性。傳統的危險接受理論站在事后立場,將危險接受的主體鎖定在了被害人身上,而把同樣參與或實施了危險行為他者僅僅作為一個待追責的主體,缺乏對其全盤審視。如果以一個事前和事中的立場審視危險接受案件,可以發現兩種不同的情形:被害人與他人共同接受風險和被害人獨自接受風險的情形。下文將對此展開進行闡述。
(一)被害人與他人共同接受風險
被害人與行為人共同接受風險意味著,被害人和他人均認識到、接受了即將實施的行為可能對自身法益產生的風險,并且也彼此認識到對方法益面臨的相同風險。在最終的結果因雙方過失的共同作用下發生時,可以認為被害人與他人之間結成了一個危險接受的共同體,過失結果的歸責在這一共同體層面因共同體的自我答責而被阻卻,不再對共同體內的個體產生作用。原因在于,過失犯中行為支配并非確證正犯的標準,所有違反注意義務的人都應當被當作過失正犯,行為具體由誰實施對于結果歸責的意義不再如在故意犯罪中重要。當被害人與行為人決意共同接受危險時,也意味著二人注意義務的一體化。這種一體化并非是將一方的特殊義務強加于另一方,而是指應當對這種特殊義務違反造成的結果一并承擔責任。從被害人自我答責上來說,由于行為人與被害人結成危險共同體時,二者都是潛在的共同危險行為的被害者,因此有必要基于同等保護的意義上對這一共同體人格化,適用自我答責理論。
例如在梅梅尓河案中,德意志帝國法院則是在認為乘客的危險接受阻卻了船夫的注意義務的角度來否定船夫的過失罪責的[ 4 ] 118。筆者認為,在暴風雨中渡河的風險問題上,乘客與船夫之間達成了一致,結成了危險接受的共同體,危險行為的實施可以視作這一共同體的作品,而不能僅僅因為船夫在具體的事實層面操縱了行為就將該行為產生的所有結果都歸責于船夫。因此最終無論發生的乘客死亡還是船夫死亡的結果歸責應當在共同體層面被消解,而不再追究共同體內個體對過失致人死亡的責任的承擔。被害人與他人成立危險接受的共同體,必須考慮以下三種情形:
其中一方具有更優越認知時,否定危險接受共同體的成立。危險共同體的成立要求被害人與行為人對危險具有共同的認知,既不能是被害人具有更高的認知,也不能允許他人具有更高的認知。原因在于,如果其中一方具有更高的危險認知,就意味著,另一方以接受的是較低的危險,而非實際上存在的高度危險。當雙方的認知不匹配時,不能成立共同體。例如,甲與乙均是同性戀者,甲明知自己曾與HIV患者進行過危險性行為,雖然自己尚未檢測確診,但仍隱瞞了這一事實,與乙發生了沒有保護的性行為。在此案中,表面上看,甲與乙進行無套性行為是一種共同的危險接受,但是由于甲確診HIV陽性的可能性極大,而乙對此并未認識到,雙方對彼此面臨的危險并無相同的認知,不能成立危險接受的共同體,如果最終造成乙感染的結果,甲至少應當承擔過失的責任。又如,在日本千葉賽車案中,由于被害人作為經驗豐富的賽車教練,對于危險的認知明顯優越于初學賽車的被告人,因此二者不能成立危險接受的共同體而直接阻卻死亡的結果的歸責,必須實質考慮被害人與被告人何者對結果的因果力作用。在結合被害人對危險的態度和高度認知以及在結果發生過程中對被告人行為起到的事實控制的基礎上,應當肯定被害人自我承擔死亡結果。
危險接受共同體接受的只能是個人法益的危險,而不能是集體或社會法益的危險。雖然,被害人同意理論不能直接適用于危險接受案件,但阻卻違法性的實質理論均在于危險行為符合被害人自我決定[ 14 ],因此可以在理論構造上對二者進行比較。被害人同意理論認為,被害人必須對被侵害的法益具有處分權限[ 15 ] 297,亦即只能對涉及自身的個體法益侵害進行承諾,而不能承諾對集體法益、社會法益的侵害。同理,危險接受的主體也只能接受可能對自身法益造成法益侵害風險的行為,而無權接受對集體法益、社會法益的危險行為。這就可以將醉酒同乘類型的案件排除出危險接受共同體的范圍。具體而言,甲雖然明知乙陷入醉酒狀態,仍然接受了其要求搭乘乙車兜風的邀請,最終由于乙因為醉酒駕駛而發生交通事故,而致甲重傷。表面上看,甲與乙就醉酒駕駛的危險作出了共同的接受,但是不能承認二者結成了危險接受的共同體。風險附著于行為才能存在,接受風險,實際上是接受風險背后的行為。乙醉酒駕駛的行為已不再是一種僅針對甲個人安全法益的危險行為,而是威脅公共交通安全的行為,作為社會個體的甲不能代表社會或集體接受這種危險行為。故甲重傷的結果應當歸責于乙的醉酒駕駛行為,而不能阻卻。
當任意一方脫離危險共同體時,先前共同的危險行為賦予了其救助另一方的義務,應當在不作為犯的框架下重新考量。危險接受共同體的結成,具有三個方面的共同意涵:其一是對于彼此面臨危險的共同接受;其二是對于共同危險行為造成后果的共同承擔;其三是對于結果的共同反對以及基于這種反對產生的互相救助的義務。當危險行為現實化為結果過程中,這種救助義務因個體陷入危險而有所緩和,同時也會因個體脫離危險而加強。如果共同體任一方脫離危險后,在具有救助能力和救助可能性時,仍放棄救助他者造成結果的,仍應追究其過失犯罪的責任。后文的“冰上行車溺亡案”對被告人追究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根據即來源于此。
(二)被害人獨自接受危險
當被害人獨自接受危險時,無論該危險是由他人與被害人共同創設,還是僅由他人獨自創設,都應當將過失結果歸責于他人。理由在于,當被害人獨自接受危險,但并未接受危險現實化的結果,所以其接受危險的前提是足以信賴并未共同身處危險之中的他人,能夠采取避免危險化的措施結果的出現,或者說是創設危險的他人提供了這種信賴。而在因發生結果從而進入刑法視野的案件中,他人恰恰是推翻了這種信賴。例如,被告人與被害人在小汽車內發生性關系時,被害人為了追求快感,請求被告人共同用手掐自己的頸部。后來被害人因頸部外力陷入機械性窒息,送往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在本案中,被害人獨自接受的危險雖然由被害人與被告人共同創設,但是被害人之所以接受這樣的危險行為,是因為有理由信賴處于安全處境中的被告人能夠避免致其死亡的結果,事實上,被告人只要掌握適當的力度,密切關注被害人的狀態即可避免悲劇的發生。但很明顯被告人推翻了被害人的安全信賴與期待,應當承擔過失致人死亡的責任。張明楷教授認為,倘若本案是被告人單獨用手掐被害人的頸部,就屬于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應當將死亡結果歸屬于被告人,但由于本案是由被告人與被害人共同用手掐被害人的頸部,就不能將死亡結果歸屬于被告人的行為。[ 1 ]筆者不贊同這種觀點。由于人體的自我保護機制與瀕死的求生本能存在,個人不可能通過自己掐自己頸部或者屏住呼吸的方式自殺,在被害人與被告人共同掐被害人頸部時,實際起到關鍵作用的仍是被告人的行為,與被告人單獨掐被害人頸部的行為在致死的關鍵性上并無太大差別。分別考慮并不會造成難以確定結果是由誰造成的結論。相反這一結論的產生恰恰是過于看重誰具體實施了行為這一標準造成的。
可能產生的質疑是,當他人為吸毒者提供吸毒工具,爾后吸毒者自己吸毒過量死亡時( 2 ),按照本文觀點似乎屬于被害人獨自接受危險的情形,最終可推導出提供吸毒工具者需承擔過失致人死亡刑事責任的不合理結論。但是筆者認為,這并不會影響本文觀點的貫徹。具體而言,雖然筆者并不支持以行為支配的標準來說明危險接受違法阻卻的根據,但是危險并非憑空而來,所以仍需要考慮危險的創設問題。當危險由他人和被害人共同創設或者僅由他人創設,同時陷入危險之中的只有被害人時,他人才具有承擔刑事責任的基礎。整體而言,單純提供吸毒工具的行為或許可以被評價為參與創設被害人吸食毒品的危險,但離參與創設被害人過量吸食毒品死亡的危險尚有一段距離,因此并不屬于本文所認可的被害人獨自陷入危險的危險接受類型。例外的情形是,當提供吸毒場所的人員同時提供吸毒工具導致吸毒者過量吸毒而死亡的情形,則屬于本文所認可的不阻卻違法的危險接受類型。這是因為場所的提供這一先行行為,對行為人產生了“基于對法益的危險發生領域的支配產生的阻止義務”,所以行為人應當承擔容留他人吸毒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數罪并罰的刑事責任。此外,如果是在吸毒者群體之間相互借用或者提供吸毒工具,那么這種行為就像普通人借用日常用品一樣平常,即使被害人使用該工具過量吸毒死亡,也不一定會進入刑法視野。因為違法性抑或社會危害性作為一種價值判斷,其必須能夠還原為一定群體的價值觀,一定群體的價值觀又必須能夠確證為構成群體的每一個人所大體具有的價值觀[ 16 ] 31。這也正是行為支配理論下自我危險化的參與類型阻卻違法的實質根據所在,只不過將之外化為了缺乏行為支配這一表象。因此如患有血友病的甲向鄰居乙借用菜刀,結果自己不慎割傷手指導致血流不止而死亡的例子不可能要求甲承擔過失致人死亡的責任一樣,吸毒者之間相互借用工具導致吸毒過量死亡的,同樣不能僅根據發生死亡結果而要求提供工具者承擔刑事責任。
四、具體案例的檢驗
案例一“相約游泳試水身亡案”:大學生周強、劉卿、劉敏相約到河邊渡口游泳,劉敏提出到水最深處看看河水到底有多深,其余二人表示同意。由于害怕危險,三人以手牽手的方式向河中央走去,由于手未拉穩,一起掉入了河中。劉敏和劉卿因被沖到岸邊被人救起幸免于難,而周強則溺水身亡[ 17 ]。
對于本案張明楷教授認識到“三人牽手試水的行為,對各自都是一種危險行為”[ 1 ] 180這一點,但沒有沿著這種思路進一步得出結論,而是最終以被害人周強的行為不符合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構成要件而否定劉敏和劉卿的責任。筆者認為,這不過是就事論事的循環論證[ 2 ],沒有說明危險的接受阻卻違法的特殊性。周強接受該種危險的前提是信賴三人拉手的協作行為能夠有效地避免危險結果,故三人手拉手試水的行為不能簡單分解為三人試水的行為,而應當作為一個危險接受共同體的整體冒險,進而應當肯定死亡結果的歸責在共同體層面被消解,幸存的劉卿和劉敏不成立過失致人死亡罪。
案例二“冰上行車溺亡案”:被告人鐘平為了近距離觀賞野鴨,在查看冰層厚度并試走后,邀請被害人龍麗娟與其一同乘車穿過冰面,龍麗娟表示同意。但當汽車行駛到河岔中心時,冰面破裂,二人落入水中,鐘平爬上岸后既未采取搶救措施,亦未報案,悄然離開了現場。最終龍麗娟溺水身亡。張明楷教授認為,被告人鐘平承擔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原因在于其完全掌控了風險,龍麗娟的死亡屬于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險化。筆者認為,雖然本案與案例一一樣,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形成了危險接受的共同體,但在具體事實上有別,因此處理結果上也有所不同。案例一和案例二中,幸存者都脫離了危險接受的共同體,但是前者劉卿與劉敏是被沖到岸邊被人救起,而非依靠自救行為脫離危險,并且周強也沉入水中被沖走,二人既無再實施救助行為的能力,也無救助的可能性,因此阻卻了結果的歸責。但是案例二則不同,鐘平自行上岸后離開,既未嘗試救助,也未報警。這才是導致龍麗娟死亡的最終原因,因此鐘平應當承擔過失致人死亡的責任。脫離了危險接受共同體的人,基于先前共同的危險行為以及團結義務,有必要對仍陷入危險中的他人提供救助,否則仍可能成立過失犯罪。
案例三“艾滋病人性交案”:女被害人明知男被告人患有艾滋病而同意在不采取保護措施的情況下與之發生性行為,并因此感染艾滋病( 3 )。張明楷教授認為,在這樣的場合,形式上是二人共同作用導致被害人感染艾滋病,但被告人并沒有強行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也沒有隱瞞患艾滋病的事實,是否發生性關系進而是否感染艾滋病完全由被害人支配,而不能認為被告人支配了實害結果的發生[ 1 ] 174。但事實明明是二人共同行為導致的結果,為了規范處理上的妥當卻只承認一方起到了支配作用,難言合理。退一步講,同樣也可以說是被告人支配了實害結果的發生,因為如果被告人堅決拒絕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也能阻止結果的發生,故上述觀點并未切中要害。筆者認為,本案中被告人應當承擔過失犯的責任,原因如下:實際接受和面臨感染艾滋病危險的只有女被害人一人,與被告人的危險接受共同體并不成立,因此屬于被害人獨自接受危險的情形。由于男被告人作為艾滋病感染者,本身屬于危險源,其避免他人感染艾滋病的義務來源于對危險源的監管或者說對自身行為的控制,例如不能參加獻血活動、不能與他人進行無保護的性接觸等。這類注意義務涉及對公共安全的保護,不會因被害人的危險接受而緩和。因此當違反這種義務造成他人感染艾滋病時,應當承擔過失犯的責任。
五、結論
對危險接受的類型化,應當立足于危險接受本身,根據被害人與他人是否結成危險接受的共同劃分為危險接受共同體和被害人獨自接受危險兩種類型。就前者而言,危險行為具體由誰實施并不重要,因為基于共同的危險接受,過失結果的歸責已在共同體層面被阻斷,原則上阻卻違法;對于后者,被害人獨自接受危險時的前提是對他人對危險的掌控不至于危險現實化為結果,如果他人違背了被害人的這種期待,導致了結果的發生,應當承擔過失的罪責。
注釋:
(1)刑法理論即使承認過失的共同犯罪,也要求二人以上具有相同的結果回避義務,并且都沒有回避結果的發生。但是在危險接受中,被害人與行為人的結果回避義務不可能相同,例如在梅梅爾河案中,被害人的結果回避義務體現在不強行要求船夫渡河即可,而行為人(船夫)的結果回避義務則是安全地將乘客渡過河。
(2)此例不包括他人事先具有殺人故意或者被害人已經陷入意識不清等情形。
(3)Vgl.OLG Bayern,NJW 1990,S.131.轉引自莊勁:《被害人危險接受理論之反思》,《法商研究》2017年第2期,第60頁。
參考文獻:
[1]張明楷.刑法學中危險接受的法理[J].法學研究,2012,34(5):171-190.
[2]莊勁.被害人危險接受理論之反思[J].法商研究,2017,34(2):55-63.
[3]何立榮,陳晨.刑法中的危險接受理論之否定[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0(5):166-173.
[4]江溯.過失犯中被害人自陷風險的體系性位置——以德國刑法判例為線索的考察[J].北大法律評論,2013,14(1):115-142.
[5]徐久生.德國刑法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13.
[6]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2卷犯罪行為的特別表現形式[M].王世洲,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0.
[7]周光權.刑法總論[M].3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164.
[8]許玉秀.當代刑法思潮[M].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584.
[9]山口厚.刑法總論[M].3版.付立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245.
[10]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下)[M].徐久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887.
[11]童德華.非法經營罪規制目的的預設與生成[J].政治與法律,2021(4):53-67.
[12]楊子瀟.經驗研究可能提煉法理嗎?[J].法制與社會發展,2020,26(3):207-224.
[13]車浩.過失犯中的被害人同意與被害人自陷風險[J].政治與法律,2014(5):27-36.
[14]蔡穎.被害人同意與被害人自陷風險的統合——以刑法中被害人同意的對象為視角[J].法學評論,2021,39(5):47-57.
[15]張明楷.刑法學[M].6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297.
[16]馮亞東.理性主義與刑法模式[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31.
[17]程成.相約游泳試水身亡,甘愿冒險責任自負[N].檢察日報,2008-11-01.
[責任編輯:馬好義]
收稿日期:2022-04-18
作者簡介:陳強(1995-),男,四川瀘州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刑法基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