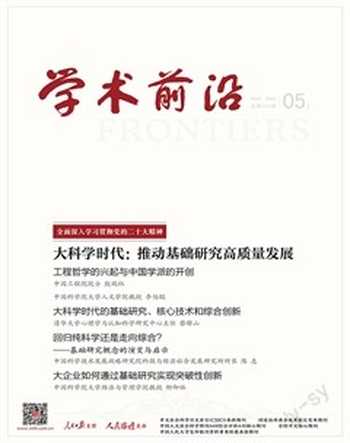工程哲學的興起與中國學派的開創
殷瑞鈺 李伯聰
【摘要】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都首先在西方開創,而工程哲學在21世紀初分別獨立開創于中國和歐美,在四個關鍵方面,中國的開創步履甚至還早于歐美一年或數年。中國工程界和哲學界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跨界合作創新,形成了工程哲學的中國學派,提出了工程哲學的“五論”框架。“五論”之中,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是開拓工程哲學的理論前提,工程本體論提出工程是現實的、直接的生產力,是“五論體系”的核心。工程方法論、工程知識論和工程演化論也都是工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創新活動中,工程創新是創新領域的“主戰場”。在工程哲學這個新學科在國內外興起的過程中,工程哲學中國學派發揮了首創作用,發出了中國聲音,體現了中國自信,作出了中國貢獻。
【關鍵詞】工程哲學? 中國學派? 工程本體論? 工程方法論? 工程知識論
【中圖分類號】N02?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8.020
人類社會中,科學、技術、工程是三種不同類型的活動,分別以三者作為哲學研究對象,可以形成三個哲學分支: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工程哲學。
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都是西方學者開創的,然后傳播、輸入到中國。而在開創工程哲學的過程中,以往那種學科發展史的“老故事”和“舊情節”沒有再次重演。中國工程界和哲學界通過跨界合作互動,實現了原創性理論創新,率先獨立地走上了開辟工程哲學的大道。雖然歐美同行也通過獨立研究開創了工程哲學,但就幾個關鍵步履的“各自第一步”而言,中國與西方相比還早了一年或數年。
工程哲學是工程和哲學的交集。而在世界工程史和哲學史上卻長期存在“工程界不關心哲學,哲學界不關心工程”的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工程界和哲學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引下,逐步樹立“工程界學習和研究哲學,提高工程界的哲學覺悟”和“哲學界學習和研究工程,提高哲學界的工程覺悟”的新風格,跨界合作,協同創新,取得了原創性理論成果,提出了由“五論”(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工程本體論、工程方法論、工程知識論、工程演化論)構成的工程哲學理論體系框架,經過20余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工程哲學中國學派,對工程哲學這個新學科在國內外的興起和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發出了中國聲音,體現了中國自信,作出了中國貢獻。
21世紀之初工程哲學在中國和歐美同時興起
根據科學社會學關于一門新學科形成標志的理論,可把21世紀之初工程哲學形成的步履簡述如下。
工程哲學專門學術著作的出版。2002年,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今中國科學院大學)李伯聰出版《工程哲學引論——我造物故我在》,中國科學院時任院長路甬祥在為該書撰寫的序言中提到,這本書“是現代哲學體系中具有開創性的嶄新著作,屬于馬克思所說的關于改變世界的哲學”[1];2003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Louis L. Bucciarelli出版Engineering Philosophy(《工程的哲學》)[2]。2007年,中國殷瑞鈺、汪應洛、李伯聰等出版《工程哲學》[3];同年,Steen Hyldgaard Christensen等出版Philosophy in Engineering(《工程中的哲學》)[4]。
專業學術會議的召開。2004年,中國工程院召開了“科學發展觀與工程哲學”研討會,同年還召開了中國首次工程哲學會議(至今已經召開了10次全國性學術會議)。在歐美,2006年,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召開了工程哲學研討會;2006~2007年英國皇家工程院接連舉辦了7次工程哲學研討會;2007年在荷蘭召開了首次工程哲學國際會議(迄今已經召開了8次國際會議,其中第四次國際會議在北京召開)。
專門學術組織和研究機構的成立。2003年,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成立“工程與社會研究中心”,工程哲學是其基本研究任務之一;2004年,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工程哲學專業委員會正式成立,成為中國推動工程哲學研究的專門學術組織和學術平臺。2004年,工程研究國際網絡(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Engineering Studies)在巴黎成立,工程哲學是其重要內容之一。2006年開始的WPE(Workshops on Philosophy and Engineering,工程與哲學工作坊)在2010年更名為fPET(The Forum on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Technology,哲學、工程和技術論壇),決定每兩年舉辦一次國際會議。
有關學術期刊(輯刊)的出版。2004年,中國開始出版《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最初作為年刊出版,2009年,經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作為季刊出版,目前為雙月刊)。2009年,Engineering Studies(《工程研究》季刊)在美國出版。這兩個“同名期刊”在突出對工程的跨學科研究時,都明確地把工程哲學作為刊物的基本內容之一。2012年,Engineering Studies在創刊三年后就躋身SCI和SSCI期刊行列,這標志著包括工程哲學在內的跨學科工程研究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認可的一個新研究領域。
以上有關工程哲學開創步履的歷史軌跡表明:工程哲學是21世紀之初由中國學者和歐美學者“分別獨立開創”的新學科分支。在開創過程中,中國和歐美在出版學術著作、召開學術會議、成立學術組織、創立有關學術期刊四個方面都表現出了令人驚訝的“不約而同”和“同步”現象,而中國在這四個方面的第一步都略早于歐美(早一年,有的甚至早數年)。
應該承認,在開創工程哲學的進程中,歐美學者走上開創之路的步伐雖然稍晚且不同于中國學者,但他們也是獨立走上開拓工程哲學之路的。換言之,我們應該肯定“工程哲學是在中國和歐美分別同時開創的,而中國又稍稍在時間上先行”——這在學科開創史上實在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
雖然在學科開創初期,中國和歐美的學術交流較少,但隨著工程哲學的逐步發展,雙方的學術交流也在逐漸增強和逐步深入。
工程界和哲學界的跨界合作創新與工程哲學中國學派的形成
工程哲學是工程界和哲學界跨界合作創新的成果。如果沒有工程界和哲學界的跨界合作創新,就很難形成工程哲學。回顧歷史,石器時代已經有了“工程活動”,而哲學卻只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歐洲和中國的哲學都誕生在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期”。
哲學誕生后,哲學與政治、科學、倫理、醫學等領域都常有交集,可是,長期以來哲學和工程卻罕見交集。孟子有云:“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在當時的社會條件和環境中,流行觀念和主流意識形態都將工程活動視為“小人之事”,將政治、科學、倫理等領域視為“大人之事”。要在“不同類型的大人之事”之間形成交集比較容易,而“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之間就很難了。正是這個“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的鴻溝導致一方面在哲學界形成了忽視和貶低工程的哲學傳統,另一方面在工程界形成了對哲學敬而遠之和不問哲學的工程傳統。這種哲學和工程相互疏遠的傳統雖然在近現代時期有了某些變化,但其影響在20世紀仍然相當強大。
與這個傳統和狀況互為表里,在中國和歐洲歷史上都出現了許多“橫跨科學與哲學”“橫跨政治與哲學”“橫跨醫學與哲學”的“跨界學術成果”和“跨界人物”。然而,由于古代社會中直接從事工程活動的農民和工匠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程度較低,限制了其跨界思考哲學的條件和可能性,而哲學家由于鄙視體力勞動而“理所當然”地認為工程活動中沒有哲學問題。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原先的工匠階層分化為“現代工人”和“現代工程師”,并且這兩個階層的人數和社會影響都愈來愈大。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主要由工匠階層推動,那么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直接推動者就是現代工程師了。雖然某些具體人物可以身兼工程師和科學家兩種角色,但這并不妨礙我們肯定工程師和科學家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角色,二者有不同的本性和特征。
“現代科學家”是現代科學革命之后出現的社會角色與社會群體,而“現代工程師”則是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出現的。前者形成較早,其角色特征相對單純,角色自覺和角色社會定位進程都比較順利。
由于最初的現代科學家都是“業余科學家”,這就使他們在定義科學家角色性質和特征時具有了很大的自主性和角色自覺性。他們把科學家角色“定義”為真理追求者,斷定科學家沒有一己私利,是全人類價值的代表者。在這種角色傳統形成和固化之后,后來的“職業科學家”和社會輿論也沿襲性地接受了這一傳統觀點。
與現代科學家相比,現代工程師無論在角色社會定位方面還是角色思想自覺方面都遇到了更大的困難,其進程也滯后很多。
如果我們把國家科學院與國家工程院的成立分別視為科學界與工程界的“角色社會認可程度”與“角色自覺程度”的重要標志,那么可以看到,在英國,1660年就成立了皇家學會,它是世界上存在歷史最長而又從未中斷過的科學學會,在英國發揮著國家科學院的作用;而英國皇家工程院則于1976年才成立,比前者晚了三百余年。俄羅斯科學院成立于1724年,俄羅斯工程院成立于1990年,二者相差超過二百年。美國科學院成立于1863年,美國工程院成立于1964年,二者相差一百余年。
對于工程師的“角色社會功能認可程度”與“角色自覺”遲滯現象的形成,其深層原因就埋藏在工程師職業的內在復雜性和工程師的“角色功能張力困境”之中。
與“不直接參與”生產活動的基礎學科的科學家不同,工程師的根本特征是“直接參與”生產活動,這就使工程師與工人一起成為了從事工程活動、發展生產力的最直接的社會角色。一方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工程師”大多是現代工廠(企業)的“雇員”,這就使工程師與工人有了共同的“雇員身份”和直接參與生產活動的“職業特征”。另一方面,工程師又是“管理”工人的生產技術管理者,這又使他們與“雇主”有了某些共同點,具有“直接參與管理活動”的“職業特征”。應該強調指出,工程活動和科學活動的本性是有很大區別的,前者主要考慮社會功利性,而后者主要考慮科學真理性,這就使工程師的角色性質和工作特征復雜起來。正如一些人所描述的那樣,工程師是“邊緣人”——“部分是作為勞動者,部分是作為管理者”“部分地是科學家,部分地是商人(businessmen)”[5];“工程師既是科學家又是商人”“科學和商業有時要把工程師拉向對立方向。”[6]
這種角色和職業“張力困境”使工程師的角色自覺道路不可避免地更加漫長,更加曲折。正如工人階級在角色自覺的道路進程中經歷過“盧德運動”一樣,工程師在角色自覺的道路進程中也經歷過所謂“工程師的反叛”[7]。“從時間上看,后者比前者晚了大約一百年;從斗爭形式上看,前者采取了經濟斗爭和社會對抗的形式,后者采取了在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中進行‘制度內斗爭的形式;但二者都成為了標志一個特定階層在‘職業自覺方面的重要事件。”[8]雖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工程師的反叛”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在20世紀下半葉,各個產業性工程師學會在章程中也都陸續明確肯定了“工程師的倫理準則和社會責任”,成為了標志工程師“職業和角色自覺”的關鍵事件。
上述狀況與工程哲學在學科開創進程中的遲滯成為了互為因果的關系。
20世紀末期,情況發生了重要變化,不但“社會對工程的認識”有了新變化,而且“工程師的自我認識”也發生了改變。與這些變化互為因果,工程哲學也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了自身發展的醞釀期。在醞釀期之后,中國和歐美迅速地在21世紀之初進入了工程哲學的開創期。[9]
如果比較工程哲學在中國和歐美的開創進程,二者既有相同之處又存在差異。
1994年,中國工程院正式成立,這是中國工程界的一件大事。2000年,中國工程院又成立了工程管理學部。工程管理學部成立后,院士們一致認為在工程活動中存在著許多重大、深刻的理論問題,必須加強對工程管理和工程實踐的基礎理論問題和相關哲學問題的研究,這就形成了中國工程界“向哲學領域跨界合作”和提高“自身的哲學自覺意識”的新形勢和新力量。
同時,中國哲學界也認識到必須提高“自身的工程意識和覺悟”,形成了向工程界跨界合作的新趨向和新動能。在這方面,作為中國哲學界重要組成部分的自然辯證法領域的專家發揮了關鍵作用。馬克思指出:“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10]反思工程發展的歷史并面對改革開放后中國作為工程大國崛起的現實,中國自然辯證法界的專家深刻認識到哲學界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樣對“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熟視無睹了,以往那種“忽視和貶低工程的哲學傳統”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哲學專家必須“跨界”走向工程,研究工程中的哲學問題。
正是由于21世紀之初中國在工程界和哲學界同時出現了“跨界合作”和“相互呼應”的新形勢,中國工程院工程管理學部于2004年6月召開了工程哲學高峰研討會,七位院士和多位哲學專家參加研討。中國工程院時任院長徐匡迪親自到會并且發表了長達一個小時的重要講話。徐匡迪指出:“工程哲學很重要,工程里充滿了辯證法,值得我們思考和挖掘。我們應該把對工程的認識提高到哲學的高度,要提高工程師的哲學思維水平。”[11]
2004年12月,在中國工程院時任院長徐匡迪和理事長朱訓的直接指導下,中國工程院和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聯合舉辦了“工程哲學與科學發展觀”研討會,緊接著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工程哲學會議,正式成立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工程哲學專業委員會,殷瑞鈺任理事長,朱訓任名譽理事長,傅志寰、汪應洛、李伯聰等任副理事長。
從2004年開始,中國工程院工程管理學部以系列課題研究的方式組織工程師和哲學專家合作研究工程哲學,通過20余年持續、艱辛的學術探索,先后出版了《工程哲學》(第1版和不斷有新修訂的第2、3、4版)[12]、《工程演化論》[13]、《工程方法論》[14]、《工程知識論》[15]。通過這些學術著作的出版,中國工程師和哲學專家提出和闡釋了一個包括“五論”(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工程本體論、工程方法論、工程知識論、工程演化論)且以工程本體論為核心的、有原創性的工程哲學理論體系框架,使其成為了工程哲學中國學派形成的最重要的理論標志。
回顧工程哲學中國學派的形成過程,中國工程界和哲學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跨界合作、跨界聯盟和跨界創新是一個關鍵因素。這個跨界聯盟由兩大支柱或者說是兩股力量組成:一方面是以中國工程院工程管理學部為主力,還包括產業界和企業界的許多工程專家;另一方面是以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工程哲學專業委員會為主力,還包括高等院校和哲學研究機構的哲學專家。這個“聯盟”中包括了工程專家、工程管理學家、戰略工程師、哲學專家、人文學者等,他們分別供職于制造業、能源與礦業、交通運輸、土木建筑、航空航天、水利、信息通訊、國防軍工、醫藥衛生、金融、教育等不同領域。僅就參加“五論”撰寫的成員而言,就有中國工程院院士20人,哲學界、教育界學者30余人,工程界、企業界人士30余人。
“五論”的理論框架是中國學派的原創性理論成果,以下對其進行簡要論述。
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與工程本體論
中國學派工程哲學“五論框架”中首先提出的是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與工程本體論。
近現代以來,特別是在20世紀,中外許多學者都把技術和工程定義為“科學的應用”,這就成為了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行的“科學一元論”。依據這種觀點,許多學者和大眾傳媒都習慣性地把工程看作是“科學的應用”,把工程成就混同為或歸結為科學成就,例如,美國、蘇聯、中國在“航天工程領域”的成就往往都被認為是“科學成就”,而未能認識其“本來面目”乃是“工程成就”。
在21世紀之初,針對“科學一元論”,我國學者提出了“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指出科學活動的核心是發現,技術活動的核心是發明,工程活動的核心是構建;科學活動的主要成果是科學概念和科學理論,技術活動的主要成果是發明專利和技術訣竅,工程活動的主要成果是直接的物質財富;從管理原則和制度規范看,科學活動、技術活動和工程活動也具有迥然不同的管理原則和制度規范。由于科學、技術、工程是三種不同的社會活動,如果分別以三者為哲學研究的對象,就可以形成三個不同的哲學分支: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工程哲學。[16]于是,科學-技術-工程三元論就成為了我國學者研究工程哲學的理論前提,成為了工程哲學學科進一步遠航發展的“啟程碼頭”。
“近代哲學巨擘”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作為基本的哲學箴言,而工程哲學提出了與其迥然不同的哲學箴言——“我造物故我在”,這就旗幟鮮明地宣示:工程哲學屬于馬克思所說的“改變世界的哲學”。
在中國工程界和哲學界合作研究工程哲學理論框架的進程中,工程本體論的提出是一個關鍵進展。
本體論在哲學中具有根本地位,但它同時又是意見紛紜的理論領域。中國工程師和哲學專家在研究工程本體論時,立足工程實踐,明確提出,在人類社會中,“工程是直接的、現實的生產力”,強調其是與“工程派生論”迥然不同的“工程本體論”觀點,強調必須立足這一工程本體論觀點來分析和認識有關工程活動的各種問題。
工程本體論是立足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理論而提出的工程哲學理論。工程本體論認為,工程有自身獨立存在的歷史和現實根源、結構及其發展規律、目標指向及其價值追求,絕不能簡單地把工程看成是科學或技術的衍生物、派生物。從本體論觀點看工程,就是要確認工程的本根和本體地位,要依據現實直接生產力標準認識和處理工程活動中的諸多問題,由此而認識工程與科學、技術的相互關系。工程本體論肯定作為直接生產力的工程活動是最基礎、最重要的人類活動,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工程活動不但塑造了社會的物質面貌,影響著人和自然的關系,而且深刻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
人類不僅從事工程活動,還從事科學、藝術、宗教等其他形式的活動。工程本體論不但要回答工程活動的最根本性質的問題,而且要從根本上——而不是從具體內容和細節上——回答工程活動和人類其他重要活動類型和方式的相互關系問題。
工程本體論由于突出了工程活動是發展生產力的活動而不同于某些哲學家主張的自然本體論或物質本體論,由于突出了工程活動是以人為本的活動而不同于神學本體論。工程本體論的內容深刻而豐富,需要不斷發展,而不能對其進行教條化、簡單化的理解。
作為獨立方法類型的工程方法和工程方法論
雖然工程師、工人和工程管理者都很熟悉“具體的工程方法”,但是他們往往不太考慮“工程方法論”問題。
“具體的工程方法”不等于“工程方法論”。工程方法論是以工程方法為研究對象而進行哲學分析、哲學概括和哲學研究的過程和結果,是對工程方法的“二階研究”和“二階認識”。
雖然學術界有關“方法論”的論著數不勝數,并且也沒有人否認工程方法是一大類具體方法,但學術界卻鮮見有人研究工程方法論,這就使工程方法論成為了一個有待研究和開拓的新領域。
工程方法論之所以成為“方法論領域”中“被遺忘的角落”,原因有很多,就現代時期而言,其最重要的原因正是“科學一元論”的影響。
依據“科學一元論”——也就是“工程派生論”,“只需要有”并且“只可能有”科學方法論,而“不需要有”并且“不可能有”工程方法論,因為依據“工程派生論”觀點,工程方法僅僅是科學方法的“派生方法”和“附屬方法”,而不是一類“獨立類型”的方法,這就“堵塞”了工程方法論的獨立研究之路。
中國學者在研究工程哲學時,由于明確了工程本體論的基本觀點,立“本”行“道”,也就順理成章地在方法論領域得出了新認識和新結論:工程方法論并不是科學方法論的“派生理論”;必須肯定工程方法論是與科學方法論“并列”的方法論分支,必須把工程方法論作為一個獨立的方法論分支進行新的開創性研究。
立足于這些認識,中國學派在2017年出版了《工程方法論》[17]。這本書首次對工程方法論的內容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述[18]。以下僅強調工程方法論的兩個重要觀點。
一是關于工程方法與科學方法的相互關系。一方面,需要承認這是兩類不同的方法,二者存在根本區別,而工程方法論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要深入分析和研究工程方法與科學方法的不同之處;但另一方面,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否認二者存在密切聯系。例如,科學方法和工程方法在結構上都是“硬件”(有關工具等)、“軟件”(有關思想方法、程序等)、“斡件”(orgware,有關組織管理的原則和方法)的統一。可是,科學方法的“硬件”主要是科研儀器,而工程方法的“硬件”主要是工程設備。雖然科研儀器和工程設備也有某些重疊之處,但科學家和工程師都會承認科研儀器和工程設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類型,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在“斡件”方面,由于科研活動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科研活動的基本管理原則就是對科研活動的失敗應該有很大的寬容度,甚至上千次的失敗也“可以容忍”。而對于工程活動,由于它必須經過“事前的可行性論證”并且工程失敗的后果極其嚴重,甚至導致災難,人們無法容忍重大工程活動失敗后再來第二次[19]。
二是科學活動以追求真理為目的,科學方法必須是“保證走向真理的方法”。表現在“科學問題的答案”上,科學方法必須是“保證取得唯一正確答案”的方法。一方面,在邏輯思維領域,科學方法論特別重視演繹法和歸納法的作用和意義。由于在真理面前不能討價還價、沒有妥協余地,這也成為了對科學方法的“硬約束”。另一方面,工程活動以發展直接生產力為目的,表現在“工程問題的答案”上,工程問題必然可以存在多種可能性答案,而不存在“唯一正確答案”。工程方法論特別重視啟發法、集成法的作用和意義。工程活動中常常要運用“協調和權衡方法”進行“比較”“妥協”“選擇”,這就深刻影響了工程方法論和科學方法論的性質和相互關系。雖然絕不能把科學活動的“自然科學真理標準”和工程活動的“生產力標準”對立起來,但對于科學活動和工程活動來說,如果忽視或混淆了“科學活動和科學方法論”與“工程活動和工程方法論”在基本性質和評價標準上的根本區別,那就必然會危害科學與工程的發展。
作為獨立知識類型的工程知識和工程知識論
雖然在哲學傳統特別是歐洲哲學傳統中,知識論[20]一向受到重視,但由于多種原因,許多哲學家都僅僅關注對科學知識和倫理知識的哲學研究,而忽視了工程知識也是一個獨立的知識類型。許多哲學家都忽視和貶低工程知識,孔子更在與樊遲的對話中,直接把工程知識排除在儒家教學知識體系之外[21],這就使工程知識論成為了知識論領域中、被遺忘的“處女地”。
21世紀以來,通過艱辛的探索和研究,中國學派出版了《工程知識論》[22],首次對工程知識論這個領域進行了初步而比較系統的論述。筆者在此僅簡要討論以下三個問題。
(1)兩類物質世界和兩類知識體系的劃分是工程知識論的核心問題。
工程哲學認為需要承認有兩類物質世界:一類是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世界;另一類是人類出現以后才存在的“人工物”世界。二者成為了有本質區別的“兩類物質世界”。
與“兩類物質世界”相應,又有“兩類知識”——關于自然物世界的“(自然)科學知識”和關于人工物世界的“工程知識”。在探討“兩類物質世界”與“兩種知識”的相互關系時有兩個關鍵的認知前提。第一,在沒有人類認識和人類知識的情況下天然物質世界已經存在了,它是“不依賴于人的認識而存在”的,是“無人類知識內蘊”的客觀的自然物質世界。第二,如果沒有相應的人類知識“在先”,就不可能出現人工物,所以它是“有知識內蘊其中”和“依賴于人類認識而存在”的物質世界。
許多古代哲學家在認識人類知識時都特別關注了人類的知識與外部自然界的關系和聯系,這固然是正確的觀點,可是他們卻忽視了另外一類知識——有關“人工物”的“創造”和“使用”的知識。就對象范圍看,“自然物世界”遠遠大于“人工物世界”,而就對人類的生活影響看,“人工物世界的影響”又遠遠大于“自然物世界的影響”。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作為唯物主義者的費爾巴哈“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甚至連最簡單的‘感性確定性的對象也只是由于社會發展,由于工業和商業的交往才提供給他的”[23],這實在是一個很尖銳、很深刻的批判。
(2)從知識的內容和本性看,科學知識主要是對自然界和自然物的反映性知識,而工程知識主要是對人工世界和人工物的設計性、工程集成性、價值性知識。
從過程上看,“天然自然界”是“在先”的已存在的對象,科學活動是“在后”的認識過程,科學知識是科學認識的結果。而對于人工物的創造過程來說,卻是要“先有”工程決策和工程設計,即工程知識“在先”。工程知識位于工程活動的“起點”,而人工物位于工程活動的“終點”。如果沒有在先的工程決策和工程設計知識,就不可能有作為目的和結果的人工物存在。
從本性上看,科學知識是對天然自然界的“反映性”知識,而工程知識是關于人工物和人類行動的“設計—構建性”知識。如果使用哲學家常用的“實在”這個術語,可以說,科學知識是關于“已有的實在”的反映性知識,而工程知識是關于人類頭腦中的“虛實在”及其“現實化”的“工程構建和集成”的價值性知識。
(3)在工程知識論領域,工程設計知識、工程集成知識、工程管理知識、工程評估知識、默會性工程知識、操作性工程知識均具有重要意義,而這些知識內容和形態都是以往的“知識論研究”所忽視的知識內容和形態。
由于人工物又被稱為“器”,工程知識論也可被稱為對“器”和“器理”的研究;而自然科學可被視為對“(自然)物”和“物理”的研究。由此角度認識工程知識論,可以看出工程知識論研究是整個知識論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的重要標志,意義十分重大。[24]
工程演化論與作為國家創新活動主戰場的工程創新
工程是不斷演化的,于是,工程演化論也成為了工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工程演化研究和工程創新研究有著密切、內在的聯系。
創新理論是熊彼特首先提出來的。作為經濟學家,熊彼特主要是把“創新”作為一個經濟學概念提出來的。熊彼特明確提出,發明不等于創新,技術和經濟之間有可能出現不一致的情況。他尖銳指出:“經濟上的最佳和技術上的完善二者不一定要背道而馳,然而卻常常是背道而馳的。”[25]
目前,創新研究已經成為一個研究內容復雜、研究對象多樣的領域,不但要研究各種各樣的創新形式和類型(包括技術發明、知識創新、工程創新、制度創新等),又要研究多種多樣的創新主體(包括企業、研究機構等)。在認識工程創新和知識創新的相互關系時,以下兩點值得特別注意。
在創新動力方面,科學發現的直接動力往往來自科學自身理論邏輯的內在要求,而工程創新的直接動力主要來自經濟、社會發展的社會需求。與此密切相關,在心理活動方面,好奇心常常成為推動科學家新發現的關鍵心理要素。沒有對科學奧妙的好奇心就難以發現科學問題和提出新的科學理論,科學就無法演進。而對于工程創新進程來說,推動工程師創新和推動工程演化的首要心理要素不是“好奇心”,而是工程師面對社會需求而產生的“社會責任心”。正是直接出于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強烈責任心,工程界人士才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工程創新之路。如果說在科學發現領域,科學家的“好奇心”往往是關鍵的心理要素,那么,在工程創新領域,工程師的“責任心”往往就成為了最關鍵的心理要素。
從工程演化論和工程哲學觀點看創新,中國學派提出了一個新的重要觀點:工程創新是創新活動的主戰場。
工程活動是技術要素群和非技術要素群(諸多經濟、社會要素)的集成和統一,必須從“全要素”和“全過程”的觀點認識和把握工程活動。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以“可重復性”為基本特征,而作為直接生產力的工程活動以“唯一性”(例如,京滬高鐵和青藏鐵路都是具有唯一性的工程活動)和“當時當地”為基本特征,這就使創新必然成為工程活動的內在要求和特征。縱觀歷史,世界各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歷程就是一個不斷進行工程創新的過程。工程創新能力直接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是興起或衰落。正如戰爭中既需要有“偵察兵”也必須有“主力軍”一樣,在“創新之戰”中既要有相當于偵察兵的研發機構創新,也要有相當于主力軍的企業創新。正如軍事活動中偵察兵和主力軍的相互作用、相互協同是軍事勝利的關鍵一樣,能否正確處理“研發領域的創新”和“工程主戰場的創新”的相互關系也就成為了工程創新和產業競爭力發展的關鍵。人們絕不能忽視研發機構的偵察兵的作用,但也絕不能把偵察兵和主力軍混為一談。沒有優秀的偵察兵,主力部隊往往就沒有正確的作戰方向,但指揮員也不可能僅僅依靠偵察兵進行決戰。工程創新是創新活動的主戰場,人們必須強化在主戰場上見勝負的概念和意識,不但必須重視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而且更要重視工程創新,必須深化對“工程創新是創新活動主戰場”的認識[26]。
結語
就工程哲學作為一個分支學科和基本理論而言,它是全人類的學術公器,無所謂國家分野或族群分野。可是,就研究者的思想指導、理論創見、學術進路而言,不同國家的學者又會有自身特色,甚至形成不同的學派。從這方面看,工程哲學中國學派的形成,意義重大。在工程哲學這個新學科在國內外興起的過程中,工程哲學的中國學派發出了中國聲音,傳遞了中國話語,敘述了中國故事,作出了中國貢獻,顯示了中國自信。
工程哲學中國學派具有和表現出了以下幾個重要特征。
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以發展現實生產力、直接生產力為理論核心,以工程本體論為基本立場,努力正確認識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社會其他要素的辯證關系。
二是努力改變歷史上工程界和哲學界相互疏離的現象,持續推進工程界和哲學界相互學習、相互滲透和跨界合作。
三是努力通過艱辛的理論探索獲得了一批原創性理論成果,提出了以工程本體論為核心的工程哲學“五論”理論體系框架。
四是堅持工程哲學理論和工程實際密切聯系的原則,深入工程實踐調查研究,堅持理論研究和案例研究并重。
五是世界眼光和立足中國本土實際相結合,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中國學派、中國話語的建設結合起來。
目前,工程哲學仍處于學科發展的初創階段,展望未來,工程哲學的中國學派應該努力作出更大貢獻。
注釋
[1][16]李伯聰:《工程哲學引論——我造物故我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1頁、第10~12頁。
[2]L. L. Bucciarelli, Engineering Philosophy, Netherlands: Delft University Press, 2003.
[3]殷瑞鈺、汪應洛、李伯聰等:《工程哲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4]S. H. Christensen; M. Maganck and B. Delahousse (eds.), Philosophy in Engineering, Denmark: Academaca, 2007.
[5]S. Beder, The New Engineer, South Yarra: 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 PTY Ltd, 1998, p. 25.
[6]E. T. Layton, The Revolt of the Engineer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886, p. 1.
[7]E. T. Layton, The Revolt of the Engineer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886.
[8]李伯聰:《關于工程師的幾個問題——工程共同體研究之二》,《自然辯證法通訊》,2006年第2期。
[9]殷瑞鈺、汪應洛、李伯聰等:《工程哲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6~44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7頁。
[11]趙建軍:《工程界與哲學界攜手共同推動工程哲學發展》,杜澄、李伯聰主編:《工程研究》第1卷,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年。
[12]殷瑞鈺、汪應洛、李伯聰等:《工程哲學》(第1、2、3、4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013、2018、2022年。
[13]殷瑞鈺、李伯聰、汪應洛等:《工程演化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14][17]殷瑞鈺、李伯聰、汪應洛等:《工程方法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
[15][22]殷瑞鈺、李伯聰、欒恩杰等:《工程知識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18]對于《工程方法論》是否可以被認定為國內外的“第一本工程方法論”著作,需要進行以下兩點說明。一是此前已經有若干以“工程方法論”為書名的著作,但其具體內容都是關于“具體工程方法”的論述,而非對“工程方法論”的研究和論述。二是美國工程師科恩在2003年出版了《方法談:工程師解決問題的進路》(Dicussion of Method: Conducting the Engineer's Approach to Problem Solving),必須承認這本書是具有“工程方法論特征”的著作,但其主要內容是著重論證“啟發法”是特征性的工程方法,而不是對“工程方法論”理論體系的全面論述。如果可以認定科恩的著作是“第一本工程方法論”著作,則《工程方法論》就只能被認定為“第二本工程方法論著作”或“第一本論述工程方法體系的著作”。
[19]某些重大工程也可能以失敗告終,例如,美國塔科馬大橋的坍塌。對于這類事件,需要從另外角度分析和研究。這類事件沒有成為也不可能成為設計師“在設計時”就“準備”“工程失敗”的理由。
[20]對于“認識論”(epistemology)和“知識論”(theory of knowledge)的關系,我國學者認識不一。有人認為存在區別,也有學者認為沒有區別。
[21]在《論語·子路》“樊遲請學稼”章中,孔子明確地拒絕了樊遲要求學習農業知識(廣義的工程知識包括農業知識在內)的要求。此章最后一句話是“焉用稼?”這就明確地在儒家教育體系中排除了學習農業和工程知識的要求。
[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頁。
[24]李伯聰:《哲學視野中的“物”和“器”與“物理”和“器理”》,《哲學分析》,2021年第3期。
[25]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何畏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8頁。
[26]李伯聰:《工程創新:聚焦創新活動的主戰場》,《中國軟科學》,2008年第10期。
責 編∕李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