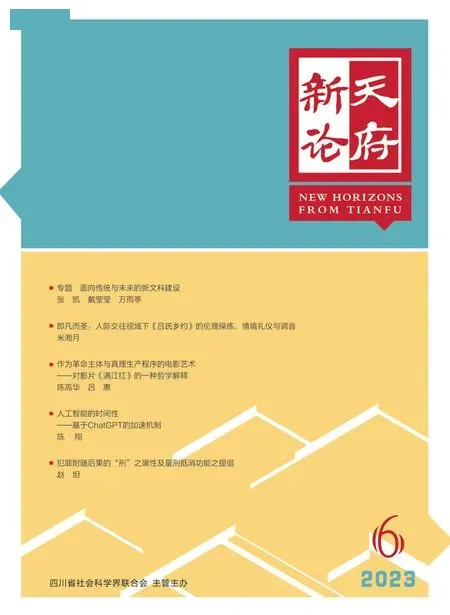情感及其規制:數字時代情感的意識形態審視
鮑 金 黃 婧
馬克思強調“在不同的財產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象、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8頁。,直接指明了意識形態與情感的內在勾連。由算法與大數據等核心技術架構的數字空間作為意識形態的新型場域,借助強刺激性的情感敘事有效調動了主體的非理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情感與意識形態的現實鏈接,凸顯了意識形態的情感之維。數字空間的意識形態樣態逐漸從追求理性規范轉向建構感性敘事。在此意義上,分析數字場域意識形態情感向度的內在邏輯具有重要意義。當前,厘清情感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分析數字時代意識形態變化的新增長點,部分學者在感性意識形態的范疇下展開了相關研究。例如,陳聯俊指出“感性意識形態與主體之間存在著共通關系,個體心理活動中的認知、感覺、情感、記憶、幻想、推理都會體現出個性化表征”(2)陳聯俊:《移動網絡空間中感性意識形態興起的價值省思》,《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2期。,宋辰婷強調感性意識形態“使得廣大網民達成了價值和情感上的共鳴”(3)宋辰婷:《網絡時代的感性意識形態傳播和社會認同建構》,《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任春華認為“感性意識形態的有效傳播需借助民眾精神世界中的情感力量”(4)任春華:《網絡空間中的感性意識形態:基本特征與傳播機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上述研究往往將情感簡化為感性意識形態的一個要素,較少探討情感與意識形態的直接關聯,這無疑弱化與遮蔽了情感在數字空間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影響。意識形態情感向度是如何在數字空間中凸顯而出的?意識形態情感向度運行邏輯是什么?如何辯證看待意識形態情感向度的雙向影響?尤其是如何應對情感敘事所引發的極端輿論風暴以及意識形態風險?結合數字技術,從意識形態的情感之維出發,思考并回答上述系列問題,是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與引領力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一、情感:數字技術變革下意識形態的重要向度
柏拉圖在《蒂邁歐篇》將人的靈魂劃分為理性與非理性(情感、欲望與意志),其中非理性部分是“惡劣部分”,因而真正的德性就是用理性壓制非理性。西方哲學中理性與非理性的結構性關系在柏拉圖處奠定了基本論調。從斯多亞學派的“消除激情”、笛卡爾的“理性—情感二分”、斯賓諾莎的“情感的奴役”到弗洛伊德的“情感的鎮靜”,將理性泛化并且凌駕于情感之上成為西方哲學視野中的主流線索。在新教觀念的影響下,資本現代性對理性主義的追崇進一步加重了情感的遮蔽與抑制。隨著晚期資本主義向后福特—新自由主義演進,放縱與激情等情感逐漸從理性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邏各斯現代性”逐漸轉化為“愛洛斯現代性”(5)Wang Ning,“Logos-modernity,Eros-modernity,and Leisure”,Leisure Studies,Vol.15,No.2,1996.。與此同時,尼采的權力意志論、康德的道德情感理論、海德格爾的現身情態思想與德勒茲的情動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當下西方人文學界的情感轉向。進入數字時代,數字技術的更新迭代進一步拓寬了情感的表達空間,豐富了情感的符號化在場范式。
數字技術變革衍生出高自主、強交互、深鏈接的技術生態系統,不僅結構性地嵌入并重塑現實社會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也顛覆了技術與人的互動維度與層次。機械時代和信息時代的傳統技術由于機械屬性的限制,只能與人的身體發生無意識與單向度的交互,甚至為了技術體系的程序式運作而壓抑人的感情。相較之下,數字技術借助數字終端所構建的立體化媒介場景則實現了視覺、聽覺與觸覺的全方位聯通與沉浸式體驗,進而在感官共鳴與感性共意中達成了對數字用戶情緒的喚醒和調動,數字空間的理性表達在一定程度上讓渡于情感輸出。與此同時,數字空間的情感宣泄所創造的快感也使得個體更加依賴數字技術對情感體驗的介入。數字空間逐漸代替現實場景,成為個體情感表達的重要場域。數字資本與數字技術聯袂合謀,瞄準了情感操控與爭奪的新靶向,建構起情感控制的技術架構。人的意識隨著“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頁。,數字技術的情感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意識形態的呈現樣態,情感躍升為影響主流意識形態吸引力與凝聚力的重要維度,意識形態情感向度的凸顯成為數字空間意識形態發展的重要趨向。
“身體—情感”的具象聯結被數字技術割裂,情感嬗變為“數字身體”支撐下游離于數字空間的擬態存在,以情感傳播與共振為特征的意識形態樣態逐步形成。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主張身體是知覺的主體,人正是作為客觀身體與心靈所辯證構成的身體而知覺世界,“身體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擁有一個身體,對一個生物來說就是介入一個確定的環境”(7)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13頁,第2頁。,“意識是通過身體以物體方式的存在”(8)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13頁,第2頁。。布迪厄實踐理論對身體與社會結構相互作用的闡述也同樣指向了身體與情感表達的關聯。身體不是客觀對象而是表情達意的意向性結構,我們只有在身體與世界的原初關系中,才能獲得對世界更加真實確切的知覺。情感內在地粘連在身體結構之中,因而,情感的生發與表達需要以在場的身體為基礎。然而,聯通各域的數字技術創設了架構在現實社會基礎上的數字空間,將現實身體阻隔在算法與數據之外,并借助數字符號將現實身體重塑為“數字身體”和“影子身體”(shadow body)(9)Stalder F.,“Privacy is not the Antidote to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Society,Vol.1,No.1,2002.。身體與情感的現實聯結隨之斷裂,情感體驗不再局限于當下的身體交往與現實經驗,而是吸附于數字空間中虛體與虛體間的數據關系。身體的缺場使得數字用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現實場域的在場束縛,情感成為數字身體在場中自由流動與脫域傳播的擬態存在,并在扁平化與去中心化的技術生態中加速復制與放大。在此基礎上,融合在數字技術中的意識形態要發揮功能效用,需要借助相應的“技術—情感敘事”捕獲和控制個體情感,形成數字用戶相互感染、共情與模仿的情感機制,將分散與流動在各數字終端的個體情感聯結起來,在情感共振的基礎上達成數字空間背后的價值共鳴,進而形成數字空間意識形態的情感認同。
數字技術對情感全景敞視與精準模塑的權力布展,使得擬態情感的生產與互動被賦予相應的意識形態屬性與價值立場,并成為當前意識形態斗爭的關鍵環節。數字技術已經不可逆轉地將社會的各個領域裹挾進數字化浪潮之中。一旦數字用戶踏入算法所構建的數字生態系統中,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技術、權力與資本設置的隱蔽的“全景敞視監獄”,進而被數字平臺操控與誘導。數字用戶在平臺的逗留時間、瀏覽內容、點贊與評論次數都將以數據的形式被納入算法的評估系統之中,用以分析與衡量用戶的情感傾向。多模態情感腦機接口與ChatGPT等新型技術甚至能夠精準地量化表征個體的情緒感知,將原本意會默存的情意敞開在細密、液態與流動的監視之網中。以情感為對象的算法“監獄”雖然顛覆了福柯所指認的監控范式,但是“監視技術產生權力效應”的實質仍未改變。在情感的歷史數據的基礎上,數字技術精準架構起重塑與操控情感的技術模型,個體在數字平臺上所產生的情感體驗被預先納入了數字權力的規劃與安排中。數字空間的情感不是個體基于當下經驗而綻出的本真情感,而是技術控制者調控算法參數的結果,承載著技術權力操控者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在數字用戶所無法接觸到的后臺,技術的掌控者可以依據情感策略將情感因素植入文字、視頻、音頻之中來喚醒用戶的特定情緒,通過特定的情感敘事誘導輿論場的情感導向。數字空間的情感會通過算法推薦機制在數字圈層快速共享與傳播,進而形成一定的情感風暴。總之,數字平臺所呈現出的信息在經由包裝與加工后,往往借助情感介質影響用戶與意識形態的互動過程,進而控制用戶的思想認知與價值觀念。數字時代的意識形態往往傾向于通過操控大眾情感來開展意識形態斗爭。
二、意識形態的情感向度:數字情感的縫合與驅動機制
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情感轉變為意識形態的重要維度,承載著一定的意識形態屬性。數字時代意識形態情感向度的作用機理表現為,數字空間的情感敘事在生活化的情感互動過程中潛在地傳遞著特定的價值立場與思想觀念,通過制造無意識的意識形態幻象實現數字用戶的情感縫合與固定,進而完成對其他主體的質詢與召喚,最終實現情感認同的意識形態目標。
首先,數字技術將情感編碼與構序為“數據—情感”結構,情感逐步理性化并被納入算法的計算模型中,數字空間的情感治理范式在此基礎上被建構起來。隨著小數據時代向大數據時代的跨越,一切人與物只有將自身虛體化為非實體性存在即數據,才能獲得數字空間的“入場券”。數據霸權使得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交流都必須建立在數據的基礎上,一切數字化存在物都必然受到數據的中介。情感作為主體互動情境的重要構成,也不可避免地嬗變為數字秩序中的數據流,轉變為由二進制代碼轉譯的數字情感。在現實世界,情感是身體基于當下經驗所誕生的表達行為與自主反應,快樂、悲傷、憤怒、嫉妒等情緒是主體情境性、體悟性、意向性的默會之意。然而,數字空間中的情感一方面在“數據—情感”的結構性存在中被理性化與量化為能夠被測量和評估的抽象符號,另一方面在主體間的情感交流中被主體自發地客觀化為視覺符號與外在標簽,“為了遇到網絡上虛擬的他者,自我也需要經歷一系列的步驟,即反思性的自我觀察、內省、自我定位以及描述自己的品味和觀點”(10)伊娃·易洛思:《冷親密:為什么愛越來越難》,汪麗譯,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16頁。。算法技術將可計算的情感數據納入訓練后臺中,根據情感分析、演算與推理的數據模型建構用戶的情感畫像,以此實時掌握用戶的情感變化,情感成為“被計算”的技術性存在。當前,情感模型已經被廣泛應用于各大主流數字平臺,甚至出現了百度情感分析、訊飛自然語言處理等專門計算與評估用戶情感的智能服務。算法與數據對情感的雙重技術統攝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情感的質性特征,將情感通約為可計算的量性存在。
基于情感的數據化及算法處理,一種數字空間的情感治理術被締造而出。作為數字用戶進行虛擬交往的重要場域,數字空間為個體情感的流動、傳播與聚集提供了全新渠道,因而吸附著海量的非理性因素。如何基于情感數據研判輿情發展趨勢、精準投放商業廣告、合理推送相關信息成為數字平臺增強用戶黏性與維護情感秩序的重要需求。數字時代,情感的數字化使其祛序為易于被技術操控的結構化數據流,在此基礎上,一種全新的情感治理范式逐漸生成。當前,數字空間的情感治理范式主要包括情感監視—情感測量—情感調節三個環節,三者共同構成情感治理的閉環模式。相較于傳統的情感治理范式,數字化的情感治理術以算法與數據為底層技術架構,能夠通過自然語言處理、面部識別、人工標注等方式敏銳地捕捉與分析用戶的情感傾向。與此同時,多媒介相互融合的柔性敘事也能夠更加高效地實現情感調控,將情感放置在預期的控制軌道之中。數字時代的情感治理術通過對情感數據的液態式全域監視,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情感控制的效度。
其次,數字用戶在消費構境下實現情感互動與共振,虛擬情感所承載的價值觀念通過情感消費滲透進日常生活。數字時代,勞動逐漸出現非物質化趨勢。哈特與奈格里指出,非物質勞動“可以稱為心腦勞動,其中包括服務業、情感性勞動以及認知勞動”(11)哈特、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9頁。,其中,情感勞動是非物質勞動的主要類型。勞動的情感化轉向使得情感的塑造與生產愈加重要,并且直接帶動了情感消費的發展。情感消費是指通過生產與加工過的愉快、輕松、激動等情感體驗來滿足自身的情感需求,“情緒化設計(Emotional Design)塑造了情緒模型,建構了將消費最大化的情緒典范。今天,我們最終消費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情緒”(12)韓炳哲:《精神政治學》,關玉紅譯,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62-63頁。。在數字空間,數字平臺的開放式發展使得單一的情感消費者身份發生了演變,情感消費與情感生產在用戶身上出現重疊,數字用戶既是情感生產者也是情感消費者。這種產消合一的形式模糊了本真情感與虛擬情感的界限,使得個體被卷入無處不在的情感景觀之中。情感景觀所創造的多模態情感敘事媒介能夠將用戶徹底包裹在情感敘事氛圍中,并通過點贊、評論、彈幕等圈層化的情感交互工具來刺激與加固用戶的情感體驗,形成強烈的情感共振與心理共意。然而,數字平臺上的情感消費存在閾值無限提升的問題,一旦用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情感體驗,就只能通過追求更新奇和更強烈的情感刺激來滿足需要,即一種注重新奇性乃至嗜新癥(neophilia)的傾向(13)Simon J. Williams,Emotion and Social Theory:Corporeal Reflections on the(Ir)Rational,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1,p.116.。正是在對情感景觀的象征性符碼的不斷追逐中,數字用戶越來越依賴于情感消費。情感消費已經成為連接日常生活與數字空間的橋梁。
在數字時代情感消費的構境下,數字用戶的日常生活被多元化的情感景觀包圍,數字情感已然深刻嵌入用戶日常的交往實踐中。然而,情感消費所創造的虛擬情感并不是純粹指向情緒本身,而是蘊含情感敘事背后的隱喻意義,“意義是被表征的系統建構出來的”(14)斯圖爾特·霍爾:《表征:文化意象與意指實踐》,徐亮、陸興華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1頁。。虛擬情感內蘊著情感勞動者、數字平臺操控者以及群體情緒傾向相互耦合所形成的價值立場與思想觀念。數字用戶在進行情感消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虛擬情感所承載的價值觀念的影響。其一,情感消費者與情感勞動者在數字平臺上建立“準交往關系”并形成相應的情感聯結,情感勞動者自身的思想方式與價值理念將通過數字交往傳遞給情感消費者。其二,數字平臺是數字時代情感消費的重要場域,平臺操控者能夠憑借絕對的技術優勢控制數字情感的呈現、遮蔽與流動狀態,因而數字用戶所接觸與消費的情感也相應地吸附著平臺的價值立場。其三,數字空間的情感消費具有公共性與共享性,即情感消費往往同時發生在具有相似情感偏好的網絡圈層之中,消費者通過評論與彈幕實時互動。有鑒于此,消費者個體的情感傾向往往易于受到其他消費者的影響并形成強烈的情感共鳴。總之,情感敘事借助感性意象“能指”與“所指”所映射的價值觀念以及所關聯的情感機制,實現了多元價值理念的隱蔽化、廣泛化與生活化傳播。
最后,虛擬情感通過意識形態幻象的質詢來實現數字用戶的情感認同。阿爾都塞創造性地從主體建構維度描繪了意識形態功能的實現過程:“意識形態將個體當作屬民質詢”(15)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項研究的筆記)》,載齊澤克等:《圖繪意識形態》,方杰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68頁,第178頁。。質詢是指個體被帶有權威性的聲音詢喚后,主動占據其在社會秩序中被指定的位置。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質詢就是意識形態把個體詢喚為特定的主體,使他自覺認同自身作為社會功能代理人的身份。個體在意識形態的質詢之下接受意識形態為自身安排的角色,同時也希望意識形態能夠承認自己的特定價值。在主體與意識形態的雙向交互過程中,個體逐漸成為意識形態的臣民。唯有如此,個體才“能夠自由地服從于大寫主體的訓誡,也就是,以便它能夠(自由地)接受他的屈從地位,也就是說,以便他將會‘完全獨立地’做出他屈從的姿態和行動”(16)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項研究的筆記)》,載齊澤克等:《圖繪意識形態》,方杰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68頁,第178頁。,意識形態正是通過詢喚機制實現社會關系的再生產。然而,質詢于其中的意識形態大他者極有可能具有不一致性。對此,齊澤克強調在阿爾都塞質詢理論的基礎上借助意識形態幻象加以縫合,“眾多‘漂浮的能指’,眾多原型意識形態要素,被結構成一個統一的領域;這是通過某一‘紐結點’(nodal point)——拉康所謂的‘縫合點’——的干預完成的,它將它們‘縫合’在一起,阻止它們滑動,把它們的意義固定下來。”(17)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季廣茂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21-122頁。
上述意識形態理論無疑為理解數字空間的情感敘事對個體情感的縫合與驅動機制提供了重要線索。數字平臺的情感敘事對特定的意識形態進行層層轉喻、編碼與計算,使其有機嵌入用戶的情感體驗之中,隱蔽地向數字用戶傳遞著特定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這種情感敘事借助數字技術快速激發情感的先天優勢,為情感消費建構了以特定價值取向為主的意識形態幻象。一旦數字用戶進入這種消費構序,將不可避免地被感覺刺激與審美享受禁錮在情感敘事之中,并在“虛假的情感需求”的驅動下進入情感敘事所遮蔽的意識形態網絡,困于情感符號所建構的意識形態幻象中無法自拔,進而在意識形態質詢中接受大他者的主體性建構。數字用戶通過意識形態的鏡像結構獲得相應的社會身份并且實現對意識形態的屈從。在多元的意識形態情感敘事中,齊澤克所謂的“主人能指”將以回溯性的方式縫合其他的意識形態元素,進而實現數字空間的情感認同。這種情感認同以潛意識的方式影響數字用戶的思想觀念,使參與數字消費的個體形成價值共鳴,進而追隨情感敘事所承載的意識形態。
三、賦能與解構:數字時代意識形態情感向度的辯證解讀
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情感敘事與價值觀念的有機耦合致使意識形態的作用機制出現變革,情感成為數字空間意識形態生產與傳播的重要介質,并逐漸凸顯為意識形態的重要之維。當前,數字空間的意識形態情感向度呈現出如下特點:其一,具有相似情感需求的數字圈層成為意識形態生產、傳播與擴散的重要場域。相近的情感訴求是締結數字用戶的重要紐帶,不同的情感符碼象征著特定的數字圈層。數字圈層在情感能量的驅動下發動互動儀式鏈,使主體形成對情感敘事所內含的意識形態的自覺認同。其二,數字平臺場景成為意識形態情感向度發揮效用的重要載體。作為現實場景的想象性再現與創造,數字場景將數字圈層納入自身立體化和感官化的擬真世界中,為數字用戶創造出輕松愉悅的情感烏托邦,是意識形態情感向度生效不可或缺的載體。其三,意識形態的情感向度易于出現同向凝聚與兩極分化的極端傾向。數字圈層營造的情感氛圍具有強大的感染力,能夠使個人情緒被放大為群體情緒,圈層內部易于出現強烈的情感同向共振傾向。然而,不同數字圈層在對待同一個社會事件時往往會表現出不同的情緒與情感反應,甚至可能出現由情感對抗導致的情感兩極分化的現象。由此可見,意識形態的情感向度具有雙面性,即意識形態的情感向度既有可能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生產、傳播、擴散的強大助益,也有可能嬗變為解構與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阻礙。
數字空間的情感敘事是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力與感召力的重要增量。數字空間的情感敘事在聚焦個人非理性之維的基礎上,借助數字技術創造出獨特的情感體驗。情感敘事的興起致使意識形態的內容表達、傳播特征與互動機制逐漸趨向感性化。其一,從意識形態內容表達上看,情感敘事摒除了純粹文字與語言敘事的枯燥性,有機融合了圖像、視頻、文字等多模態媒介,能夠在充分調動人的感性因素的基礎上建立起立體、鮮活、豐滿的意識形態形象。情感敘事顛覆了意識形態以理論體系為根基、以話語言說為核心、以邏輯推理為前提的傳統表達范式,將抽象的理論觀念具象化為視覺場景,將政治性與嚴肅性的話語娛樂化為貼近生活的網絡熱詞,將嚴謹的邏輯敘事碎片化為感性內容的拼接。這種情感化表達擺脫了意識形態“高高在上”的高勢位姿態,注入了對大眾的情感關照,滿足了數字用戶的情感需求。與此同時,情感敘事借助強化情緒的背景音樂、短小精悍的內容結構和極具觀賞性的視覺畫面,生成了一種撲面而來的瞬時沖擊漩渦,將數字用戶卷入情感體驗背后的意識形態之網,使得主流意識形態更容易被認同與接受。其二,從意識形態傳播特征上看,日常生活的情感滲透有助于實現意識形態的生活化傳播。在數字技術廣泛嵌入日常生活前,意識形態往往借助報紙、圖書與雜志進行傳播。受篇幅、場景與空間的限制,這種傳播方式只能盡力以理性言說的形式呈現意識形態內容,并且在有限的時空場域中展開意識形態宣傳。數字空間的情感敘事以數字技術為底層架構,有效地連接了虛實兩重空間,最大限度地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維度的限制,能夠隨時隨地實現意識形態滲透。與此同時,情感體驗作為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成為意識形態切入日常生活的最佳途徑。數字空間的情感景觀無縫嵌入數字用戶的日常生活,借助情感控制實現了意識形態規訓,“隨處可見的景觀實現了意識形態的具象化和碎片化控制”(18)居伊·德波:《景觀社會》,張新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36頁。。其三,從意識形態的互動機制來看,數字圈層的情感互動突破了單向性的說教式傳播模式,有助于在整體雙向互動的基礎上實現群體的情感共鳴。傳統的意識形態互動機制具有單向性與中心性,以上位者的單向灌輸為主的意識形態互動機制難以讓大眾形成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真正認同。數字圈層的演變使得數字用戶能夠借助數字平臺實現與意識形態傳播者的雙向情感交互,同時,圈層內部也能夠達成整體性的交流互動,進而減少意識形態互動的低效、盲目和灌輸屬性。
不可否認,情感敘事借助數字技術有效激發與傳播了群體情緒與群體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意識形態在數字空間中的快速滲透,成為提升主流意識形態認同度的有效助益。但是,意識形態情感向度的凸顯使得數字空間充溢著不同的情感樣態,不同利益集團所在的數字圈層都能夠借助情感景觀散播群體的價值觀念,進而加劇意識形態格局的復雜性。意識形態的情感向度有可能嬗變為影響數字空間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最大變量。
數字圈層極易成為大規模情感煽動的對象,并在情感風暴的裹挾下被卷入輿論場的斗爭與博弈,進而影響主流意識形態的結構性安全。數字空間無時無刻不充斥著海量的情感敘事,一旦數字用戶進入數字技術場域,不可避免地被各種情感景觀包圍,甚至在群體圈層中不自覺地生產與傳播情緒,進而陷入情感交互、快感享受、盲目追從的集體狂歡之中。滲透進數字圈層的情感在不斷煽動個體情緒與推動群體情感極化的過程中,隱蔽地傳播著情感內蘊的價值觀念與思維邏輯,將數字圈層裹挾進輿論場的激烈博弈中。情感傾向的交鋒是價值取向的交鋒,相悖的情感立場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意識形態的對立。這一現象的出現是技術、情感與平臺相互耦合的結果。其一,從技術邏輯上看,數字空間的身體缺場與符號表征解構了現實身份規訓下的話語限制,重塑了虛擬世界的身份與交往語境。在數字場域下,個體的情感表達與交往常常具有隨意性與非理性的特點,導致大量網絡謠言、暴力與極端話語的滋生與泛濫,并有可能在數字場域的傳播過程中煽動公眾情緒,引爆數字輿論場。其二,從情感邏輯上看,數字空間的情感敘事往往是碎片化的無序表達,感性化的敘事方式雖然提升了情感的傳播效率,但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理性話語的敘事邏輯,容易簡單化甚至歪曲和遮蔽事件的本真面貌。這種敘事邏輯使得個體易于在非理性化語境下做出情緒化、極端化的情感表達,弱化了理性視角的省思。其三,從平臺邏輯上看,數字平臺的情感勞動者在數據—流量導向下,更加傾向于創造強刺激性的多元“情感盛宴”來博取用戶的注意力,這種情感商品更易于實現用戶情感的煽動與傳染,原來具有正當性與合理性的情感表達轉變為純粹的情感宣泄,甚至衍生為數字群體內部的極端情感。當前,西方意識形態正不斷在數字空間中傳播精心包裝與巧妙設計的情感景觀,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消費主義等社會思潮披著情感敘事的外衣,隱蔽地在數字場域蔓延與滲透,對數字圈層進行意識形態滲透與價值觀植入,干擾了主流意識形態凝聚力與引領力的不斷增強。
四、情感規制:數字時代意識形態情感向度的優化策略
數字時代是情感能量爆炸的時代,“當代文化的特點是越來越情緒化”(19)Wahl-Jorgensen,Emotions,Media and Politics,Cambridge:Polity Press,2019,p.2.。在情感被數字技術充分激發與調動的情境下,意識形態的情感向度愈加明顯,“感性敘事成為意識形態傳播的新形式”(20)羅紅杰:《論意識形態感性敘事及其正向建構》,《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12期。。意識形態的情感向度一體兩面的雙向影響,決定了必須在合理利用情感敘事的同時加強對意識形態情感向度的規制。在建設新時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語境下,充分借助情感敘事傳播主流價值觀念、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情感認同,規制情感敘事所引發的意識形態風險,使情感敘事從意識形態發展變量演變為發展增量,是提升主流意識形態感染力、凝聚力與吸引力的有效路徑。
首先,規制個體在數字空間的情感表達,彌合個體理性與虛擬世界的斷裂,完善數字空間意識形態的情感治理。數字空間的數字化在場消解了現實空間的身份規訓與交往限制,減輕了個體在數字場域的言行束縛。這種更為自由的數字化在場模式,加之數字技術對人非理性因素的調動以及數字平臺的流量驅動,使得個體情感表達的非理性化甚至極端化特征更加明顯,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數字空間的意識形態秩序。“情感是一種需要對其進行限制、調節和治理的能量”(21)田林楠:《網絡情感是如何極化的?——一個情感社會學的視角》,《天府新論》2017年第2期。,必須依靠一定的技術與法律手段治理數字場域的用戶情感。對于數字平臺匿名設置所導致的虛假信息、謠言、網絡暴力等極端言行,必須制定更加完善的賬號注冊制度以及完善實名認證形式,對使用虛擬身份信息、第三方登錄、代理注冊等非常規的注冊操作模式進行審查。借助算法技術實時監控數字平臺發布的內容,對輿情信息的來源、發布平臺與發布者的主觀意圖進行核查。對于數字平臺算法推薦機制所導致的情感消費成癮等問題,須用主流價值觀念引導算法推薦機制向上向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明確指出,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不得設置誘導用戶沉迷、過度消費等違反法律法規或者違背倫理道德的算法模型。要用主流意識形態增強算法技術的價值理性,擺脫數字資本操控下技術理性的傾向。對于流量邏輯下注意力搶奪所滋生的低劣、媚俗與惡搞的情感景觀,要依靠相關的法律制度進行規制與治理。通過法律法規的有效供給,加大對數字空間情感景觀的審查力度,引入專業規范的信息審查與懲戒規范。
其次,每個數字圈層都有獨特的價值觀念與情感偏好,要將數字圈層治理融入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邏輯中,借助數字圈層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在數字時代,數字圈層內部的群體情緒具有強影響力、高擴散度、深交互性的特點,能夠通過建立群體身份認同控制數字用戶的情感走向,并且借助情感表征系統向個體滲透相應的價值觀念,因而是關涉主流意識形態發展的重要因素。鞏固主流意識形態在數字空間的話語權,必須把數字圈層邏輯納入主流意識形態的生產、傳播、呈現、反饋的全過程環節,構建具有積極情感導向的主流意識形態數字圈層,借助數字圈層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將數字圈層治理融入主流意識形態建設邏輯的關鍵在于,了解與調查不同數字圈層的情感與價值偏好,尋找能夠實現圈層破壁的情感通道,進而建構與拓展主流意識形態的情感社群。一方面,引導數字圈層自覺接受與內化主流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觀念,形成數字空間情感認同的群體基礎;另一方面,推動主流意識形態的數字圈層加強互動交流,在跨圈層交往與聯動中縮近不同圈層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距離,實現對大眾情感、價值、信仰的召喚。對處于主流意識形態情感認同邊緣的數字圈層,要實時關注該圈層釋放的情感信號尤其是負面的社會情緒,及時化解與糾偏消極情緒與錯誤輿論,構建數字場域的情感引導機制,放大積極的社會情感與正向輿論。
最后,建設主流意識形態的情感敘事,增強數字用戶的情感歸屬與情感凝聚,提升主流意識形態的情感認同度。特納強調“情感是把人們聯系在一起的‘黏合劑’,可生成對廣義的社會與文化的承諾。”(22)喬納斯·特納、簡·斯黛茲:《情感社會學》,孫俊才、文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7頁。有效的情感敘事能夠憑借故事化的情節設定、生活化的話語表達以及審美化的視覺呈現來引發情感共鳴,快速填充與占據數字用戶的價值信仰場域。要形成主流意識形態情感認同的同心圓,應將主流意識形態與情感敘事有機融合起來,依托突飛猛進的數字技術構建主流意識形態的情感敘事。其一,要創新主流意識形態內容敘事邏輯,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敘事內容中嵌入相應的情感因素。主流意識形態可以借助經數字技術編碼與加工的情感隱喻來傳遞主流價值理念與思維方式,將核心價值觀念演繹為具象化的數字圖像,將政治性話語轉化為生活化表達,將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轉變為微小的情感敘事,使主流意識形態更易于被大眾接受與認同。其二,要堅持“人民至上”的主流意識形態敘事視角,呈現主流意識形態的情感脈絡主線。主流意識形態要在“以人民為中心”的情感敘事視角下構建內含共同情感向度的敘事框架,將“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情感邏輯貫穿主流意識形態的各個環節,直觀地呈現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遵循與實踐指向,并轉化為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正面認知與情感共振。其三,要優化主流意識形態的敘事結構,實現理性敘事與感性敘事的結構性互補。理性敘事保證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嚴肅性與政治性,感性敘事則保證了主流意識形態的生活化傳播。破除兩者的互動壁壘,在實現理性敘事與感性敘事互補的基礎上發揮兩者的優勢,能夠使主流意識形態更具親和力與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