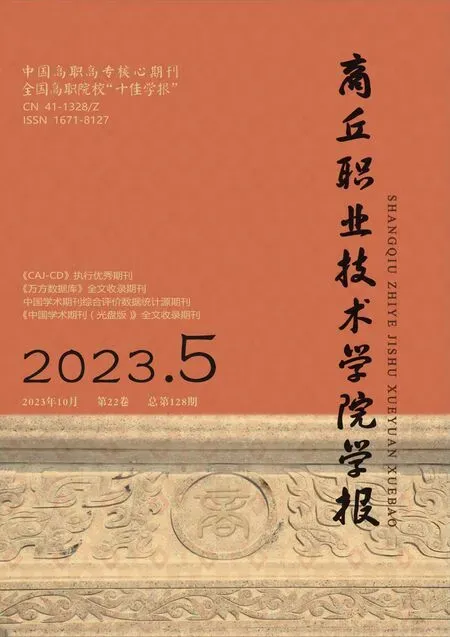民族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與研究
——以《民族學研究集刊》為中心的歷史考察
王俊俊
(寧夏大學 民族與歷史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
民族學作為一門對民族社會文化特征及其形成演化規律進行綜合研究的社會學科,起源于19世紀,此后被傳播到世界許多國家[1]1-3。中國民族學的探索始于對西方民族學學術思想的引進和翻譯,1903年京師大學堂出版的《民種學》是國內最早翻譯的西方民族學著作,此后大量西方民族學著作被翻譯介紹到中國。1926年,蔡元培首次在國內學術刊物上提出“民族學”的術語,明確了民族學的學科定義,對民族學的學科體系、理論和方法進行了簡要的闡述[1]62。之后,民族學在中國快速傳播。1936年中山文化教育館創辦的《民族學研究集刊》,是民國時期影響最大的民族學專業期刊之一[2],該期刊前后共出版六期,其中所刊載的大量民族學相關知識和研究成果,不僅推動了中國民族學學術研究的交流與發展,而且集中體現了民國時期學界關于民族學的研究。本文以《民族學研究集刊》為中心,探討民族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及研究情況。
一、普及民族學相關知識
現代民族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推動了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由于民族學傳入中國的時間較晚,國內民眾對這一學科缺少客觀的認識,而《民族學研究集刊》中很多普及民族學相關知識的文章,不僅引起了民眾的關注,而且擴大了民族學的影響。
黃文山在《民族學與中國民族研究》一文中對比了兩種不同的“民族學”觀點:一是巴斯鏜、羅索爾所認為的“一切無文字的土人或民族,方是民族學的中心對象”;二是史美德、文達尼斯、叔耳次等所認為的“民族學為研究人類整個范域之科學”[3]。黃文山分析了民族學與人體學、民族志、古物學之間的區別與聯系,介紹了民族學研究的現狀。他指出,歐美各國自19世紀末就對民族學進行了不遺余力地研究,并派遣大學或學術團體探險隊分赴各地,采訪各地的種族與文化,為其施政及經濟與文化侵略制定方針。
黃文山還介紹了嚴復、郭沫若、劉師培等人開展的民族學研究工作。他還特別強調歷史上中國民族志關于少數民族的記載以及中國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各地區的民族學研究成果,認為研究民族學不僅有助于建立一個穩定的多民族國家,而且“民族學之純理論研究,可以供給社會科學以無數之可靠的假定……民族學之實地調查,尤其可以供給民族改造之妥善計劃”[3]。
衛惠林在《民族學的對象領域及其關聯的問題》一文中,系統地介紹了民族學的發展歷程。衛惠林從民族學的起源開始,追述了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著名民族學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巴黎民族學會、倫敦民族學會等機構在民族學發展中的貢獻。重點討論了民族學的研究對象,對各民族學派的不同觀點進行了闡釋:法國人類學派認為,民族學主要是研究種族的科學;德國傳統民族學派認為,民族學主要研究的是人類心理方面的特質;英國民族學派認為,民族學研究的是各種文化的科學;還有一些學者則認為,民族學是研究民族的科學。衛惠林更傾向于民族學是研究現代原始民族文化科學的觀點,認為民族學最原始的時期,主要研究的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特質。
衛惠林還討論和分析了與民族學相關聯的問題,主要對民族學中的一些術語,如“race”“people”“ethnie”“culture”“civilization”等的中文譯名及用法進行了討論,并分析了“原始民族”所包含的五種意義:“(1)社會組織化比較簡單、其集合的人數比較少;(2)社會制度與個人行為以神秘力量之信仰為基礎;(3)物質生活受自然環境的嚴格支配;(4)生產手段靠人力與簡單的工具,不知使用機械與動力;(5)對事物之認識與行為之方向,嚴守習俗的傳統,而不依靠理性的判斷和科學的指導。”[4]
凌純聲在《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一文中,對民族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民族志與民族學的關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和對比,指出“我們現在以前者為民族志,后者為民族學,對于這兩字的解釋,英德法三國學者大致尚能同意……民族志為敘述的,民族學為理論的……民族志屬于敘述的研究,找出各民族各種文化的情形,民族學屬于理論的研究,說明各民族的文化不同的原因……前者敘述各民族的文化,而后者為比較各種文化的現象,并求出他的規律來……民族志是民族學的主要部分,通常稱民族學即可概況民族志”[5]。
實地考察法是民族學研究廣泛運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凌純聲重點介紹了幾種實地考察的方法,如:筆記——“要得到準確而詳盡的知識,必定要立刻詳盡地記下各種報告,民族學者所需要的就是這類的材料”;繪圖——“一種情景或某一建筑的主要形式,可以用簡單的圖畫速寫下來,或是用圖畫來說明照片上的各瑣細部分,這價值是很大的”;實地觀察——“記下你所看見的,并找出關于你所見的事物的一切應用知識”;個別訪問——“最好找出一個土人……等到一有機會,便可詢問”;日記法——“從和土人第一次接觸的日子起應有一本日記,將各種所見的事情,不論如何瑣屑,一概記錄下來”[5]。此外,他還指出,在進行實地考察中要注重側重點,涵蓋諸如地理、住所、飲食、裝飾、人工改造身體、衣服、武器、生存方式、嗜好品、游戲、音樂、交通工具、貨幣、技術、社會組織、醫藥等方面。
黃文山是享譽海內外的文化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學者[6],衛惠林也是知名的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7],凌純聲同樣是現代著名的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8]。上述三篇文章均見刊于1936年,其從不同的角度介紹了民族學的概念、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等。之后,林惠祥的《民族學學說的新綜合——新進化論》、楊坤的《民人學與民族學》、吳文藻的《功能派社會人類學的由來與現狀》、張少微的《民族學體系發凡》、戴裔煊的《民族學理論與方法的遞演》等也介紹了民族學的基本概念、發展歷史等,這些文章普及了大量民族學的相關知識,拓展了學界對民族學的認知,提高了中國學者對民族學的關注度,也擴大了民族學在中國的影響力。
二、開展中國少數民族研究
除刊載傳播民族學的文章外,《民族學研究集刊》還刊載了大量有關中國民族史研究的文章,這些研究成果對中國各民族歷史和文化進行記錄和描述,為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民族史、少數民族文化提供了廣闊視野,對深入研究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和意義。
劉咸的《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一文從多方面考察了海南島黎族人的文身。作者認為,黎族人文身的起源來自三種傳說:一是祖先行文身之俗;二是不同族群的互殘;三是來源于神話。無論是哪種說法,都承載著黎族深厚的文化底蘊。同時,進行文身的工具以及手術過程也是黎族文身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者對此進行了考察:“施術者大抵為年老有拍刺經驗之婦女,端坐地上,受術者則仰臥于地上,以頭承于施術者之大腿上……施術者左手執黃藤針,右手執拍針棒,依所畫黑線拍刺之,針刺入肉、血即隨出,頗為痛苦,每刺一線,即將血拭去,而以用水和就之煙灰,或擎就墨汁,敷于創口上,至刺畢為止。”[9]此外,作者對黎族人文身的部位和圖譜進行考察,指出其主要文身的部位在面部、胸部、臂部和腿部,所紋圖譜一般分為斜紋類、橫紋類、圓紋類,并用文字和圖畫介紹了37種面紋圖式、14種手紋圖式、10種腿紋圖式。作者對文身圖譜進行了詳細解讀,借以討論文身所蘊含的文化內涵,認為文身是政治地位的體現,是進行婚姻的禮儀,是圖騰崇拜的表現,可以辟邪和裝飾。這篇論文在黎族文身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開山之作,其所達到的高度迄今仍難以超越,也是被后來學者引用最多的黎族文身方面的研究論文[10]。
馬長壽的《康藏民族之分類體質種屬及其社會組織》一文對康巴藏族進行了深入研究,不僅介紹了前人對康藏民族的五種分類方式以及康藏民族的六大部族,而且從頭指數、鼻指數、面指數、身長等體質方面考察了康藏民族與漢族、蒙古族、卜丹人、尼泊爾人、印度人、歐洲人等的區分和相似情況,以此為依據借以史籍加以佐證,得出“康藏民族與漢族、蒙古族之血統關系最深,卜丹人、尼泊爾人次之,至于與印度人及歐洲人之關系,雖有一二相互婚姻之事件,可謂絕無僅有”[11]的結論。康藏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是了解其社會發展的關鍵環節,作者從社會階級、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婚姻及親屬制度、政治制度、法律與德儀方面等詳細研究了康藏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指出雖然康藏民族社會發展較為原始,但與漢族早期社會發展卻有相似之處。馬長壽對康藏民族的這一研究,不僅回應了此一時期流行的將“西康”區域及其民族同歸到所謂“大西藏”的謬論,還使國人對于錯綜復雜的康藏民族內部族群分布狀況有了一個更加清晰的認知,并證明了康藏民族與漢族之間的緊密聯系,論證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性[12]。
丁骕的《新疆住民與維吾爾人》一文先從歷史學的角度詳細地考察了新疆住民的變遷過程,指出“新疆之維吾爾人,乃南疆地理環境融匯多族所得之總結果,史上入南疆之人有漢人、大月氏、匈奴、突厥、契丹、吐谷渾、藏人、乃蠻、畏吾兒、蒙古等,大抵不外蒙古族之血統也。其他各族,如塔塔兒為元室貴族,本蒙人;柯族即史上之烏孫;哈薩克即漢之康居;歸化本白俄人;塔吉克即屬阿富汗系統,除哈薩克外為數皆微,多在北疆,惟柯族在南疆而已;新疆俗稱十四民族,即漢、滿、蒙、回、維、哈、柯、錫、索、歸、三塔加一烏”[13]。新疆住民不斷變遷,不同民族的人群遷移至此,種族構成逐漸復雜化,維吾爾族的血統也發生了融合變化。作者對此進行考證,認為“維族實為一融合多種民族血統之人,以古之回紇、突厥為主,蒙古次之,契丹又次之。漢族血統由漢代以后即不斷滲入,為量最大。其混雜情形,例如,哈密維人合衛拉特血統頗強,和闐維人視之頗類漢人,其中一部膚色潔白,似寬頭白種人之血統,喀什維族除少數類似喀什米爾人外,大部為突厥遺裔。考維吾爾人不僅系突厥、蒙古、回紇諸人之后代,即在文化方面,亦為混雜之結晶”[13]。丁骕以歷史記載為依據,詳細考證歷史上新疆住民及維吾爾族的形成,試圖從歷史中探尋古代族群與現代民族之間的關系。這種嘗試促進了新疆民族研究的開展,深化了當時國人對于新疆少數民族,甚至對于整個中華民族的認知[14]。
《隋書之吐蕃——附國》一文是著名歷史學家岑仲勉早期關于邊疆民族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該文詳細考證了《隋書》中記載的“附國”的淵源:地理位置方面,利用《西域記》《隋書》等史料以及朱希祖、馬長壽等人的研究,對比女國、黨項等族群的地理與疆域,指出“附國之所在……正包括前藏全部”,附國境內河流,“闊百丈余”,“則謂金沙江或瀾滄江比較近是”;國名讀音方面,附國與吐蕃“言音既合,方向復符,又附國即后來吐蕃之強證也”;王號讀音方面,《隋書》記載“附國王字宜繒”,“字”即是王號,唐代關于吐蕃王號的翻譯“贊普”實際上與《隋書》中“宜繒”翻譯是“完全吻合”的;建筑方面,雖然《舊唐書》記載吐蕃“頗有城郭”,但據其他史料可證明這些建筑是吐蕃后來兼并和建筑的,并不是貞觀初年的,因此與《隋書》記載的附國“無城柵”并不矛盾;物產方面,《隋書》中稱附國“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雞,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與《西藏圖考》中所說“西藏與產青稞、小麥、金、銀、細鱗魚”相符,產白雞則與《吐蕃考》的記載吻合。綜合以上論點,作者得出結論——“附國為隋代吐蕃之異稱”[15]。岑仲勉的這篇關于“附國”考證的征引廣博、考訂精審的論文[16],對于古代西藏民族政權、社會文化的發展以及隋唐時期漢藏民族關系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介紹國外民族學相關研究
《民族學研究集刊》也有對國外民族學研究現狀進行介紹的文章,這些文章主要關注國外民族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和發展動態,涉及民族學不同方面,有助于增加對國外民族學研究的了解,為國內民族學的研究提供借鑒。
1943年,戴裔煊發表《鮑亞士及其學說述略》一文,詳細介紹了素有“美國人類學之父”之稱的德裔美國人類學家夫朗茲·鮑亞士(Franz Boas,今譯弗朗茲·博厄斯)的研究成果及影響。該文主要從其對人類學研究目的與范疇的意見、對心理歷程與文化關系的意見、對地理經濟與文化關系的意見以及他的人類學研究方法論等方面進行介紹。文中寫道,鮑亞士認為,人類學所研究的“一是歷史之重造,二是歷史現象的類型及其順序之決定,三是變遷之動力……前兩者使人類學與史學發生關聯,后者則與社會學發生關聯”[23],而“在各個文化階段中,人心所宣示者之懸殊,全由個別經驗之形式,此種經驗之形式則受個別之地理與社會環境所決定,種族雖不同,其心理組織在大體上相似,個別心理歷程之形式雖相似,而一個社團之心理活動,則有表示一種特色的歷史的發展之傾向……所以鮑亞士之結論為‘人類唯一,文明各殊’”[23]。他不認同地理和經濟決定人類文化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和“經濟條件決定論”,認為雖然二者可以影響文化,但不能創造文化。鮑亞士對人類學研究的方法主要有考古學方法和比較研究法,他認為,研究人類學要重視田野調查,要科學地分析所獲取的文化資料,還要熟悉所調查對象的語言,這也是民族學家所應該注意的。該文最后詳細介紹了鮑亞士的著作,并指出鮑亞士對人類學的研究雖然有獨到的見解,但是缺乏綜合的一般性結論和鮮明的旗幟。
1940年,楊坤在《法國民族學之過去與現在》一文中,從五個方面介紹了法國民族學研究的發展概況。該文介紹了拉費頭(Lafitau)、馮德迺勒(Fontenelle)、德布柔斯(De Brosses)、德莫尼葉(Demeunier)等幾位法國學者對民族學誕生的推動,借德國民族學家巴斯典的言論來評價法國學者在民族學誕生中的歷史貢獻:“法國本來是在許多國際的學術上全是打先鋒的,而這次關于建設民族學的功勛,仍然是法國的思想家,鑒于當時之需要,而能獨具慧眼,在民族學尚未進入于黎明之時,給我們籌劃出一種科學的大概輪廓來。”[24]除此之外,法國民族學者的研究成果和巴黎民族學院的研究工作為民族學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由于民族學的發展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其發展是各個學科綜合發展的結果,楊坤在文章中介紹的法國人類學者和機構以及法國社會學家對民族學發展的貢獻,使我們更全面地了解了該學科的發展歷程。
1946年,徐益棠在《法國的民族學及其研究機關》一文中,對法國民族學研究機構進行了全面的介紹。巴黎民族學院是法國最早的民族學研究機構之一,對法國民族學的發展意義重大。作者主要從發展歷史及其具體開設課程、主講教師、出版叢書等方面對其進行詳細介紹。其他民族學研究機構和相關的研究學會也在民族學發展方面做出重大貢獻,例如,法蘭西學院、巴黎高等學術實習學院、自然歷史博物院人類學實驗室、特柔加德柔(Trocadéro)民族學院博物院、羅浮博物院考古學校、人類古生物學學院、東方語言學校、地理學院等民族學研究機構,巴黎人類學會、巴黎民族學會、里昂人類學會、格侖諾勃(Grenoble)人類及民族學會。同時,一些研究機關在民族學領域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法國人類學院、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院等主辦的刊物等[25],促進了法國民族學的縱深發展。
除此之外,《民族學研究集刊》還刊載了一部分關于國外民族學研究的文章。如1940年衛惠林發表的《世界現代人種分類的研究》一文,介紹了當時關于世界人種分類的兩大分類標準:一種是“為純粹根據各種之主要體質、特質”而進行的分類,傾向此種分類的學者有瑞典博物學家林奈(Carl von Linné)、法國博物學家布封(Leclere de Buffon)、德國人類學家布魯門巴赫(Blumenbaéh)等。另一種是將種族的發展與形態學及地區聯系起來而進行的分類,傾向此種分類的學者有德國人類學家施特拉茨(Stratz)、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Franz Boas)、意大利人類學家科吉歐佛瑞達·拉格里(Ginffrida Ruggeri)等。作者指出,后一種分類較前一種分類“有廣大之基礎為運用現代諸人類科學,以至生物學、地質學之新結論與種族特質之新資料研究所得之結果,但前者似拘泥于舊的分類之理論,故有牽強造作之象,而后者則過渡應用生物學的法則,使其分類中幾個種族的隸屬于形態學、地理學的事實相背馳”[26]。作者更為推崇法國民族學家蒙登東(G.Montandon)等人的分類方法:“蒙登東的分類已經運用著更廣大的現代知識……不只努力融合形態學與發生學的兩種方法,并且能運用歷史與地理的知識。”[26]作者根據“環境的對于體質變化的影響、自己馴致、種族交混”三種因素修正了蒙登東的分類,將現代人種分為“吠達澳洲人種”“皮格美人種”“奈格羅人種”“歐洲人種”“美洲印第安人種”和“蒙古人種”以及“吠達種族”“澳洲種族”“達拉維地安種族”等十九個種族和“巴布門西阿亞種族”“美拉奈西安亞種族”“包虛曼亞種族”等二十九個亞種族。不同人種、不同種族具有不同的體質,具有不同的特色,作者詳細分析了各個人種、不同種族的不同體質以及不同種族的地理分布區域等,如文中介紹道:“(吠達澳洲人種)主要的共通的特質是眉棱骨隆起、眼深陷、顴骨高、鼻闊、發質波狀至卷曲,身材小或中等,皮色褐、長頭型……(皮格美人種)有若干共同的體質,如身材甚小,一米五十以下,發質極綣縮至成粒狀,腿短,軀干較長……”[26]
《民族學研究集刊》中大多是國際前沿的研究動態,這有助于國內學者了解國外民族學研究情況,推動國內民族學發展與國際的接軌。
四、結語
清末民國時期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大變革時期[27]。在這一時期,一批學者以《民族學研究集刊》為陣地,介紹民族學的概念、研究范圍、發展歷程以及學術流派,發表有關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成果,介紹國外民族學研究的概況,并嘗試開展國外民族學的研究,使民族學得以在本土落地生根,開始作為獨立的學科躋身于中國的學術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