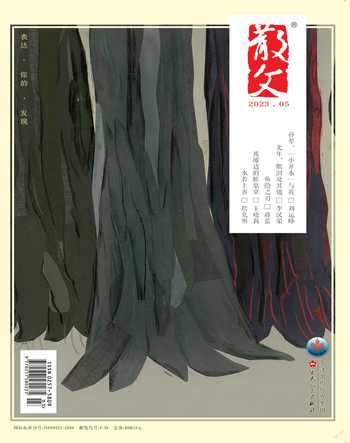魚隱之刃
蔣藍
怒有萬人之氣,其妻一呼即還
梁啟超將《史記·刺客列傳》所述五大刺客分為“為國事”“報恩仇”“助篡逆”三類,批評“助篡逆”的專諸乃“私人野心之奴隸”“無意識之義俠”。在《中國之武士道》里,他評析了豫讓的壯烈之舉后,特意以“新史氏又曰”補充說,他并不認為專諸具有真正的尚武精神,專諸只是狹義上的忠君,實際上是為傀儡君主而死,于是將專諸排除在俠客門墻之外。
專諸,是《史記·刺客列傳》中第二個出場的人物。作為暗殺者,他是被后代貼上“最富有政治色彩”標簽的殺手,人們鸚鵡學舌,往往說專諸是公子光、伍子胥以及吳王僚之間權力斗爭的犧牲品。可惜的是,歷史并不因為標簽的存在而被迫改變它本來的色澤。
專諸(?—前515年),春秋時代棠邑(今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人,長得高額凹眼,虎背熊腰,異于常人。異人自有異相,異相必有異能,這一點,古人是深信不疑的。東漢趙曄的《吳越春秋》里有一段記載我非常喜歡:“專諸方與人斗,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映入人們眼前的“畏妻”者,古書里只有八個字:“雄貌,深目,侈口,熊背。”這個細節刻畫絲絲入扣,精妙無比,這暗示專諸有胡人血統。事后伍子胥問他為什么不打架了,專諸說:“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這非常能說明專諸的性情就像質地優良的劍,可柔亦可剛。
從字義上說,專諸古書寫作“鱄諸”,鱄固然為一種姓氏,但也指一種淡水魚,即古書上說的:“魚之美者,洞庭之鱄。”移之于專諸,尤其是聯系到后來裂魚腹而出的魚腸之劍,我總以為,他的姓氏似乎暗示了他與危機的某種難以割裂的聯系。魚,成為這一切兇相的和諧征兆。
伍子胥(棠邑大夫伍尚之弟)長得“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堪稱偉岸的男子漢,因父親伍奢、兄長伍尚皆被楚平王冤殺,他身負血仇逃離楚地來到吳國,一見專諸,且得知專諸有“內志”之時,真是與之惺惺相惜,電光石火間,明白這是不可多得的勇士,遂與之結交。
伍子胥覲見吳王僚,用攻打楚國的好處予以游說。對此,公子光私下自有一番評論:“那個伍員,父親、哥哥都是被楚國殺死,所以才鼓吹攻打楚國,他不過是為報私仇,并非替吳國打算。”吳王一聽,就不再議伐楚的事。伍子胥私下得知公子光打算除掉吳王僚,就乘機進言:“公子光有奪取王位的企圖,現在還不宜勸說他向國外出兵。”在穩住局勢之際,他立即把專諸推薦給公子光。
公子光的父親是吳王諸樊。諸樊有三個弟弟,按兄弟次序排,大弟弟叫余祭,二弟弟叫夷眛,最小的弟弟叫季札。諸樊知道季札賢明,就不立太子,希望依照兄弟的次序把王位傳下去,最后把國君之位傳給季札。季札的確賢明,千方百計逃避君位。于是立下規矩,王位不再傳子,而按兄弟順序傳。諸樊認為,王位早晚還是季札的。于是,諸樊死了,輪二弟;二弟死了輪三弟;三弟終于死了,這回可算輪到季札了,季札卻在人們的期盼中失蹤了。畢竟國不可一日無君,老三的兒子遂繼承了王位。這就是吳王僚。這樣老大的兒子能服氣嗎?這就是公子光頓起殺機的原因。
公子光說:“如果按兄弟的次序,季子當立;如果一定要傳給兒子的話,那么我才是真正的嫡子,應當立我為君。”他是有準備的,秘密供養一些有智謀的人,指望他們助自己奪位。
公子光一見專諸,待若上賓。吳王僚九年(前514年),楚平王死。這年春,吳王僚想趁著楚國辦喪事之際,派他的兩個弟弟公子蓋余、屬庸率領軍隊包圍楚國的譖城,派延陵季子到晉國,用以觀察各諸侯國的動靜。楚國出動軍隊,斷絕了吳將蓋余、屬庸的后路,吳國軍隊不能歸還。一直注視著局勢變化的公子光覺得差不多了,對專諸說:“這個機會不能失掉,不去爭取,哪會獲得!況且我是真正的王位繼承人。季子即使回來,也不會廢掉我。”屠夫出身的專諸并不只懂得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他是懂得刀路的:“僚是可以殺掉的。母老子弱,兩個弟弟帶著軍隊攻打楚國,楚國軍隊斷絕了他們的后路。當前吳軍在外被楚國圍困,而國內沒有正直敢言者,這樣,僚還能把我們怎么樣呢!”這句話火一樣把公子光點燃了,他心神大動,起身叩頭:“我公子光的身體,也就是您的身體,您的事,我會負責到底!”至此,歷史的演繹像一個魔咒,立即掀動了歷史的水盆,是那樣覆水難收。這句“光之身,子之身也”的豪言,就是最大的應許,專諸履行了承諾,公子光也兌現了自己的豪言,兩不相欠。
燒一條美味的劍魚
但吳王僚是機警的,他的弱點在哪里?
公子光在與之觥籌交錯、換盞推杯的記憶中,恍惚記得吳王僚喜吃魚。烤魚的香味總會讓人忽略一些細節。這個回憶讓公子光很是興奮。《風土記》載:“吳王闔閭女,驕恣,嘗與王爭魚炙,怨恚而死。”為爭吃燒魚,竟郁怨而死。《姑蘇志》記有“吳地產魚,吳人善治食品,其來久矣”的風俗。可見,在普通的一條魚上,可以寄托更多的非凡之思。專諸立即去太湖,師從烹制魚菜的高手太和公學習“炙魚”,三月而精此技。
專諸準備施展一次前無古人的陰翳智慧——燒一條美味的藏劍之魚,這的確是春秋手法,名字就叫“魚藏劍”。
魚隱,利刃像一條魚那樣回到水中。殺氣就像魚香那樣,蟄伏于味蕾打開時的磅礴口水里。
魚隱,比起后起的作為看破紅塵之舉代表的“漁隱”,深刻體現出古漢語的鋒刃,以及倒刺。
這年四月的丙子日,公子光趁王僚派兵遠征被困楚國之際,決定請王僚赴宴。公子光對王僚說:有庖人從太湖來,善炙魚,味甚鮮美,請王嘗魚炙。地下室埋伏身穿鎧甲的武士,又命伍員暗約死士百人,在外接應。吳王僚肯定已猜測到公子光的宴請不是出于友情和敬意,但他過于自信,低估了公子光的謀略和決心。赴宴時,他身穿鐵甲,沿途布兵,席間衛士隨身不離。然而他沒有料到,最大的危機,卻是埋伏在誘人的魚香當中。
宴席終于開始。酒到暢快處,公子光詭稱腳痛,退到地下室。就像導火索被悄悄點燃,一個預謀周密的計劃紋絲不亂,依次鋪排:專諸把匕首藏到烤魚的腹內,喬裝膳者,端著魚上去了。
走到吳王僚眼皮下,專諸的動作很緩慢,在放下魚盤的一瞬,比魚刺更鋒利的手指插進魚腹,掰開,拿刀,發力,出擊,行云流水,直插吳王僚的胸部。細而窄的匕首面對“鐵之甲三重”是一種角力,衛士的長劍——“鈹”,像樹枝一樣環衛在吳王僚左右,劍身抵住了進食者的身體——可見局勢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但“倚專諸胸,胸斷臆天,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的記載中,這“貫甲達背”四字——即魚腸劍刺入吳王僚的身體,與衛士的長劍刺入專諸的身體成正比——凸顯了匕首的鋒利,以及專諸更為果決的殺氣。
這細弱的匕首,在從空中劃過的過程中,帶動了一個巨大的陣勢,直到匕首徹底停止運動,它所牽動的氣場才滾滾而起。唐雎贊之為“彗星襲月”,言其猶如彗星掃過月亮,按古人說法這是重大災難的征兆。如此修辭,使贊美者在高揚專諸殺氣的同時,又讓某種不軌于正義的道德指責蟄伏其中。
沒有任何反常,吳王僚當場斃命。猛醒過來的侍衛撲上來,亂劍戮殺專諸,場面混亂不堪。公子光覺得大局已定,放出埋伏的武士發起攻擊,一舉消滅了吳王僚部下。他遂自立為君,這就是吳王闔閭。他沒有忘記自己的承諾,封專諸的兒子為上卿。
遠在楚國作戰的吳王僚的弟弟蓋余、屬庸聽到公子光弒君自立的消息,知道大勢已去,棄軍逃走。后來兄弟倆又投奔楚國,楚把養邑(今河南沈丘一帶)分封給他們。從此,吳王的后裔就在河南沈丘一帶繁衍,后代分別以兩公子的名字蓋余、屬庸為氏,成為姬吳的兩大分支。
季札回國后,不愿看到吳國再起內亂,只好承認闔閭為君的合法性。《史記》記季札說:
茍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
太山一擲輕鴻毛
根據專諸生前一定要死后葬于泰伯墳旁的遺愿,吳王從優安葬專諸,在當時的王宮(位于現在的崇寧路和小婁巷一帶)一側修建了專諸的優禮冢,名為專諸塔。塔直到“文革”前夕,都一直矗立在無錫城的大婁巷。因專諸在太湖邊學燒魚之術,后人把他奉為廚師之祖。
專諸塔是一座喇叭形的小塔,塔在一間房子里,1966年被拆除。邑人秦頌碩曾寫《專諸塔》一詩:
一劍酬恩拓霸圖,可憐花草故宮蕪。
瓣香俠骨留殘塔,片土居然尚屬吳。
這很能說明,專諸的血雖沒有能感化儒生們的學理,但在故土,仍催生出了一蓬紅如火焰的曼陀羅花。
明代大儒陳懿典稱:“專諸助篡,聶政借軀,報一人之仇,皆不軌于正義。”(《讀史漫筆·刺客傳》)這是歷史的老調了。章太炎先生在《徐錫麟等哀辭》里說:“專諸、聶政死二千年,刺客之傳,郁堙弗宣。”這是有感于同盟會刺殺清廷官員的革命性,認為他們再現了凌厲的古風。正如太炎先生分析的那樣:“天下亂也,義士則狙擊人主,其他藉交報仇,為國民發憤,有為鷗梟于百姓者,則利劍刺之,可以得志。”這正是俠的品格。
1907年,黃季剛先生撰寫了《釋俠》一文。文章稱:“俠之名,在昔恒與儒擬。儒行所言,固俠之模略。”這種俠、儒并舉的模式,章太炎的《訄書·儒俠》早已有言在先。但在曹劌那樣兵不血刃的“儒俠”少之又少時,渴望“儒俠”來匡扶正義,就成了文人的葉公之好。
有意思的是,黃季剛在《釋俠》中對暗殺卻予以大力鼓吹:
俠者,其途徑狹隘者也。救民之道,亦云眾矣,獨取諸暗殺,道不亦狹隘乎?夫孤身赴敵,則逸于群眾之揭竿;忽得渠魁,則速于軍旅之戰伐。術不必受自他人,而謀不必咨之朋友。專心壹志,所謀者一事;左右伺候,所欲得者一人。其狹隘固矣,而其效或致震動天下,則何狹隘之足恤乎?
在這樣的認識下,逐漸廓清了一個事實:那些搖唇鼓舌的人,一當面對鮮血和死亡,就立即露出了他們的軟與小。歷史不因車載斗量的事后評說而有絲毫改變,就猶如刺出去的鋒刃,不會軟成紙刀。
“以理殺人”,其實在宋代之前就是存在的。
王元化在《思辨隨筆》里認為,韓非反反復復地說:“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難二》)“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墨子主張利人,韓非則主張利己。《外儲說·左上》說:“(人)皆挾自為心。”這是說人人都只知道愛自己,為自己,全都是自私自利貪生怕死之徒。韓非子還舉例說明:
鱧似蛇,蠶似蝎。人見蛇則驚駭,見則毛起。漁者持鱧,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
(《說林》)
所謂“賁”,是孟賁,“諸”是專諸。韓非很喜歡這個故事,把它寫在《內儲說·上》里,以說明人是如何見利而趨。但是,韓非也知道世上畢竟還有“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不可以賞使”的硬漢子。對這類人怎么辦呢?韓非子在《外儲說·右上》說:“勢不足以化則除之。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那么,像專諸這樣的人,韓非子認為不過是被利益沖昏頭腦之輩,他不但忽視了專諸的智慧,而且忽略了專諸置生死于度外的血性。其實,他是渴望“專政”掉這樣的血勇之人的。看來,所謂學理,其殘酷更勝于刀。
反過來看,李白是歌頌豪俠最力的詩人,他寫過多首同類磅礴詩作,但我最喜歡這首《結襪子》,可以看作是李白讀《刺客列傳》后的詠史之作,也可以看作李白頓悟生命價值即興抒發的漫天豪情: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
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
吳地尚武之風由來已久,吳人尚武,最突出的表現形式是好劍輕死。在專諸飛鷹一般的影響背后,還有一件著名的利器,那就是魚腸劍。劍因人而雪亮,人因劍而影響深遠,劍與人互相彰顯。魚腸劍名字的來歷有兩個說法:一是出自《史記》因劍出魚腹一說,但司馬遷并未直言這把利刃之名,僅以“匕”稱之;后來《越絕書》明確指稱此劍名為“魚腸劍”。還有就是沈括《夢溪筆談》里的說法。魚腸以團鋼鑄就,劍成則現紋路,因類魚腸,故得名,暗示魚腸劍為鋼制。
存世最早的方志史書《越絕書》卷十三《外傳·記寶劍》記載:
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廬,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閭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廬……時闔閭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閭使專諸為秦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于敵邦,未見其大用于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覆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
這就明確指出,吳越名劍都是青銅劍。青銅劍是否能夠洞穿三層鎧甲?一直引起人們的熱烈追問。
魚腸劍據傳是鑄劍大師歐冶子為越王所制,他使用了赤堇山之錫、若耶溪之銅,經雨灑雷擊,得天地精華,制成了包括魚腸在內的五口劍。
魚腸劍既成,善于相劍的薛燭被請來為劍“把脈”,薛燭的眼睛很毒,他感受到了魚腸劍中蘊藏的亂理和殺意,認為它“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后來,魚腸劍被越國作為寶物進獻給吳國。
責任編輯: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