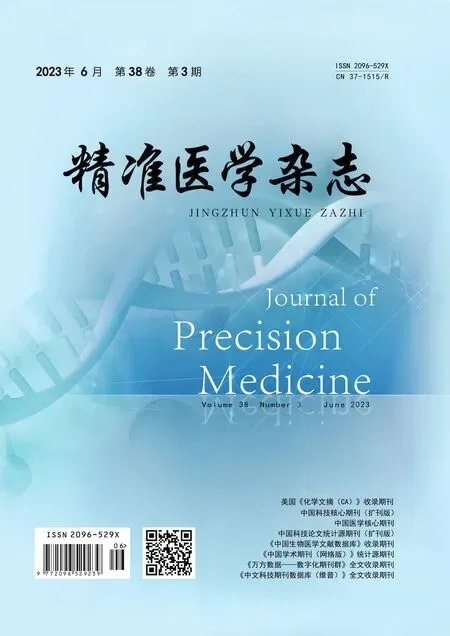SCN1A基因突變致遺傳性癲癇伴熱性驚厥附加癥家系1例報告并文獻復習
徐凱 黃碩 朱海芳 孫妍萍
(1 青島大學附屬醫院神經內科,山東 青島 266003; 2 青島市黃島區人民醫院神經內科; 3 山東科技大學校醫院)
遺傳性癲癇伴熱性驚厥附加癥(generalized epilepsy with febrile seizures plus,GEFS+)是一種兒童期起病的家族遺傳性癲癇綜合征[1],家系成員臨床表型呈異質性[2],最常見的臨床表型為熱性驚厥(FS)和熱性驚厥附加癥(FS+),其次為FS/FS+伴失神、失張力及肌陣攣發作等,甚至少數表現為Dravet綜合征(DS)。據文獻報道,GEFS+相關致病基因包括SCN1A、SCN2A、SCN1B、GABRG2、GABRD等,其中研究最多的基因為SCN1A,但僅10%的SCN1A基因突變與GEFS+發生有關[3]。本研究現報道1例SCN1A基因突變所致GEFS+患兒及其家系,并對相關文獻進行復習,以提高對SCN1A基因突變的認識,為GEFS+患者的臨床診療提供依據。
1 臨床資料
患兒,女,7歲,因“發作性抽搐4年余”于2016年首次就診于我院神經內科。患兒3歲時出現第1次癇性發作,發作前嘔吐,發作時意識喪失、抽搐。2015年患兒共癇性發作5次,其中2次發作同時伴有發熱。患兒4歲6個月時開始進行治療,口服奧卡西平片(每晚150 mg),1周以后調整為早晚各150 mg,2周后加量為早150 mg,晚300 mg;服藥后1個月出現癇性發作次數增多,半月內發作4次,調整奧卡西平片口服劑量為早晚各300 mg,癇性發作次數增多,且集中在服藥后0.5~1 h內。再次就診后聯合服用丙戊酸鈉片早晚各250 mg,仍有頻繁癇性發作,對比患兒口服奧卡西平前后腦電圖,服藥后新出現全導聯同步3~4 Hz棘慢復合波(圖1)。采集患兒及其父母、表姑的外周血標本進行癲癇相關基因檢測,提示患兒及其父親、表姑均為SCN1A突變,遂明確診斷為SCN1A基因突變致GEFS+,將奧卡西平減量至停藥。2017—2018年患兒服用丙戊酸鈉片早晚各250 mg,2年來僅在發熱時發作一次,至2019年最后一次隨訪未再發作。患兒為足月剖宮產,出生體質量2 600 g,無窒息,圍生期無異常,智力及生長發育符合同齡兒水平。其父有癇性發作史。入院檢查:患兒發育正常,無神經系統異常體征;血、尿常規及肝腎功能、電解質、血糖、遺傳代謝物等檢查未見異常;腦脊液常規、生化、細胞學及病原學檢查均未見異常。
患者父親,35歲,于5歲時癇性發作1次,臨床表現為意識喪失、口吐白沫、肢體抽搐,發作前后無發熱,持續2~3 min緩解,此后未發作,亦未診治。患兒表姑,37歲,其智能及生長發育符合同齡人水平,無癇性發作史。
采用靶向測序對患兒及其父母、表姑的外周血DNA進行三代基因測序分析,測序結果顯示患兒、其父親及表姑均存在有SCN1A基因c.4787G>A(p.R1596H)雜合錯義突變(圖2),該突變為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患兒母親該基因位點無異常。

圖2 患兒及其父親、表姑的SCN1A基因突變位點圖
2 討 論
GEFS+是一種兒童期發病、家庭各成員表型各異且家族性遺傳的癲癇綜合征。GEFS+家系診斷主要依據是家族成員中有FS、FS+等病史,并根據其發作類型和腦電圖特點確定其家系表型,最終診斷基于家系之中多個成員有相關致病基因突變。GEFS+家系成員總體預后良好,青春期后不再發作,但如果為DS,則預后不良[4-5]。目前GEFS+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多數研究認為其是一種離子通道病,可能與以下幾方面相關:①遺傳易感性:熱性驚厥患者中癲癇發病率約是普通人群的2倍,而一級親屬中有熱性驚厥病史患者的癲癇發病率是普通人群的20~30倍;熱性驚厥患者的一母同胞出現FS的風險明顯增高,且同卵雙生子較異卵雙生子發病率更高[6]。癇性發作體溫閾值的不同,說明其與遺傳易感性相關。②體溫影響離子通道功能:腦組織神經元鈉離子通道功能調節受體溫影響,體溫升高能夠增加神經元放電,SCN1A基因突變使鈉通道對于體溫升高更為敏感,從而誘發癲癇[7]。③炎性遞質:發熱可導致巨噬細胞增加白細胞介素-1β的釋放,從而引起酪氨酸激酶聚集,進一步導致神經元興奮性延長[8],由于SCN1A基因導致了鈉通道對神經元興奮性閾值的降低,容易誘發癇性發作。GEFS+應與熱性驚厥鑒別,熱性驚厥是一種與發熱密切相關的驚厥發作,多于兒童期起病,且不能用其他原因解釋驚厥發作。熱性驚厥與癲癇雖有相似的臨床表現,且都與遺傳有一定的關系,但熱性驚厥多表現為患者發病年齡偏小(多在6歲以下)、發熱高峰出現驚厥、發病后2周復查腦電圖正常等。本例患者為7歲女童,口服奧卡西平治療加重而丙戊酸鈉治療效果顯著,且對比口服奧卡西平前后腦電圖,有全導聯同步3~4 Hz棘慢復合波出現,提示鈉通道阻滯劑奧卡西平誘發患兒腦神經元異常放電,加之基因檢測發現SCN1A基因突變,故可與熱性驚厥鑒別。
目前GEFS+與基因關系的研究當中,SCN1A基因研究最為多見[9-11]。SCN1A基因定位于常染色體2q24.3上,其編碼電壓門控鈉通道α1亞基。SCN1A基因突變在中樞神經系統的廣泛表達可導致一系列疾病,包括癲癇性疾病(如GEFS+、隱源性局灶性癲癇、隱源性全面性癲癇等)和非癲癇性疾病(如家族性偏癱型偏頭痛、孤獨癥)。SCN1A基因編碼蛋白主要調節神經環路電活動,而神經環路的破壞可導致各類神經精神疾病。既往研究發現SCN1A基因突變所致GEFS+與該基因突變類型及位點相關[12-14],不同突變對離子通道的功能產生不同影響(如鈉通道功能喪失或活躍),從而導致GEFS+的不同臨床表型,包括DS、FS、FS+、FS/FS+伴失神、失張力及肌陣攣發作等,其中FS最為常見[15-17]。研究發現SCN1A多為錯義突變,也存在截斷突變[18],發生在鈉離子通道蛋白核心區域外的錯義突變臨床表型較輕,而臨床表現嚴重的DS突變則常常發生在SCN1A基因的重要功能區域。DS是GEFS+較為少見的一種臨床表型,其發病機制亦與SCN1A密切相關,本患兒需與之鑒別。DS的臨床特征為:①多1歲內起病,起初多為熱性驚厥,逐漸出現無熱驚厥,可出現多種發作形式,易出現癲癇持續狀態;②早期發育正常,1歲后逐漸出現智力落后甚至倒退;③腦電圖1歲前無異常,1歲后出現廣泛棘慢波、多棘慢波或局灶性、多灶性放電;④抗癲癇治療效果差,預后欠佳。本例患兒從發病年齡、智能發育及腦電圖表現等均可與DS鑒別。
在SCN1A突變所導致GEFS+患者的藥物治療中,左乙拉西坦、丙戊酸鈉等非鈉離子通道阻滯劑往往可以有效控制癲癇發作,而奧卡西平、拉莫三嗪等鈉離子通道阻滯劑常誘發癲癇加重[19-20]。BERTOK等[21]研究發現,抗癲癇藥物如奧卡西平對原發性癲癇的主要作用位點是神經元電壓門控鈉離子通道,而SCN1A不同基因位點突變能夠引起電壓門控鈉離子通道不同的改變,導致奧卡西平不能夠有效地控制神經元異常放電,甚至誘發癇性發作。DE LANGE等[22]曾對10例SCN1A基因突變患兒使用鈉離子通道阻滯劑治療,患兒發作均未能緩解,且有3例加重,8例有不同程度認知功能落后,這可能與鈉通道阻滯劑通過減弱抑制性神經元鈉通道的功能,進一步加重癇性發作有關。
本例患兒以發作性抽搐起病,發熱時易出現癇性發作,患兒外周血常規及生化檢查、腦脊液各項檢查均未見異常,故排除顱內感染;使用奧卡西平后發作增多,而丙戊酸鈉治療效果良好;結合多次腦電圖表現、其父親癇性發作史及SCN1A基因檢測結果,符合GEFS+診斷。患兒SCN1A基因c.4787G>A(p.R1596H)為雜合錯義突變,其父及表姑該位點均異常,該突變為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提示其較高致病性。通過本家系病例及總結文獻,GEFS+最常見的致病基因為SCN1A,但SCN1A突變中僅有10%與GEFS+有關。GEFS+臨床表型的異質性與SCN1A基因突變的類型以及位點相關,且抗癲癇藥物的療效與SCN1A突變導致的蛋白表達密切相關。
倫理批準和知情同意:本研究涉及的所有試驗均已通過青島大學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審核批準(文件號QYFYWZLL26227)。所有試驗過程均遵照醫學倫理學相關規定的條例進行。受試對象或其親屬已經簽署知情同意書。
作者聲明:徐凱、孫妍萍參與了研究設計;徐凱、黃碩、朱海芳參與了論文的寫作和修改。所有作者均閱讀并同意發表該論文。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