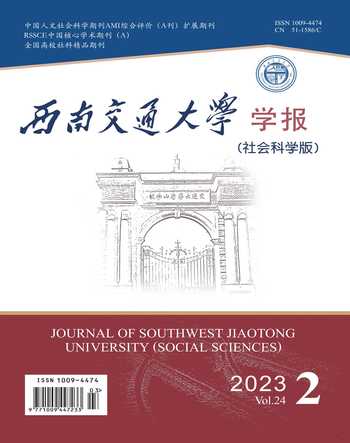“去理想化”:對西方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類型的再審視
摘 要: 運用馬克思·韋伯的“理想類型”方法論思想,以“國家—高校—個體”三大實踐主體的功能性需求的實現為分析框架發現:西方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在國家層面是作為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支點;在高校層面是作為建構學術話語能力和延攬商業利益的基本途徑和功能導向;在個體層面則是深化跨文化理解和形塑個體全球勝任力的關鍵支撐。而面對全球化的新變局,西方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將呈現出新樣態,包括: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將被進一步“去中心化”,傳統范式向多元范式進一步轉換,由“中心—邊緣”格局轉向形成多中心格局。
關鍵詞: 西方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理想類型;實踐主體;全球化;新變局
收稿日期: 2022-08-06
基金項目: 2022中國科協“一帶一路”國際科技組織合作平臺建設項目(2022ZZGJB041415)
作者簡介: 鄭 淳,西南交通大學歷史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高等教育國際化、外國高等教育史、國際科技組織研究,E-mail:zccole@swjtu.ecu.cn。
通訊作者: 劉長軍,西南交通大學黨政辦公室,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高等教育國際化、高等教育管理、國際科技組織研究,E-mail:liuchangjun@swjtu.edu.cn。
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無論是作為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載體,還是人類對世界主義的“共同想象”,高等教育國際化正不斷重塑大學這一人類最古老的社會機構的復雜功能。此外,全球資本市場的形成和勞動分工的細化所導致的全球競爭早已迫使大學走出知識無國界傳播的“烏托邦”。在全球經濟、知識和人才競爭的浪潮中,國際化成為大學適應并勝任這種外部環境的關鍵抓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全球延攬頂尖人才”等成為當前大學推動國際化發展的主要政策話語。在全球化正遭遇更為深層次的、結構性的外部挑戰的現實情境下,全球化的新變局必然會外溢至高等教育領域,尤其體現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實踐層面。
事實上,通過觀察西方國家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可以發現,在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不同時期,西方國家在國際化實踐中表現出明顯的利益偏好和路徑偏好。由于各種歷史原因,西方國家建構了對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理解”和“想象”,通過內在地規定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基本要素結構、價值維度和實踐模式,為非西方國家制定高等教育國際化政策及開展各類實踐提供了知識前提。要打破這種“內嵌型”知識的限制,就需要深化對這種知識本體的系統認識。因此,有必要對西方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類型進行深入研究,為進一步廓清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實踐路向提供一定的知識助力。
一、方法論思想淺釋與分析框架
(一)“理想類型”方法論的內涵淺釋
“理想類型”是馬克思·韋伯(Weber,M.)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內容。雖然韋伯并未在其任何著作中對“理想類型”進行直接界定,但其通過對相關“理想類型”的提出,包括“資本主義精神”“新教倫理”等,都表達了“理想類型”的方法論思想。韋伯指出了兩種不同的“理想類型”,分別為歷史形態的“理想類型”和關于歷史實在中的抽象組成部分的“理想類型”〔1〕。
1.一種理想圖像的建構
在1904年《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中,韋伯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只能抽象出一種“幻象”(illusion)。而這種“幻象”在任何時候都不會以一種純粹的自然形態存在于現實或現實經驗中。“理想類型”是對某項文化事件的發生過程的描述,給描述提供明確的表達手段〔2〕,而不是對這實際發生事件的描寫。“理想類型”所生成的思想圖像將歷史活動的某些關系和事件聯結到一個自身無矛盾的世界之上,這個世界是由設想出來的各種聯系組成的。這種構想在內容上包含著烏托邦的特征,而這種烏托邦的特征是通過在思想中強化實在中的某些因素而獲得的〔2〕。而強化那些關涉因素的選擇在于構造這種圖像的主體,即對某些實在感興趣的個人或研究者。他們通過定位自己的價值興趣、行動動機和實施社會行動的觀念等,從而選擇與哪些因素發生關聯并作為建立圖像的出發點。對于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來講,“理想類型”構成了面向某個對象的“共同想象”。
2.一種認識圖示的建構
無論是在科學研究中還是在普遍的社會活動中,概念建構是人類認識客觀實在的基礎,構成了認識的基本前提。韋伯的“理想類型”學說就是確立了文化科學研究的最基本前提的嘗試〔2〕。“理想類型”就是要在實在的無限性關系當中找到一個支點,從這個支點確定認識的范圍和向度。對于研究者來說,“理想類型”劃定了文化科學中的單個片段的某些特征的集合,而研究通過比較和衡量這個“集合”和實在,并借助這個“集合”能夠將這個片段的某些特征描述出來。如果達到了這個結果,它(“理想類型”)就完成了它的邏輯目標,這恰是因為它(“理想類型”)證明了自身的非實在性〔2〕。在韋伯看來,“理想類型”就像是一個為航海者提供庇護的緊急避風港,直到這個航海者學會了如何在浩瀚的經驗事實的海洋中航行時能夠找到自己的方位〔3〕。
綜上,韋伯所提出的“理想類型”是社會科學研究者面向各種社會現象和社會行動而開展相關研究的一種概念性工具,即“通過片面強調一種或幾種觀點,通過綜合許多散亂的、不連貫的、時有時無的具體的各種現象,并按上述片面強調的觀點將這些現象安排到一個統一的分析結構中去,就可以形成一個理想類型”〔1〕。“理想類型”是對經驗現實的某種特征的“無限放大”,以嘗試形成關于研究對象的精確明了的概念性描述,從而形成一種“概念強調”(conceptual accentuation)〔3〕。“理想類型”能夠幫助社會科學研究者通過比較“理想類型”和現實的異同點,通過獲得解釋多種現實偏離的可檢驗假設〔4〕,而更好地處理經驗現實。需要強調的是,“理想類型”是一種研究手段而并非目的,即借助“理想類型”可以對經驗事實或社會行動作出觀察與比較。同時,“理想類型”不是研究者隨心所欲的“虛構”,而是通過把研究者認為具有典型意義和特征的那些因素予以突出或簡化,從而形成一種獨特的觀察視角。
(二)基于“國家—高校—個體”的分析框架
國家、高校和個體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三大實踐主體,分別本著不同的行動動機開展實踐活動。首先,基于教育本身的社會教化功能以及教育實踐服務于國家治理的事實,國家政府利用教育及其外延形式實現國家治理目標具有較高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從國家層面看,由于受到教育實踐以及鑒于國家政府與高校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西方國家高校一直在如何提升自身績效表現以獲取更多外部資源和提供更多的社會公共產品之間“搖擺”。依靠自由市場競爭機制推動高等教育服務化與貿易化的持續轉變,尤其是推動高等教育實現全球流通與擴散,為西方國家高校拓展經費來源創造了可行之道,也成為西方高校存續與發展的基礎性條件。最后,從個體層面看,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直接行動者和受益者,其能動性將直接關系高等教育國際化項目的執行效益。同時,個體在意識、知識、能力等方面的直接提升又將影響社會多方利益共同體對高等教育國際化項目的認同與支持。從“國家-高校-個體”三個層次分析不同的功能性需求,能夠為系統認識西方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類型提供一個整體視角。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基于“理想類型”的方法論視角,也僅僅是從一個側面強調了西方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某一特征,其目的在于更為直接有效地觀察實踐樣態,而不是尋求對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類型的劃分。同時,這里需要澄清應用“理想類型”研究方法與奈特(Knight, J)、陳學飛等學者提出的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動因說”的區別〔5~6〕。“動因說”強調從政治、市場、學術和文化的角度解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生成邏輯,為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合理性提供辯護,而本文嘗試應用“理想類型”方法,能夠更為直接地觀察西方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實踐類型和特征。此外,“動因說”并未從實踐主體的角度,即從“主體理性”對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類型進行系統探討。
此外,使用“理想類型”可以將復雜的現象分析簡化,提供達到實在認識的中介手段,并能夠利用自身相對性與暫時性的特點,在理論結構的演化中促進對實在認識的發展〔2〕。霍姆斯(Holmes,B.)和許美德(Hayhoe,R.)是在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領域應用“理想類型”的主要學者。比如,霍姆斯借鑒了波普爾(Popper,K.)的“批判二元論”,提出了開展跨國比較教育研究的資料分類模式〔7〕。作為霍姆斯的學生,許美德承襲了霍姆斯的方法論體系,將中國作為一種高等教育的“理想類型”進行探索,嘗試澄清中國高等教育發展背后的文化與價值觀(根植于儒家哲學中關于人、知識及社會的觀點〔8〕、中國的大學模式〔9〕),為中國建構符合自身傳統文化內容及認識邏輯的高等教育體系提供了一定的路徑參考。事實上,雖然“理想類型”由于其自身的復雜性和內在矛盾性導致其在經驗研究中的應用程度并不高〔10〕,但在許多經驗研究中,或多或少都使用了“理想類型”的方法,包括克拉克(Clark,B.)的經典“三角理論”〔11〕、馬金森(Marginson,S.)的“全球-國家-地方”(Glonacal Agency)認識框架〔12〕以及奈特(Knight,J.)對“國際化大學”(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的分類〔13〕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對“理想類型”方法的應用。
二、認識西方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類型的三重底層邏輯" 基于不同的價值認識與行為動機,國家、高校和個體這三類實踐主體采納了不同的實踐模式。對于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應服務于其整體性的國家治理目標;高校作為社會組織,獲取外部資源確保其存續與發展是其開展實踐的第一要義;而對于個體,提高自身在全球化環境中的勝任力和生存力,構成了個體介入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價值依歸。秩序觀念、工具理性和沖突思維分別在三個層次解釋了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生成動因。
(一)秩序之理:建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泛”制度框架
雖然從中世紀開始高等教育國際化就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存在于高等教育實踐中,但高等教育國際化作為一種具有一定目標指向的國家行為或學術行為則是在二戰結束后,而真正組織化的、具有更明確目的性的國際化行為實踐則是在冷戰結束后。二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嘗試建構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通過劃定各國的權責邊界,試圖在全球實現權力平衡,達到新的均勢。其中,為促進國際理解,特別是盡可能地消解由于文化沖突而導致的地緣政治沖突,撫平戰爭對人類的心理創傷,在西方國家的主導下設立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行等致力于促進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通過開展高等教育援助、設立面向全球的學者交流計劃等途徑,西方國家在全球搭建了一個開展高等教育國際交流的行動框架,并將促進國際理解作為共同的價值目標。西方國家從一開始便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行動路線和價值選擇設定了一個基本的方向。一直到20世紀結束,學術資源和人力資源呈現出兩種相反的流向,即“從北到南”和“從南向北”以及阿特巴赫(Altbach,P.G.)等持新馬克思主義觀點學者所提出的高等教育“中心-邊緣”的秩序觀。需要認識到,當前這樣一種“秩序觀”或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泛”制度框架,形成了一套共同的行動邏輯以及在高等教育利益相關者內部促成了一種“共同體想象”。這將推動現代高等教育“西方模式”在各民族文化情境中進一步扎根。
(二)工具之義:構成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行為內涵
根據貝克(Beck,U.)的風險社會理論,當代社會的復雜程度已遠超科技理性的控制范圍,一種強烈的“不確定性”的氛圍正籠罩在人類社會之上。工業現代性的病根不是理性過多而是理性的缺乏、非理性的盛行〔14〕。科技的進步已經不再是解放人類的偉大力量,反而成了社會壓抑的主要手段,工具理性的肆虐成為現代各種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15〕。韋伯(Weber,M.)則是通過“鐵的牢籠”隱喻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化的作用。此外,工具理性還超然于價值理性,強化了人類對一切客觀實在“物化”的行動邏輯。有學者認為,工具理性是指在功利行為的驅使下,借助理性達到自己的預期目的,是一種“實然”狀態的實現,而價值理性是指在合理動機的指引下,運用正確手段達到自己的目標,是一種“應然”狀態的體現〔16〕。在萬物關聯的全球化時代,工具理性主義不可避免地外溢到了教育和文化領域,表象為將某些社會現象的基本特征“無限放大”,以過分追逐某些社會現象的附屬價值來實現自身利益的跨越式增長。西方國家高校為進一步實現其在存續和發展上的“自給自足”,在高等教育領域注入商業資本并將高等教育商品服務化,這些行為都是其對工具理性主義認識的外化。
(三)沖突之治:建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價值內涵
從古希臘智者學派將沖突視為一個社會事實,到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N.)在沖突中發現國家及其核心制度的緣起,再到休謨(Hume,D.)、斯密(Smith,A.)等將近代沖突思維從理性批判的傳統中轉置于經驗的考察之下〔1〕,再到馬克思(Marx,K.)和恩格斯(Engels,F.)將社會沖突思維理論化以及亨廷頓(Huntington,S.P.)提出的“文化沖突論”,可以說,沖突學說一直貫穿于現代社會思想的發展史,還曾在20世紀60年代力圖成為一種取代結構功能主義或與之競爭的社會學分析范式。隨著全球化進入不確定性時期,沖突更多的是指社會充滿各種張力的氛圍、全球經濟競爭以及不同民族之間在目標實現與價值標準上的分歧。從某種意義上講,沖突思維構成了西方意識形態的一種底層思維,更是構成了西方文明觀的基礎以及西方國家認識社會功能結構的一種方法論。在西方文明觀看來,人類總是身處于一種沖突的秩序當中,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17〕,只能通過合作、利益妥協等途徑緩和這種沖突。縱觀高等教育國際化行為實踐及基本價值觀的演化進程,可以發現,這種沖突思維不僅能夠解釋西方國家從國家利益層面致力于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深層次動機,更能解釋在全球化融合與沖突并存的環境中,個體作為沖突的被動參與者,借助于高等教育國際化這一中介形式,對沖突進行管理從而維護自身利益的內在動機。
三、西方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模式述評
(一)國家層面:建構軟實力構成了西方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價值理性的根本基礎
自“軟實力”(Soft Power)學說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以來,由于其在政治和文化研究領域均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因此其一度成為具有較高熱度的學術話語。在進入21世紀以后,“軟實力”學說成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或國際教育研究領域的“熱頻詞”,以至于在各種學術會議、學術期刊、媒體平臺上廣泛出現〔18〕。一個國家“軟實力”的構建成效與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公共外交政策高度相關。反觀二戰后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高等教育國際化通常會被作為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以及內政的延續,不斷灌輸和傳播本國的政治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進而實現其政治目的〔19〕。以高等教育國際化為支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構建了一個較為系統的行動框架并以此嘗試建構一個以西方文化為核心并宣揚其普世價值的文化層級結構,將“安格魯—美國”式的學術范式推向高等教育標準范式的頂端〔20〕。
從實現這一目標的要素結構來看,這個行動框架以提升西方文化軟實力為行動目標,以推進知識外交和文化外交為行動邏輯,以實施各類高等教育援助(包括各類獎學金體系)、構建各類國際組織及制定相關規制為具體手段,最為關鍵的是在這其中高校作為重要參與者推動這一行動框架得以轉化為具體的行動。以美國為例,美國政府于1948年通過了《信息與教育交流法案》(Public Law 80-402)和成立了美國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NAFSA),以面向全球分享其在教育、藝術和科學領域的成果,促進美國高等教育的國際輸出。《信息與教育交流法案》為美國政府所實施的相關交流訪問項目、開展公共外交建立了基本框架〔21〕。杜魯門還于1949年提出了著名的《第四點計劃》(Point Four Program),使得高校的知識與技術援助成為戰后美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個重要領域〔22〕。正如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所言(Powell,C.),在美國接受教育的未來世界領導人對美國所表現的友誼將高于其他一切外交政策或制度所帶來的價值〔23〕。此外,包括富布賴特項目(Fulbright Program)、 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歐盟Erasmus Mundus以及世界銀行(WB)、經合組織(OECD)的發展合作項目都是高等教育實現國家及地區文化軟實力提升的重要途徑。以世界銀行為例。從1981年到1996年,世界銀行貸款承諾一般是同一時期聯合國接受官方發展援助(ODA)金額的3至4倍,世界銀行是各國教育發展最大的外部經費來源〔24〕。再如澳大利亞面向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科倫坡計劃”(Colombo Plan),其中就設立了專門的獎學金為受援國的學生提供了接受教育訓練的機會。然而需要認識到,雖然西方高等教育模式表現出非常明顯的“西方中心”傾向,是西方價值觀體系實現全球傳播的重要路徑,為維護“西方文化”高于“東方文化”的價值判斷提供了辯護基礎,但毋庸置疑的是,這種模式也為促進國際理解以及在各民族內部建構一種“世界主義像”提供了一定的基礎。
(二)高校層面
1.延攬商業利益構成了西方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工具理性的基本途徑
從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末,全球化進程的廣泛興起、商業資本的全球擴散、知識經濟社會形態的出現以及新興經濟體高等教育適齡人口的井噴式增長即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趨勢為高等教育作為一項商品服務實現跨境交付創造了適宜的外部條件。而世貿組織將教育作為一項服務列入關稅總協定又為高等教育商品化創造了合理性前提。同時在新公共管理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旗幟下,高等教育被視為是一項私人物品,超越了其作為公共物品的傳統屬性〔25〕,尤其是隨著西方國家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撥款持續減少〔26〕以及社會法人地位的進一步深化,推動西方高校將國際學生的學費作為經費的重要來源之一。以美國為例,根據國際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和美國國務院聯合發布的數據,從2008年到2018年,國際學生為美國帶來的直接或間接經濟收益增長了10倍多,即從2008年的不足4億美元到2018年的45億〔27〕。再如英國,其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始于撒切爾政府的私有化改革,是私有化政策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發揮作用后外溢至教育領域的結果。也正是在市場化改革思路下,英國政府從1980年起面向國際學生推行“全額成本學費”制度〔28〕,即按照本國學生學費的4倍收費。國際學生的學費收入及其在英國的消費性支出不僅解決了英國高校所面臨的財政危機,也帶動了英國本土經濟的增長以及創造了更多的本土就業崗位。根據《泰晤士高等教育》統計的本土學生、歐盟學生與一般國際學生的學費情況〔29〕,國際學生赴英國學習所需支付的平均學費遠高于本土學生及歐盟學生。再以澳大利亞的高等教育“國際貿易化”為例,澳大利亞政府及高校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理解仍停留在對外援助的思維,并未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對高等教育國際化進行理解。但從1985年開始,尤其是隨著英國政府宣布在國際學生招收政策方面的改革,澳大利亞對其高校所招收的全額自費的國際學生不再進行限制,并于1990年開始要求所有國際學生都需要全額繳納學費,澳大利亞以貿易為導向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模式于此形成。根據普拉特(Pratt,G.)和普爾(Poole,D.)的研究,僅從1983年到1996年,澳大利亞招收國際學生的數量增加了14%〔30〕。馬金森(Marginson,S.)甚至提出了澳大利亞“企業大學”(Enterprise University)的表述〔31〕。根據《澳大利亞國際教育路線圖》(AIE 2025 RoadMap),雖然其強調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國際化應回歸其應有的“價值理性”,但新時期澳大利亞政府仍舊強調貿易取向的國際化發展,教育依然被視為出口產業〔32〕。為保持其高等教育作為商品輸出的競爭性,西方國家設計了一系列的教育產品,包括提供高等教育海外(跨境學習計劃的實施)和本地化學習計劃(建立海外分校)以及圍繞這兩大產品而構建的支持體系,包括支持英語語言外教的國際輸出、設立海外語言培訓中心和海外招生辦公室、設立跨國流動綜合服務體系(如提供簽證信息服務、面向國際學生的在地服務、為促進國際學生融入當地社區而提供的支持等)。
2.建構學術話語能力構成了西方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功能導向
從柏拉圖的“學園”到地中海文明的傳播中心亞歷山大圖書館,從中世紀時期的“隱世組織”博洛尼亞大學再到作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再生產中心的多科技術大學,大學作為一種學生學者行會組織所獨有的自治與自由精神和對知識的傳播與分享以及學術權威的社會形象,始終構成了大學作為人類最古老的社會組織的合法性基礎及存在特征。然而,知識隨著民族意識和國家主權意識的覺醒而被附上了“自我意識”,而作為知識生產的學術研究活動也被貼上了民族的標簽。從福柯的“知識-權力”共生關系來看,權力制造知識,建構一種知識領域才能生成相應的權力關系,而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才能生成知識〔33〕。西方國家對捍衛知識價值無涉和知識生產網絡普世價值的敘事邏輯,隱蔽了其對其權力體系構建的終極價值追求。這種價值追求在知識經濟時代下愈發凸顯。在進入知識經濟社會以后,各民族之間的競爭從傳統的軍事“硬實力”較量轉向知識與科技的競爭,知識創新能力成為各國提升綜合競爭力的核心關切。作為知識創造和傳播的承載組織,現代高校自然參與到人類社會的現代性及可能存在的后現代性的進程中。鑒于西方國家維護其政治霸權和經濟霸權的意志早已外溢至高等教育領域的事實,西方國家高校通過構建全球創新體系以實現對知識創新的全球治理并賦予知識主權屬性,從而確保西方國家位于學術話語的中心。為充分把握對學術研究議程的設置和學術資源的流向以及對學術權力的分配,西方國家政府設立專項經費鼓勵其高校設立高水平學者海外訪學計劃和聯合科研計劃,以實現構建以西方學者為中心的學術矩陣,并通過開辦高水平國際學術期刊、構建國際學術評價體系以及推動國際科技組織落地等途徑,影響國際學術倫理及價值觀的演化進程。就大部分西方國家來看,雖然國家政府對高校的整體撥款是持續減少的,但就國家政府所關心的關切國家核心利益的科技議題來看,其所提供的經費表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換言之,西方國家政府或大型資本財團通過設立專項經費計劃以資助其高校面向特定領域開展科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規定高校開展國際交流合作的領域與內容。此外,把握學術話語不僅可以賦能西方學術研究的產業化及資本化路向以及主導全球學術生態的治理,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斷優質人力資源從北往南“回流”的發展態勢,為緩解西方國家核心人力資源矩陣優勢的流失提供保障。
(三)個體層面
1.深化跨文化理解構成了西方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功能外延
高等教育國際化體現了高校作為一種獲得部分授權的超國家行為體的共同行為趨向,其制度化發展離不開持續的全球和平發展環境。而教育作為形成民族認同、思想整合和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制度工具〔34〕,在促進全球和平發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實上,高等教育國際化與維持全球和平發展環境存在一種“共生”關系。也正是基于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才在其章程中明確指出,教育應通過開展各類型的國際合作,在促進理解和促進和平上做出貢獻,并于1946年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屆大會上強調,各國應致力于培養國際理解意識,增進國家間的相互理解,促進世界和平。可以說,從全人類共同利益的角度,促進國際理解為開展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定下了價值基調,也規定了各國開展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合作的價值向度和行為路向。從國家內部角度來看,高等教育國際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那些移民國家由于社會的多民族性而造成的社會分裂危機,為西方社會的多元文化的存置拓展了必要的空間,從觀念上整合了西方社會內部不同文化群體過度維護其本文化合法性的激進思維。以美國為例,作為移民社會,美利堅民族是一個由異質性人口所構成、規模龐大、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民族〔35〕。雖然美國社會自殖民地時期起就是跨民族、跨種族的〔36〕,但美國在二戰后建立的文化霸權思想,即“美利堅文化”所表現的優越感造成美國社會內部具有明顯的文化排他主義思想,在接受異文化的認識上具有明顯的狹隘性。這導致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前,相對于大量接收外國學生的事實,美國在派出本國學生方面一直落后于歐洲國家。隨著大量異文化群體涌入美國社會所造成的文化沖突以及美國社會本身的民族認同缺失,從美國高校到聯邦政府均認識到通過高等教育派出美國學生赴異文化環境學習交流的必要性,以提升美國公眾的國際理解能力以及參與全球化進程的勝任力〔37〕。再看歐洲地區,20世紀90年代,日益增多的外國移民對歐洲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社會安全產生了一系列的沖擊和影響。多民族性和多元文化所造成的社會張力使歐洲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壓力。歐洲開展的“伊拉斯謨”項目、“蘇格拉底”計劃以及后來的“博洛尼亞進程”都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歐洲內部的相互理解,緩解了由于本文化與異文化之間沖突所造成的社會動蕩與危機,特別是推動了“歐洲認同”(European Identity)的形成〔38~39〕。根據羅素大學集團(Russell Group)于2018年開展的針對“伊拉斯謨”校友的跟蹤研究,發現“伊拉斯謨”及“伊拉斯謨+”項目的參與者由于在異文化環境中開展了一定時間的學習與生活,其跨文化理解能力的成熟度得到提升〔40〕。盧爾德(Llurda,E.)還通過對參加“伊拉斯謨”項目的學生群體進行研究,發現項目的實施有助于“歐洲公民”(European Citizenship)意識的形成〔41〕。
2.形塑全球勝任力彰顯了個體參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價值理性
世界經濟全球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對勞動力的要求〔42〕。高校學生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行動者,要想勝任全球市場對人力資源的高要求,就需要習得與全球化相適應的知識和能力。全球勝任力作為一種政策話語被提出,體現了西方國家同時追逐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內在矛盾。一方面,西方國家試圖通過改造高等教育實踐的類型和內容,擺脫工具理性的奴役,轉而迎來價值理性回歸的戰略預設,即以謀取全人類共同福祉為話語基礎拓寬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合理與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經濟效應作為檢驗人力資源質量的核心參照,又使得西方國家不得不將全球勝任力與高端人力資源積累掛鉤,并納入促進國家經濟增長的敘事框架。這從經合組織(OECD)使用人道主義的話語對全球勝任力意涵的表述即可看出。西方國家通過自上而下的機制安排以及通過明確的資源導向完善項目設置,鼓勵其學生赴異文化環境中學習與交流,融通內嵌于異文化中的思維邏輯與行事方式,既在異文化環境中拓寬認識異文化的路徑,也在異文化環境中建立擴散本文化的支點。而高校學生則通過多元的跨境學習交流項目,通過在異文化環境中的沉浸式文化體驗,厘清了對異文化的認識邏輯以及與異文化者溝通的方法,無論是在生活中還是在工作中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文化差異。同樣以澳大利亞為例,作為高等教育國際貿易大國,隨著澳大利亞聯邦政府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介入高等教育體制變革以及高等教育事業的海外擴張,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國際化實現了工具理性向統合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視域的轉換。根據《澳大利亞國際教育戰略2025》(National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25),澳大利亞國際教育將聚焦于加強與合作伙伴的聯系,從而提高澳大利亞學生的全球競爭力。當然,西方國家也認識到了學生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實踐主體的重要性,也正是基于此認識,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進程就經歷了從“個體視角”(實施“伊拉斯謨計劃”等)朝“組織視角”(開啟“博洛尼亞進程”)再到基于“個體”的“組織視角”(以學生利益為核心節點的組織化)的轉變。歐盟委員會在其《歐洲高校發展戰略計劃》(A European Strategy for Universities)中強調加強高校國際合作的必要性,從而提升高校為年輕人、終身學習者和研究者習得適當技能而提供必要支持的能力〔43〕。
四、全球化新變局下西方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新樣態" 當今世界處于大發展大變革的調整期,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正經歷深度的歷史性調整〔44〕。新興國家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正在打破舊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45〕,一種新的全球權力平衡正在加速形成,全球化不僅表現出一以貫之的斷裂性,還表現出多變性與反復性。在新變化的浪潮中,西方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呈現出新的樣態。
(一)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將被進一步“去中心化”
現代大學體制濫觴于歐洲大陸而興起于美國。隨著商業資本、人力資源、文化符號等在全球的擴張與流通,高等教育的“西方模式”被遷移至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因而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模式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了“舶來品”,都不同程度地嵌入了“西方模式”所規定的內在要求,形成了高等教育“中心—邊緣”的場域結構。基于這種場域結構而形成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主要類型及其空間流向,體現出以西方為中心的特征。這樣一種場域結構所生成的話語權力限制了非西方國家對全球化的想象及其關涉領域,導致各國把西方國家對高等教育的理解作為其制定具體規制及政策的參照。然而,各國高校的國際化實踐行為仍離不開其所在民族國家規制的框架,這尤其體現在非西方國家在開展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豐富樣態上。這種多態化的趨勢并未與以西方為中心的傳統實踐模式發生明顯抵觸,甚至還呈現出一定的互補性特點。在過去的十幾年里,在創設世界一流高校的浪潮下,亞洲高校的崛起對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意涵做出了新的詮釋〔46〕。正如約翰(Jones,E.)和德維特(De Wit,H)所指出的那樣,由于全球更多的國家和機構參與高等教育發展進程,應該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概念本身被全球化這一事實進行反思,即國際化不應再被視為西化的、主要是“盎格魯-薩克遜式”的、以英語語言為學術交流語言的范式〔47〕。面臨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的變化外溢至本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多態性特征將得到進一步拓展,高等教育國際化以西方為中心的路徑依賴將被打破。
(二)傳統范式向多元范式的進一步轉換
首先,高等教育國際化正加速從一個以人員流動為基本特征的“松散化”的相對“無序狀態”朝一種以愈加制度化的范式轉換,體現出戰略性議程設置的特點。劍橋大學、東京大學等亞洲高校均制定了國際化發展戰略,以一種“過程化”的系統觀推動國際化發展。國際化不僅從高等教育發展的邊緣位置來到了中心位置〔48〕,更是不斷鞏固了其中心位置。其次,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對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合作的阻斷為各國政府及高校加強對在地國際化實踐的重視提供了窗口期。以在線教育為主要實施手段的在地國際化實踐將成為傳統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重要補充〔49〕。高等教育國際化“普及化”或許不再是一種純粹想象。再者,根據吳寒天和查強提出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模式新的類型學框架〔50〕,處于“邊緣”或“半中心”位置的高校正在從一種“向內”的模式向一種“向外”的模式轉變,正構建一種“雙向”的交流模式。同時,這種流向的轉變不僅體現在人員、資源等物質要素上,還體現在知識的跨國整體性遷移〔51〕。
(三)從“中心-邊緣”格局到多中心的形成
新冠疫情從時空意義上所造成的全球互動的斷聯驚醒了將高等教育作為經濟增長點的部分西方國家。根據國際大學聯合會(IAU)的報告,全球有近60%的高校遭受影響。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甚至有接近90%的私立高校面臨關閉的風險〔52〕。當前,雖然在線教育能夠補充跨境教育不足的問題,但物理性流動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實施跨境教育的主要解決方案。一方面,西方高等教育傳統強國仍將保持對國際學生的顯著吸引力,但這種吸引力會被分散。根據“先發劣勢”理論(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西方高等教育傳統強國由于受限于對先發學術場域和傳統國際交流合作范式的路徑依賴,因此在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領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滯后性”〔53〕。另一方面,得益于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經濟增長潛力、在全球學術場域中的話語能力的持續提升、良好的科技創新政策和文化空間、靈活設置的獎學金體系等因素,包括中國、印度、韓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正逐漸成為國際留學生新的目的地。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估算,中國和印度在2022年和2023年的經濟年增長率將維持在5%以上(而歐美國家的2022年年增長率均值為3.9%以下)〔54〕。此外,根據科睿唯安(Clarivate)發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至2022年),有14所中國大學的高被引論文數量的年增速在12.5%到658%之間;如果照此增速,就高被引論文數量這一指標來看,中美頂尖大學間的差異將在很大程度上不復存在〔55〕。可以預見的是,隨著國際學生的流向由從南到北的單向流動逐漸轉變為現今的多向流動,高等教育全球市場版圖正在被重塑。
(四)高等教育國際化功能話語的轉向
根據奈特(Knight,J.)在2004年對高等教育國際化所作出的經典定義,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將國際的和跨文化的維度融入教學、科研的過程〔56〕。為突出高等教育的功能,奈特于2008年在其原有定義上進行了修正,即“在國家、部門和機構層面的國際化是一個將國際化的、跨文化的、全球化的維度整合進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和辦學的過程”〔57〕。很顯然,由于戰后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以各類援助項目、人員流動出現的局部現象,因此這一時期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解釋更多的是停留在高校內部或面向高等教育本身,并未從一個基于社會整體的功能觀對高等教育國際化作出解釋。然而,從過去的十余年來看,各國高校已有意識地通過國際交流合作更大程度地介入那些關切人類重大利益的共同問題,這包括實施大范圍的文化項目以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構建雙邊及多邊型高校國際聯盟等。這正如德維特(De Wit,H)和阿特巴赫(Altbach,P.G.)所指出的那樣,高等教育國際化應更多的聚焦如何提升高等教育質量和研究水平以及如何能夠更多地造福于人類社會〔58〕。不僅如此,當前霸權主義與權力多極化之間的激蕩愈發激烈,全球權力體系與均勢結構正進入深度調整期〔59〕,西方文化的“普世價值”將遭到進一步動搖〔60〕,而高等教育國際化那種西方化的(主要是“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和以英語為學術語言)并帶有“強制式”〔61〕的典型范式也將被修正。
(五)高等教育國際化“自我意識”的進一步“政治化”
從中世紀開始的以“游學”“游教”為典型特征的知識無國界自由傳播的現象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弱政治性”或“政治中立性”的敘事方式確立了合理性基礎。西方高校曾以學術自由和自治,即“主體意識”,作為其作為最古老社會組織存續的根本性條件,嘗試遠離政治爭斗的“漩渦”。然而,當國家遭遇核心利益沖突尤其是根本性的價值觀沖突時,這種“主體意識”便會消失殆盡,徹底倒向權力的一端。在此條件下,西方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表現出典型的“政治意識”。比如中美貿易戰時期,為打壓并限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崛起,特朗普政府通過出臺法案和簽證手段等,限制中國學生赴美國學習STEM相關專業。再從最近的俄烏沖突看,為表達對俄烏沖突的抗議,歐盟于2022年3月4日暫停了俄羅斯參與“歐洲地平線計劃”(Horizon Europe)的資格并終止了在該計劃框架下已經開展的相關研究項目〔62〕。而俄羅斯當局也從2022年3月起下令驅逐反戰學生,包括俄羅斯內政部在2022年3月9日驅逐了13名外籍學生〔63〕。可以預見,在這樣一個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激蕩的時代,無論是主動介入還是被動卷入,西方國家高校將在各種政治議程中闡明更為鮮明的價值立場,以表明其向“政治正確”的無限靠攏。如此,高等教育國際化或許會陷于一種無限循環的價值想象,而高等教育的價值無涉也將真正成為一去不復返的“烏托邦”。
參考文獻:
〔1〕于 海.西方社會思想史(第三版)〔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220,320,292.
〔2〕馬克思·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韓水法,莫 茜,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5-46,xxii,58,xxiii-xxiv.
〔3〕Whimster S. The “Objectivity”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M〕. London: Routledge, 2012:133,124.
〔4〕 Priyadarshini S. Webers “Ideal Types”: Definition, Meaning, Purpose and Use (Your Article Library)〔EB/OL〕.(2015-06-22)〔2022-03-11〕. https://www.yourarticlelibrary.com/sociology/webers-ideal-types-definition-meaning-purpose-and-use/43758.
〔5〕Knight J. Internationalization Remodeled: Definition, Approaches, and Rationales〔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04,8(1):5-31.
〔6〕陳學飛.高等教育國際化:跨世紀的大趨勢〔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15-21
〔7〕薛理銀.問題法與比較教育——對布萊恩·霍爾姆斯的一次采訪〔J〕.比較教育研究,1992,(3):25-30.
〔8〕卡倫·芒迪,凱西·比克莫爾,許美德,等.比較與國際教育導論:教師面臨的問題〔M〕.徐 輝,朱 紅,王正青,等,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9:38.
〔9〕Hayhoe R. China in the Center: What Will It Mean for Global Education?〔J〕.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2017,12(1):3-28.
〔10〕Swedberg R. How to Use Max Webers Ideal Type in Sociolog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2018,18(3):181-196.
〔11〕伯頓·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M〕.王成緒,徐 輝,等,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123-135.
〔12〕Marginson S., Rhoades G. Beyond National States, Markets, and 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 A Glonacal Agency Heuristic〔J〕. Higher Education,2002,43(3):281-309.
〔13〕Knight J.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Misunderstandings and Emerging Models?〔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5,19(2):107-121.
〔14〕烏爾利希·貝克, 安東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代化: 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 傳統與美學〔M〕.趙文書,譯.北京:商務出版社,2001:43.
〔15〕張風帆. 科技非政府組織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04:i-ii.
〔16〕王延隆,王華華.高等教育:現代性批判與共同體構建〔J〕.湖北社會科學,2019,(10):142-148.
〔17〕馮 鉞.沖突與優越感并存的西方文明觀〔EB/OL〕.(2019-09-17)〔2022-03-08〕.http://www.rmlt.com.cn/2019/0928/558061.shtml.
〔18〕Knight J. The Limits of Soft Power in Higher Education〔EB/OL〕.(2015-01-21)〔2022-03-23〕.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40129134636725.
〔19〕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引進國外智力工作分會.大學國際化理論與實踐〔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73.
〔20〕Yang R. What Counts as ‘Scholarship’? Problematising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in China〔J〕.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2006,4(2):207-221.
〔21〕Ruther N.L. Barely There, Powerfully Present: Years of US Policy o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M〕.Lonon:Routledge,2014:62-64.
〔22〕Gumperz E.M.D. Internationalizing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R〕.California: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1970:34-35.
〔23〕Nye J. Soft Power and Higher Education〔C〕∥Forum for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Archive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2005:11-14.
〔24〕閆溫樂.世界銀行教育援助研究:特征、成因與影響〔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2:2.
〔25〕Kirp D L. 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 The Marketing of Higher Education〔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11-12.
〔26〕Wanna J., Forster J., Graham P., et al (Eds.).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C〕.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AU,1996:122.
〔27〕NAFSA Analysis.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Enroll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A Ten Year Tend〔2021-03-05〕〔2022-03-27〕.https://www.nafsa.org/policy-and-advocacy/policy-resources/nafsa-international-student-economic-value-tool-v2.
〔28〕易紅郡,繆學超. 市場化道路上的英國高等教育〔N〕. 中國科學報,2012-10-31(007).
〔29〕Times Higher Education. Annual Tuition Fee Data for Full-time Courses at UK Institutions〔EB/OL〕.(2016-09-19)〔2022-03-25〕.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features/international-and-postgraduate-fees-survey-2016.
〔30〕Pratt G., Poole D. Internationalisation Strategies as a Response to Market Forces-Directions and Trends〔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Australasia,1998,7(2):9-25.
〔31〕Marginson S., Considine M. The Enterprise University: Power, Governance and Reinvention in Australi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11.
〔32〕甘永濤.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歷史形態:起因、發展與未來趨勢〔J〕.高等理科教育,2021,(2):116-123.
〔33〕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29.
〔34〕安迪·格林.教育、全球化與民族國家〔M〕.朱旭東,徐衛紅,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201-203.
〔35〕米爾頓·M·戈登,著.美國生活中的同化:種族、宗教和族源的角色〔M〕.馬 戎,譯.譯林出版社,2015:67.
〔36〕魏南枝.美國的文化認同沖突和社會不平等性——種族矛盾的文化與社會源流〔J〕.學術月刊,2021,53(2):85-96.
〔37〕Knight J.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New Directions, New Challenges: 2005 IAU Global Survey Report〔M〕. Pari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2006.
〔38〕Strath B. A European Identity: To the Historical Limits of a Concept〔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02,5(4):387-401.
〔39〕Kohli M. The Battlegrounds of European Identity〔J〕. European Societies, 2000,2(2):113-137.
〔40〕Cole J. Why Erasmus is important for Students〔EB/OL〕.(2018-02-09)〔2022-03-21〕.https://russellgroup.ac.uk/news/the-importance-of-student-exchange/.
〔41〕Llurda E., Gallego-Balsà L., Barahona C, et al. Erasmus Student Mobi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Citizenship〔J〕. The 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2016,44(3):323-346.
〔42〕胡 敏.全球勝任力:面向未來的青少年核心素養〔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9:18.
〔43〕European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EB/OL〕.(2022-01-05)〔2022-03-17〕.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xnt/EN/TXT/PDF/?uri=CELEX:52022DC0016.
〔44〕羅建波.在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中把握戰略機遇期〔J〕.科學社會主義,2019,(3):14-22.
〔45〕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M〕.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217.
〔46〕Geerlings L R C, Lundberg A. Global Discourses and Power/Knowledge: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Futures of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Rise of Asi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2018,38(2):229-240.
〔47〕Jones E, De Wit H. Globalized International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Practice〔J〕. Management,2014,33:95-104.
〔48〕De Wit H. Internationalis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 Western Paradigm or a Global, Intentional and Inclusive Concep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2020,7(2):31-37.
〔49〕菲利普·G·阿特巴赫,高 媛,劉 進,西蒙·馬金森,彭 鳳,烏爾里希·泰希勒,盛曉彤,許美德,李新宇,漢斯·德·維特,林松月,法扎勒·里茲維,高勝寒.后疫情時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未來走向〔J〕.高校教育管理,2022,16(1):1-14,86.
〔50〕Wu H., Zha Q. A new Typology for Analyzing the Direction of Mov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8, 22(3): 259-277.
〔51〕沈文欽.國際學術流動與中國大學的發展:逆全球化趨勢下的歷史審視〔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20,72(4):47-70,186.
〔52〕Marinoni G, Vant Land H, Jensen T.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Higher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R〕. Pari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2020:23.
〔53〕Zambrana R. Dialectics of Progress〔J〕. Philosophy Today, 2017, 61(4): 1047-1057.
〔54〕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ising Caseloads, a Disrupted Recovery, and Higher Inflation: Latest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rowth Projections〔EB/OL〕.(2022-01-11)〔2022-03-21〕.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2/Update/January/English/Data/WEOJanuary2022update.ashx.
〔55〕西蒙·馬金森,楊力藶.生生不息的火焰:全球科學中的中國〔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20,18(4):2-33,185.
〔56〕Knight J. Internationalization: Elements and Checkpoints (Research Monograph, No.7)〔R〕. Ottawa: Canadian 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1994:7.
〔57〕Knight J. Higher Education in Turmoil〔M〕.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2008:21.
〔58〕De Wit H., Hunter F., Howard L., et al (Eds.).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R〕. Brussels: European Parliament, 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l Policies (Culture and Education),2015:29.
〔59〕孟祥青,程 煒.新時代中國全球安全治理的理念與實踐〔J〕.國際問題研究,2021,(6):16-31,140-141.
〔60〕Rui Y. Globalis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 Critical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2003, 49(3): 269-291.
〔61〕Teferra D. Defining Internationalisation-Intention Versus Coercion〔EB/OL〕.(2019-08-11)〔2022-06-23〕.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190821145329703.
〔62〕European Commission. Commission Suspends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EB/OL〕.(2022-03-17)〔2022-06-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1544.
〔63〕Lem P. Russian Universities Expelling Large Numbers of Anti-war Students〔EB/OL〕.(2022-03-29)〔2022-06-23〕.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russian-universities-expelling-large-numbers-anti-war-students.
Abstract: Based on Max Webers “Ideal Type” methodology, and tak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ctional needs of “country-university-individual”, the three major practice subjects, a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found that different functional needs make different practice typ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HE) among western countries. Firstly, IHE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national soft power at the national level. Secondly, IHE serves as the basic approach and functional orientation for constructing academic discourse ability and attracting commercial interests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Thirdly, IH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epening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shaping individual global competenc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However, facing the new changes as to globalization, the practice of IHE among western countries will display new patterns, including that the 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model will be further “decentralized”,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will be further transformed into a pluralistic paradigm, and the “center-periphery” pattern will be turned to form a multi-center pattern.
Key words: wester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deal type; practice subject; globalization; new changes
(責任編輯:閆月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