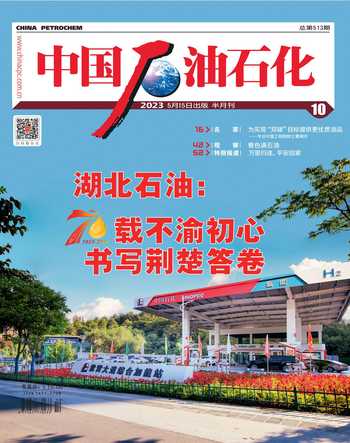將海底油氣田繪成星座圖
秦怡然 楊瑞君

謝仁軍一直堅守著“設計雖繁不敢輕懈怠,科研雖難不敢忘初心”的“工匠精神”。
少有人知道,幽深的海底究竟奔涌著多少寶藏。也鮮有人見過,洶涌海面之下發生的驚心動魄。
中海油研究總院鉆采研究院副院長謝仁軍的工作,就在看不見的海面之下。在鉆頭入水之前,他已經用數據和模型為無數油氣田繪出了一整套開發藍圖。
工作14年來,他主持和參與了30多個油氣田的鉆采設計方案,其中不乏像“深海一號”超深水大氣田、我國首個海上高溫高壓氣田這樣在國內無先例、無經驗的高難度項目。榮獲中國青年五四獎章,是對他堅守“設計雖繁不敢輕懈怠,科研雖難不敢忘初心”的“工匠精神”的充分肯定。
但行前路,無問西東
當謝仁軍獲得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的消息傳到鉆采研究院,“實至名歸”是身邊人的第一反應。
謝仁軍自己卻有些“勝之不武”的赧然:“30位獲獎者里,我年紀最大,是踩著青春的尾巴得了這個獎。”
不過隨即他又釋然:“科研工作就是這樣。沒有十年、二十年的沉淀,是很難做出像樣的成績來的。”
他深刻地記得入職的第3年,接過了東方13-1氣田開發前期研究項目鉆采負責人的工作。這是中國海上第一個高溫高壓氣田開發項目。自此,他開始了馴服高溫高壓這頭猛獸的征程。
高溫高壓油氣田,就像一個溫度高、壓力高的大煉爐,開發技術條件要求極為苛刻。但這是必須要攻克的難關——我國南海油氣資源極其豐富,而高溫高壓領域的天然氣就占三分之一。
高溫高壓氣田開發過程中,井筒環空帶壓問題突出。一旦超過允許值,就會影響安全生產。
兩年時間,謝仁軍給出了東方13-1高溫高壓氣田開發的鉆采方案。在后續實施鉆完井過程中,7口井全部實現零環空帶壓:“這在世界上的高溫高壓井中都是少有的。”
回想第一次做項目的過程,謝仁軍提到最多的是前輩們的幫助。“那時候很有壓力,但是前輩們的一句話、一些指導,就能給我很大的啟發。”
第一次高溫高壓氣田項目干得漂亮,很快第二個項目來了。在目前中國海上最大的高溫高壓氣田項目——東方13-2氣田中,謝仁軍仍然擔任鉆采技術攻關與方案設計項目經理。
2014到2017年,面臨低油價的壓力,謝仁軍在東方13-2氣田的鉆采方案中做了很多技術方案優化。其中就包括將原先只能打不到4000米的高溫高壓定井拓展到打超過5000米的高溫高壓大位移井,水平段長度由300米延伸到600米。
但是,在項目前期審查時,他的方案受到不少專家的質疑。
面對質疑,謝仁軍習慣用數據說話。一次次建模,一次次計算,最終的計算結果讓專家豎起了大拇指。2020年,東方13-2氣田成功投產,入選當年“央企十大超級工程”。
經過多個高溫高壓項目的研究積累,謝仁軍帶領團隊突破的高溫高壓井設計關鍵技術作為關鍵成果之一獲得了2017年的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不負熱愛,不負使命
成績不是結束。謝仁軍仍在馴服更多猛獸的路上。
2014年,在時任“深海一號”項目經理朱海山的推薦下,謝仁軍擔任我國首個超深水大氣田“深海一號”的開發鉆采設計項目經理。他解決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布置鉆井水下井口。
一般的油氣田,井口分布范圍也就30~50平方公里。但是,“深海一號”氣藏極其分散,150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分布著7個“土豆塊”。要開發11口井,最后全部連接到一個平臺,怎樣布置水下井口才最合理?
常規的做法,要么每口井都做一個井口,要么做一個大管匯。謝仁軍和同事們設計了不下上百套方案,又從中優選出七八種,但不是效果不理想,就是經濟效益不夠。
一天晚上,天氣晴朗,謝仁軍帶著孩子散步。抬頭便是漫天星辰,看著狀似無序卻又能連成星座的星星,他的腦海中突然冒出一個新思路:那么大的區域沒法一條線穿起來,那就分區考慮,各個擊破!
“大串接小集中”的模式就這樣誕生了。
“你看,是不是很像星座圖。”謝仁軍舉著最終的井網圖興奮地解釋,“從繁星點點,到串成海底星座,海上的平臺就能定位了。”
提到工作,謝仁軍的眼神總是放著光,奇思妙想層出不窮,熱情與精力仿佛永遠用不完。
“你必須熱愛你的工作,否則就很難百分之百投入。”在謝仁軍看來,工作不能只是“感不感興趣”,而是要有足夠的責任感。“只要是我負責的任務,我就一定會盡全力,做到自己滿意。”
在同事們眼中,他是出了名的“超人”。超長待機不在話下,多線程工作游刃有余,遇到再刁鉆的問題,也能快速答出一二三。就連辦公桌,他也永遠收拾得井井有條。
雖然被同事們稱作“身邊的鐵人”,但他也有感覺力不從心的時候。
2019年初開始,謝仁軍突然反復低燒兩個月,遲遲查不出病因。當時,全球首個超稠油規模熱采項目旅大5-2N油田I期開發基本設計項目即將進行中期審查。領導同事勸他回去休息,但作為鉆完井項目經理,他一天都不愿耽誤,拖著病軀加班加點趕進度。
4月底,項目的中期審查通過,他也拿到了初步診斷結果。醫生認為95%的可能性是淋巴瘤。如果確診,平均5年生存率僅38.4%。
36歲,風華正茂。如果生命開始倒計時,應該做些什么?謝仁軍抱著最大的希望,希望自己是那幸運的5%,也做了最壞的準備。
“我走了沒什么,但最放心不下家人孩子。”他開始研究應該給孩子買什么保險,又把購物車里那臺想買很久的筆記本電腦默默刪掉。
幸運的是,命運跟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最終檢查結果是嚴重的淋巴炎。
在醫院,他和妻子抱頭痛哭。那種劫后余生的恐懼打破了他向來的冷靜。
從醫院出來,謝仁軍去買下了那臺心儀已久的筆記本電腦:“換個新電腦,工作就更方便了。”
廿載磨礪,一朝玉成
2022年6月6日,由謝仁軍具體負責牽頭起草的ISO3421《石油與天然氣工業——海洋隔水導管下入深度與安裝設計》國際標準經ISO正式向全世界發布推廣。這是中國海洋鉆井技術領域以“模型、算法”為核心的首部ISO國際標準。
一項國際標準能夠立項,就意味著它填補了這一領域的空白。從標準發布的那一天起,就說明有人第一次把隔水導管下入深度計算和施工控制技術,用38頁紙40多個公式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這項成果的背后,是中國海油人20年的堅持。
隔水導管是海洋鉆井的咽喉要道。2002年,因為一次隔水導管變形事件,當時的中海石油研究中心鉆井專業科研人員開始了隔水導管關鍵技術相關研究。
有沒有可能有一套標準的算法,能計算出精準數值,讓隔水導管在不同海域都能站得住、不下沉、不倒下?
2017年,起草國際標準的擔子落在謝仁軍肩頭。當年10月,他首次在ISO標準化年會上做了全英文演講。“創建標準算法”的想法,獲得了ISO下設的負責石油天然氣工業方向的技術委員會主席的肯定。
ISO是國際上最大的標準化組織。想要正式發布,必須經過多次論證,再由各個成員國共同進行多個階段的投票。
2018年6月,項目成功立項。一年半的時間,起草團隊打磨出了第一版草案。但當謝仁軍帶著團隊成員前往美國參加第一次工作會議時,遭遇了莫大的打擊:“可以說非常不認可。”
最直指要害的一個問題是:“你們的草案都是根據中國海域情況分析的。在世界其他海域,這套標準還適用嗎?”
緊張、失落,加上13個小時的時差,那幾天謝仁軍過得恍恍惚惚。
看著大家士氣低落,當時帶隊的中國海油集團公司科技信息部負責人周建良鼓勵他們:“都要有個陣痛的過程。”
回國后,謝仁軍和團隊成員們重振旗鼓,搜集世界各海域資料,充分調研,多番打磨。
2020年國際標準化日這一天,謝仁軍將獲得各國專家認可的草稿提交給國際標準化組織進行投票。
這次投票的結果讓謝仁軍在幾分鐘之內經歷了情緒過山車:“非常驚喜的是,我們獲得了100%支持率,這是對我們極大的認可。緊接著心里又是一沉,各國專家共提了380多條意見,其中有不少是針對核心算法的,而我們要在3個月之內完成修改。”
沒時間氣餒。
一個星期封閉辦公,沒日沒夜,一個一個解決問題。7天時間,謝仁軍帶領團隊成員給90%的技術問題找到思路,并針對核心難點再進行大量模擬驗算,力求得出有充分說服力的結果。
2022年4月27日,反復打磨的提案最終稿獲全球ISO全票通過。美國、英國、挪威、巴西等12個成員國全部贊成支持。
“這個標準里全是公式和模型算法,這意味著我們堅持做基礎研究、做交叉學科研究有了成果。”時隔近一年,謝仁軍仍難掩激動。
做科研,最重要的是什么?
“質疑,求實。”謝仁軍說。做研究,是從無到有的過程。敢于質疑傳統,才能做到創新,實事求是,才能把每一步走扎實。
“最重要的,還是堅持。”就像走到國際舞臺,謝仁軍走了40年;就像一部國際標準的發布,需要幾代人20年的努力。
科研路無涯,攀登與沉淀永遠是進行時。
責任編輯:陸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