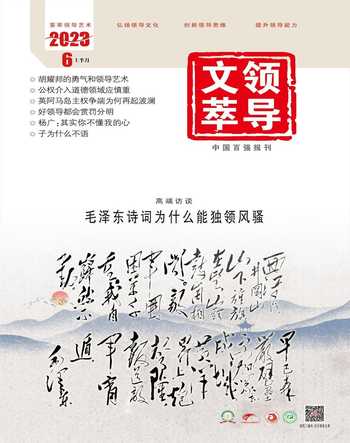應避免“劣質城鎮化”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課題組

縣城是我國城鎮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標志著縣域城鎮化建設進入新階段。我們認為:欠發達地區縣域建設的目標是服務于鄉村振興、統籌城鄉發展,要警惕地方政府追求城鎮化率的過快提升,錯誤定位縣城經濟社會功能,陷入嚴重“劣質城鎮化”。
正確認識縣域城鎮化的基本特征
1.縣域是人口流出地,縣城常住人口規模不大。相對于中小城市,縣城人口規模不大。縣城及縣級市城區人口占全國近9億城鎮常住人口的近30%,縣域鄉村人口比縣城常住人口要多得多。我們在中部三個省九個縣調研,發現縣域人口流出普遍。統計數據顯示,河南省110個縣級單位中,僅有三個縣為人口流入狀態,這三個縣全部位于鄭州周邊,其他的縣人口凈流出,16個縣人口流出率超過30%,50個縣人口流出率超過20%。“十四五”期間,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推進,人口流出率還要進一步提升,縣域范圍的平均人口規模還要進一步下降。
2.縣域經濟分化,中西部縣城和東部發達地區縣城性質不同。從經濟發展能力來講,縣域經濟是分化的,這反映在產業結構特征、經濟總規模及地方財政收入等方面。這是一個大國建設統一大市場必然會出現的格局。有兩類完全不同的縣域:沿海縣域是城市帶的一部分,是經濟發展重要節點;中西部大多數縣城屬于鄉村的一部分,是分散的,主要功能是服務鄉村振興和以大中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沿海地區,經濟密集、人口密集,是人口主要流入地。相對來說,中西部以地級市為單位的市域經濟因為達到相對合理的人口規模和具有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而形成了二三產業聚集,具有一定的產業發展能力,吸納本地部分鄉村人口就業與定居。
3.縣城主要吸納本地農民,城鎮化質量不高。縣城經濟不發達,吸納的外來流動人口很少,通過產業發展吸納的本地鄉村人口也非常有限,進縣購房的農民并不是完全融入城鎮的人口。也就是說,進入縣城的中西部農村的“農民”并不因為進入縣城購房、就業、陪讀就成了“城里人”。調查發現,以縣城為載體的城鎮化,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服務驅動的城鎮化,農民為了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務資源,主動或被動在縣城買房,多數農民仍然要到沿海或大中城市務工,老年農民仍然要在農村務農和養老。因此,大部分進入縣城購房的農民的城鎮化質量其實并不高,仍然是“半城鎮化”。
“劣質城鎮化”的諸種表現
1.農民“被上樓”。農民“被上樓”造成惡劣影響的典型案例,是2020年一些地方推動的大規模“合村并居”。我們在中西部調查,發現不少地區規劃了大型農村新型社區。其主要政策工具是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大規模合村并居被作為騰退土地指標、換取城鎮發展空間的操作方式。實踐證明,大規模合村并居的效果和預期大相徑庭,違背了農民建房和村莊建設規律,造成了“劣質城鎮化”。如果違背農民意愿、不顧實際條件,通過行政強制手段把村莊拆掉,把農民集中到新社區、過上“城鎮化”的生活,地方政府很快就會面臨農民“上樓”之后產生的生計困境。
2.限制農民自建房。我們在蘇北某市調研了解到,地方政府已經十幾年不審批農村宅基地,盡管沒有非常明確的政策依據。農民收入不斷提高,反而農村住房日益破敗,農民不得不進城購房,導致該地城鎮商品房價格非常高;或購買村集體引入的房地產商統一建設的小高層住房(一般是農村集體土地上的“小產權房”)。這不僅增加了農民家庭的建房支出,而且對仍然要在村從事生產、在村莊生活的弱勢農民造成嚴重不便。
3.“貧困戶”向城鎮平移。在很多地區的政策執行過程中,政府認為把貧困戶搬入城鎮就能解決貧困問題,主要表現為在安置點的選擇上存在明顯城市偏好。我們近幾年對西南地區11個城鎮集中安置型“易扶”社區的調研發現,城鎮集中安置型的易地搬遷貧困戶雖然借助國家力量實現了居住空間、戶籍和部分公共服務的“跨越式城鎮化”,但是這些貧困戶短期內無法實現生計能力的快速提高,以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質等方面的“能力城鎮化”“素質城鎮化”,仍處于“半城鎮化”狀態。
4.教育“房地產”的膨脹。所謂“教育新城”開發模式,是為了吸引農民購房,地方政府把教育這一核心公共服務作為“城鎮房地產開發”的手段,通過把優質教育資源向新城區集中,擴大城鄉教育差距,刺激形成農民新的教育預期,誘導農民進城買房以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目前中部地區縣城房地產價格高漲。一套普通的縣城商品房,約100平方米,一般需要50萬元以上,加上利息就等于六七十萬元,相當于一個農民家庭十多年的純收入。大量的農民工收入并不高,進城購房的結果是農民家庭經濟更為緊張,農民被卷入了高消費、高負債、高風險的“透支型社會”,沖擊了相對弱勢農民的家庭生計穩定性,造成了縣域高風險的城鎮化。
(摘自《田野來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