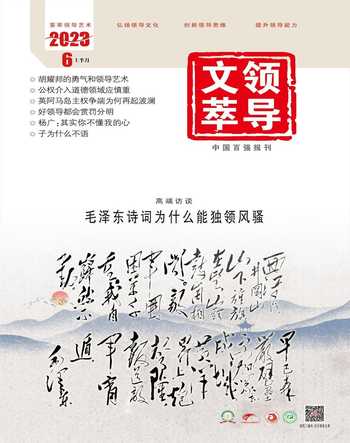蘇式坦克和西方坦克的外形選擇
譚保羅

由于爆發在東歐的戰爭,很多朋友開始關注起坦克這種武器。坦克在一戰時開始投入實戰,那時候,只有坦克可以讓陸軍步兵克服對重機槍的恐懼。在二戰中,坦克更成了陸地決勝負的關鍵。
二戰之后,全球坦克的發展分為兩個流派,蘇式坦克和西方坦克。兩個流派差異挺大的,對一般人來說,我們最容易看到的是外形差異。
首先,蘇式坦克更小,很多主戰坦克的重量都在50噸以下,西方坦克普遍更大,主戰坦克基本上都在50噸以上。從外形上看,蘇式坦克整體上更矮,炮塔更小,趨近于圓形,線條極度圓潤。西方坦克無論是美國的,還是德國的坦克,整體更加高大,炮塔棱角分明,而且炮塔的尾部很大,上翹并且突出。
從氣質上看,蘇式坦克顯得收斂和圓滑,好像是貼著地面,匍匐前進的鋼鐵烏龜,它們似乎很怕被擊中。而西方坦克顯得張揚和豪爽,開起來搖搖晃晃,有很濃厚的重型皮卡氣質,它們看起來并不害怕被別人發現和攻擊。
造成氣質不同的根源,當然是設計思路的不同。蘇式坦克崇尚“快”和“多”,在單位時間內,我發射的炮彈更多,那么我即使前幾發沒有打中,那么經過快速校準,也有機會干掉你。因此,蘇式主戰坦克采用了自動裝彈系統,炮彈被儲存在炮塔下方,環繞著炮塔,以便于提升自動裝彈系統的運行效率。
這樣的設計也帶來了副作用,炮彈存儲的位置并不理想,等于坦克乘員的肩膀上扛著一圈炮彈。而且,炮塔下部是坦克被擊中的概率最高的幾個位置之一。因此,一旦被穿甲彈擊中,那么很容易發生集體爆炸(術語叫“殉爆”),不但炮塔會被炸飛,而且坦克乘員生還的可能性也會很低。
西方的很多主戰坦克,則采取了另外一個思路。西方人把炮塔做得更大,把炮彈存儲在炮塔尾部,因此炮塔看上去“屁股更大更翹”,這樣做的好處是,炮塔尾部被擊中的概率很低,即使被擊中,那么距離乘員也有點距離,乘員還有一定的概率生存下來。但壞處是,需要有一位粗臂大漢站在炮塔內部,人工從彈倉中取彈填裝,不如自動裝彈效率高。
于是,蘇式坦克不用人工填裝,那么炮塔就可以做得更矮更小,縮小體積也就降低了被擊中的可能性。但西方坦克不行,炮塔做得太矮太小,填裝手就沒法站立,體積大了,那么也必然增加了被擊中的概率。
以上這兩種不同的設計思路,是導致蘇式坦克和西方坦克外形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實,所謂設計思路歸根結底也必然基于一種武器研發領域的經濟理性,它植根于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
在冷戰時代,蘇聯是一個各方面實力都很強大的存在。但客觀地說,蘇聯的科技實力與歐美相比,還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進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電子元器件和信息技術開始大規模運用于軍事工業之后,蘇聯和歐美的常規武器差距更在不斷拉大。
對歐美坦克來說,它們擁有更好的紅外技術和電控技術,打得更準;還有優異的發動機,即使更重(更重一般意味著對乘員的保護更好),也能跑得很快;同時,還擁有更優異的立體作戰能力,比如空中力量可以對坦克集群進行更好的保護。因此,即使坦克有很濃厚的“皮卡風”,依然不影響其作戰能力。對比來說,蘇聯的一大優勢則是有著無與倫比的國家動員能力,比如,乘員可以快速地補充等等。因此,蘇聯可以保持規模驚人的裝甲部隊,以個體作戰單位的“快”和整體數量的“多”來取勝,鋼鐵洪流,讓西方戰栗了幾十年。
一件武器長什么樣,并不是偶然的,它背后是一整套的系統和基于這套系統的權衡與取舍。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