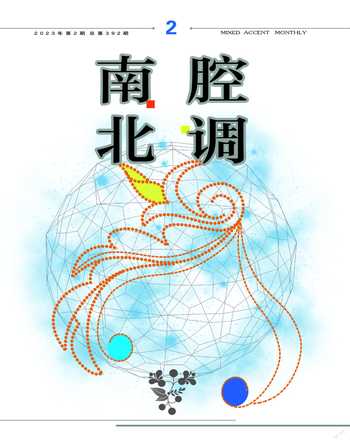張愛玲與陳染的互文性性別形象構建
伍越
摘要:張愛玲和陳染是現當代文學史中極為重要的兩位作家,雖然她們相隔半個多世紀,所代表的文學風格和寫作潮流也迥然不同,但在女性主義視角下,她們作品中的性別形象構建,卻具有頗為深刻的歷史互文性。二者作品里無論是異性的隱匿還是同性的傾軋,最終都造成了女性深陷輪回的命運困境,展現出不同年代女性共通的生存面貌,也為女性寫作和女性主義研究,提供了可以縱向交錯的范例。
關鍵詞:張愛玲;陳染;性別形象;女性主義
陳染與張愛玲是距離半個世紀的作家,雖然在時空上相隔久遠,但五四運動的啟蒙聲浪與20世紀80年代的回響,帶來兩個時代的作家的碰撞。從劉心武與魯迅的“救救孩子”遙相呼應開始,越來越多的作家找到了本土文學的血脈:汪曾祺與廢名、賈平凹與孫犁、莫言與趙樹理……斷裂十余年的文學史,也在重寫者的奮筆疾書下慢慢地撫平溝壑,淵源貫通,而人道主義、人文精神、思想解放等思潮也如“重放的鮮花”招展在文壇的角落。但對于女性作家而言,這樣的脈絡似乎并不明晰。暫且不談男性主導話語下的歷史建構,僅就女權主義這條線索而言,其串聯下的女性文學嬗變,也顯得磕磕絆絆。謝冰瑩、廬隱、馮沅君、冰心作為現代第一批女作家,她們筆下濃厚的反封建色彩,使之成為當時對抗父權的“逆子”,卻不期然地隱去了作為女性的主體身份;丁玲、蕭紅、楊沫等則受縛于社會矛盾和政治號召,對于革命的熱情壓抑住了內心深處的性別敏感,同宏大敘事時而和諧融洽,時而格格不入;而張愛玲與鴛蝴派、新感覺派中的女作家,則直接被排斥在正統文學史之外,只能徘徊于勾欄瓦舍之中。時至今日,研究者也在不斷地探尋當代女作家背后的歷史源流,以期待從多元角度撰寫大文學史框架,并為完善作家創作風格和深度文本闡釋提供創新思路。那么對于張愛玲,常規思維里與之相匹配的最佳人選,無疑是有著相似城市文化標簽的王安憶,但在女性主義視角下,陳染作品中的性別形象更像是對張愛玲進行了一次文學預言的印證。張愛玲與陳染一隱一顯,一張一合,將女性視角下的性別沖突展現得淋漓盡致。
一、異性的隱匿
異性之間的矛盾是一場亙古難解的戰爭,男性用原始生產中的生理優勢,將女性從繁衍生殖的神壇上拉下,逐漸將其變成奴隸、私產、工具,耗盡血淚后又視之為禍亂心智的妖物、厄運纏身的魑魅、毫無價值的牲畜。男權與父權融合而搭建的社會制度,仿佛鎮壓白素貞的雷峰塔,高貴又合理地矗立數千年。當人道主義的旗幟緩緩升起在世界的各個地方,民族獨立、種族平等星火燎原,男女平等的口號看似是前者順理成章的結果,實則在實踐中更像是無奈的“城下之盟”,用以抵抗更強大的力量。女性在自我覺悟和外來理論的雙重刺激下,漸漸理解其被后天建構的社會性別,也開始對“異性同盟”秉持審慎的態度。
與女性存在著最普遍和最激烈矛盾的異性,毫無疑問是其父親。這位集異性和權威于一體的人,既是女性的創造者,也是女性痛苦的來源。張愛玲的父親是紈绔子弟,他符合人們對家道中落的始作俑者的所有想象——放縱、暴虐、吸毒、嫖妓,但他在物質層面上也給了張愛玲較為優渥的童年生活。在精神與物質的拉扯下,張愛玲筆下的父親形象,永遠是殘缺不全、模糊不清的。在《第一爐香》里,葛薇龍的父親只在對話中隱約出現,像一位嚴肅持重的老學究,又像一位尖酸刻薄的老古董;在《茉莉香片》里,聶傳慶父親糜爛的生活和惡毒的思想一再加重其作為“惡父”的陰暗一面,而言子夜的文質彬彬又更像是敘述者對父親溫柔一面的想象,但兩者被戲劇性的關系完全分割,無法合成為一個整體的父親形象,或者說,單獨的任何一角都顯得虛浮;在《傾城之戀》中,白流蘇的父親并未出現在文本之中,其幾位兄長的形象也過于單薄,難以擔當“長兄為父”的重任。在張愛玲筆下,上一輩更多地展現為母親形象,而父親則被強制拆解或隱匿。這種父親形象的隱匿是作者刻意塑造人物而采用的文學手法,或是其過往記憶于筆尖不期然地流露,又或許兼而有之。但隨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喧囂一時,研究者對此更傾向于以“戀父”或者“弒父”的理論加以解釋,即更偏重于將其理解為張愛玲童年生活中父母角色不同程度地缺位而產生的病態心理。但“過分執著的戀父情結會遮掩女性的真實表達”[1],張愛玲以女性視角所體察的生活被兒女身份下的家庭倫理所掩蓋。許子東對于張愛玲作品中的人物視角有過極為準確地發現,他提出張愛玲習慣將敘述者的視角來回切換以實現場景變化的效果[2]。而她在作品中將父親形象隱藏在文本之后,既是全然用外部視角(多為女性視角)來進行一場“審父”的行動,也是避免陷入自己不熟悉領域的寫作策略。無論是對戀父還是對戀母的分析,都不免會延伸到文本外的作者心理考察而顯得脫離主題。因此,以敘述方式來看待張愛玲作品中頻頻消失的父親形象,不僅可以規避洪治綱教授所提醒的文本闡釋的界限問題[3],也與當代女性作家的創作很好地進行了連接——陳染即屬其中之一。
陳染作品中父親形象的隱匿更加明目張膽,《私人生活》《與往事干杯》中的女主人公父母離異而跟隨母親生活;在《無處告別》中,父親直接以死亡的方式告別文本敘述;在《時間不逝,圓圈不圓》中,維伊完全獨立在家庭之外,而林子梵的父母也不過是故事必要的背景并未靠近故事核心。這場父親形象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很明顯是作者的深謀遠慮,一方面為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同身邊男性產生復雜情感關系提供空間和緣由,另一方面也為女性的精神回溯之旅提供記憶碎片,使女性的自我尋找與構建過程變得曲折但快捷。葛薇龍和肖濛、白流蘇和黛二、長安和倪拗拗,她們在冥冥之中,在迥然相異的語言風格下將彼此的命運串聯,其所遭遇的生活起伏,其所陷溺的情感挫折,其所作出的未來選擇,都在背后指向了隱藏起來的那個“從未缺席”的父親。而在敘事效果層面,這必然為女性視角敞開了空間,作品的意義也在讀者心里烙上了更深更痛的社會文化印記。就此看來,陳染與張愛玲的“私人生活”,或許使之無法建立起完全的父親形象,但將其作為文學創作或小說虛構特點的唯一解釋,未免過于先驗主義而失之偏頗。
相比較父親形象,張愛玲與陳染作品中女性的愛人或情人角色,則是一種隱形的即精神意義上的隱匿。當文學現實中的父親驟然消失,母親無法幫助女兒完成精神領域的完全成型,其目光自然轉向身邊的男性。但在最后,這次精神的成長,卻只能伴隨著全部男性的隱退,而以不知何去何從告終。張愛玲將這個過程寫得華麗而婉轉,凄涼且優美。無論是葛薇龍和喬琪喬之間的愛情的難言其妙又感慨莫名,還是白流蘇和范柳原之間的愛情的海誓山盟與生死與共,都使人不禁驚嘆于戰亂年間滬港兩地青年男女千瘡百孔的情感經歷。而從女性的視角出發,讀者的自我感動和故事本身的蒼涼華美,并不代表這場精神成長的完成。喬琪喬也好,范柳原也罷,他們只是在物質與肉體上帶領女性走出了困頓,而且是在某種不得已而為之或機緣巧合之下實現的。也正因如此,在精神方面,女性在現實中的空虛和對未來的迷茫,仍無法得到填充,也看不到本應由其寄希望的男性所引領的方向。當葛薇龍選擇委身于喬琪喬并同他一起開車駛入代表著理想中美好新生活的“熱鬧新春市場”時,喬琪喬嘴上那“開了又立刻謝掉的花”,在葛薇龍“她們是不得已的,我是自愿的”[4]這無奈之語的映襯下,仿佛瞬間墜入寒冷與黑暗,立刻凋謝下去。當白流蘇成為范柳原名正言順的妻子之后,“然而流蘇還是有點兒悵惘”[5],她面對“柳原現在再也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6],只能用自我安慰來平復。然而,這種寬慰又不斷加劇思想的迷惘蔓延開來,使其不斷思索城市、歷史與人之間的復雜糾葛,最后以“笑吟吟地站起身來,將蚊煙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7]來掩蓋這場無疾而終的精神成長。張愛玲把“已經燃燒殆盡”的葛薇龍和“傳奇里大抵如此”的白流蘇擺在讀者面前,而理應作為她們精神成長的偕同者、協助者、引領者的男性,卻不知身在何方。當人們驚羨于張愛玲作品中纏纏綿綿的愛情故事時,那場困難重重的精神成長之旅,又變回了女性一個人的戰爭。
陳染作品中男性戀人的隱匿表現為一種被動的方式,他們是在女性的自主放棄之后,慢慢地消失在文本中。在《與往事干杯》里,肖濛出于倫理道德的愧疚,先后同隔壁男醫生和其兒子老巴結束事實上的戀愛關系;在《無處告別》里,黛二與瓊斯也是在女方匆忙從美國返回中國后以無聲作為告別;在《私人生活》中,倪拗拗同T老師和之后男友伊楠的感情,都是她自己主動選擇開始與結束。陳染比張愛玲多了更為強烈的女性自省,此時文本中的女性已不再作為柔弱的、可憐的、需要男性保護的群體,而是躋身成為男性成長的幫助者、引領者與不可或缺的支撐者。這與張愛玲乃至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文學作品都是不同的,男女兩性情感地位的置換,多是從其大膽的身體寫作處體現的:在《與往事干杯》中,隔壁男醫生對肖濛身體的開拓,既有女性性啟蒙的意味,更有莊嚴隆重的男性成長內涵。男醫生正是在同肖濛的交合中實現了身體與靈魂的雙重升華,在此過程中,女性不再是欲望發泄的容器而是圣女降福的恩賜。同樣,老巴在肖濛赤裸的胸懷中,喃喃自語著“故鄉、故鄉”,這是他生的源頭和死的棲所,是他唯一心心念念并愿意為之付出終生的土地。等到肖濛回國,老巴的生命也在作者的預示下終結。陳染的身體寫作,在生理意義上對女性積壓的欲望進行了細膩優美地表達,而且也在本體上逆轉了兩性的地位。沒有女性參與的男性世界,仿佛總是迷蒙昏暗的,女性以天使的姿態帶來了希望的光亮,也同樣在離去時將男性自我臆想中的美好愿景旦夕摧毀。但“倪、肖和尹楠、老巴‘正常的異性戀,并不意味著追求叛逆、拒絕‘治愈的女主人公們從此就被‘治愈了”[8],男性在失去精神啟蒙的能力并逐漸隱退之后,她們反而陷入更加深邃的絕望,并將自己幽閉起來,拒絕他人和自我的救贖,深陷進退兩難的維谷。相比于張愛玲創作策略型的男性隱匿,陳染更講求精神上的私人感受。但二者都把女性的焦慮、迷茫、不安、困惑,不約而同地朝向文本中變成空洞能指的男性,也在語言背后默默地透露出對激進女權主義的深刻疑問:當男性變成不堪大用的傀儡并逐漸消失在女性世界之中,這種“盛景”真如女性所愿嗎?
二、同性的傾軋
同性之間的關系具有極端的兩面性,一方既可以視同性對方為傾心信賴的對象,也可以將其瞬間逆轉成頗為對立的勁敵。因此,戴錦華將同性之間的關系描述為“最危險的關系”[9],這不僅是針對同性密切交往而容易產生同性戀傾向所言的,其深層也對同性之間各種紛繁復雜的糾葛進行了定調。在張愛玲和陳染的作品中,同女主人公聯系密切的同性,包括母親和朋友,都以各種方式在對其進行不同程度地傷害,表面深厚的情感在現實的拉扯下變得令人厭惡乃至恐懼。
母女之間并不像父子一樣,在漫長的歷史里,存在著順位繼承或弒君自立的權力更迭沖突。她們都是作為被奴役的、被迫害的、被利用的一方,悲慘地延續命運的無情。但“女兒對于母親來說,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個人;母親對女兒既過分疼愛,又懷有敵意。母親把自己的命運強加給女兒:這既是在驕傲地宣布她具有女性氣質,又是在以此為自己雪恥”[10]。這種本應在異性矛盾和親情加持下堅實穩固的同盟,卻被漸漸異化為父權制度的變體,由母親搭建起女兒痛苦的牢籠,并一代代傳遞下去,使母女在時間流逝中成為彼此的施暴者和受害者。在《金鎖記》中,曹七巧以無情拆散女兒長安未來幸福婚姻的方式,將自己身上的“金鎖”牢牢地銬在她手上;在《第一爐香》中,作為替代葛薇龍母親形象的姑母梁夫人,一開始就將葛薇龍看作“接班人”并一步步誘使其變成自己的翻版;在《小團圓》中,九莉和母親蕊秋從衣食住行到情感生活,無處不在地形成競爭關系,作者甚至在第三人稱視角下都不采用“母親”或“媽媽”的稱謂而是直呼其名,以此來表明自己將這種隱藏在直系血緣關系背后的你來我往的對抗放置在明面的寫作態度。這些獨居守寡的家庭主母,形成了同父親極為相似的權威模型,昭示著女性無法逃脫的被傾軋的命運,也暗示了一場走向自我對立面的痛苦道路。比起理解男性,張愛玲更理解女性,尤其是受自身身世影響的母女關系。溫馨的親子時光,不僅在歲月代溝、思想觀念、立場地位等外部因素的撕扯下一片狼藉,更在來源于女性本能無差別的敏感下,互相碰撞而致關系岌岌可危。作為純粹女性的身份壓倒了作為母親的身份,有的則直接惡化為破壞美好的強力,并由此帶來自我的寬慰和平衡。從親密到競爭到嫉妒再到摧毀,張愛玲沿著女性的身體解剖出其殘忍的心靈動態,而她作品的開放式結局,也不曾提供某種解決的方式,只留下引人遐想的空間以待后來者探尋。
父權至高無上的威嚴,伴隨著時代的滄海桑田結束了對女性強有力的統治,與此同時,被消磨掉的還有假借其名的母親的威懾。西方女權主義者西蒙·波伏娃的觀點——“養兒育女便足以使女子的一生光明燦爛的思想完全是無稽之談”[11]。也使人重新思考圣母形象的合理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成為象征歷史的文字符號,無法在新中國的法律法規和社會良俗面前發揮難以抗拒的作用。但母女之間的糾葛,卻延續著并轉向幽暗的地下,在精神領域爆發著依舊鮮血淋漓的戰爭。陳染與張愛玲筆下的母親,形式上都具有失夫婦人的特征,但陳染走出了張愛玲的殘忍而把“病態的愛”中的“愛”字放大,“病態”更多地呈現在嫉妒與呵護的拉扯中。在《與往事干杯》里,母親放棄之前同女兒在尼姑庵艱苦環境下的相依為命,突然間不顧女兒高考的焦慮、獨處的孤獨和離父的傷痛,義無反顧地尋找自己同蘇聯外交官的幸福;在《無處告別》中,黛二的母親在長久的寡居生活里變得極度敏感,女兒失業后的自閉讓其擔憂,但她又將無人陪伴和青春已逝的煩悶夾雜其中化作對女兒無時無刻地不滿。毋庸置疑,即使不再有物質上的壓迫,這種情緒或精神上的不正常,也給女兒帶來了不輸于肉體上的折磨。陳染筆下的女主人公,都一度走向死亡與精神崩潰的邊緣,追其原因,母親的傾軋遠大于父親的隱匿。“父親的退場代表著成年儀式的開始”[12],而母女之間的相愛相殺,則表明這場儀式長久的未完成狀態。母親仁愛寬厚的原始形象,在作為封建父權的幫兇時,被五四時期作家進行了第一次大膽地瓦解,而張愛玲則為其添上了社會經濟文化驅動下宿命輪回的慘痛標簽。到了陳染這里,前人著重批判的外部因素開始退居其次,精神方面的問題變換著各種形狀輪轉開來。陳染無意但也深刻觸及女權主義內部的分裂性問題:母親對于自我幸福的追求和情感欲望的釋放,同樣屬于女性權力范疇,而與此同時所必須造成的對女兒心靈的傷害,又是否可以被視為對女性權益的侵害?此間矛盾到底是由教育問題導致的還是由女性問題導致的?二者又是否存在明晰的界限?但張愛玲與陳染都讓作品中的女性在同母親無聲地對抗、沉默地忍受下精疲力盡,青春的熱情在無以依靠的空虛和苦痛中,走向一片黑暗的漫漫前路。
較為有趣的是,張愛玲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同性友誼并不多見,只有零零散散的細節可以一窺。在《小團圓》里,九莉與比比、項八小姐、劍妮等同學之間或有不淺的朋友情誼。在《第一爐香》中,葛薇龍和幾位女仆的關系也勉強可以算作好友。九莉在日軍轟炸香港時,隨朋友來到臨時避難的教堂,她一面擔憂戰爭的前景,一面忍受朋友的排擠和鄙夷。葛薇龍則直接目睹自己未婚夫喬琪喬和女仆的偷情,本就稀薄的同屋感情也驟然煙逝。張愛玲因孤傲冷峻的性格在實際生活中鮮有好友,因而作品中并不太多著墨于女性友誼的描寫,其一生的后半段于美國的孤苦伶仃也可算作現實例證。但在不多的文本中,張愛玲仍然夾雜著女性之間的算計和侵害,并不打算放過已身陷重圍的她們,而是以無情地鞭撻和辛辣地嘲諷,讓人們正視女性陰暗病態的心理和不幸悲涼的境地。
陳染承接了五四時期冰心、謝冰瑩、廬隱等作家對女性情誼的細致描寫,但又并不將之視作反抗男權的堅固同盟或是給予慰藉的避風港灣,她對女性情誼比張愛玲多了一份溫情,并對此進行了更加深入地剖析。在《私人生活》中,倪拗拗與喬寡婦的情誼,不僅跨越了年齡的阻隔,也超過了朋友的界限,在一種不過分極端的情況下,徘徊在同性戀的邊緣,這種情誼在寬慰倪拗拗心靈的同時,也使其加重了對男性愛與恨的情感分裂。在《無處告別》中,黛二與謬一、麥三的姐妹情感總閃爍著罅隙:麥三的丈夫對黛二時時表露愛慕之意,而麥三對此又毫無防備,依舊表現得大大咧咧,這給黛二的單身生活帶來巨大的情感困擾。謬一身嫁豪門之后,躋身黛二難以企及的上層社會,逐漸拉開倆人之間的階級距離,撕扯成一道無形的心靈鴻溝。對于生活,黛二的辛苦經營與謬一的如履薄冰,構成了對倆人友誼的極大反諷。陳染把女性之間的情誼置于放大鏡下,極力描寫“女性尊嚴的細膩幽微”[13]。隨著時間的推移,朋友不再是女性追求解放的伙伴,友情也不再是女性對自我處境的確認。女性成為拉康鏡像理論中的那面具有雙重審視功能的鏡子[14],映照出女性內心求而不得的欲望,又在自我道德和美好理想的要求下,反復自省和批判,隨之而生出苦痛的感受。朋友之間的傷害在心理層面或許是一種必然,但有可以挽回的辦法。而陳染放棄了挽救的措施,并將這種傷害融入其他領域中,對女性進行持續地傾軋。可憐的女性弱者同盟,不需要外力的破壞就已經分崩離析,孤立無援的女性眺望遠方,等待戈多的到來。
三、陷入循環的圈套
在異性的隱匿和同性的傾軋之下,“逃離”成為女性經久不息又痛徹心扉的命運核心詞語。自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把娜拉的出走精神帶給中國以來,一場慘烈無比的抗爭,也從歷史書籍的角落浮現出地表。對于女性而言,這次出走或者逃離莫過于一次背叛,對傳統、禮教、家庭、自我的背叛,因此也必然招致各方勢力的強硬彈壓。即使新文化運動的風浪推動,為其容留下狹隘的生存空間,但女性本身在這次逃離的過程中卻不斷地深陷迷宮,最終又無奈地返回原點。
張愛玲作品中那些企圖以犧牲身體沖破束縛以躋身上流社會的女性們——《金鎖記》中的曹七巧、《怨女》中的銀娣,其結果都是墮入另一個水深火熱的深淵;那些持有單純夢想,期待愛情會沖散日下苦難并攜來未來光明的女性們——《第一爐香》里的葛薇龍、《傾城之戀》里的白流蘇、《紅玫瑰與白玫瑰》里的王嬌蕊,卻也在現實的擠壓下艱辛度日。讀者和批評家固然可以指責這是由女性自身的貪欲和軟弱而造成的自作自受的結果,但當時社會能夠為她們提供的生存技巧、生存資源和生存空間微小,僅僅思想上的沖擊,難以助推女性逃離荊棘叢生的生活環境,甚至無論女性作何選擇,總有許多看不見的手,將其拉入循環的圈套。張愛玲固然明白掙脫禮教藩籬的女性可敬可嘆,但那些在她筆下生生死死的女性們,“令我們刮目或側目相看,不是因為她們的激進,而是因為她們的保守”[15]。
“陳染的作品一開始便呈現了某種直視自我,背對歷史、社會、人群的姿態”[16],這讓她筆下的女性穿透現實表面和歷史陰霾,體驗同上述張愛玲作品中的女性一樣的輪回痛苦:沉寂—逃離—歸來—沉寂。在《與往事干杯》中,肖濛為擺脫童年記憶中的尼姑庵施加于自己的情感魔咒,只身前往澳大利亞與老巴相會,卻在命運的捉弄和無法丟卸的道德壓力下,歸國返鄉并就此封閉,徹底淪為創傷記憶的俘虜;在《無處告別》中,黛二抱著體驗新環境新文化而改善自我現狀的想法遠赴美國,與瓊斯的激情和因遠離母親、擺脫厭煩的工作而帶來的快活,卻使其感到生命無法承受之輕,她僅逾兩月便毅然回國,繼續在人際社會和畸形親情中來回奔波;在《時間不逝,圓圈不圓》中,維伊告知林子梵自己所編織的身份謊言,并對其芳心自許,她期待用真誠來換取林子梵接受自己,以告別看似放蕩的虛假自我,但得到的卻是林子梵的荒唐地沉默。維伊又回到了之前自我營造的虛假面具下,如夢初醒。“風的后面是風,道路的前方還是道路”,在持續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中,女性只是砍斷了有形的束縛,但依然被無形的命運之神的絲線牽引著,如同無助的寵物循環往復地生活。
張愛玲與陳染具有互文性特點的寫作,是歷史螺旋式上升的范例,也是女性命運輪回的苦證。在敘事風格上,前者的外顯內隱和后者的外隱內顯相輔相成,在相距幾十年的尺標上,共同繪制了不同時代女性共通的生存畫像,也在面對西方女權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上,有意無意地提供了風格各異的文本表述。時至今日,女性對于個體自我價值追求的行動,依然在很多情況下被冠以淫蕩不潔的污名,而女性文學也在各種壓力下漸趨凝滯,脫離文學中心。但陳染對張愛玲的呼應并不是個例,女性文學的進步有著源遠流長的脈絡。在不斷前行的同時,也應當回望過往,尋找同前人的聯系并以之為創新的信心后盾和經驗來源,不斷地助力女性文學的長足發展。
參考文獻:
[1]印芷儀,林春美.孤獨經驗與社會想象——陳染小說《與往事干杯》的主題意義論析[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5(04):95.
[2]許子東.許子東細讀張愛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14.
[3]洪治綱.有效闡釋的邊界——以20世紀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研究為例[J].探索與爭鳴,2020(06):64.
[4]張愛玲.第一爐香[M]//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40.
[5][6][7]張愛玲.傾城之戀[M]//傾城之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154.
[8]楊曉雯.男性:女性心靈史中的行動元——對《私人生活》《與往事干杯》的男性形象分析[J].學術探索,2004(01):122.
[9]戴錦華,孟悅.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M].河南:河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47.
[10]成紅舞.他者間的關系——西蒙·德·波伏瓦對母女關系理解的倫理闡釋[J].婦女研究論叢,2011(02):81.
[11][法]西蒙娜· 德· 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569.
[12]于文秀.戀父情結書寫與女性意識的渺茫走向[J].求是學刊,2017,44(06):107.
[13]姬冰雪.從“房間”出走的“泅渡者”——陳染與文珍小說中的“孤獨者”形象比較[J].名作欣賞,2022(09):55.
[14]苑琨瑤.雙重審視下的女性身份認同與精神困境——鏡像視域下的陳染《私人生活》解讀[J].名作欣賞,2021(24):74.
[15]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M].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47.
[16]戴錦華.陳染:個人和女性的書寫[J].當代作家評論,1996(03):49.
作者單位:燕山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