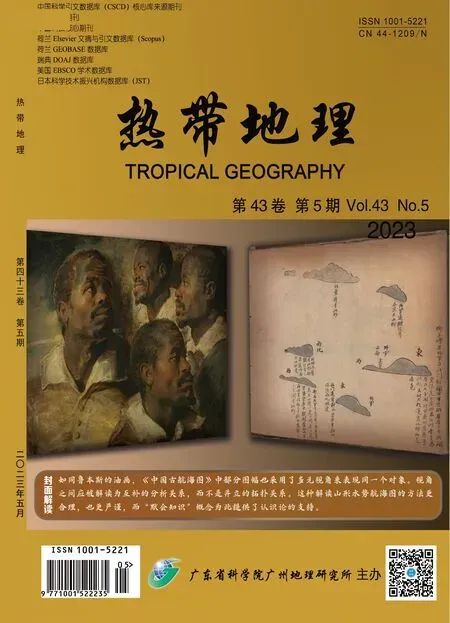旅游發展背景下雙廊古鎮客棧語言景觀分布特征及演變邏輯
曾 莉,鄭詩琳,呂光耀
(1.淮陰師范學院 美術學院,江蘇 淮安 223300;2.廣東財經大學 文化旅游與地理學院,廣州 510320;3.西南林業大學 園林園藝學院,昆明 650224)
語言是文化價值和意義的主要體現,是人類認識世界、理解世界和進行生產生活的重要媒介(霍爾,2003)。20世紀90年代,“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在地理學科研究中興起,地理學家開始聚焦于“語言政治”(the politics of language),將語言視為一種地理現象來解讀各種人文地理過程(Desforges et al., 2001;徐茗 等,2015)。其中,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以一種典型文化景觀的身份被廣泛探討(徐茗 等,2015),并逐漸成為地理學家展開多類型區域研究的樣本以及透視社會文化現象的窗口。近年來,旅游地理學開始關注語言景觀現象,相關研究多聚焦于城鎮空間中的語言景觀,如商業街區、旅游景區等,較少關注鄉村地區的語言景觀(Juncal, 2019; Lu et al., 2020);在研究內容上,以雙語或多語言共存現象的解讀,以及其對游客、旅游地的影響為主,在旅游發展對語言景觀的作用研究上則稍顯薄弱(Nash, 2013; Abdul‐lah, 2021);在研究方法上,多以觀察、訪談和文本分析等傳統研究方法為主(徐茗,2017;張藹恒等,2021;Nie et al., 2021),較少從時空大數據及社會網絡分析等思路展開探究。
語言景觀作為公共空間建構的主要組成部分,是重要的人文地理表征(張藹恒 等,2019),其指在公共區域中展示的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具有一定規模或視覺效應的語言文字及其物質載體,能反映社會意識形態與社會實踐(Landry et al., 1997)。在旅游地,語言景觀常以招牌、標語、廣告牌等刻有書面文字的媒介形式分布于公共空間,幫助游客快速獲取信息并理解地方。客棧作為鄉村旅游地的主要住宿形式(黃和平 等,2021),其名稱是鄉村旅游地語言景觀中的代表性語言景觀。一方面,其蘊含了經營者對地方、旅游關系的深刻理解。客棧名稱相較于旅游地其他形式的語言景觀,因其登記、辦證等流程的復雜性而更具穩定性、長久性,審慎的命名思考背后是旅游業從業人員對商業發展的理解和對地方的細致解讀。另一方面,客棧名稱是游客認知地方的重要窗口。游客受客棧名稱影響而進行住宿消費的行為反映其對地方的認知態度,而該態度又反過來影響客棧名稱的發展方向。客棧名稱的信息性功能交織出游客、經營者與旅游地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近年來,旅游地語言景觀逐漸引起學界關注,相關研究大多聚焦于旅游地可視范圍內所有語言景觀,對其進行標準化統一解讀(巫喜麗 等,2017;魏超 等,2023),但旅游地不同類型的語言景觀營建動機、發展過程及作用效應往往差異較大(Shoval, 2013),將客棧名稱、路牌、標語等納入一個分析框架中難免消弭掉不同人群對旅游地的認知差異。
客棧名稱是經營者解釋地方并通過精心編碼與設計而形成再現的視覺文本,其發展演變過程受游客影響并反映游客對旅游地的情感認知,對其分析有助于深刻理解地方在旅游從業者與游客的建構中所形成的精彩紛呈的社會文化圖景。基于此,本研究選取國內知名的“客棧之鎮”——雙廊為研究案例地,從客棧名稱視角切入,回答客棧名稱此類語言景觀在旅游地發展過程中呈現怎樣的時空演變特征,又是以怎樣的演變邏輯來適應地方向鄉村旅游目的地的轉型發展。以期為旅游地語言景觀規劃設計提供決策參考。
1 文獻綜述
文化景觀演變是地理學、旅游及相關學科的重要研究內容。文化景觀是在自然景觀之上疊加人類活動結果而形成的景觀(湯茂林,2000),通常劃分為物質文化景觀與非物質文化景觀(徐茗 等,2015)。20 世紀以來,隨著城市化、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傳統地域文化景觀結構發生巨變,文化景觀的破碎化與邊緣化現象、演變內容及其驅動因素、原真性保護與商業性發展等(王云才 等,2009;盧松,2014;云翃 等,2021)逐漸成為研究熱點。其中,學者普遍認為旅游發展已成為地方文化景觀演變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Palang et al., 2005),旅游業與文化景觀交織的旅游地文化景觀演變逐漸成為學者探究地方發展的重要切入點,研究主體涵蓋了以農業、工業或建筑遺產景觀、文學旅游地等為代表的物質文化景觀,以及以飲食文化和傳統節慶等為代表的非物質文化景觀(Xie, 2015;劉彬 等,2019;Wang et al., 2021)。語言景觀作為典型的文化景觀,兼具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屬性,其演變研究是當前旅游地文化景觀研究領域的前沿方向(徐茗等,2015;杜克·戈特,2020;張藹恒 等,2021)。
語言景觀概念源自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領域,20世紀80年代初,比利時和加拿大魁北克的語言規劃者是首批認識到語言景觀重要性的人。20 世紀90 年代末,Landry 等(1997)基于對上述地區的觀察,提出語言景觀的初始概念,將其定義為“廣告牌、街道名稱、地名、道路標志、商業標志和政府建筑物上的標志等語言組合在一起,形成的特定領土區域的語言景觀”。之后,該研究對象在語言學研究中興起,其定義隨著研究的深入被拓展至“不斷變化的公共空間中的文本”,因此,游行口號、臨時橫幅、甚至是T恤與紀念品上的文字皆可作為語言景觀的重要組成(Shohamy et al.,2009)。由此可見,語言景觀的生產路徑可概括為自上而下(top-down)與自下而上(bottom-up)2種模式(Karam et al., 2020)。前者是指由政府或相關組織設置的標語文字,如地名、路名以及空間中的政治話語等,此類語言景觀與語言政策、國家意識形態等聯系緊密,其生產過程多由專家、社會精英或政府人員主導。如地方政府以發布規章條例的方式來推進旅游地景觀上的少數民族語言書寫(徐紅罡 等,2015)。自下而上生產的語言景觀是指個人自由創作的、非官方的,以表達自身想法或出于商業等目的的語言標語,如商店招牌和墻繪等,此類語言景觀更能體現語言實際使用情況及人們對其真實態度(單菲菲 等,2016;Nie et al., 2021)。
目前,對語言景觀的研究主要從應用語言學或社會語言學角度展開(張藹恒 等,2021),語言景觀相關研究中,語言傳播與多語現象、語言政策、語言教育和語言商品化是研究的熱點(Muth, 2018;杜克·戈特,2020)。如Leeman等(2009)通過考察華盛頓唐人街商業招牌中的文字標志,發現中文書寫在社會互動與交流中的作用性逐漸降低,逐步成為一種象征性的設計元素,用于構建商業化的城市場所。Huebner(2006)通過對曼谷街區多語言現象的研究,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英語語言景觀在多語言地區的重要影響力。在國內,語言景觀研究在中外語言文字、旅游兩大學科領域內占有相當高的比例。近年來,在地理學中成長的書法景觀(calligraphic landscape),其對文化認同(張捷 等,2014)、旅游地形象構建(尹立杰 等,2011)和地方感知(蔣長春 等,2015)等人地互動關系的探討,為旅游地理學開展語言景觀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語言景觀具有時間與空間的雙重屬性,并與旅游地聯系密切。在時間維度上其作為物質文化景觀經歷著“恒定”或“轉換”,從而逐漸構成旅游地豐富的旅游景觀;在空間維度上,其又基于多變的地形與獨特的景色不斷重構,從而反映旅游地的文化內涵。同時,語言景觀的象征功能又將旅游地地理空間塑造成復雜的社會空間(徐茗 等,2015),引發新空間的生產與消費(張藹恒 等,2021)。在旅游地發展中,獨具特色的語言景觀不僅成為強化旅游地形象、給予游客新鮮感與真實感體驗的主要工具(Kallen, 2009),亦是研究旅游發展對地方影響的重要窗口(Lu et al., 2020)。
迄今為止,西方學者已在全球多民族多語言旅游地開展了較多扎實的語言景觀研究,如西班牙的Bruye 等(2015)、澳大利亞的Nash(2013; 2016)、美 國 的Leeman (2009)和 加 拿 大 的Hoffman(2017)。在他們的研究中,語言景觀本身(如語言的可見性、發展歷程及多語言環境中各種語言的書寫順序等)是探索特定地區社會權力關系、文化融合和發展政策導向等方面的有利工具。國內對旅游地語言景觀的研究起步較晚,且數量較少,一方面關注書法景觀的演變及其對旅游業、游客的作用(張捷 等,2014),另一方面關注旅游發展對少數民族旅游地語言景觀的影響(張藹恒 等,2021)。在研究對象上,相較于對地名標識(趙巧艷 等,2019)、民族語言(徐紅罡 等,2015)等由政府相關單位主導生產的語言景觀的討論,尚未有對住宿業語言景觀這一“自下而上”發展類型的集中探討。在研究方法上,對語言景觀構建過程的分析較依賴于以訪談、觀察為主的傳統文化地理學研究方法(張藹恒 等,2021;Abdullah, 2021; Nie et al.,2021)。就研究地而言,國內研究形成了以東南部城市為中心、以西南民族鄉村地區零散分布的空間格局(Nie et al., 2021),可以說,國內鄉村旅游地語言景觀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其中,單菲菲等(2016)分析了西江千戶苗寨多語關系及其社會地位,指出旅游業改變了鄉村語言景觀結構,并壓縮了苗族語言文化生存空間。也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如Nie(2021)通過對香格里拉獨克宗古鎮語言景觀的統計調查,發現旅游業在促進少數民族語言中發揮積極作用;但在認同方面,附近村落的藏民因其文化信仰(佛教)對語言景觀中藏語的廣泛使用普遍持負面態度。張藹恒(2021)通過對陽朔西街語言景觀的分析,認為全球化進程中,地方語言景觀呈現典型的“聽眾設計(audience de‐sign)”特征,流動性以弱化主客交往的方式推動了鄉村旅游目的地語言景觀的轉變。誠然,語言景觀作為旅游地營銷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需不斷重構以適應地方快速商業化所帶來的影響,并以一種象征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形式參與到地方營建與消費中(Light, 2014;徐紅罡 等,2015)。但是,地方發展是系統性的,并非所有旅游地的語言景觀生產皆以商業盈利為主要目的,主流研究中的國家意識形態、語言政策、游客動機與商業發展也不全是影響語言景觀演變的主要因素。因此,鄉村旅游地語言景觀相關研究中,需加大對語言景觀生產者主觀能動性的探討。此外,中國地域遼闊,各地民族文化異彩紛呈,社會結構作為語言景觀構建動力之一(張藹恒 等,2021),也應被納入旅游地語言景觀演變分析網絡中。
2 研究區概況與方法
2.1 研究區域概況
近年來,中國西南地區客棧層出不窮,大量以文藝情懷為噱頭的客棧民宿在擁有文化底蘊與文藝氣息的歷史名村名鎮中迅速“生根”(中商情報網,2017),成為旅游地的一大特色。雙廊古鎮景區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是云南省省級旅游名鎮與國家4A 級旅游景區,其區域范圍由雙廊村、康海村、天生營、大建旁村及島依旁5個自然村與南詔風情島構成(圖1)。隨著雙廊旅游業的發展,其“沿海”經濟收入逐漸轉向旅游業,大量白族民居被改建為客棧(羅秋菊 等,2018),雙廊從傳統的以漁業為主、農業為輔的小漁村發展為成熟的鄉村旅游目的地(婁陽,2018;孫九霞 等,2020)。如今雙廊客棧呈現顯著的地理空間傾向,其名稱也演變出多種類型,在塑造大理世外桃源、風花雪月般(李東紅,2004)的旅游地意象的同時,逐漸成為雙廊文化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往鄉村旅游地語言景觀研究,多選取政府或相關單位干預較多的案例地展開探討,鮮少討論雙廊這種“自下而上”發展的普通鄉村旅游地的語言景觀;此外,隨著住宿行業在中國充滿“異域”風情的西南地區迅速蔓延,游客也于旅游地開始向“駐客”或“生活方式型旅游企業”等身份轉變,開客棧成為其重要生計方式,但收入的增長并非其首要關注點(楊慧 等,2012;錢俊希 等,2015),雙廊古鎮即是此類旅游業從事人員的典型聚集地,對雙廊古鎮客棧語言景觀的解讀或將不同于其他研究——將旅游地語言景觀演變僅僅歸結為以市場為導向(徐紅罡 等,2015;Lu et al., 2020)。因此,選取雙廊古鎮景區作為案例地具有一定代表性與典型性。
2.2 語料收集與研究方法
于2016—2021年前往雙廊古鎮進行5次實地調研,于2017年獲取到古鎮景區管理機構于同年統計的雙廊鎮服務業(住宿)匯總數據,其中包括客棧名稱、所屬村域和開業時間等信息。在剔除掉雙廊古鎮景區范圍外的客棧后,共得到412家客棧的基礎數據。然后,在地方精英①為村落長者以及大理客棧協會雙廊分會會員。的帶領下,分片區對412 家客棧逐個展開走訪調查,標記客棧地理空間位置、拍攝客棧名稱。同時,向客棧經營人員詢問客棧命名的原因,并對其中28 家客棧進行二次走訪。針對收集的調研材料,將客棧名稱歸納為包括5 個主范疇與14 個子范疇的客棧名稱分類初表。2019年,以上述方法又對古鎮客棧進行了調查,并請客棧經營人員按其命名想法在表格中選擇相應的范疇,發現有8家客棧對其名稱的解釋與首次調研記錄出入較大,為此對這8家客棧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訪談以確保調研記錄的準確性。此次調研還發現了29家新開設的客棧,并對其數據信息做了及時記錄。另外,按照部分客棧經營人員意見,對客棧名稱分類初表作出改動,將客棧名稱主范疇刪減至4個,子范疇擴充至17 個。2020 年,再次對雙廊古鎮客棧命名原因進行調查,期間補充了7家新開設客棧的相關數據信息,通過與2019年統計的客棧名稱分類表對比未發現有過多出入。2021年,筆者前往雙廊進行最終的補充調研,期間并未發現有新開設的客棧。至此,共計448家客棧的數據信息作為本研究的基礎文本。
本研究綜合應用質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前者包括半結構化訪談法和文本分析法;而量化研究是指基于GIS 空間分析工具(核密度分析)對景區客棧名稱的時空演變展開探究。核密度分析被廣泛應用于點數據的空間集聚研究,通過對點數據的空間可視化操作,能反映研究范圍內不同業態的聚集特征與聚集規模(張程遠 等,2017)。調研期間對客棧經營人員、本地村民、政府工作人員和游客等共計30位旅游地實踐主體進行半結構化訪談(表1),時間在30~60 min,主要圍繞景區發展歷程、旅游影響以及對客棧名稱的命名、發展等方面展開。文本分析法主要是對政府所提供的景區相關規劃文件、政策和景區餐飲業管理文件,以及各大旅游網站游客所提供的相關游記與點評等進行輔助分析。

表1 訪談對象的基本信息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3 研究發現
3.1 景區客棧名稱分類
本文得出的包括4個主范疇、17個子范疇的雙廊古鎮景區客棧名稱數據庫如表2所示。客棧經營者所勾選的范疇能清晰地展現其客棧命名思路。但值得注意的是,客棧命名思路是復雜的,有些客棧命名緣由不單屬于一個范疇,作為吸引游客的重要手段,客棧經營者在申請營業執照前會對命名萬般謹慎,因此會出現一個客棧名稱被分類到多個范疇的情況,如表2 中的360 觀景客棧、水岸陽光客棧和蒼雪海月客棧等。整體上,在主范疇中:景觀元素類別共有8 個子范疇,其涉及的客棧數量最多;而文化參照運用涉及的客棧數量最少,其中,對流行詞匯的引用較典故少。具身認知體驗與表達描述技巧所涉及的客棧數量相差不大,前者在客棧名稱的運用中側重于情感與行為表達,而后者看重描述語的運用。綜上所述,以客棧名稱為研究對象的景區語言景觀呈現種類繁多,各范疇分布不均的總體特征,整體表現出較強的語言活力。

表2 雙廊古鎮景區客棧名稱數據庫Table 2 Shuanglang ancient town inn name database
3.2 景區客棧語言景觀時空演變內容
3.2.1 時間演變 客棧語言景觀依附客棧實體而存在,對其探討離不開對客棧實體的統計歸納(圖2)。2002年,雙廊古鎮景區開設了第1家本地人經營的客棧。隨后,2005—2010年客棧以每年1~3家的數量緩慢增長。自2011年起,景區內的客棧行業開始蓬勃發展,新開設的客棧數量逐年增加。2015年景區新開設客棧數量達到峰值,僅此一年便開設了110家客棧。而自2016年起,景區新開設客棧數量逐年減少,2020年僅新開設7家。景區客棧新增數量以2015 年為節點發生顯著變化,2015 年之前(包括2015 年)共建客棧308 家,占客棧總數的68.75%;2015 年之后僅建140 家,占客棧總數的31.25%。截至2020 年10 月,雙廊仍在營業客棧數量為448家。

圖2 2002—2020年客棧數量變化Fig.2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inns from 2002 to 2020
2002—2020年,隨著景區客棧數量的變化,客棧名稱總體數量呈上漲趨勢,且于2011—2015年增速較快(圖3)。景觀元素類別(C)自2007年起便占據著客棧名稱的主導地位,并于2014 年達到峰值,其中又以強調山水、海景的山水地物形態范疇(C2)與表達自身房屋形態的建筑及工程設施范疇(C5)占比最多,分別為29.90%和25.40%。具身認知體驗范疇(A)的占比居于第二位,除2010 年外,其在每一年皆有不同程度的運用,且以情感與行為范疇(A2)表述為主。表達描述技巧范疇(B)的運用相對較少,其作用多服務于其他范疇,以保證客棧名稱的完整性與可讀性,其中,多為由精品、藝術以及夢幻等概念組成的描述語(B2),在2015 年得到廣泛運用,占比達51.28%。文化參照運用范疇(D)在景區客棧名稱上的運用最少,自2009 年出現后其數值始終遠不及其他3 個主范疇。語言景觀作為一種文化載體,其在地域文化的表達上若表現出較弱的可見性,通常表明其并未呈現出較有族群特色的地方性(張藹恒 等,2019),因此,客棧名稱中的文化參照運用范疇所締造的地方性十分微弱。此外,典故(D1)與流行詞匯(D2)范疇中的字詞運用頻率也相對較低,從側面說明以此類范疇命名的客棧在旅游地具有一定獨特性。

圖3 2002—2020年客棧語言景觀主范疇(a)與對應范疇(b)變化Fig.3 Changes of main category (a) and corresponding category (b) of inn linguistic landscape from 2002 to 2020
語言景觀具有信息功能(徐紅罡 等,2015),每一家客棧名稱都有與眾不同的名字來傳達自身特色。景區內客棧數量從激增到驟減再到趨于平穩的變化過程,折射出景區客棧語言景觀從逐漸豐富到衰減再到趨于穩定的發展歷程。與此同時,客棧名稱近20年的時間變化反映雙廊古鎮景區客棧語言景觀以山水地物環境要素為核心、強調居住空間特色、重視個人體驗的主要特征。
3.2.2 空間演變 基于采集的客棧地理坐標信息,建立景區客棧語言景觀數據庫,并以2016年為節點繪制2002—2015 年(圖4-a)與2016—2020 年景區客棧位置熱點(圖4-b)。整體上,景區客棧在空間分布上呈現差異明顯、塊狀聚集與多中心發展的分布格局。2002—2015年,景區客棧廣泛分布于景區南部且表現出近海特征,形成“一主多副”的空間形態:以具有規模優勢的天生營為主要聚集地,其路域兩側客棧鱗次櫛比,形成核心區;而在核心區南部,島依旁與大建旁村沿洱海區域的客棧也呈現顯著聚集特征。在2016—2020年,景區客棧聚集性趨于平緩,核密度最高的區域主要聚集在安南街、安北街兩側。該時段景區客棧整體相較上一時期向遠海方向集聚,在景區內部也出現多處小規模集聚。另外,存在部分區域客棧稀缺,如良甸古道東側,這與該區域地理位置不佳、交通不便、本土白族居民密度高以及居民商業意識淡薄等可能相關。

圖4 雙廊古鎮景區客棧位置熱點Fig.4 Heat map of Shuanglang ancient town inn location
為進一步分析景區客棧名稱在近20年內的空間分布特征,針對表2 中的17 個客棧語言景觀子范疇,繪制2002—2020年空間熱點(圖5)。整體上,各子范疇呈現較為復雜的空間形態,客棧語言景觀的空間結構較不均衡。其中,建筑及工程設施范疇(C5)呈現顯著集聚特征,其在大建旁村、天生營內集中連片分布,而其余子范疇的空間布局皆較為分散。依據高值聚類分析,可將研究范圍劃分為古戲臺周圍區域、天生營、海街東側區域、島依旁、老漁港和大建旁村的魁星閣區域等6個區域。具體地,人物名稱表達類(A1)在古戲臺周圍與天生營點狀聚集;情感與行為類(A2)在空間分布上較為均勻,僅在魁星閣區域零星分布;生活狀態及愿景類(A3)在島依旁、老漁港與天生營點狀聚集;數字類(B1)在古戲臺周圍高熱點聚集;描述語(B2)與時間表達(B3)2 個子范疇皆在島依旁高度聚集;方位類(B4)在古戲臺周圍點狀聚集;地理區域類(C1)在古戲臺周圍、島依旁和老漁港的聚集程度較高;山水地物形態類(C2)在海街高熱點聚集;自然天象類(C3)在天生營和海街形成點狀聚集;動植物(C4)與事物(C6)兩類范疇主要聚集于老漁港附近;顏色類(C7)在古戲臺周圍點狀聚集;聲音子范疇(C8)在客棧名稱中運用較少,并未形成空間意義上的熱點聚集。典故類(D1)在天生營附近臨海區域點狀聚集;流行詞匯類(D2)則在古戲臺周圍點狀聚集。綜上所述,各子范疇在景區的空間分布上存在較大重疊。對17類子范疇熱點圖進行疊加分析發現,風情街西側的海街、天生營和老漁港3個區域是景區客棧語言景觀各范疇聚集程度最高的空間區域,3 個區域皆呈現臨海特征;而在風情街東側,各子范疇并未出現明顯聚集趨勢。

圖5 2002—2020年雙廊古鎮景區客棧名稱各范疇熱點Fig.5 Heat map of various categories of inn name in Shuanglang ancient town from 2002 to 2020
3.3 景區客棧語言景觀時空演變邏輯
綜上可知,雙廊古鎮景區客棧語言景觀的時空演變過程是循序漸進的。在時間維度上,其經歷了前期以人物名稱表達(A1)為主,到中后期強調外部山水地物形態(C2)與建筑及工程設施(C5)等子范疇的轉變過程;在空間維度上,客棧語言景觀各范疇間既有共性又存在差異,共性上,海街、天生營及老漁港等臨海且旅游業發展較早熟的空間場所是各子范疇的高聚集區域;差異上則表現在各子范疇在各空間的集中程度不同,如山水地物形態類集中于海街,而生活狀態及愿景類則在老漁港周邊高度聚集。如Urry(1995)所言,旅游是基于地方的消費,反過來消費本身又能改變地方。客棧語言景觀作為旅游地的重要消費物(Light, 2014),其演變邏輯的解讀應與復雜的地方發展過程相關聯。
依據圖2所展現的2002—2020年客棧數量變化可以看出,雙廊古鎮景區的客棧數量變化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分別以2010、2015、2017為節點表現出增速、減速、平穩的發展狀態,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雙廊古鎮景區的發展特點。客棧語言景觀隨著客棧數量變化同步生產與再生產,因此,下文以往年客棧數量的階段性變化為劃分依據,將雙廊的旅游發展過程劃分為萌芽期、增速期、減緩期和平穩期4個時期,詳細分析旅游發展背景下客棧語言景觀的演變邏輯(表3)。

表3 不同時期客棧語言景觀時空演變特征Table 3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in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different periods
3.3.1 萌芽期:名人效應下以人物名稱表達為主導 雙廊原是西南地區典型的白族村落,其到1990年仍保有傳統的打漁種田的生活方式,天生營、康海村與雙廊村之間隔有大片水田和農地。1996 年,畫家趙青學成返鄉并于金梭島修建自身居所——“虛設之城”;后因金梭島更名為“南詔風情島”并于1999年成為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定點接待單位,趙青搬至天生營,為自己與好友楊麗萍分別修建了名為青廬、太陽宮和月亮宮的3 個住所。這3 幢建筑融合傳統白族民居所使用的石頭、青磚和瓦頂,結合西方后現代產物,如鋼筋和玻璃等,吸引來眾多背包客與藝術工作者,楊麗萍的名人效應及其頗具風格特色的建筑居所成為雙廊旅游發展的初始動力。隨著背包客增多,雙廊的住宿業開始發展,涌現出船家、雙福以及粉四等以強調自身身份的客棧語言景觀。2008 年,洱海開海節在雙廊成功舉辦,投資者開始關注雙廊的價值潛能,而后出現了海月樓、千里走單騎?楊麗萍藝術酒店以及水時光等具備商業經營意識的客棧。屆時,海、水與月等自然景觀語言在客棧名稱中迸發,但雙廊客棧名稱整體仍以強調人物屬性及表明人物身份為重點,在空間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各自然村村口與村中心區域(圖6-a)。

圖6 不同時期客棧語言景觀的空間分布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different periods
正如雙廊本地白族村民(L1)所說:“零幾年的時候,這也沒什么游客,開的客棧可能都不算客棧,主要是給外來泥瓦匠工人們住,客棧起名也隨意,自家是干什么的就叫什么。太陽宮一(建)起來,游客就變多了,當時有些人(本地人)開客棧還想著能不能沾沾楊老師的名氣”。可見,旅游地發展萌芽期地方交通閉塞,經濟不發達,名人的名字以一種文化產品的身份被展示消費,以達到快速吸引人流的目的,如楊麗萍、粉四等。
3.3.2 增速期:旅游市場濫觴下景觀風光凸顯隨著楊麗萍回歸雙廊生活,畫家沈見華、導演張楊等藝術家也先后入駐雙廊,為雙廊帶來更多關注與資本,開啟了雙廊客棧“井噴式”發展時期。出于經濟收入的需求與轉變,傳統白族民居被村民自發性地推倒重建,一系列鋼筋混玻璃樣式的海景客棧成為景區主要建筑,客棧語言景觀隨之多方位發展。在2011—2015年,天生營新設客棧名稱便已涉及4類主范疇;隨著天生營客棧市場趨于飽和,經營者將目光轉向與天生營相距較近的康海村、大建旁村與雙廊村,客棧選址由天生營向東、南、北3個方向擴散,傳統的街巷脈絡和道路肌理受新建客棧的影響,愈發密集緊湊。原本閑置的水田、土地被占滿,各村落之間的邊界逐漸模糊,山水地物形態與自然天象等子范疇在海街和老漁港等臨海區域逐漸呈點狀聚集。“12 年以后,游客越來越多,好多都是來過四五次的,西南這邊重慶的、成都的、貴州的來得很多。來了不走的也有,就跟村民商量著租地蓋客棧。你像現在(2020年)基本上外地人開的客棧占到了六成以上”(G2,景區管委會人員)。這期間共開設碧水清波、蟲二、云七海景、洱邊風、海視星辰、海月灣、蒼雪海月、水韻半島、雙水廊橋和近水樓臺等總計298家客棧,以海、海景、山、水、島等山水地物形態(C2)為突出特征的客棧名稱,說明景區自然性景觀已成為新時期客棧語言景觀書寫的偏好,如“這個客棧原先叫的名字很文藝,跟雙廊也沒啥關系,住宿的人很少,用當年的話來說住的都是文藝青年;我接手后就換了個名字,村民也都說要取得和蒼山洱海有關系客人才會多”(I6,客棧經營者)。可見,書寫旅游地自然景觀特色的客棧語言景觀已成為雙廊客棧重要的特色宣傳工具,大多數經營者心照不宣地以蒼山洱海為噱頭來實現接待量的上漲。
其次,如圖6-b所示,客棧語言景觀中以度假、緣等概念為代表的情感與行為子范疇(A2)以及以雅、韻等概念為代表的生活狀態及愿景子范疇(A3)也達到運用峰值,且常與地理區域子范疇一同標記,如夢廊客棧,“雙廊生活是很慢的……我覺得夢是很貼合雙廊生活狀態的,溫柔緩慢,多年來都是這個樣子。一個夢一個廊就是我想表達的雙廊形象”(I7,客棧經營者)。此外,有游客表示(T3):“雙廊這樣的客棧這幾年開始變多了,名稱里沒什么景觀元素,寫的嘛都是些體驗類的詞;但是基本上都是一個主題,那就是浪漫的、悠閑的生活,其實這就是我們打工人所向往的”。可見,客棧經營者通過客棧名稱的生產,構筑了游客對雙廊地方性的想象與表征,地方在客棧經營者構建的話語中,從普通傳統白族漁村形象逐漸過渡到游客所追尋的“蒼洱風光第一鎮”的代名詞,滿足了游客對雙廊地方性的想象與解讀。綜上,該時期雙廊古鎮景區客棧語言景觀受市場導向較多。
3.3.3 減緩期:政府主導管控下居住空間形態強化 雙廊旅游業發展除了帶來收益外,也引發了洱海水污染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市場與政策雙重推動下,旅游景區處于被動發展的局面。2016 年,政府在管理上開始積極“補位”,并于2017年初劃定洱海流域水生態保護區核心區范圍,開展大面積的客棧整改和拆除行動,共關閉628 家客棧餐廳(中國新聞網,2020),客棧行業在經濟巔峰期后隨即進入“寒冬”。縱觀此階段新增的104家客棧,大部分語言景觀的生產在村內進行,在風情街東側形成了小規模高值聚類區域,對景區自然景觀山水形態的凸顯有所減弱,更多是對客棧居住空間的描繪,如以居、舍、庭院、花園、院等小體量的建筑詞匯組成客棧名稱,不乏有苑、軒、廬等詩意化的表述。
如Cresswell(2004)所言,特定社會群體所棲居和體驗的地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自下而上建構起來的。在雙廊,隨著本地人紛紛將“家”重建為客棧,以及游客向“駐客”(客棧經營者)的身份轉變,客棧成為上述二者的“新家”,“客棧經營者”成為他們統一的新身份,其在客棧名稱中傾注自身情感、經歷與愿望,并將商業空間書寫為小體量的、充滿人情味的舍、居、庭院或花園等空間。減緩期客棧語言景觀中,建筑及工程設施子范疇(C5)的逐漸增多便是他們建構“吾家依舊”“他鄉即吾鄉”地方性的重要表征。如I12先生是安徽人,2015年,他為了減輕在大城市中朝八晚十的工作壓力來雙廊游玩,期間愛上當地姑娘,與其結為連理后,夫妻二人在2016 年將自家房屋加高改建為有10 間房的客棧。I12 特地請一位當地德高望重家庭圓滿幸福的老先生給客棧賜名“雅林軒”,希望客棧名稱在招財進寶的基礎上,能凝聚住家的福氣,重要的是保佑兩地家人的安康。I12 還表示“和我差不多情況開客棧的不少,也算是在網上聽說慕名而來。大部分都是15年左右旅游市場飽和后多起來的。基本都不在洱海邊,沒啥地理優勢,索性掙錢也不是最主要目的,求的是個安穩生活”。可見,客棧名稱被賦予多種意義,并在一定程度上給予遠游的人心靈慰藉,在此種語言景觀塑造邏輯下,鄉村旅游地也被建構為溫暖的社會空間。總之,隨著雙廊旅游業的發展,大多“商住同用”的客棧經營者會利用客棧名稱重新建構地方,找尋地方意義,客棧名稱的書寫即是其中一個維度。此時,客棧語言景觀已不再以市場需求為中心,開始強調自我意識表達。
3.3.4 平穩期:旅游市場飽和下地方“詩與遠方”的營銷 2018年中旬,雙廊景區旅游服務業漸漸復蘇。但在其旅游經濟遇冷(主要指洱海生態問題)過后,以雙廊景區管委會為代表的政府主導力量加大了對景區的規限,一系列制度政策導致在景區開設客棧困難重重。此外,雙廊住宿業已近飽和,這在近3 年客棧開設數量上便可見一斑。該階段(2018—2020年),景區每一年客棧的開設數量分別為12、17和7家。該時期出現的客棧語言景觀在空間分布上,以古戲臺西側臨海區域為主,同時伴有客運中心和環海東路東側山坡2個副聚值區域,可見,雙廊客棧語言景觀發生了由臨海向村內再向景區邊界擴展的趨勢。其具體名稱以景觀要素類別為主,以具身認知體驗為輔,甄別其具體子范疇,在山水地物形態中,仍以海景、海和山等概念運用居多;在情感與行為類范疇中,運用觀和看等概念與山水地物形態類詞匯搭配使用,保證名稱的可讀性。“原先山下那家客棧被(政府)關了,我們就在山上又建了一家。正好能俯瞰洱海和整個雙廊,所以我們就選了瞰海和山居兩個詞來組成了新客棧的名字……有山有海的,網上咨詢的游客也多了”(I15,客棧經營者)。“大家(經營者)都挺聰明的,知道什么能吸引客人,所以后來叫海啊、水啊、月啊的特別多……現在很多游客都下意識覺得雙廊是體驗蒼洱風光最好的地方,雖說離不開政府的宣傳,但我們覺得也離不開這些名稱的洗腦”(I6,客棧經營者)。客棧經營者出于招攬生意和獲利的目的,積極滿足游客對蒼洱“詩與遠方”的“凝視”訴求,對客棧名稱的把控主要囿于海、海景、山及水等自然性景觀的描述,蒼山洱海已然成為“詩與遠方”的代名詞。至此,雙廊古鎮客棧語言景觀中再無不落窠臼的客棧名稱出現。
4 結論與討論
自傳統白族村落向鄉村旅游目的地發展過程中,雙廊客棧語言景觀演變主要呈現以下特征:
1)生產主體:“駐客”與本地白族村民是客棧語言景觀的生產者,生產過程遵循自下而上的發展模式,但在后期受到政府的間接干預。
2)演變過程:時間維度上,客棧語言景觀與地方旅游發展緊密相關,經歷了逐漸豐富到衰減再到趨于穩定的發展過程。景觀元素類別自2007年出現后便始終占據客棧語言景觀的主導地位;具身認知體驗范疇次之。空間維度上,2002—2015年,客棧名稱以南部天生營為主要聚集地、以島依旁與大建旁村為副聚集地且表現出近海特征,形成了“一主多副”的空間形態;2016—2020年,客棧名稱表現出較不均衡的空間結構類型,多以離散分布為主,近海特征減弱,客棧語言景觀的生產逐漸向風情街東側轉移。總體上,海街、天生營和老漁港此類臨海特征顯著的區域始終是客棧語言景觀熱點聚集區域。
3)演變邏輯:客棧語言景觀萌芽期較為強調人物身份,在空間分布上以各村村口及村中心等交通便利區域居多。隨著客流量的增多,客棧語言景觀開始將蒼山洱海等山水地物形態與自然天象納入書寫范圍,同時,受社會話語建構的影響,為滿足游客對雙廊地方性的想象,情感與行為、生活狀態及愿景等子范疇開始受到重視,語言景觀在洱海邊聚集且呈現豐富多元的特征。在住宿業趨于飽和、環境生態問題顯現后,客棧語言景觀生產量驟減,整體自洱海邊向風情街東側進行空間轉移,其內容開始以客棧經營者的自我意識表達為主,描繪居住空間的建筑及工程設施的名稱居多,客棧語言景觀成為經營者建構地方的一個維度。如今,雙廊客棧語言景觀已成為景區獨特的文化景觀,其整體表現出較強的語言活力,呈現以山水地物環境要素為核心,強調居住空間特征,重視個人情感體驗的主要特征,“詩與遠方”的鄉村旅游地形象在客棧語言景觀中得以再次強化。
旅游地語言景觀受市場導向影響,呈現典型聽眾設計特征(徐紅罡 等,2015;Lu et al., 2020;張藹恒 等,2021)。但雙廊客棧語言景觀不同的是,其有很大一部分存在自我意識表達的特征,在雙廊商業化過程中,客棧經營者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折射出的是對當前社會劇烈現代化的反思,這點在風情街東側的“商住同用”型客棧中尤為明顯。現代性體驗是后改革時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一個重要維度,現代化過程在賦予人更多自由的同時也帶來新的壓抑與束縛(錢俊希 等,2015),雙廊客棧語言景觀作為過去社會實踐創造而成的物質景觀,其演變受到現代性與流動性的綜合影響。一方面,流動性的加強催化著鄉村向旅游地發展,促使居民將“家”改建為客棧,眾多語言景觀范疇應運而生。隨著旅游市場日漸擴大,雙廊旅游地形象逐漸形成,雙廊客棧語言景觀成為客棧經營者建構旅游地形象的重要表征。另一方面,對大城市現代性的逃離致使人們將主流話語中“落后”的西南鄉村想象為“異域”的、富含原真性、浪漫化的地方。由此雙廊迎來了大量“駐客”,由游客身份轉變為旅游移民,其在大城市劇烈現代化的掙扎中,帶著逃離現代性的想法棲居于雙廊,此時獲取利益并非客棧語言景觀生產的首要目的,對地方意義的想象或過往經歷的總結才是其書寫客棧語言景觀的重要基礎,雙廊客棧語言景觀也成為其建構地方意義的重要表征。故此,雙廊客棧語言景觀形成了以“聽眾設計”為特征的風情街西側語言景觀,及以“自我意識表達”為特征的風情街東側語言景觀。
在案例研究層面,雙廊為已有認為旅游地語言景觀演變呈現聽眾設計特征的研究提供了新發現,部分“逆市場化”的語言景觀演變特征背后實際上是現代人對現代性的厭棄,但這種“避世”行為并非僅是消極的,旅游發展減緩期,客棧語言景觀對居住空間的“溫暖書寫”可看作其對美好生活期許的重要實踐。在學術層面,語言景觀為繪制旅游地特色提供了新視角,其作為旅游地文化景觀研究領域的新興話題,未來有著較大的發展空間。其一,強調跨學科研究的可行性與必要性。文化景觀也是風景園林學、城鄉規劃學的重要研究內容,未來可借鑒其研究范式,在民族志和質性方法的基礎上,結合圖像識別處理、結構方程模型和數字景觀(Digital Landscape)等技術方法進行語言景觀的識別、采集與處理,以彌補當前語言景觀研究對物質屬性分析的不足。其二,重視其作為文化景觀的文化屬性,將其納入地方歷史與文化脈絡中進行解讀。未來可參考文化景觀與地方性建構的相關研究,考察語言景觀與地方性構建主體的互動、語言景觀在人們地方感形成過程的作用、語言景觀商品化與地方發展等議題。
語言景觀為解讀旅游地發展建設提供了新對象,亦有助于增進對地理學核心概念,即文化景觀內涵的理解。此外,由于客棧命名的復雜性、歷史資料的難獲取性,本文所用資料難以達到準確無誤。旅游地語言景觀的演變本身會受社會生產過程的復雜影響,其演變背后的動力機制也在不斷變化,政府、游客、地方精英和村民等旅游地多元主體在客棧語言景觀的生產演變過程中是怎樣互動與協商的,他們對旅游地語言景觀的理解和認同呈現怎樣的特征,是本文后續探討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