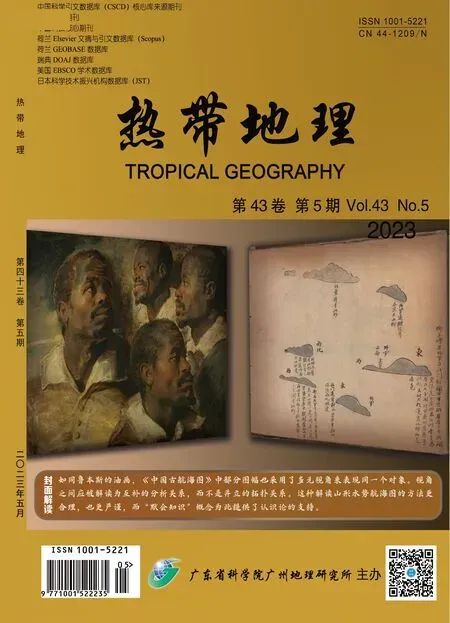都市區建成環境對“共享單車+地鐵”通勤使用影響的空間異質性
——以深圳市為例
郭源園,吳 磊,曾 鵬
(1.天津大學 建筑學院,天津 300072;2.湖南大學 建筑與規劃學院,長沙 410082)
公共自行車(Public Bicycle 或Bike-Sharing,本文對有樁的單車租賃系統統稱為“公共自行車”)一直以來都被廣泛認為是一種綠色、可持續的交通出行方式,一方面,公共自行車本身作為交通出行方式不產生尾氣排放和能源消耗,另一方面,公共自行車的使用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傳統小汽車的出行,如轉向騎行出行,從而進一步改善城市交通擁堵、提高城市公眾健康以及減少城市尾氣排放等(朱瑋 等,2012;郭素萍 等,2017)。公共自行車自誕生以來共經歷了四代,從第一代白色自行車系統,到第二代的押金系統,以及到第三代信息技術系統和第四代需求響應系統(周楊 等,2014)。與此同時,隨著無線通訊、QR code(Quick Response code)、移動支付、移動互聯網等技術的發展,在“互聯網+共享”的發展理念下,以無樁和大數據管理為特征的新形式公共自行車開始逐漸涌現,并被稱為無樁共享單車(Dockless Bike-Sharing)、互聯網租賃自行車(Internet-Based Rental Bike)等(魏宗財 等,2018)(以下簡稱“共享單車”)。尤其在中國,以ofo 和摩拜為代表的共享單車迅速席卷各個城市,并掀起了“共享出行”“健康出行”“綠色出行”的騎行熱潮。
相比傳統的公共自行車,共享單車本身的可自由移動性和自由停放特征使得使用者在目的地的路徑選擇和出行方式上有較大的靈活性,這也使得共享單車本身更易獲得(Chen et al., 2020),因而受到公眾的廣泛使用和關注,尤其是對于被“最后一公里”問題所困擾的地鐵使用者。隨著共享單車的快速發展,共享單作為地鐵的接駁手段之一,在中國諸多城市(尤其是高密度的大都市區,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越發普遍,也極大地提升了地鐵使用者的出行移動性(Travel Mobility)(黃一哲等,2018;張可 等,2019;馬庚華 等,2020)。在實際運營中,共享單車也被運營商重點分布在地鐵站及地鐵沿線附近,如北京和上海分別有44%和51%的共享單車主要活躍于地鐵站點附近(郭蒙,2017)。
“共享單車+地鐵”多模式出行實際上是地鐵出行者對于接駁方式(即連接地鐵站點的方式)的選擇結果,這種選擇往往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在影響個體出行方式選擇的因素中,建成環境一直被廣泛關注。建成環境反映物質空間形態(如土地利用、城市設計等)活動的空間分布以及活動之間連接的時間約束(阻抗),影響人們的出行行為(Cer‐vero et al., 1997; Ewing et al., 2010;曹新宇,2015;Yang et al., 2021)。近年來,逐漸有研究關注建成環境對“共享單車+地鐵”接駁使用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并揭示其與以往公共自行車接駁研究的差異(Guo et al., 2020, 2021a, 2021b; Ni et al., 2020)。然而,盡管有上述少量研究涉及建成環境對“共享單車+地鐵”接駁使用的影響,但對建成環境影響的空間非平穩性(Spatial Heterogeneity或Spatial Non-Stationary)的關注非常少。尤其是大都市地區,建成環境在空間上的分布往往存在明顯的空間異質性(Yang et al., 2020a; 2020b),這種空間異質性對接駁使用的影響不應被忽略。
基于此,本文以深圳市為例,結合ofo 單車的停車位置大數據信息,應用半參數地理加權回歸(Semiparametric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SGWR)模型,探討建成環境對共享單車用于地鐵接駁使用的影響以及該影響的空間異質性。以期有助于共享單車運營商在地鐵服務內對共享單車的分布進行優化,同時也可以為地方政府改善地鐵接駁騎行環境,并進一步推動大都市區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的建設提供科學的參考依據。
1 文獻綜述
1.1 自行車接駁
自行車是一種相對快速、靈活且經濟的方式,并能減少接駁的等候成本。自行車接駁主要有4種模式:“騎—乘”“乘—騎”“騎—乘(不攜車)—騎”以及“騎—乘(攜車)—騎”(Krizek et al.,2010)。前2 種方式下,地鐵乘坐者的單車擁有情況、地鐵站點周邊停車空間及設施、騎行安全感、天氣等是影響其接駁體驗的重要因素,這2種騎行接駁方式在歐洲部分國家最為常見,如荷蘭超過40%的接駁使用者采用這2 種方式(Keijer et al.,2000)。但在美國(騎行分擔率相當低),分別僅有2.2%和2.6%的人選擇“騎—乘”和“乘—騎”方式接駁(Wang et al., 2013)。而對于“騎—乘(攜車)—騎”接駁方式,車廂的駐車空間和對便攜式單車的可容納性是接駁者最大的顧慮,攜車上車甚至可能會引起其與其他乘客的沖突,因而在一些地方自行車并不被允許在高峰時間攜帶上車(盡管可折疊的自行車在常規時間內被允許)(Pucher et al.,2009)。
當考慮自行車的擁有屬性時,自行車作為接駁方式還可以進一步分為3類:自有自行車接駁、租賃自行車接駁和公共自行車接駁。在公共自行車出現的很長一段時期,接駁并不是其主要的功能,自有自行車接駁和租賃自行車接駁一直是主要方式。直到21 世紀00 年代后期,隨著第三代公共自行車的迅速普及以及軌道交通建設的大量開展,公共自行車才開始被廣泛用于接駁。在實踐中,公共自行車車樁大部分被建于軌道站點附近以方便通勤者騎行接駁,從而不需要攜車進站或出站。相比自有自行車和傳統的租賃自行車接駁,公共自行車為“最后一公里”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更加快速和便利的選擇,并且不需要擔心停放、維修及盜竊等問題(潘海嘯 等,2012)。但高效運營的公共自行車接駁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公共自行車本身在車樁及車樁單車容量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再平衡(曹雪檸 等,2015;黃一哲 等,2018)。
1.2 建成環境與公共自行車/共享單車接駁
當前關于公共自行車/共享單車接駁使用的相關研究對建成環境要素的關注主要集中在接駁距離、密度、土地利用和興趣點(Point of Interests, POIs)的分布、騎行設施和其他交通設施的分布上(尹秋怡 等,2018;Ji et al., 2018; Ma et al., 2018; Lin et al., 2018; Guo et al., 2020, 2021a, 2021b,, 2021c)。
一般地,接駁距離是影響地鐵乘客選擇接駁方式最為決定性的因素之一(申犁帆 等,2018)。Zhao等(2017)的研究表明,適度的接駁距離(如1~4 km,北京)能讓地鐵乘坐者更愿意選擇公共自行車接駁;相反,過近的距離,公共自行車會被步行取代,而當接駁距離過遠,公交車和出租車則會取代公共自行車。人口密度對公共自行車接駁的影響尚未明確。在人口密度較低的北美地區,郊區的地鐵通勤者比較傾向于使用公共自行車接駁,但在東亞城市(如新加坡、中國北京和成都等),公共自行車接駁則往往多發生在密度較高的城市區域(蔣聰之,2015;Lin et al., 2018)。此外,就業密度的影響在不同地區表現出一致性,一般來說,由于公共自行車車樁通常分布于地鐵站附近,滿足通勤需求也是公共自行車的主要用途(Ji et al., 2018;Lin et al., 2018; Ma et al., 2018)。
在土地利用與POIs方面,Ji等(2018)發現公共自行車的接駁使用與政府用地、商業用地和工業用地有很大的關聯,但教育用地和居住用地并未觀測到明顯的接駁使用。但也有研究表明,地鐵站閾內的居住用地與公共自行車的地鐵接駁使用呈顯著正相關,并且這種接駁使用在有中學的站域地區往往較高(Lin et al., 2018),即意味著中學生也經常使用公共自行車進行地鐵接駁。同時,混合的土地利用也會增加公共自行車接駁的可能性,而分布于地鐵服務區范圍內的商場的出現對于共享單車的接駁使用有阻礙作用,但綠色空間和公共空間(如公園、廣場)的出現則會鼓勵公共自行車接駁(Zhao et al., 2017; Ma et al., 2018)。
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設施的分布對于公共自行車的接駁使用也有一定影響,如在主干道分布較多以及有較多路口的地鐵服務區范圍內,公共自行車的接駁會受到抑制,而專用自行車道對接駁的使用可能低于預期,原因在于很多專用自行車道往往被私家車占用,尤其是在高峰期,從而帶來不好的接駁騎行體驗(Zhao et al., 2017)。此外,由于公共自行車與公交車在接駁上存在比較明顯的競爭性或相互替代效應,地鐵服務范圍內的公交車站數量越多,地鐵乘坐者使用公共自行車接駁的意愿越低(Zhao et al., 2017; Ji et al., 2018)。
雖然關于傳統公共自行車與地鐵的接駁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鑒于公共自行車與無樁的共享單車在使用模式以及單車分布上的差異,上述建成環境對傳統有樁公共自行車的影響是否能適用于無樁的共享單車尚存疑問。近年來,也開始有少量研究關注建成環境對“共享單車+地鐵”接駁使用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相關研究雖證實了部分建成環境要素(如接駁距離、公交站點等)具有相似的影響效果,但也揭示了其與以往公共自行車接駁研究的差異(Guo et al., 2020, 2021a; Ni et al., 2020),如Ni等(2020)強調了居住用地、辦公用地和城市支路對“共享單車+地鐵”接駁使用的吸引性,也發現了岔路口帶來的負面影響;Guo等(2020)提到混合土地利用、工業用地和公園與“共享單車+地鐵”接駁使用的正相關關系,也特別指出過密的地鐵站分布可能導致較低的共享單車接駁意愿,此外,還著重強調建成環境要素對駛入和駛出接駁的影響存在差異,并且這種差異也同樣反饋在早、晚高峰通勤時間上。同時,共享單車在地鐵口和居住地/工作地附近的可獲得性也是影響其作為地鐵接駁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Guo et al., 2020, 2021a)。
2 研究區域與數據
2.1 研究區域
深圳市作為中國的一線大城市,是一個典型的人多地少的高密度城市,總計有1 344 萬人口,面積1 977 km2(2019年),共計10個行政區。深圳市傳統意義上的主城區包括福田、南山和羅湖3 區,也被成為“關內”(另加鹽田區),其余城市區域即為“關外”(自2010-07-01 起,“關內”與“關外”的行政管理分割被取消)。這種長期以來的行政分割也使得主城區和郊區的城市發展差異明顯,如郊區以加工制造業為主,工廠分布眾多,主城區則以高新技術和金融產業為主,是主要的就業集中地(如南山科技園、福田中心區等)。同時,由于主城區居住成本高昂,多數白領傾向于居住在城市近郊地區(如龍華南、寶安南和鹽田西等),即產業和住房在空間上的差異也導致職住的分離,使得通勤者需往返于主城區和郊區之間,形成明顯的“潮汐”特征。
深圳市同時也是公共交通導向型城市。根據《2019 年深圳市綜合交通年度評估報告》顯示,有超過40%的出行由地鐵承擔,地鐵出行的分擔率相當高,尤其是在通勤高峰期,并且軌道交通占公共交通客運量的比例也高達56.1%(深圳市交通運輸局,2020)。截至2019 年年底,全市地鐵線路全長315.1 km,共計201個站點(包括換乘站),日均客流量達556.8萬人次。如圖1所示,約2/3的地鐵站點分布于主城區(即福田、南山、羅湖3區),但客流量較大的站點往往集中分布在城市的近郊,如深圳北站、五和站等。與此同時,隨著深圳市地鐵系統的快速擴張,共享單車也蓬勃發展并被廣泛用于地鐵通勤者的接駁使用。深圳市于2016年9月引入首個共享單車項目,即摩拜單車,截至2022年初,深圳市的共享單車車輛總規模約為41.65 萬輛,注冊用戶量(含重復注冊用戶)2 911萬人,日均使用量138 萬人次,車輛日均周轉率3.3 次(肖晗,2022)。據《深圳市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發展評估報告(2019年4月)》,52.3%的用戶將共享單車用于通勤(直接騎行上班或接駁使用),有45%的共享單車使用發生在高峰期,同時在某些地鐵站,共享單車接駁的比例高達13%(深圳市交通運輸局,2019)。

圖1 深圳市地鐵分布Fig.1 Distribution of Shenzhen metro system
2.2 共享單車停車位置及建成環境數據
采用的共享單車數據來源于ofo 單車停車實時位置數據,由網絡爬蟲而得。該數據包含了ofo 單車的ID,停車時間和停車位置(X、Y坐標)。網絡爬蟲的打點時間間隔為3~7 min,即每隔3~7 min對深圳市全域范圍內的單車進行爬取,每個時間間隔內的數據量大約為22萬條。由于數據的限制,僅獲得2017-09-26、27和28(對應周二、三、四)的爬取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日間差異。同時通過查詢氣象日歷記錄,這3 d 天氣均為多云或晴,日均溫在27~32℃,比較適合騎行。
建成環境數據主要涉及人口/就業密度、興趣點、土地利用和交通設施等方面。其中,人口/就業密度數據來自于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劃定的交通分區(Traffic Analysis Zone, TAZ),是GIS 矢量數據,包含有每個TAZ單元的人口和就業信息;POIs數據來源于百度地圖,同樣也為GIS數據;土地利用數據是基于深圳市土地利用現狀圖(2016)的GIS矢量數據(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提供)計算而得;此外,與交通設施相關的數據,包括公交站點、地鐵線及站點分布、自行車道和城市道路等數據信息來源于Open Street Map在線地圖①https://www.openstreetmap.org。上述不同來源的數據需通過坐標系轉換,以進行圖層的疊加分析。
3 研究方法
3.1 變量
本文探討是建成環境對“共享單車+地鐵”接駁行為的影響,在分析中以每個地鐵站點的共享單車接駁次數作為因變量,以地鐵站一定緩沖區范圍內的建成環境要素特征及地鐵站的自身特征作為自變量。
3.1.1 因變量:“共享單車+地鐵”接駁使用 參考Guo等(2020)對共享單車的接駁使用的定量方法,對“共享單車+地鐵”接駁使用進行測度。首先,該研究對爬取的停車位置數據進行清洗,將一直處于靜止狀態(即在1 d 之內未有位置移動)的單車排除,也對重復記錄的位置點進行刪除(1 輛單車可能在1 d 之內僅移動了1 次,但被記錄了多次);然后,基于清洗后的位置數據進行O-D分析,得到每對O-D的時間和距離,同時將O-D的起始點坐標通過API導入高德地圖,基于高德地圖的路網,對每條O-D進行騎行路徑模擬,計算每條模擬路徑的距離;建立一定的準則將異常的O-D排除,包括:O-D距離在100~5 000 m范圍內;模擬的路徑長度亦在100~5 000 m范圍內;O-D的時長需<30 min。
考慮到“共享單車+地鐵”接駁使用涉及駛入接駁(即達到地鐵站)以及駛出接駁(即從地鐵站出發)2 種類型,需建立一定的空間范圍對共享單車的到達點和出發點進行空間臨近關系的分析,以分別識別駛入和駛出接駁。首先,對地鐵站各個出口建立100 m 緩沖區,并將其視為接駁識別的空間范圍,即在地鐵站出口100 m 范圍內的停車和用車均被認為是有效的接駁使用(Guo et al., 2021a);其次,用該緩沖區分別對篩選后的O-D終點和起點進行提取分析,從而得到每個地鐵站的駛入接駁和駛出接駁數量。需假設的是,對于在100 m 緩存區范圍內的停車和用車,均認為其目的是為了進行地鐵接駁,而不是恰巧路過地鐵站而停/用車。因此,將O-D 的時間限定在通勤早高峰期(T 07:00-09:00),以盡可能保證共享單車用于地鐵接駁。
綜上,因變量包括早高峰期每個地鐵站的駛入接駁(YA)和駛出接駁(YE)數量,YA和YE均為3 d的平均值。
3.1.2 自變量:建成環境 在出行行為研究中,通常采用接駁距離的累計85%確定地鐵服務范圍(Wang et al., 2017; Zuo et al., 2018)。Guo等(2020)的研究表明,共享單車的駛入接駁和駛出接駁的85%累計換乘距離分布分別對應1 960 和2 040 m。因此,選擇2 000 m 作為半徑約數以提取地鐵站服務范圍內的建成環境要素。本文選取的建成環境要素主要涉及人口/就業密度、土地利用、POIs 以及交通設施,表1 為變量描述和描述性統計,合計2個因變量和21個自變量。

表1 變量描述和描述性統計Table 1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3.2 地理加權回歸及半參數地理加權回歸
傳統的OLS回歸分析假設每個觀測個體是獨立的,并且假設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是均質化的。但在現實中,建成環境變量往往存在明顯的空間異質性,因此需將空間非平穩性考慮進模型中。地理加權回歸分析模型(GWR)是在OLS 模型上的延展,在地理學領域已被廣泛用于討論模型分析過程中的空間異質性問題(Brunsdon et al., 2002;古恒宇 等,2020)。GWR的模型表達為:
式中:yi代表第i個地鐵站的共享單車接駁次數;βik是第i個地鐵站對應的第k個建成環境自變量的系數;xik是第i個地鐵站對應的第k個建成環境自變量;εi即為誤差項;(ui,vi)是第i個地鐵站的空間坐標,βi0(ui,vi)為第i個地鐵站點的回歸常數;βik(ui,vi)是第i個地鐵站點的第k個回歸參數,是一個地理位置的函數。在GWR 模型中,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會隨空間變化而有所差異,其對應自變量的系數可通過最小化加權平方和的方法進行估計:
式中:wij為空間權重矩陣,該矩陣基于地鐵站點之間的幾何直線距離進行計算而得(即基于距離的函數)。
然而,GWR 模型往往假定所有的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都存在空間異質性,但可能的情況是,往往僅有部分自變量的影響表現出空間非平穩性,需考慮其影響的空間差異,這些變量可以稱為局部變量(Local Variable),而其他并未有顯著空間差異影響的自變量則稱為全局變量(Global Variable)。當全局和局部變量同時存在時,傳統的GWR 模型不再適用,而作為GWR模型的延申,半參數GWR(SGWR)模型允許同時將局部和全局變量納入模型回歸分析中(Brunsdon et al., 2002),其模型公式為:
4 結果分析
4.1 空間自相關檢驗
對自變量進行成對Pearson 相關性檢驗,并對每個自變量進行方差膨脹因子分析(VIF)以檢測變量之間的共線性,其結果均顯示,自變量之間存在共線性。在移除了就業密度、工業用地、餐館、商場和支路5個自變量(VIF>10)之后,再進行相關性檢驗,顯示所有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均<0.8,且各個變量的VIF<10。因此,在后續的模型分析中刪除上述5個變量。進一步地,通過OLS對建成環境變量與“共享單車+地鐵”接駁使用的關系進行模型分析,結果顯示,駛入接駁與駛出接駁模型下的調整R2分別為0.400和0.450(表2),表明OLS回歸模型能分別解釋40%駛入接駁和45%的駛出接駁方差差異。同時,在駛入接駁情境下,呈現顯著影響的變量包括人口密度、辦公用地、中學數量、地鐵站點、城市快速路、主干道、交叉路口、CBD距離和進站客流量;在駛出接駁情境下,表現出顯著影響的變量包括辦公用地、居住用地、中學數量、公園廣場、公交站點、地鐵站點、CBD 距離和出站客流。

表2 OLS分析結果Table 2 Results of OLS analysis
對OLS分析結果中的2個因變量殘差進行空間可視化,駛入接駁和駛出接駁的殘差在空間上分布存在明顯的空間集聚(圖2)。對于駛入接駁,近郊的地鐵站的駛入接駁多為正殘差,而對于駛出接駁,正殘差多分布于市區。與此同時,對駛入接駁和駛出接駁因變量進行全局Moran'sI分析,Mo‐ran'sI指數值分別為0.168和0.169,且均在P=0.001水平顯著,即表明地鐵站點的駛入和駛出接駁存在空間自相關。

圖2 深圳市2017年共享單車駛入接駁(a)與駛出接駁(b)的變量殘差空間分布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iduals for dependent variables of access (a) and egress (b) integration by dockless bikeshare in 2017
4.2 模型比較
在上述OLS回歸分析的基礎上,將影響駛入和駛出接駁使用的顯著變量分別篩選,進行GWR 分析以探討空間異質性的影響。在GWR 4.0中先將上述顯著變量均視為局部變量(Local Variable),運行時將核函數設置為Adaptive bi-square函數,帶寬選擇方式是黃金分割搜索(Golden Section Search),選擇標準為AICc,分析結果中既包含OLS 全局回歸分析結果,又包含GWR 的回歸結果,兩者可作為對比。進一步地,在GWR4.0中勾選“Geograph‐ical Variability”,以測度每個變量的空間異質性,并通過DIFF值予以定量顯示。具有正值DIFF的自變量被認為是沒有顯著的空間非平穩性,并被設置為全局變量(Global Variable),反之,具有負值DIFF的自變量為局部變量。將全局變量和局部變量進行歸類后,分別將對應的變量在GWR 4.0中設置為Global 和Local,再進行GWR 分析,此時的GWR分析即為SGWR。
從R2、調整R2、和AICc 等模型的表現參數(表3)可知,對于駛入接駁,GWR 模型的擬合效果顯著優于OLS模型,同時SGWR模型的表現(調整R2=0.645,AICc=1 814.335)也略優于傳統的GWR 模型(調整R2=0.619,AICc=1 847.087);但對于駛出接駁,盡管GWR 模型表現(調整R2=0.622,AICc=1 730.700)顯著優于OLS模型(調整R2=0.453,AICc=1 761.907),但由于所有變量均為局部變量(DIFF<0),故無需進行SGWR分析。

表3 OLS、GWR和SGWR模型結果對比Table 3 Comparisons between OLS, GWR,and SGWR modeling results
4.3 GWR及SGWR模型結果
表4、5 分別顯示了駛入接駁SGWR 和駛出接駁GWR 的分析結果。總體而言,影響駛入和駛出接駁情境的建成環境因素存在一定的差異,僅中學數量、地鐵站點和地鐵客流量3 個變量在2 種情境模型中均表現出顯著相關性。

表4 駛入接駁的SGWR分析結果Table 4 Results of SGWR model for the access integrated use
4.3.1 駛入接駁的SGWR 模型分析 對于駛入接駁,辦公用地、城市快速路和CBD距離3個變量為全局變量(見表4),但在SGWR模型中,辦公用地變量不顯著,而其余2個變量的顯著性則與OLS分析結果一致,這說明城市快速路和CBD距離對“共享單車+地鐵”駛入接駁的影響具有全局性,在整個市域范圍內并不存在空間差異。在城市快速路較多的地鐵服務區內,“共享單車+地鐵”駛入接駁使用往往較多,這與城市快速路的交通阻隔效應有關,城市快速路的存在使得地鐵服務區內的公交和私家車通勤者增加了繞線的可能性,而騎行接駁所受影響較小,故而促進“共享單車+地鐵”駛入接駁(尤其在較為擁堵的早高峰通勤時段)。同時由于深圳市的城市快速路不僅在市郊區而且在福田、南山等中心城區均分布廣泛,因此其對“共享單車+地鐵”駛入接駁的影響有全局性。而距離CBD越遠,駛入接駁往往較少,主要是由于深圳遠郊地區的制造業工廠分布廣泛(越遠離市中心,這種工廠分布越明顯),吸收了大量外來務工人員,由于租房壓力較大,外來務工人員也大多住在工廠內部或工廠附近,高峰時段對地鐵通勤的需求較弱,故而“共享單車+地鐵”駛入接駁較少。
相比之下,人口密度、中學數量、地鐵站點、主干道、交叉路口和進站客流6個變量為局部變量,即這些變量對駛入接駁的影響在空間上存在明顯的差異(或非平穩性)。
為進一步體現這些變量對駛入接駁的影響在空間上的分布差異,對上述變量影響的顯著性(t值)在ArcGIS 平臺上進行空間可視化,以更好地呈現SGWR 分析結果。圖3顯示,人口密度與“共享單車+地鐵”駛入接駁的正相關關系在城市近郊地區非常明顯,如龍華南和寶安南等區域,由于住房相對市區便宜且離市區相對較近,這些地區往往集中了較多的地鐵通勤者,因此在早高峰期間有較多的家與地鐵站之間的駛入接駁需求;中學數量的影響在空間上存在明顯的差異且僅集中在少數地區,在龍華南部和龍崗西部地區,地鐵服務區范圍內的中學數量與共享單車的駛入接駁呈顯著負相關,但在福田中心城區,兩者則為正相關,由于學校校門往往是擁堵的集中區域(尤其是在早晚通學高峰),故地鐵站域內的中學數量增加會使得站域擁堵加重,降低了通勤者使用共享單車接駁的意愿,這一點在道路交通并不十分完善但居住人口密度相對較大的龍華南部和龍崗西部片區尤為明顯。相比之下,福田中心區作為商務區,中學數量較少,居住人口密度也低于龍華南和龍崗西,完善的道路交通,尤其是廣泛分布的自行車道有利于中學生采用共享單車進行接駁,因此福田區的地鐵站域內中學數量與共享單車+地鐵的接駁使用有一定的正相關性。

圖3 影響駛入接駁的局部變量相關性空間分布(t值)Fig.3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effects of local built environment variables on the access integrated use (t value)
地鐵站點對駛入接駁的顯著負向影響(地鐵站點之間的競爭性)集中體現在深圳市的南山、寶安和龍崗等西部和北部片區,而在福田、羅湖等地的影響相對較弱,主要原因在于這些地區是就業集中地(如南山科技園、寶安中心等),且大量地鐵通勤者居住在附近,過密的地鐵分布可能會導致駛入接駁方式的變換,如步行;主干道因素的正向影響集中于福田和南山兩區的銜接片區,這部分地區是深圳市區內居住的主要聚集區(如白石洲、香蜜湖等),駛入接駁需求較大,而且主干道也通常伴有人車共行的混合自行車道,騎行環境較好,有助于共享單車的接駁使用(Guo et al., 2020);交叉路口的負向影響在空間上明顯集中于市區,如道路較為密集的福田和羅湖兩區(深圳市傳統意義上的老城區),一般地,較多的交叉路口會增加騎行的停車次數和等候時間,也會帶來一定的危險性,對于騎行而言是不利因素(Guo et al., 2021a);進站客流的影響幾乎在所有地鐵站點都呈現明顯的正相關性,尤其是在地鐵客流相對較少的遠郊地區(如寶安西部)。
4.3.2 駛出接駁的GWR 分析 對于駛出接駁,包括辦公用地、居住用地等在內的建成環境變量均為局部變量(見表5),表明這些建成環境因素對駛出接駁的影響存在空間差異。同樣地,對上述變量的顯著性在ArcGIS 平臺上進行空間可視化,以更好地呈現GWR 分析結果。辦公用地往往與就業和通勤相關,也是地鐵通勤者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因此辦公用地往往與共享單車的接駁使用呈正相關,這種正相關性在南山和寶安分布最為明顯,而在其他地區幾乎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圖4);而居住用地對駛出接駁的影響呈顯著負相關,并主要集聚于南山和福田的就業集中區,比例越大的居住用地片區意味著用于就業的辦公用地比例越小,其駛出接駁自然也隨之降低;中學數量對于駛出接駁的影響同駛入影響一樣,也呈負相關,且同樣表現在龍華南和龍崗西片區,具體原因有待進一步實證挖掘;公園和廣場等開放空間對自行車接駁使用的正向影響在已有研究中被提及(Zhao et al., 2017),但并未指明是駛入還是駛出接駁,圖4顯示公園廣場對駛出接駁有正向影響(而非駛入接駁),在深圳市的南山區尤為明顯;已有研究多認為,公交站點密度對公共自行車的接駁影響是負向的(Zhao et al., 2017;Ji et al., 2018; Ma et al., 2018),即公交車與公共自行車之間存在競爭,然而在本研究中呈現截然不同的結果,即公交車站點密度大的地鐵服務區,共享單車的接駁同樣也多,并且尤其在居住密度非常高的龍華南部(見圖4),可能的原因是,在近郊的高密度居住聚居區,公交通勤也很普遍,這也意味過多的公交站容易導致更多的停車載客/落客,同時也會吸引更多的通勤者乘坐公交進而導致擁堵,反而降低了采用公交進行接駁的便捷度,因此共享單車會更為受歡迎;地鐵站點密度對于駛出接駁的負向影響在南山區比較明顯,表明在該地區臨近地鐵站點往往有較高的駛出接駁(南山區為深圳市工作密度最大的區域);此外,CBD 距離的負向影響在深圳市遠郊的寶安西地區非常明顯,但在東部的龍崗遠郊地區則較為微弱,可能的原因在于,臨近南山(就業集中區)的寶安更具備吸引地鐵通勤的空間優勢;同時,出站客流也顯然與駛出接駁有正相關關系,并且也主要集中在就業聚集區(南山和福田區)。

表5 駛出接駁的GWR分析結果Table 5 Results of GWR model for the egress integrated use

圖4 影響駛出接駁的局部變量相關性空間分布(t值分布)Fig.4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effects of local built environment variables on the egress integrated use (t value)
5 結論與討論
以深圳市為案例,應用OLS、GWR 和SGWR綜合分析建成環境因素對“共享單車+地鐵”接駁使用(包括駛入接駁和駛出接駁2種情境)的影響,并揭示該影響的空間非平穩性。主要結論為:
1)“共享單車+地鐵”的接駁使用,無論是駛入接駁還是駛出接駁,在早高峰通勤期間均表現出明顯的空間非平穩性,具體表現為近郊地區地鐵站的駛入接駁較高,駛出接駁則在以高新科技園為代表的中心城區有明顯集聚,這與深圳市當前的職住空間分離密切相關。
2)影響駛入和駛出2種不同的接駁類型的建成環境要素有所差異。人口密度、主干道和進站客流3個正向因子以及中學數量、地鐵站點和交叉路口3個負向因子對駛入接駁的影響呈明顯的空間差異;辦公用地、公園廣場、公交站點以及出站客流在大部分地鐵站點對于駛出接駁的影響表現出正相關,而居住用地、中學數量、地鐵站點及CBD距離則表現出負相關。
3)建成環境對早高峰通勤的駛入和駛出接駁的影響差異性,一方面,在于歷史上深圳市施行嚴格的關內和關外空間隔離措施,相關建成環境要素的建設投入存在明顯的關內-關外空間差異,這種差異性對于“共享單車+地鐵”接駁使用的影響是顯著的;另一方面,在適宜的接駁距離范圍,出發地/目的地決定了駛入/駛出接駁的客觀需求,出發地附近的建成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地鐵通勤者在駛入接駁時對共享單車接駁方式的選擇,對應地,目的地附近的建成環境對“共享單車+地鐵”駛出接駁有決定作用。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于促進“共享單車+地鐵”接駁使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和運營意義。首先,共享單車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再平衡(Rebalance)對于共享單車和軌道交通之間的無縫連接至關重要。雖然共享單車的自由可移動特性有助于地鐵-居住地以及地鐵-工作地在微觀尺度上的平衡,但仍需關注城市層面上的時空差異。“職-住失衡”以及通勤流動特征表明,共享單車的接駁使用需要以居住地/就業地為重點,從而滿足對駛入和駛出接駁使用的巨大需求。雖然共享單車一般不能進入居民社區,但仍然需要在居民區附近提供相對固定的時間和地點以提供更多的共享單車,如運營商應該在上午高峰時段,在居住社區的各個出入口實現定期調配并設置易見的停車位,以降低通勤高峰時段內通勤者搜索共享單車的時間。此外,在近郊區的中學附近,需要改善學校附近的騎行接駁安全和擁堵環境,對學生采用共享單車進行通學接駁實現交通引導。考慮到綠色/開放空間在高峰時段對騎行的促進作用,也建議在高峰時段在地鐵站附近的公園和公共廣場增加自行車的投放。
其次,共享單車的再分配需要與公共交通的分布相匹配才能有效提升“共享單車+地鐵”接駁使用。無論是既有公交站點的分布還是地鐵站點的分布,都對共享單車的接駁使用有顯著影響,這種影響在中心城區和近郊區有所差異,故需要制定差異化的交通政策。如,在人口密度大、公交分布密集的近郊地區,可以適當提升共享單車的投放以緩解公交接駁的擁擠。同時,運營商在分配單車時需考慮地鐵站的密度,避免在地鐵站密度較大的片區分配過多的單車(步行接駁更多),遠郊等地鐵分布較少地區由于接駁需求不高,單車的投放不應過大,而更建議在地鐵站密度適中的地區增加自行車的投放(可以取代公交接駁)。
第三,通過改善城市道路分布和道路條件,在地鐵站域內建立友好的自行車騎行環境可以促進共享單車的接駁使用。需要注意的是,當前諸多大城市的城市道路沿線仍然缺乏足夠的自行車道,在通勤高峰期間內,車流和人流量大,缺少管控的混行騎行非常危險。因此,有必要實行多樣化、安全化和人性化的自行車道策略,這在城市道路空間非常有限的大都市中心城區顯得尤為重要。此外,減少交叉路口或設置路口提醒警示,以及在地鐵站域內的站點主要連接道路上增加騎行標記,有助于提供更佳的騎行環境。
本研究可為促進共享單車與地鐵的無縫接駁進而解決困擾城市地鐵通勤者的“最后一公里”問題提供參考,并進一步提升城市交通的可持續性。在具體實踐中,本研究不僅能為共享單車運營商提供合理的單車空間分布和再平衡策略,亦能為地方政府在管理共享單車的接駁上提供政策引導,也可對建設騎乘友好的建成環境和設施規劃提供助力。然而,由于數據獲取的限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如對于接駁的識別還不夠精確以及缺乏長時段的動態變化分析,未來將繼續針對這些不足進行深化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