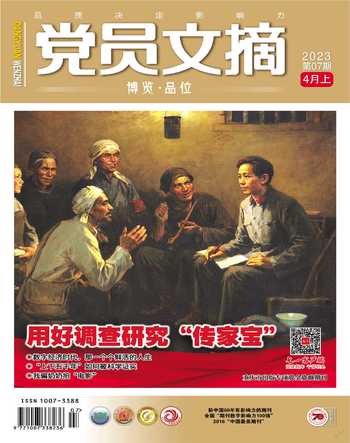一家拉鏈工廠的數字化試驗
陳寧
在著名的“產業微笑曲線”中,生產制造處于價值鏈的低谷。
傳統制造工廠的變革,因此也被品牌和技術兩面裹挾。越來越多變的時尚,會“強迫”工廠對生產設備、流程管理、人員組織和協作進行全面革新。
“個性化”和“大規模工業生產”,看似天平兩端此消彼長的砝碼,現在卻需要被同時兼顧。智能化和數字化,成了當下工廠必須作出的選擇。
這樣的大潮,也與每一個工人息息相關,受影響的不只是他們的工作方式,還有他們作為生產者主體意識的蘇醒,他們會主動去想:什么對我是便利的?系統可以幫我做什么?
車間試驗
每天早上7點半,何周華從宿舍步行前往工廠,路程大約十分鐘。沿途的林蔭路上有許多像她一樣穿著藍色工裝衣的工人,他們是潯興拉鏈廠的員工。

從紙質化到數字化,工人們需要時間去學習和適應
在晉江這座以捕撈業和紡織服裝業聞名的福建沿海小城,潯興拉鏈廠的規模數一數二。成立30多年來,潯興只制造拉鏈,現已成為全球第二的拉鏈供應商。
何周華來潯興后才知道,看似簡單的一條拉鏈,生產卻要經過133道工序。她工作的車間負責尼龍注塑環節,在生產鏈條上屬于成品階段,拉鏈的布帶和拉頭在這里匯集,被加工成一條完整的拉鏈。
尼龍拉鏈的需求量巨大,何周華所在的班組一天需要生產將近20萬條拉鏈,這意味著她每小時要保證班組能有序產出近2萬條拉鏈。
這樣的高效生產發生在車間的數字化試驗之后,然而在試驗之初,沒有多少員工愿意嘗試改變。
2018年,潯興拉鏈廠信息部推行了一項生產制程變革,推動MES(制造執行系統)的實施,意圖將訂單過程的管理變得系統化和數字化,賦予每張制程工單一個PDA(掌上電腦)條碼,掃碼后,就能從終端調出MES系統中的訂單信息,進行查看和變更。每一道工序的工人在完成制作后,通過掃碼來更新訂單的狀態,流程管理將更為便捷。同時,系統也根據訂單情況自動計算工人的工作量,省去了后續人工計算工作量的麻煩。
然而,該系統在車間推行的第一步就遭遇了失敗。對工人們來說,學習、使用新的操作方式意味著改變原有熟練的一套規則,不僅耗費精力,還可能耽誤生產進度。
車間主任羅又華一開始只敢讓一個班組嘗試。“為什么不敢全面推行?如果一推行,現場變亂了怎么辦?車間畢竟有交貨期和質量的要求。”羅又華回憶。于是,離辦公室最近的C組被選中,試驗期一年。
試驗期間,操作設備在電腦端,C組的生產區域放了3臺電腦,工人們需要拿著訂單來電腦前,用掃碼槍掃描。剛開始推行時,即使信息部給工人們集中演示、培訓了,還是有很多人會掃錯,比如穿拉頭的工人,不注意就點到檢驗去了;集中掃碼也是一個問題,有時候來掃碼的人多了,還得在電腦前排隊。
這些問題引起工人們的反感,有人對羅又華說:“我原來用得好好的,多方便,隨時寫個單就可以了。”
一場勢在必行的改革
盡管遭遇了來自一線的壓力,潯興拉鏈廠的改革勢頭還是堅定地往下進行,如開弓之箭,直指數字化的目標。這背后,是制造業的沉疴和市場轉型的逼迫。
拉鏈行業在整體上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進入門檻不高,市場集中度較低,大部分工廠在選擇拉鏈供應商時關注就近服務和價格因素,潯興始終面臨著中小型拉鏈企業的威脅。
擺在潯興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提升效率,通過產量和價格優勢占領市場,增加營收;二是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打造品牌、增強技術,發力中高端拉鏈生產制造。兩條路都離不開智能化和數字化。
如何提升效率是潯興一直在探索的重要課題,從手工時代到機器產業鏈,車間效率已不可同日而語。十幾年間,車間的月產量從200萬變為1300萬,而工人數量只增加了一倍。
雖然機械化帶來了產量的成倍提升,但近幾年來,服裝市場出現了新的變化。不僅僅是貿易量的增長,還在于品類的愈加精細化、個性化。反映在拉鏈上,以往拉鏈樣式雷同,差別只在材質、顏色、大小和長短上,而現在不同品牌、不同款式的服裝設計大不相同。反映在訂單上,呈現出訂單量極多,單個訂單產品的需求量反而極少的特點。“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衣服是獨一無二的。”潯興拉鏈廠信息部負責人林宇用一句話總結。服裝市場都對拉鏈產業的“柔性生產”提出了高要求。
然而“柔性生產”對車間的管理和技術要求很高,林宇觀察了大數據研究車間的生產趨勢,“原來一個訂單都是幾萬條、十幾萬條,多批量、少規格,而現在一個訂單可能只有幾百條,當中的幾十條可能又是另一個規格,訂單就很雜了。如果按數量來算,以前一個訂單就夠這個車間生產一天了,現在訂單數翻了幾十倍,加上設備的問題、質量的問題、其他生產要素的問題,管理的難度呈幾何式增長”。
“必須要數字化。”林宇說,“如果再靠人去跟蹤、協調,沒有數字化的手段,整個車間就跟一鍋粥一樣。”
解救“無意義”
尼龍注塑車間C組的數字化試驗進行時,工人的反饋來到信息部,給了林宇和團隊優化的壓力:如何改進掃碼的體驗?
在正式推行時,信息部做了一個全面的調整,將企業微信作為載體,將訂單管理系統和掃碼流程從電腦端遷移至手機端。
這樣一來,不僅僅是尼龍注塑車間,所有車間的工人都要學著使用新的系統和操作方式。
信息部在每次推行新功能的培訓時,都會給大家做集中演示。一些年紀大的工人在使用中還是會出現問題,但他們會主動來信息部學習。
數字化的推行是自上而下的,但信息部的經理王慶隆覺得,車間工人們不完全是單方面被動地接受數字化變革。為了收集使用意見,信息部將意見和建議的版塊也嵌入了企業微信中,一線工人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在線提交給信息部。出乎王慶隆意料的是,他平均每天能收到一二十條建議,除了“系統怎樣可以更方便一點”的建議外,還有“可不可以上線新的功能”。王慶隆感慨:“大家用得越多,越會主動地產生想法。”
好的意見和建議會被公司給予獎金,激勵一線員工更主動地體驗、思考數字化變革,他們不僅僅被數字化管理著,也成為數字化的參與者。
“最后一公里”
通過統計分析,林宇發現數字化為潯興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十幾年前,潯興福建公司約有6000名員工,年收益6億元至7億元,而現在約3000人,年收益超13億元。人少了一半,收益卻翻了一倍,而且訂單還比過去復雜,這就是從人到設備、到數字化手段提升效率的成果”。
在數字化的加持下,車間里的一切工序和進度都清晰透明了起來,上至管理層,下至每一個工人,都可以通過企業微信中的程序,在自己的手機上查看訂單和生產信息。
面對紛繁復雜的訂單,何周華也不用拿著一張張訂單去跟蹤、核對,一掃碼,信息全出來了。何周華一邊拿著手機操作,一邊解釋:“如果‘漂染車間顯示‘進行中,說明布帶沒有送來,‘電鍍顯示‘已完工,說明拉頭已經到了……每張訂單都可以這樣查。”她甚至能知道每一張訂單目前正由哪一臺機器制作。
數字化的“最后一公里”,就這樣被企業微信打通了。生產的各個環節流暢運行后,何周華的效率明顯提高,最多的時候,她一天能夠跟蹤處理80多個訂單,這是以前手寫訂單時想都不敢想的數量。
在這場數字化改革的洪潮里,何周華最初無所適從,作為一名工人,她也不知道企業正在經歷著怎樣的時代變革。但何周華最終熟練地掌握了數字化的生產流程,讓自己的工作變得更為清晰高效,她借助數字化的連接,在龐大的拉鏈工廠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摘自七一網 七一客戶端/《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