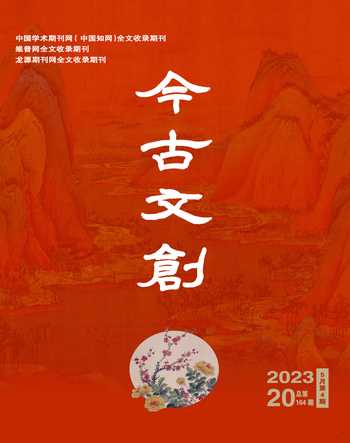踏歌與麗江納西族打跳的關聯性研究
康厚良 楊玉婷



【摘要】 踏歌是一種群舞藝術,它起源古老、歷史悠久、流傳廣泛。如今,原始的踏歌已不復存在,而與其形式相似的活動仍還在民間廣泛開展。為論證踏歌與現有活動的關聯性,以云南麗江納西族廣泛開展的打跳為研究對象,從納西東巴象形文字和相關文史資料入手,對踏歌和打跳的舞蹈形式、出現和發展時間、相互關系等進行了詳細調查和論證,證實打跳是踏歌的遺存。并且,通過分析納西族祭天儀式中踏歌的變化,也再次證實打跳不但是踏歌的遺存,而且還是簡單化、規模化的踏歌,是踏歌適應社會發展需求的新形式。
【關鍵詞】 納西踏歌;納西打跳;踏歌遺存
【中圖分類號】J722?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20-009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0.030
基金項目:蘇州市職業大學引進人才科研啟動金項目(201905000034)。
踏歌,以踏地為節,舞者成群結隊,手拉手,配以輕微的手臂動作[1],邊歌邊舞。踏歌是一種群舞藝術,它起源古老、歷史悠久、流傳廣泛。作為中國的一種傳統民間舞蹈,踏歌以歌舞的形式在民間興起,到唐朝時期達到鼎盛[2]。
如今,原始的踏歌已不復存在,但是與其形式相似的活動卻仍然還在民間廣泛流行,其中包括:納西族的打跳,彝族的跳大三弦,苗族的跳樂,佤族的打歌,傈僳族的哇其,拉祜族的葫蘆笙等[3][4]。這些活動是否與踏歌有關,甚至就是來源于踏歌,卻很難證實。
納西族目前仍然還在使用的東巴文,是世界上唯一存活著的圖畫象形文字。納西語稱為“森究魯究”,直譯為“留在木石上的印記”[5]。東巴文具有明顯的圖畫特征,文字取象于客觀事物,形體往往直接描畫事物的全部外在特征[6]。納西先民用東巴文記錄了他們早期的生產、生活,也記錄了納西族文化、歷史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因此,以云南麗江納西族廣泛流行的打跳為研究對象,從東巴文和相關文史資料入手,探尋納西先民早期的群體性活動與古代廣泛流傳的踏歌、現代納西族的打跳之間的關聯性。
一、踏歌的起源及云南麗江的踏歌
遠古先民以舞蹈來表達“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中最常見的舞蹈是“踏歌”。踏歌對參與者的人數、人員身份及地位沒有要求,舞蹈突出群體特征,是人類群體意識的體現。群體部落的生活給人們帶來了安全感和歸屬感,反映在舞蹈中,即是手拉手、肩挨肩,合節拍而舞[7]。隨著踏歌在群體部落中的盛行,遠古先民們還將踏歌的活動場景刻畫在各種器物上,將踏歌融入他們的生活之中。著名的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出土的舞蹈紋彩盆(如圖1),其內壁繪有15人3組舞蹈場面的圖案,形象生動地展示了三人為從,五人為伍,連臂投足,踏地為節的歌舞形態[8]。另外,青海同德縣宗日遺址出土的繪有24人分組集體舞蹈畫面的舞蹈紋彩陶盆(如圖2)也再次描繪了踏歌的生動場面,說明青藏高原很早就出現了踏歌[9]。
現居住在麗江的納西族,是遠古時期居住在我國西北河湟地帶的羌人遷徙至麗江[10],并與當地土著居民融合雜居而逐漸形成的民族。西北河湟地帶位于甘肅省與青海省的交界處,且大部分位于青海省境內。在宋代王讜所撰《唐語林》的踏歌曲目中對河湟的描述是:“有曰《蔥嶺西》者,士女踏歌為隊,其詞大率言蔥嶺之士,樂河湟故地。” [11]根據彩陶盆出土的地理位置、納西先民的發源地及文獻描述可知,從河湟地帶遷徙到麗江的羌人,不僅融合了麗江的本土文化,同時也將羌人的踏歌帶到了麗江,傳承了下來。
雖然,麗江地區沒有關于踏歌的相關文物線索,但是有文獻對相關現象進行了描述。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記載:“末些蠻(納西族),在大理北,與吐蕃接界,臨金沙江……不事神佛,唯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極嚴潔,男女動百數,各執其手,團旋歌舞以為樂……”它描述了納西族在正月十五登山舉行祭天儀式,并在此期間進行手拉手的“團旋歌舞”,這種舞蹈就是踏歌[4]。到了明代,在麗江當地詩人木公的詩句中有了直接描述踏歌的場景:“官家春會與民同,土釀鵝竿節節通。一匝蘆笙吹未斷,踏歌起舞明月中。”
在東巴象形文字中,也有專門表示踏歌的文字——
[12]。據麗江“東巴大法師”和力民老師介紹,踏歌“? ? ”是一個古老的詞,其中“? ? ?”意思是唱歌,“? ? ?”意思是肋,用來標聲。在東巴字中,與踏歌“? ? ”同樣古老的還有歌詠“? ? ”,說明納西先民當時已經在開展這兩種活動。《詩經·大序》中有描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說的也是歌詠和踏歌。由于《詩經》收集的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詩歌,從形成時間上看,踏歌的凝練和發展應處于該時段,或者是早于該時段的。
從東巴象形文字的形成時間來分析,李霖燦和董作賓先生認為東巴字最晚形成于明代,而方國瑜和何志武先生推斷東巴字的形成年代應該更早一些[13]。而東巴字中有與踏歌相關的文字,說明在東巴字形成的過程中,踏歌就已經在納西先民的生活中廣泛開展了,然后才被作為圖畫文字記錄下來,說明傳入云南麗江的踏歌是早于東巴字的形成時間的。
二、麗江納西族的打跳
現在,原始的踏歌已經不復存在,而目前廣泛流行于麗江納西族中的是一種與踏歌極為相似的群舞性活動——打跳。打跳是一種使用笛子或葫蘆笙伴奏的樂舞藝術,麗江東部的摩梭人稱其為“甲蹉”或“跳鍋莊”,而麗江西部的傳統納西語則稱其為“革案磋”,漢語可譯為“笛子跳”“葫蘆笙跳”或“打跳”[14]。
據記載,納西族的打跳原有70多種,至今保留下來的有20多種。組織形式上,打跳一般由樂器演奏者領頭,參與打跳的人相互牽手(或左手叉腰,右手搭在前者右肩)、圍成圓圈跟著前面的人隨著伴奏音樂或節律做統一的舞蹈動作。打跳的動作重心放在下肢,上身隨膝部起伏、左右擺動或前仰后合,重拍向下(如圖3)。現在,納西族開展打跳的范圍已經從原來的婚喪嫁娶、節令和聚會等發展成為一種集景區旅游體驗、社區居民娛樂健身為一體的大眾項目,其應用范圍更加廣泛,普及度更高,大眾的參與性更強,發展速度也更快。
但是,在東巴象形文字中,沒有表示“打跳”的詞匯。作為一種流行性很強、大眾喜聞樂見的群體性活動,卻沒有與之對應的東巴字,這與東巴字“直接描畫事物全部外在特征”的造字習慣是相矛盾的。另外,麗江作為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地理位置上位于玉龍雪山、金沙江等大山、大河的環抱之中。其天然的屏障使東巴象形文字和東巴文化免受外來文化的沖擊,確保了東巴字從造字之初至今都沒有發生過改變。那么,東巴字中沒有“打跳”一詞,只能說明在東巴字的造字過程中還沒有誕生打跳,或者打跳是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的。
三、踏歌與打跳的關聯性分析
由于近現代打跳活動的盛行,為了便于描述,各地的東巴法師根據自己的觀察、用字習慣等選擇與其意思較為接近的東巴字“唱歌(? ?)”“跳(? ?)”“舞(? ?)”或“邊唱邊跳(? ?)”等來描述打跳,最終產生了使用多個不同東巴字來表示“打跳”的情況。容易看出,這些用于描述打跳的東巴字,同樣也可以用于描述踏歌,只是東巴法師從未想過踏歌和打跳可能就是同一種活動的兩種不同稱呼,如圖4所示。而從各自的形成年代上來看,云南麗江的踏歌是早于東巴字的形成時間的,而打跳是晚于東巴字的形成時間的。因此,以東巴字的形成時間作為分割點,踏歌、打跳和東巴字的形成年代分別為:踏歌(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納西族的踏歌(明代以前)→東巴字(明代)→打跳(明代以后)。
圖 4 踏歌與打跳圖文對比
清乾隆年間,仉蛻在《滇黔小記·蘆笙》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滇黔夷歌,俱以一人捧蘆笙吹于前,而男婦拍手頓足,倚笙而和之。蓋古聯袂踏歌之遺也。”[15]它是對云南和貴州地區少數民族中廣泛流傳的一種舞蹈形式的詳細描述。并且,文中強調這一舞蹈形式是踏歌的遺存。而它所描述的這種舞蹈與現在云南麗江盛行的打跳完全相同。在形成時間上,仉蛻記錄該舞蹈的年代也與打跳形成的年代吻合(明代之后),說明打跳是踏歌遺存的可能性非常大。
四、打跳是踏歌的遺存
在云南麗江,以祖先崇拜為主的祭天是納西族最隆重的傳統節日[16],其主要目的是在祭天活動中,以念東巴經的方式,講述本民族的歷史,追憶祖先的功德,緬懷他們艱苦創業的英雄歷史,教育和激勵后代子孫,以祖先的英雄事跡為榜樣,進取向上,自強不息。但是,祭天儀式只允許本族男子進入祭場參與祭祀。由于祭祀儀式時間跨度較長(一般需要數天時間),不能進入祭場的婦女和外族男子就在家中準備餐飲,確保祭祀順利進行。同時,他們也會在祭祀場外舉行慶祝活動,而其中就包括踏歌,元代李京對納西族在正月十五登山祭天的記載也證實了這一點。可見,踏歌在當時已經成為祭天儀式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納西族祭天儀式的舉行過程和傳承體系是極其嚴謹、系統和完整的。它有專門主持祭典的祭司,嚴謹的祭祀程序、專用的祭祀工具;有傳承不變的祭壇設置,固定的以血緣紐帶為基礎的祭天社會群體;有共同遵守的祭祀規程和時間,共同的祭祀對象和神祇體系;有特定的專門用于祭天的東巴經書、祭神歌和舞蹈[17]。
隨著時間的推移,納西族祭天儀式變得更加隆重,舉行儀式期間的慶祝活動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參與人數不斷增加。到20世紀末,在祭天期間,除了繼續舉行傳統慶祝活動外,有的納西族村子會搭建秋千架供大家蕩秋千;有的納西族村子會組織跳牦牛舞、獅子舞、白鶴舞和麒麟舞等[18]。但是,其中順應祭祀活動發展規律,可有效提高群眾參與度的踏歌卻突然消失了,而取代它的是在組織形式和表現方式上都極為相似的打跳,這和納西族祭天儀式嚴謹、系統、完整的傳承方式是完全不相符的。因此,根據祭天儀式的傳承方式,結合仉蛻在《滇黔小記·蘆笙》中的記載可證實打跳確實就是踏歌的遺存,并且是規模化、簡單化了的踏歌。
五、結語
踏歌與納西族的生活息息相關,并在納西族的宗教祭祀、情感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時間的流逝,納西族的生活環境及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根植于納西族中的踏歌也隨之改變,并以更符合人們需求的打跳留存了下來。雖然名字變了,但是它保留了踏歌的動作特征,傳承了踏歌的集體協作精神,并順應人們的需求不斷發展、進化,使踏歌得以傳承,使這一受到人們喜愛的活動得以發揚、壯大。
參考文獻:
[1]新華詞典編纂組.新華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863.
[2]漆佩玉.傳承千年的歌舞藝術——踏歌初探[J].中國民族博覽,2016,(01):135-136+156.
[3]裘亞萍.踏歌在少數民族舞蹈中的傳承[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3):117-119.
[4]王玲.云南踏歌圖像溯源[J].民族藝術,2015, (03):155-161.
[5]戈阿干.東巴文化勝攬[J].民族藝術研究,1999,(2): 71-80.
[6]鄭飛洲.納西東巴文字字素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03.
[7]楊名.從唐代踏歌的文化內涵解讀李白《贈汪倫》[J].蘭臺世界,2013,(03):58-59+42.
[8]朱狄.原始文化研究[M].北京:三聯書店,1988: 532-533.
[9]安海民.先秦時期青藏高原的民族與文化[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42(01):76-81.
[10] 方國瑜,和志武.納西族的淵源、遷徙和分布[J].民族研究,1979,(1):33-41.
[11] 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8:656.
[12] 方國瑜,納西象形文字譜[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57-72.
[13] 林向肖.東巴文、東巴經形成時代的探討[A].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二輯)[C].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 1993:10.
[14] 楊杰宏.納西族民族通論[M].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2007:300-305.
[15] 紀蘭慰,邱久榮.中國少數民族舞蹈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192,245.
[16] 楊福泉.納西族祭天儀式的功能和特點[J].云南社會科學,2009,(04):15-19.
[17] 趙重合,楊曉林.納西族的祭天習俗[OL/E]//www.sohu.com.2018.8.
[18] 李四玉.論納西族祭天儀式的現代性變遷[J].集寧師范學院學報,2016,38(03):69-73+78.
作者簡介:
康厚良,第一作者,男,碩士,教授,主要從事民族文化與數字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