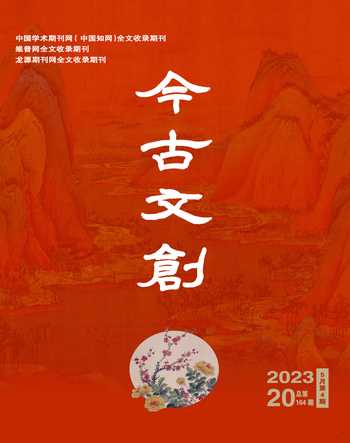目的論視角下《長明燈》文化負載詞德譯研究探析
狄亞男
【摘要】 文化負載詞指的是承載某種文化信息,反映社會生活的常見詞匯或短語,是時代內涵的依托者,常見于文學作品中。《長明燈》是魯迅先生作的一篇思想啟蒙的短篇諷刺小說,知名度不比《狂人日記》等,但同樣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本文從翻譯目的論視角出發,分析譯者杜納德對魯迅先生的作品《長明燈》德譯本中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說明了翻譯目的論在翻譯實踐中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 翻譯目的論;文化負載詞;《長明燈》
【中圖分類號】H315?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20-010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0.032
一、翻譯目的論
“翻譯目的論”由功能派翻譯學家漢斯·費米爾于1978年提出,在翻譯理論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漢斯·弗米爾把翻譯定義成是一種具有目的性的跨文化交際活動,任何翻譯行為都是由翻譯目的決定的,即目的決定手段。目的論包括三個重要原則:目的原則、連貫性原則和忠實性原則。目的原則是翻譯目的論的首要原則,要求翻譯結果能夠在目的語語境與文化中,達成譯文的交際目的。而譯者要在此目的下,決定采取何種翻譯策略與方法。連貫性原則指的是,翻譯應遵循內在連貫性原則,即譯文應被目的語受眾理解和接受,在目的語文化和使用譯文的交際環境中具有意義。連貫性原則從屬于目的原則,即譯文的語內連貫要以翻譯的目的為前提。忠實法則是指忠實于原文,即原文和譯文之間的語際連貫,但忠實性原則也是從屬于目的性原則,翻譯目的和譯者對文本的理解決定了翻譯對原文的忠實程度,譯文不是一定要與原文字對字對等。
二、關于《長明燈》
小說《長明燈》是魯迅先生1925年發表的作品,最初連載于北京《民國日報副刊》, 后被收入到短篇小說集《彷徨》當中。該作品講述的是吉光屯中供奉一盞長明燈,據傳從梁武帝時期點亮后便再沒熄滅過。愚昧迷信的吉光屯居民認為若是熄滅了這長明燈,吉光屯就會變成海,所有人都會變成泥鰍,所以大家都對其小心維護。由此可見,此長明燈與“屯上的居民們”具有強烈的內在精神關聯。屯民們的心目中始終認為天條難犯,神明報應。而屯里卻有一個“瘋子”,他不僅不信長明燈能保佑這吉光屯平安,反而是吹熄后,就不會有蝗蟲,不會有豬嘴瘟……為了熄滅這盞象征封建傳統中君權神權崇拜的長明燈,“瘋子”甚至不惜“要放火”,但全吉光屯上下一心阻止他,連兒童都設法借助“城隍”神威,要祛除附在他身上的“邪祟”,“瘋子”寡不敵眾,以失敗告終。這篇小說表面寫“瘋子”在吉光屯中其他所有人的阻撓和打壓下未能熄滅長明燈,實際是在講即使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接受了民主自由等科學思想的洗禮,傳統中國舊的因襲仍然十分滯重。“五四”新文化思潮,只是在精英知識分子的世界中刮起了強烈的風暴,而對于那些遠離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廣大農村,依然沒能產生魯迅們所預設的期望洗禮,“吉光屯”里的人仍然生活在封建傳統的桎梏之中。
《長明燈》整篇都透漏出濃厚的時代氣息和鄉土氣息,這都依托在文化負載詞之上。想要準確傳達這篇小說的寫作背景的時代特點和主題思想,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當是重中之重。因此本文以目的論為理論框架,聚焦文化負載詞,探究譯者在德譯《長明燈》中所采取的翻譯策略。
三、目的論視角下文化負載詞的翻譯
(一)直譯
直譯的特點主要體現在詞義和修辭的處理上,不使用轉義的方法,既保持原文內容,也保持原文形式。
例一: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動不動就須查黃歷。
譯文:Die Einwohner gingen nicht oft aus,und wenn sie
sich einmal aufmachten,mu?ten sie erst den kaiserlichen Hofkalender studieren.
歷書是宣揚吉兇與忌諱,指導擇日與風水的行為準則規范。自唐代起, 官方對歷書的頒行有著相當嚴格的要求,須由皇帝親自審定后才可開印,因而稱作“皇歷”。到清代末年,使用過的歷法多達百余種,基本屬于陰陽歷的性質。其中,黃帝歷使用最多又最為古老,影響更為廣泛, 人們因此習慣統稱為“黃歷”了。因此,原文中“黃歷”,也就是“皇歷”,譯者將其直譯為der kaiserliche Hofkalender,“皇帝的日歷”,貼合該文化負載詞的基本含義,忠實于原文,符合忠實性原則;這也讓目的語讀者擁有閱讀中國文學作品的感觀,對該詞背后承載的中國文化,即封建時期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有所了解,也能更好地理解黃歷這個詞的含義,符合目的論中的連貫性原則。
例二:沉默像一聲清磐,搖曳著尾聲,周圍的活物都在其中凝結了。
譯文:Tiefe Stille herrschte,wie wenn der scharfe Ton
eines Klangsteines verhallte,und in ihr erstarrten die Umstehenden.
《說文》中寫道:“磬,樂石也。”明確地表示“磬”的本義為“指可制樂器的石料”。除此以外,磬還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打擊樂器,形狀像曲尺,多由用玉、石制成,可懸掛在架子上,用木槌擊奏。原句中的“清磬”指的則是磬石受到擊打后,發出的清脆悠揚的聲音。譯者在這里使用了直譯的翻譯方法,將其譯為“音石發出的清脆聲響”,將該文化負載詞的基本含義完全保留了下來,符合目的論中的忠實原則。
例三:你怎么會知道?那時你們都還是小把戲呢……
譯文:Wie sollst du das wissen?Damals wart ihr alle noch kleine Spielm?tze...
“小把戲”是地區方言,指小孩子。譯者使用直譯法,保留了原詞的形式,將其譯為“玩游戲的小孩兒”,忠實于原文,且翻譯出了此文化負載詞背后的詼諧意味,符合目的論中目的性與忠實性原則。
(二)意譯
意譯指的是保留原文的內容,但不一定保持原文的形式,不作逐字逐句的翻譯。
例四:“那怎么行!他的祖父不是捏過印靶子的么?”
譯文:"Wie gingen das an! War sein Gro?vater nicht Beamter?"
印靶子也寫作“印把子”,官府機構的印的把子,代指官印,捏過印靶子意指此人手里握過政權,當過官。若譯者單純照字面含義直譯出來,那么缺少對應文化背景的目的語讀者就不免無法理解通透,譯文也便失去了意義。譯者在大學期間主修漢學,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頗深,有著很高的文化素養,因此他將其意譯為Beamter(官員),除去了指代的外衣,直截了當地譯出該文化負載詞的核心含義,語意連貫,便于目的語讀者理解與接受,符合目的論當中的目的性原則和連貫性原則。
例五:這不是不肖子孫?我們上縣去,送他忤逆!
譯文 : Ist das nicht ein entarteter Enkel?Wir gehen auf den Bezirk und verklagen ihn wegen Ungehorsams gegen die Eltern!
成語是漢語中的一種獨特的表達方式,意思精辟,結構緊密,成語的翻譯本就是翻譯中一重要部分,而“不肖子孫”這一成語負載著文化意蘊,更屬文化負載詞一列。該成語指的是不能繼承祖先事業的、沒有出息的,也指不正派、品行不好的子孫。德語中entartet是“退化的,墮落的”,ein entarteter Enkel即“不如祖先的子孫、墮落的子孫”,譯者使用的詞是貼合原詞含義的,較好地將該文化負載詞中隱含的文化意蘊傳遞給讀者,而且便利于讀者的理解與接受,符合目的論目的性和連貫性原則。
例六:莊七光的臉上就走了油。
譯文:Auf Dschuang Tij-Guangs Gesicht brach der Schwei? aus.
“走了油”是中國民間一句方言,意思大致為“臉上顯出油光,微微慍怒的樣子”。該詞在原句中表現的是被方頭奚落自己無知后,莊七光臉上出了汗,略微生氣的樣子。譯者讀出了原詞的真實含義,沒有拘泥于原詞的形式,而是使用意譯的方法將其翻譯為der Schwei? ausbrechen (冒汗),這個詞組不僅點出莊七光流汗了的這個動作,也體現出當事人的情緒波動,用符合德語語法規約的表達方式,同樣將原義大致傳達了出來,意思清楚明了,表達順暢自然,符合目的論三原則。
例七:“闊亭!”方頭突然叫道,“你昨天的牌風可好?”
譯文:"Kuo Ting",rief der Eckenkopf unvermittelt,"hattest du denn gestern Glück im Spiel? "
此處“牌風”指的是人在打牌時的運氣,“牌”即打牌、賭博,“風”為“氣運”之意。由于德語中對應“風”的“Wind”一詞沒有該引申含義,若采取直譯方法進行翻譯,目的語讀者將很難實現主動聯想,譯文也將無法體現該詞內的文化因素,因此譯者將其概括為“好運氣”,意譯為Glück im Spiel,即“賭博中的運氣”,同樣向目的語讀者明確傳達出原句含義,實現了翻譯目的,語義銜接通順自然,符合目的論中目的性與連貫性原則。
(三)替換
替換法指的是在翻譯時不能按照原文的詞類機械地照搬,而是將原文不被熟知的詞替換成目的語讀者可以理解的詞。
例八:可是,沒有辦法,幸虧我家的死鬼那時還在,給想了一個法。
譯文 : Zum Glück lebte damals mein Seliger noch,der tüftelte ein Mittel aus.
此處的文化負載詞“死鬼”是詈詞,用于昵稱或開玩笑,關系親密的人之間使用,常用在妻子對先生的諷稱。文段中作者原注為“該屯粗俗女人有時以死鬼稱自己的亡夫”,即指灰五嫂已過世的丈夫。由于該詞的構成表達對于德語國家讀者來說較為陌生,理解上有出現偏差的可能,因此譯者并未照搬照抄原文中目的語讀者不熟知的詞,而是選擇使用德語中的常見表達mein Seliger(我那已故的丈夫)做了替換,增強了譯本的可讀性,使得目的語讀者做到能夠輕松理解該詞在文段的含義,實現了翻譯目的,符合目的論中的目的性原則和連貫性原則。
(四)錯譯
例九:老年人不都說么:這燈還是梁武帝點起的,一直傳下來,沒有熄過……
譯文:Die alten Leute sagen alle,dass diese Lampe noch von Kaiser Liang Wu-Di angezündet worden ist und uns direkt überliefert wurde,ohne je zu verl?schen...
梁武帝,即蕭衍(464年—549年),為中國南北朝時期梁朝政權的建立者。“梁武帝”三字中,“梁”為國號,“武”是這位皇帝去世之后,朝廷依據其生前所作所為,給出的具有評價意義的稱號,即謚號,而“帝”則代指“皇帝”,即德語中的Kaiser,而譯者將其翻譯為Kaiser Liang Wu-Di,錯誤將“武帝”理解為皇帝的名字,進行了音譯,使得譯文中同時出現了Kaiser和Di兩部分,造成了譯文的語義重復,翻譯不恰當。皇帝謚號屬于中華文化專有項,此類詞匯應該在譯者完全清楚詞義內涵與了解其承載的歷史信息后,再結合具體語境等因素進行翻譯。而“梁武帝”這個詞的翻譯未能準確傳達原詞含義,不符合目的論中目的性原則與忠實性原則。
例十:灰五嬸對茶館里在座的人說:“你怎么會知道?那時你們都還是小把戲呢,單知道喝奶拉矢。”
譯文:Wie sollst du das wissen?Damals wart ihr alle noch kleine Spielm?tze und konntet nichts als Milch trinken und mit Pfeilen schie?en.
“矢”字具有多個含義,最常用義為“弓箭”,《釋名》里有寫——“矢又謂之箭”,譯文中所體現的便是“矢”的這個含義。不過,原文中“拉矢”一詞并非“拉開弓箭”之意,而是同“拉屎”的詞義。該文化負載詞展現了漢字的多義性與通假性的魅力。譯者單看該詞的表面形式,未能領悟到該古詞背后蘊含的真實含義,使用了直譯法,進行了錯譯。結合語境來看,“只知道喝奶和射箭”并不通順,語義也缺乏連貫性,可能會造成目的語讀者不明就里,無法理解該句段的含義。因此該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未能完成翻譯目的,不符合目的論中目的性原則與連貫性原則。
四、結語
中國文學作品的德語翻譯隨著“文化走出去”政策得到了發展的沃土,承載中國文化精神的文化負載詞的翻譯在此過程中意義非凡。本文從翻譯目的論視角出發,根據目的論三原則對《長明燈》德譯本中文化負載詞的翻譯進行賞析。在這部作品的翻譯工作中,譯者杜納德展現了十分優秀的漢語底蘊,在德譯過程中主要靈活使用了意譯和替換等翻譯方法,使得譯文具有可讀性,即在目的語國家的文化和交際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意義,使讀者可以理解文化負載詞的基本含義,有些翻譯成功傳達出中國的文化特色,將這些詞語中承載的文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傳達給讀者,完成了翻譯目的,將這部作品很好的推向了德語受眾,符合目的論中目的性原則和連貫性原則;而針對有些文化負載詞的翻譯,譯者選用直譯方法,忠實于原文,符合了忠實性原則。
總的來看,該德譯本中文化負載詞的翻譯實現了《長明燈》的翻譯目的,基本保證了譯文的接受度。不過筆者認為,該譯本也有不足之處。由于譯者使用意譯與替換的方法較多,一些文化因素在德譯本中有所缺失,而在某些采取直譯翻譯的詞上,可能會出現錯譯,使得句段蘊含的中國文化難以向目的語讀者傳達。在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外語的過程中,尤其是在文化負載詞的翻譯過程中,有效傳播中國文化與保證譯文的可讀性具有同樣的重要意義。譯者應在翻譯過程中更加重視文化傳播,選取多樣靈活的翻譯方式,創作出符合翻譯目的的優質譯文,使得中國文學更加受到世界關注。
參考文獻:
[1]宋健飛,黃克琴.中國文學名作德譯本選讀[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9:31-42.
[2]王曉飛.啟蒙思想的多重變奏——魯迅小說《長明燈》細讀[J].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37(04): 112-118.
[3]秦世慧.魯迅“冷門”小說研究[D].湖北師范大學, 2022.
[4]陳欣,朱月芳.目的論視角下文化負載詞翻譯策略研究[J].文學教育(下),2021,(02):172-173.
[5]朱靜文.翻譯目的論視角下《哈姆雷特》漢譯對比研究[J].文學教育(上),2021,(08):131-133.
[6]清偉.皇歷與黃歷不一樣[J].國學,2012,(1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