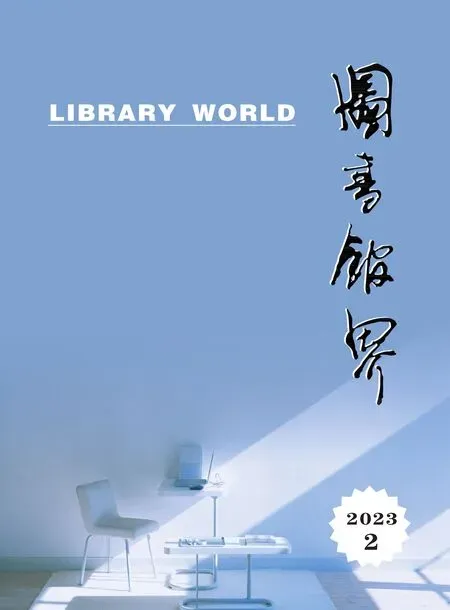黃本驥《避諱錄》編纂與價(jià)值谫論
巫佳燕
(暨南大學(xué)文學(xué)院中國(guó)史籍文化研究所,廣東 廣州 510632)
黃本驥(1781—1855年),字仲良,號(hào)亞卿,別號(hào)虎癡,湖南寧鄉(xiāng)人,是清代嘉慶、道光年間著名的湖湘學(xué)者。黃本驥在歷史、地理、方志、姓氏、職官、經(jīng)學(xué)和目錄學(xué)等方面都頗有建樹,因嗜愛(ài)金石,名其居室曰“三長(zhǎng)物齋”[1]152—153。晚清張之洞撰《書目答問(wèn)》時(shí)在卷末附有《國(guó)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將黃本驥列為清代湖湘的八位著名學(xué)者之一[2],其學(xué)術(shù)成就堪為學(xué)界共識(shí)。他一生著述宏富,有《隋唐石刻拾遺》《三長(zhǎng)物齋詩(shī)略》《三長(zhǎng)物齋文略》《避諱錄》《湖南方物志》《姓氏解紛》《歷代職官表》《三禮從今》《皇朝經(jīng)籍志》等三十余種,近三百卷。除《三禮從今》《隋唐石刻拾遺》《金石萃編補(bǔ)目》《元碑存目》《顏書編年錄》等少數(shù)幾種外,黃本驥的大部分著作都被匯刻收錄在《三長(zhǎng)物齋叢書》中。其中,《避諱錄》首次對(duì)周代至清代的避諱現(xiàn)象進(jìn)行了系統(tǒng)梳理,此書“不僅對(duì)帝王諱例,而且對(duì)一般人的家諱也作了全面的述說(shuō),還特別地注意到了歷史上由于避諱而導(dǎo)致的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年號(hào)的更改現(xiàn)象”[1]4。然而就目前所見,學(xué)界對(duì)黃本驥的生平、家世、交游等基本情況雖已有所關(guān)注,但《避諱錄》尚未有專門的研究成果面世。基于《避諱錄》在避諱學(xué)研究方面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本文試探討《避諱錄》的編纂成書、版本著錄、書籍性質(zhì)等問(wèn)題,考察其學(xué)術(shù)價(jià)值,借此豐富黃本驥及其著述的研究。
1 《避諱錄》的編纂與成書
1.1 編纂目的
《避諱錄》以匯錄避諱史料、考證避諱為核心,是一部用途甚廣的避諱類知識(shí)工具書,便于自用或其他讀者查檢與避諱相關(guān)的信息。《避諱錄》最初的編纂目的可從黃本驥《避諱錄·自序》中清晰窺見:

黃本驥追述了避諱文化現(xiàn)象的起源與發(fā)展,認(rèn)為“諱始于周”,但先秦時(shí)對(duì)避諱記載之文獻(xiàn)寥寥可數(shù),而秦漢以后,“臨文之諱”雖興,卻因避諱不嚴(yán)而近似未諱。到了唐宋,避諱更加謹(jǐn)慎但可惜史傳記錄混淆,沒(méi)有專書裒集避諱知識(shí)以供參考,導(dǎo)致各種避諱現(xiàn)象“時(shí)改時(shí)復(fù),幾于理棼絲而迷歧路矣”。同時(shí)他又指出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兩部避諱研究文獻(xiàn)《野客叢談》和《齊東野語(yǔ)》的疏漏,前者“稍為摭拾”,后者又不加分辨地因襲,從而以訛傳訛,因此兩者“皆不足為考據(jù)定本”。針對(duì)這種現(xiàn)狀,黃本驥決心編纂《避諱錄》一書,以理清各朝各代的避諱現(xiàn)象,“以備遺忘”。
黃本驥亦在《避諱錄》卷二起首明確指出:“避諱興而經(jīng)籍淆,漢唐以來(lái)改復(fù)不一,至宋尤甚。淳熙《文書式》,有一帝之名避之四五十字者。紛紛更易,傳寫易訛。撮其可考者錄之,以便查檢。”[3]233可見,梳理歷代避諱現(xiàn)象以備遺忘與以便查檢是黃本驥編纂《避諱錄》的主要目的。
1.2 編纂背景
其一,《避諱錄》的編纂與清代盛行“文字獄”有關(guān)。清代是“文字獄”發(fā)展的高峰,避諱之風(fēng)也大興,不少“文字獄”的冤案都與御名廟諱有關(guān)。“清之避諱,自康熙帝之漢名玄燁始,康熙以前不避也。雍乾之世,避諱至嚴(yán)。當(dāng)時(shí)文字獄中,至以詩(shī)文筆記之對(duì)于廟諱御名有無(wú)敬避為順逆憑證。”[4]135因觸諱而被下獄的例子有很多,典型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舉人王錫侯的《字貫》一案。他刪改《康熙字典》,編為《字貫》,卻因在書中列康雍兩朝廟諱及乾隆御名遭同鄉(xiāng)王瀧南舉報(bào),而被乾隆投入獄中最后問(wèn)斬。據(jù)金性堯《士中錄》前言記載:“順治至雍正三朝,文字獄約為三十余起,乾隆一朝,卻達(dá)一百三十起以上,即是以一朝而抵三朝的倍數(shù)。”[5]雍正、乾隆年間是清朝避諱制度執(zhí)行最為酷烈的時(shí)期。為避雍正的名字“胤禛”,北宋開國(guó)皇帝趙匡胤名字被改為“趙匡允”;明崇禎皇帝年號(hào)作“崇正”;雍正兄弟名字中的“胤”字一律用“允”字代;著名詩(shī)人王士禛,也不可用原名,而需避“胤禛”之諱,以王士正之名行世。“文字獄”的橫行以及避諱之嚴(yán),產(chǎn)生了許多諱例,這為編纂《避諱錄》的內(nèi)容提供了土壤。無(wú)論是閱讀書籍還是科考行文,若不知避諱,很容易犯下禁忌,招致彌天大禍。在民間恪守避諱也成為一種遵循禮教的規(guī)矩,與人交往、應(yīng)酬,都需事先了解對(duì)方的家諱,以免言行不得體,或傷害對(duì)方。因此,對(duì)避諱進(jìn)行系統(tǒng)研究和整理顯得十分必要,《避諱錄》的編纂整理有很大的現(xiàn)實(shí)需求。
其二,《避諱錄》是樸學(xué)和致用之風(fēng)的產(chǎn)物。明清之際,理學(xué)下沉,樸學(xué)大興,顧炎武、閻若璩、錢大昕等人高舉反理學(xué)旗幟,倡導(dǎo)經(jīng)世致用、實(shí)事求是。而在清代嚴(yán)苛的政治環(huán)境下,許多文人學(xué)者更是埋首故紙,潛心考據(jù)。與每位文人命運(yùn)攸關(guān)的避諱現(xiàn)象也成為他們重要的研究?jī)?nèi)容,許多著錄、考證歷朝避諱的論著應(yīng)運(yùn)而生。清代學(xué)人在避諱學(xué)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謂豐碩,有周廣業(yè)《經(jīng)史避名諱考》、周榘《廿二史諱略》、陸費(fèi)墀《歷代帝王廟謚年諱譜》、黃本驥《避諱錄》等專書。亦有一些避諱學(xué)研究成果散見于清人的學(xué)術(shù)札記中,如顧炎武《日知錄》、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yǎng)新錄》,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陔余叢考》、杭世駿《訂訛類編·歷朝避諱字宜改正》、張之洞《輶軒語(yǔ)·敬避字》等。而這些作品的著者或編者也都是清代赫赫有名的樸學(xué)大家,他們學(xué)風(fēng)平實(shí)、嚴(yán)謹(jǐn),講求證據(jù),不尚空談,使得避諱研究不為研究而研究,而是致力于實(shí)用。黃本驥作為清代樸學(xué)陣營(yíng)的一分子,治學(xué)追求實(shí)地搜討,也重考據(jù)求證。《避諱錄》是其重考據(jù)之作,是他遵樸學(xué)風(fēng)氣,行致用之實(shí)的產(chǎn)物。借助《避諱錄》,士人學(xué)子可以解決一些版本、校勘、辨?zhèn)蔚确矫娴目甲C問(wèn)題,平民百姓也能了解到更多諱例與相關(guān)知識(shí),既可避統(tǒng)治者的高壓,也方便在日常生活中謹(jǐn)言慎行。
其三,《避諱錄》編纂于黃本驥暇居黔陽(yáng)期間。據(jù)黃本驥在《避諱錄》自序中言“時(shí)道光二十六年四月望日,龍標(biāo)學(xué)長(zhǎng)黃本驥自識(shí)”[3]229,又《虎癡先生年譜》記載“四月十五,著《避諱錄》五卷成”[6],可確知《避諱錄》的成書時(shí)間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黃本驥時(shí)年六十六歲,此時(shí)他已被選為黔陽(yáng)縣教諭將近十年了。《避諱錄》成書于此時(shí)此地,不僅離不開黃本驥深厚的學(xué)問(wèn)功底,而且與他在黔陽(yáng)教諭任期潛心著述密切相關(guān)。將近花甲之年才正式踏入仕途,且黔陽(yáng)縣偏居一隅,黃本驥可謂官閑心冷。也正因此,他官務(wù)不忙,更有精力沉潛學(xué)術(shù)。此后黃本驥在黔陽(yáng)完成了一生中的大部分著述,并在湘陰蔣環(huán)的幫助下,將舊作與該期的新作匯刻成二百余卷的《三長(zhǎng)物齋叢書》,其中便包括《避諱錄》。其自序云“本驥齋居多暇,不揣固陋,因以目所及見者,匯錄成編”[3]229,亦是他精力有余,足以潛心編撰《避諱錄》的明證。
1.3 成書體例
《避諱錄》既成,分為五卷。卷一為本朝敬避字樣,詳述清圣祖玄燁、清世宗胤禛、清高宗弘歷、清仁宗颙琰四位皇帝的帝諱。卷二至卷四為歷朝國(guó)諱,按順序分述了周代、秦、(西)漢、東漢、三國(guó)、(西)晉、東晉、十六國(guó)、(南朝)宋、齊、梁、北魏、北齊、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十國(guó)、宋、遼、金、元、明各代帝王諱例,依力所能見及所考而有詳有略。卷五為家諱,考述了民間常見的避諱之禮及現(xiàn)象,如“卒哭而諱”“入門而問(wèn)諱”“凡祭不諱”“君所無(wú)私諱”“夫人之諱”等等[3]252。五卷之后又有《避諱錄》補(bǔ)正材料七則,分別補(bǔ)述了(西)漢、東漢、三國(guó)、隋、唐、十國(guó)和宋的避諱之例。各卷之間可謂遞進(jìn)關(guān)聯(lián),共同構(gòu)成一個(gè)整體。
從體量上看,卷二至卷四是全書的重點(diǎn)部分,占四分之三的篇幅。王建《中國(guó)古代避諱史》指出:“在所有的避諱用例中,避君主之諱的用例占了絕大多數(shù)。避諱雖然是流行于全社會(huì)的習(xí)俗,但能載入史冊(cè)的大都是避君王諱的記錄。不但先秦如此,直至清末的整個(gè)古代社會(huì)均是這樣。”[7]17帝王之名幾乎是古代社會(huì)所有人都要回避的對(duì)象,所以在歷代避諱的研究中,因避帝王名諱而產(chǎn)生的史例也最多。而黃本驥在《避諱錄》卷一至卷四中便重點(diǎn)而系統(tǒng)地梳理了周代至清代的帝王避諱現(xiàn)象,全書以避帝諱例居多。
此前的學(xué)者對(duì)避諱這種文化現(xiàn)象已有一定的研究,如韓愈、洪邁、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王鳴盛等,但多是零星的篇章論文或不成體系的學(xué)術(shù)札記,《避諱錄》對(duì)周朝至清朝的避諱現(xiàn)象的梳理可謂突破了這些學(xué)者在避諱研究上的局限。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周廣業(yè)的《經(jīng)史避名諱考》(46卷),該書成書于乾隆時(shí)期,在《避諱錄》之前,其考證精良、內(nèi)容豐贍雖在《避諱錄》之上,但是分類駁雜,在當(dāng)時(shí)又并未刊行,流傳受限[7]276,對(duì)于普通讀者而言,查檢和使用上均不如《避諱錄》便利。綜上所及,《避諱錄》是中國(guó)古代避諱學(xué)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部研究著作。
2 《避諱錄》的著錄與性質(zhì)
現(xiàn)存《避諱錄》主要通過(guò)叢書得以保存流傳,主要版本有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刻《三長(zhǎng)物齋叢書》本、清道光二十六年知敬學(xué)齋刻本、清鉛印本、清光緒四年(1878年)貞史氏古香書閣刻本四種。其中《三長(zhǎng)物齋叢書》由前已知是以黃本驥居室“三長(zhǎng)物齋”命名,在其好友蔣環(huán)的幫助下匯刻而成的,《避諱錄》作為一種被收入其中。而知敬學(xué)齋,則是黃本驥在黔陽(yáng)任教諭時(shí)辦公的一處學(xué)署[8]。道光二十六年,《避諱錄》成書,亦在黃本驥黔陽(yáng)教諭任期內(nèi)。從可見的知敬學(xué)齋本《避諱錄》書影中能看見卷一有落款“《三長(zhǎng)物齋叢書》”,《三長(zhǎng)物齋叢書》本《避諱錄》其目錄頁(yè)處亦有落款“寧鄉(xiāng)黃本驥仲良編輯,湘陰蔣環(huán)維揚(yáng)參校”[3]230,通過(guò)對(duì)比可知知敬學(xué)齋本應(yīng)為《三長(zhǎng)物齋叢書》本的單行本。清光緒四年(1878年)古香書閣刻本則屬貞史氏重刻本[9]。
而《避諱錄》著錄于各書的情況則較為復(fù)雜。其中《八千卷樓書目》《清朝續(xù)文獻(xiàn)通考》《清史稿·藝文志》《中國(guó)類書》等書都將《避諱錄》歸入子部類書類;《叢書集成續(xù)編》和《中國(guó)古籍總目》將《避諱錄》收進(jìn)史部政書類儀制之屬謚諱一類中;《清朝續(xù)文獻(xiàn)通考》除了子部類書類,其史部譜牒類和子部雜家類亦重復(fù)收錄了《避諱錄》;《書目答問(wèn)補(bǔ)正》則將其放在譜錄類姓名之屬;另在一些綜合性叢書目錄中,《避諱錄》多被載于《三長(zhǎng)物齋叢書》名目下,如《中國(guó)叢書綜錄》《增訂叢書舉要》《中國(guó)古籍總目》叢書部、《美國(guó)哈佛大學(xué)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叢書部叢書類等均載有《避諱錄》五卷。由上述記載可見各書對(duì)《避諱錄》歸屬的劃分并不一致,分類的不同實(shí)則反映了人們對(duì)《避諱錄》性質(zhì)的多樣性認(rèn)識(shí)。
在各個(gè)目錄中,《避諱錄》被分為類書類的情況最多。如前所論,《避諱錄》是一本用以查檢避諱知識(shí)的工具書,它雖沒(méi)有采用傳統(tǒng)類書的抄集群書、分類排纂的編排體例,但它系統(tǒng)地以時(shí)間順序鋪排各朝諱例,同時(shí)旁征《左傳》《周書》《周禮》《春秋》《詩(shī)》《尚書》《論語(yǔ)》《史記》等書以進(jìn)一步分析述說(shuō),全書結(jié)構(gòu)清晰、井井有條,查檢起來(lái)十分便利。類書按其內(nèi)容性質(zhì),又可分為包綜自然界與人類社會(huì)的全部知識(shí)的綜合性類書,以及僅含某一方面知識(shí)的專門性類書。《避諱錄》顯然是一本避諱現(xiàn)象研究的專書,全書只有避諱一種分類。《清朝續(xù)文獻(xiàn)通考》《清史稿》等書將《避諱錄》分入類書類,正是抓住了《避諱錄》作為專門性類書的特點(diǎn)。
在古代,避諱是一種習(xí)俗,更是一種與禮制、政治密切相關(guān)的制度和律法。如《禮記·王制》:“大史典禮,執(zhí)簡(jiǎn)記,奉諱惡。”[10]《隋書·禮儀志》:“漢法,天子登位,布名于天下,四海之內(nèi),無(wú)不咸避。”[11]又《避諱錄》記載清朝法律規(guī)定:凡犯諱者,“舉人罰停會(huì)試三科,進(jìn)士罰停會(huì)試三科,進(jìn)士罰停殿試三科,生員罰停鄉(xiāng)試三科。雖經(jīng)缺筆,仍各罰停一科,生員均發(fā)學(xué)戒飭”[3]231。檢閱《避諱錄》可知,其所關(guān)注的研究對(duì)象以及援引的避諱史料中,敬諱居絕大多數(shù),也即由于政治、禮制的規(guī)定而回避和君主、官員、尊長(zhǎng)名字相關(guān)的名物,所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因而《叢書集成續(xù)編》《中國(guó)古籍總目》諸書將《避諱錄》歸入史部政書類的儀制之屬,亦屬妥當(dāng)。
譜錄是一種專門收錄各種圖譜和記載專書的圖書分類。宋代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始設(shè)譜錄一門。“其子部別立‘譜錄’一門,以收香譜、石譜、蟹錄之無(wú)類可附者,為例最善”[12]。譜錄雖以記物為主,但也有記人的書籍,如《小名錄》《侍兒小名錄》等。譜錄類書籍記物時(shí),除了記錄某物的客觀特征,還會(huì)附錄關(guān)于此類事物的趣事;而記人時(shí),除了記錄某人的籍貫家世、生平經(jīng)歷,還會(huì)附載人物的逸聞故事。《避諱錄》亦記載了一些有關(guān)避諱的人物典故,簡(jiǎn)列了帝王的生平事跡,并將人物之間的關(guān)系、故事加以串聯(lián)。例如,舉唐代帝王諱例時(shí),列唐高祖至唐朝末代皇帝哀帝的名號(hào)、字號(hào)、避諱字及其父、兄、弟、子的關(guān)系等。這些都符合譜錄的一般特點(diǎn)。至于譜牒類圖書,大多記載的是帝王將相、門閥顯貴、地方望族的姓氏或宗族世系。綜觀《避諱錄》所記避諱之事,其所避諱的對(duì)象主要也是與帝王將相、姓氏或宗族世系有關(guān)。就以上所論,《避諱錄》被《書目答問(wèn)補(bǔ)正》《清朝續(xù)文獻(xiàn)通考》歸為譜錄或譜牒類也是合理的。
每部目錄著作的分類類目和標(biāo)準(zhǔn)都不一致,對(duì)其所收書籍的內(nèi)容性質(zhì)的判斷也各有所持,因此無(wú)須斷言《避諱錄》為何類書籍更為恰當(dāng),但是《避諱錄》一書可屬多種分類,且被眾多目錄著錄,亦可見其性質(zhì)之多樣、流傳之廣泛和價(jià)值之可貴。
3 《避諱錄》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
《避諱錄》自問(wèn)世以來(lái),隨《三長(zhǎng)物齋叢書》見著于多書中,被今人運(yùn)用于多方面,它不僅被認(rèn)為是研究避諱改字的代表作、通行專著,也被認(rèn)為是研究歷史和風(fēng)俗文化學(xué)、風(fēng)俗史的必讀書,應(yīng)用于史料學(xué)、漢語(yǔ)語(yǔ)諱學(xué)、人物傳記研究、方志研究等等。但是,在避諱方面的功用仍是《避諱錄》最突出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所在。避諱學(xué)是史學(xué)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陳垣稱:“避諱為民國(guó)以前吾國(guó)特有之體制,故史書上之記載,有待于以避諱解釋者甚眾,不講避諱學(xué),不足以讀中國(guó)之史也。”[13]他認(rèn)為避諱學(xué)乃史學(xué)一門輔助學(xué)科,由于各朝各代所諱不同,避諱方法也不一致,因此古代典籍中有不少因避諱改易文字的地方,甚至對(duì)年號(hào)、姓名、官名、地名、書名等進(jìn)行刪改或?yàn)E用,致使古書淆亂不清。若缺乏一定的避諱學(xué)常識(shí),史學(xué)研究會(huì)遭遇許多困難,因此必須重視避諱學(xué)知識(shí)的獲取和學(xué)習(xí)。
《避諱錄》作為清人在避諱學(xué)方面的重要成果之一,在避諱研究方面有其獨(dú)特價(jià)值。比之前書,如陸費(fèi)墀的《歷代帝王廟謚年諱譜》(簡(jiǎn)稱《諱譜》)、周榘的《廿二史諱略》(簡(jiǎn)稱《諱略》),《避諱錄》在篇幅、體例和內(nèi)容上都有所突破。首先,《諱譜》《諱略》均只有一卷,在篇幅上小于《避諱錄》的五卷,所能承載的內(nèi)容相對(duì)有限。其次,三書的體例和內(nèi)容也有不同。《諱譜》主要以表格的形式,收錄自西漢至明末歷朝帝王的廟謚、名、世次、歷年、紀(jì)元、葬、所諱字(即替代字)七項(xiàng)內(nèi)容,簡(jiǎn)明扼要,便于查檢;《諱略》則在宋余懷《帝諱考略》的基礎(chǔ)上增輯了歷代國(guó)諱諱例;而《避諱錄》按照朝代分卷而專記避諱,且不限于帝諱,還有家諱及其他避諱典故。再次,《諱譜》《諱略》《避諱錄》三書在查檢歷代避諱方面都各有自己的特色和一定的參考價(jià)值,使用時(shí)可互相補(bǔ)充參看,但相較而言,《避諱錄》所著避諱史料較其他兩書更為豐富。如《諱譜》不載清代避諱材料,而《避諱錄》卷一“本朝敬避字樣”則記有清代避諱材料若干條,如:
圣祖仁皇帝諱……(康熙)陵號(hào)曰景。北魏宣武帝、唐憲宗、明宣宗,陵號(hào)相同。策內(nèi)稱某帝某宗不得以某陵稱。古竟陵縣,今湖北安陸府,后晉避敬字嫌名,改竟作景,歷代因之。本朝改名天門,以避陵號(hào)[3]231—232。
《諱譜》《諱略》二書對(duì)許多朝代的帝諱例均失載,缺漏了很多避諱字,而《避諱錄》則對(duì)周至清各朝各代的帝諱避字都有所說(shuō)明或考述。《避諱錄》中還有詳盡的舉例,材料可謂豐贍,如卷三黃氏輯錄劉知幾之不避唐代國(guó)諱的材料:
劉知幾《史通》不避世字,其論李百藥《齊書》曰:“變世祖為文襄,改世宗為武成。茍除茲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別。”是譏百藥不應(yīng)避時(shí)諱也。其他征引書目則《世本》《世說(shuō)》屢見于篇,其第五篇以《世家》標(biāo)目。書中泛言世字,如春秋之世、高惠之世,不下二十余處。又曰“民者,冥也”,兩言“民無(wú)得而稱焉”,“民到于今稱之”,皆一以人代民,則直書民字。是太宗二名皆不諱也。其引古人則石虎、劉昞、鄧淵、張淵、石顯、蕭子顯、韓顯宗、高堂隆、衛(wèi)隆景,皆直書其名。崔伯淵、季彥淵,皆直書其字。其泛言虎、淵等字,則曰畫虎不成、虎踞龍盤、臨朝淵默、治國(guó)字人、旦行不臣、之禮窳龍、異等基業(yè)、未彰而用、顯微顯晦、隱顯幽顯等字亦不下十有余處,皆不用同義字代。是于祖宗廟諱、明皇御名皆所不避,又不獨(dú)太宗偏諱也。然《史通》稱魯莊公曰嚴(yán)公,稱楚莊王曰嚴(yán)王,遠(yuǎn)避漢明之名,而于本朝不諱,殊屬怪謬,且知幾以明皇嫌諱,改以字行,嫌且改避,隆基正名絕不顧忌,是謹(jǐn)于問(wèn)安小禮而不顧父母之養(yǎng)。惡得為孝子哉?然亦可見唐初國(guó)諱,視后世禁例尚為疏略矣[3]241—242。
陳垣曾在《史諱舉例》序言中批評(píng)《避諱錄》和《諱譜》《諱略》“三書同出一源,謬誤頗多,不足為典要”,“人云亦云,亦未深考。其所引證,又皆不注出典,與俗陋類書無(wú)異”[4]2。誠(chéng)然,五卷本的《避諱錄》并不恢宏,陳垣所指出的“人云亦云”“謬誤頗多”的弊端也在《避諱錄》中存在,但若因此貶斥其“不足為典要”“與俗陋類書無(wú)異”則又太過(guò)。
黃本驥在《避諱錄》自序中曾表明自己是“因以目所及見者,匯錄成編”,并且希冀“至詳征經(jīng)史,使歷朝掌故一字無(wú)遺,尚有待于博雅君子”,因此也可理解《避諱錄》的確存在搜采未備,僅錄其大略,考證不夠嚴(yán)密等缺點(diǎn),但也不能因其疏略處就全然抹殺其閃光點(diǎn)。比如《避諱錄》敏銳地注意到了各種避諱現(xiàn)象之起源并進(jìn)行了歸納:始皇名政,兼避正字,乃“避嫌名之始”[3]233;漢元帝后王氏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乃“外戚避諱之始”[3]235;孫權(quán)太子名和,赤烏中,改禾興為嘉興,避嫌名也,為“儲(chǔ)嗣避名之始”[3]236;郭崇韜父名宏,改宏文館為崇文,為“朝廷避大臣家諱之始”[3]245。黃本驥還認(rèn)為“避諱之論,備載于前學(xué)者,所當(dāng)遵守而勿泥也”[3]253,“后人名字之外,各有別號(hào),古所無(wú)也,不必泥于潁濱之稱”[3]257。他亦反對(duì)避諱過(guò)甚而致自諱其名,出情理之外,鬧出謬極的笑話來(lái),并舉例闡發(fā)之:“如田登為州守,諱燈為火。值元夜,吏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3]256可見黃氏對(duì)避諱問(wèn)題是有很多補(bǔ)充與創(chuàng)見的。
除了運(yùn)用于避諱研究,《避諱錄》在校勘、考證、辨?zhèn)巍㈣b定方面也有一定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黃本驥認(rèn)為該書的避諱知識(shí)在鑒定文物方面能起到較大的作用:“余撰是錄,不獨(dú)可證史氏之訛,即世之瞎買古董者,亦當(dāng)奉為刮目金篦矣。”[3]248《避諱錄》的考據(jù)成就也得到了今人的肯定和贊揚(yáng)。完顏紹元稱《避諱錄》是同類書籍中搜羅最稱詳備者[14]。《湘學(xué)》將黃本驥的《避諱錄》和其《古志石華》《集古錄跋尾》《歷代職官表》《歷代紀(jì)元表》等都列為近代湖湘考據(jù)史學(xué)的名作[15]213。羅志歡則認(rèn)為黃氏開一代風(fēng)氣,對(duì)清代學(xué)術(shù)有很大貢獻(xiàn),其《歷代統(tǒng)系錄》《避諱錄》《姓氏解紛》諸書為甚便學(xué)者查考的工具書,《避諱錄》更是有利于史書閱讀和考證[16]。
黃本驥曾得心應(yīng)手地運(yùn)用《避諱錄》上的避諱知識(shí)進(jìn)行考據(jù),如在編訂《顏魯公集》時(shí),黃本驥發(fā)現(xiàn)宋代留元?jiǎng)偹獭吨伊x堂帖》收錄的顏真卿一帖有可疑之處,據(jù)《避諱錄》唐代諱例帝祖名虎,應(yīng)以“武”字替“虎”字,睿宗名旦、太宗名世民,“旦”字與“民”字不可直書等現(xiàn)象與知識(shí)而考訂該帖為偽:
唐避國(guó)諱,改虎邱作武邱,詩(shī)題不應(yīng)仍稱虎邱。魯公書虎字皆缺末挑,帖本不缺。詩(shī)中旦字及珉字偏旁之民,皆唐代廟諱,帖亦直書不避。謂此帖為魯公書,則種種可疑,然其詩(shī)則確為公作,而書與歟蓋后人偽托也[17]。(《顏魯公文集》卷十二《刻清遠(yuǎn)道士詩(shī)因而繼作》)
諸如此等用避諱知識(shí)進(jìn)行考據(jù)的例子,證據(jù)確鑿,令人信服。
《避諱錄》中提供了歷代的帝諱、家諱、禮諱,研究者可依據(jù)書中的諱法、諱例、諱字,查找帝王、妃嬪等名諱,以及他們的祖諱、家諱等,識(shí)別和掌握諱字規(guī)律及因避諱而改姓名、改年號(hào)、改官名、改地名、改書名,辭官棄舉或獲刑入獄等現(xiàn)象,從而實(shí)現(xiàn)考定古書時(shí)地和鑒定版本的目的。《避諱錄》亦可在鑒辨檔案史料之真?zhèn)紊习l(fā)揮重要作用,諱字尤其帝王之諱,可謂時(shí)代之標(biāo)志,通過(guò)《避諱錄》可熟悉周至清代主要的避諱字樣,迅速查檢某個(gè)時(shí)期有哪些應(yīng)予避諱的文字,以及某個(gè)避諱文字的書寫替代情況等,有利于對(duì)檔案史料的時(shí)間做出進(jìn)一步的判斷。
總而言之,在《避諱錄》成書之前,雖已有不少記錄、訓(xùn)釋避諱資料的書籍,但是它們大多數(shù)僅停留在藉避諱以釋疑解惑,未進(jìn)行有系統(tǒng)之梳貫整理,勒成專書。直至《避諱錄》,以時(shí)間為序,將西周至清代的帝諱、家諱等條敘分明、清晰羅列,雖不免有訛誤、疏漏之處,但仍不掩其珍貴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其提供的避諱知識(shí)可用于校正文字訛脫、辨別古書真?zhèn)巍㈣b定古書版本、考證史實(shí)時(shí)代、研究古書疑滯等。雖然當(dāng)今對(duì)避諱學(xué)的研究整理,較之清代,文獻(xiàn)資源更加全備,研究領(lǐng)域更為廣泛,后出的避諱研究書籍轉(zhuǎn)精轉(zhuǎn)博,亦不在少數(shù),但對(duì)于《避諱錄》的篳路藍(lán)縷之功,仍須予以充分肯定。通過(guò)本文的考察,我們應(yīng)對(duì)此書的價(jià)值有更加客觀、全面的認(rèn)識(s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