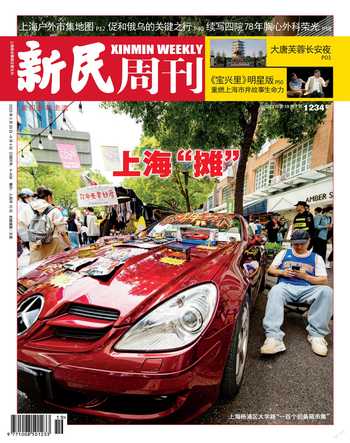聞黎明:研究西南聯大四十年
聞黎明 張英

聞黎明回憶祖父聞一多以及西南聯大往事。
我理解的祖父聞一多
作為聞一多的孫子,西南聯大后代第二代,我沒有見過祖父。
我是從1985年開始研究聞一多的。之前,聞一多作為中國近現代作家群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學界研究的一個熱點。我受邀參加一次全國性的聞一多學術研討會,第一次正式以歷史研究者的身份接近他。在此之前我沒有想過做聞一多研究,因為怕受感情因素影響,怕不客觀。
那次研討會看了各地學者提交的論文,總覺得重復的東西很多,總體來講沒什么突破,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新的材料。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那時我就想,也許可以做一些史料梳理,填補當下聞一多研究中的空白,也提供給相關研究者和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人參考。
后來我開始有意識地收集關于聞一多的各類基本資料,很多年的時間里,我走遍聞一多生活過的地方,查閱那些地方的報刊等歷史資料,從茫茫史料中不斷發現一個新的祖父。
聞一多其實不用步行去昆明的,許多老同事對于我祖父的決定大惑不解。因為從長沙去往昆明的安排有幾種,體力較弱的老師,以及女生,安排汽車送去。聞一多的身體狀況不算好,并且作為清華大學文學院的教授,他是可以和陳寅恪等很多老師一樣,從長沙出發,穿越湖南、廣西、廣東,從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港,坐車到河內,從河內坐火車到磐山,最后到達昆明校區的。
祖父當時的理由是: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大學里教書,在城市里生活,并未見到最底層的社會,那才是大部分中國人居住的區域。只有通過這樣的徒步旅行,不斷地田野調查,才能接觸到真實的中國社會。
他參加的西南聯大“湘黔滇旅行團”,這支隊伍由30多名教師和284名學生組成,在2月19日從長沙出發,4月28日到達了昆明,正值清華校慶。過了幾天,1938年5月4日,西南聯大正式開課。
這次旅行徹底改變了祖父,讓他從一個大學教授,成為了一個關心社會現實、關心政治的民主運動人士。這次旅行也改變了學生們,“經過艱難徒步的天之驕子們,再也不會覺得祖國和人民是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
一路西行的師生們,從長沙到昆明的路上,睡地鋪、挑腳泡、在野外支鍋做飯、在極簡陋的茶館小憩;聞臺兒莊大捷,師生們舉行了慶祝大會;聽說前方有匪,他們走小路行軍。他們還對沿途之地進行了人文社會考察與地理寫真。
其中,哲學心理教育學系的學生劉兆吉組織的詩歌采風小組采集到2000多首民謠,后來在祖父的指導下編成了《西南采風錄》;政治系學生錢能欣則根據自己的日記整理出了《西南三千五百里》,他后來回憶說:“臨行前,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資料,遺憾的是關于我國西南地區的記錄多是外國人寫的。因此,出發前我已經有準備,要把沿途的見聞記錄下來……我要寫一本中國人自己的西南實錄。”
上世紀80年代,許多和祖父有過交往的同輩人物都還健在。我在史料收集過程中遇到有疑問的地方,就千方百計找當事人求證,比如馮友蘭、冰心、王力等人,厘清了許多基本史實。
當年梁實秋提到過一件事,1924年中國留學生組織在哈佛大學演出中國傳統戲劇,寫信邀請聞一多助陣,但聞一多回信說有事不能去。梁實秋據此信在文章里說聞一多沒有參加那次演出。但當我見到冰心,問起這件事時,冰心很肯定地告訴我:“怎沒去呢?是他給我化的妝啊!”
對于戰爭局勢,聞一多并不悲觀。他蓄起胡須,聲明抗戰不勝,他便不剃須。但戰時民生的艱難,卻讓他飽受煎熬。物價一漲再漲,當時家里8口人,靠祖父的薪水生活,只能對付半個月。他想了各種法子,帶孩子們去河溝里撈小魚小蝦打牙祭、替人治印取些潤筆費貼補家用,到后來,還經人介紹到昆華中學兼課。當時,西南聯大很多教授,錢都不夠花,日子一樣過得清苦。
由于通脹驚人,生活所需商品價格飛漲,錢不斷貶值,1945年初,祖父將自己刻章的潤例漲為1000元每字。我大伯聞立鶴(長子)責問祖父,這不是發國難財嗎?聞一多沉默了一會回答他:“立鶴,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著。”
抗戰勝利后,以聞一多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希望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1945年至1946年,國民政府迫于美國壓力,終于同意與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共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 天津南開——近代中國最早的私立大學,首遭戰爭催折,接著國立北大、清華,亦難逃劫運。三校遂先約會于湖南長沙臨大,繼被迫流徙云南。1938年,昆明建起了一個臨時聯合學府——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祖父得知消息,十分高興,在和吳晗喝茶聊天時,他認為中國政治有了希望,自己終于可以重回書齋做些純粹的學問。政治畢竟不是他的志業。之前因為無人問政,所以他站出來;現在有人問政,他認為自己就可以回去做研究了。然而內戰爆發,使他的希望破滅了。
1946年,聞一多在昆明街頭被暗殺,成為我們一家人心中無法抹去的傷痕。7月11日,民盟負責人李公樸在昆明遇害,作為同志和朋友,聞一多悲憤欲絕,祖父15日出席了李公樸先生殉難經過報告大會,公開活動譴責國民黨暴行。
其實,當時的政治氣氛已經非常緊張,全家人也非常擔心祖父的人身安全。有一天夜里,家人都已睡下,突然聽到外面有人拍門,一個學生在門外說:“聞先生,最近一段時間請你盡量不要外出。內部有消息說,你是他們的第二號目標,千萬要當心。”第二天晚上,又有人來報警,讓家人的擔憂達到了頂點。
我祖母高孝貞是家庭婦女,對于外間的情況了解不多,但也知道形勢非常惡劣。她有心臟病,那段時間更是提心吊膽。但祖父不以為意,一方面,他有他的天真,低估了對手的殘忍;另一方面,他骨子里詩人的浪漫讓他對生死看得不那么重。
本來那幾天祖父出入都有人護送。但15日下午,他到府甬道的民主周刊社參加記者招待會,離家非常近。下午17點會議結束,參會者陸續離開,早早等候在外的我大伯聞立鶴接到父親,一同往家走去。
那是夏天,7月份昆明的天很亮,回我們家的那條路,不是很繁華但也不偏僻,平時路上也都有行人經過,誰能想到會在這時候出事呢。在離家只有十幾步的地方,槍聲響了,祖父的頭部、胸部、手腕都中了槍。大伯試圖用身體保護父親,他的肺部被子彈打穿了。
在外敵入侵、硝煙彌漫的危難之時,在師生以“跑警報”為常課的惡劣環境中,西南聯大繼承并發揚了五四運動的光榮傳統,形成了這所大學最寶貴的精神支柱——愛國主義。
我父親聞立雕和祖母、兩個妹妹沖出門,祖父和大伯都躺在大街上了。大家急著把他們送往云南大學醫院急救。我姑姑(聞銘)當時在場,她很不愿意提這事,說一次傷心一次:“我看著爸爸的嘴唇,由鮮紅變成深紅,再變成黑色;初時眼睛還能動,逐漸不行了。”
祖父去世后,除了奶奶高孝貞,我們一大家人在家里很長時間里,聊天的時候都不談起祖父,怕祖母傷心難過。我們家里人后來提到祖父,講的也大多是一些生活小事。比如小的時候,一家人一塊吃飯,我奶奶會突然插一句“今兒這菜呀,做得淡了。要是你爺爺在,他得擱一碟鹽在邊上。喝咖啡要加兩份糖,吃飯要蘸鹽;剛回國的時候,他還把我們家屋子涂成黑的……”我祖父性格當中有某種比較極端的東西在,所以他好沖動,個性比較強。如果不是這樣,在那個時候站出來的可能就不是他。
我搜集、發現的祖父的這些新材料,遠遠超出了人們對聞一多的一般認知。1994年,我編著的《聞一多年譜長編》首次出版,很快成為海內外聞一多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西南聯大研究與現代中國
我想從歷史的角度,回顧一下西南聯大的研究狀況。
西南聯大,我們到現在都稱它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座豐碑。我自己認為,它不僅僅是現代教育史,而且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座豐碑。因為它的成就,遠遠超過了教育本身,有很多方面的造就。
在外敵入侵、硝煙彌漫的危難之時,在師生以“跑警報”為常課的惡劣環境中,西南聯大繼承并發揚了五四運動的光榮傳統,形成了這所大學最寶貴的精神支柱——愛國主義,譜寫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筑就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一座永久的精神豐碑。
我們最早寫西南聯大,不是寫西南聯大的教育,而是寫西南聯大的政治,一二九運動,反對蔣介石,反對內戰。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從政治史、統戰史的角度,寫西南聯大。后來慢慢才轉化到愛國史、教育史、文學史、科技史等角度,對西南聯大的功能和歷史作用,全方位地進行審視和研究。
西南聯大在短短八年六個月里,作為一所戰時高等學府,師生們懷著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心,忍耐著難以想象的困苦,以堅毅剛卓的精神履行了教育救國、讀書報國的職責。學校的根本職責是教育,這個教育落實在行動上,就是老師要教好書,學生要讀好書。
在當時戰火不絕、兵荒馬亂、艱難困苦的年代里,西南聯大的師生,展示了心系國家、民族前途的時代新人情懷,他們的心胸到底是什么?特別是和今天的環境對照,西南聯大這段歷史,還有哪些層面的價值?我覺得還是有很多價值的,既有傳統文化的延續,也有精神價值,表現了天下興旺匹夫有責的知識分子擔當,對今天的教育發展,也有很大的啟發。

重走當年路。
西南聯大很多歷史事件,其實和學校的教育沒有關系,而是和當時的國家遭遇,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民族的存亡有關。因為當時我們國家抗戰時期的最高國策是抗戰建國。我們今天只講抗戰,不講建國。實際上這兩個字是分不開的,抗戰不過是建國的一個部分。最高目的是建設新中國。恰恰這一方面,西南聯大在建國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本人是搞政治史研究的,我比較關注西南聯大對中國政治建設的貢獻。我覺得,西南聯大那段歷史的研究,其實某種角度進入、探索了學術教育界推動抗戰建國的途徑,這方面有很多實踐和摸索。
我有一本書,書名是《西南聯大與現代中國》,五年前就寫完了,后來因為作為國家學術資助項目,又讓我補充了一些東西,全書大概80萬字。我認為,西南聯大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可歌可泣的一頁,而且它是中華民族優秀遺產濃重一筆。能列入優秀遺產的就是我們要繼承的,要發揚要弘揚的精神文化遺產。
如今,西南聯大的歷史地位和巨大作用,我們都知道了。但是很可惜,我們中國國內的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對于西南聯大這么一個特殊時期形成的特殊文化群體,在那個特殊環境里所作出的特殊貢獻,對西南聯大的認知也要晚于國外。
我們的國內學者晚于日本和美國的學者。很多人接觸西南聯大,都是從美國易社強寫的那本《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開始的。其實那本書寫作時間是上世紀80年代,差不多和我同一時期開始。當時我做聞一多資料收集,他做西南聯大的資料收集,因為種種原因,最后出版的時候,因為有幾張照片有敏感問題,出版社認為要刪,易社強不肯刪,一直拖到1998年,才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
比易社強這本書出得還早一年,是日本同志社大學教授楠原俊代的《日中戰爭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研究》。這本書我拿回來以后,給了云南師大,請他們翻譯。因為各種原因,到今天為止這本書也沒有翻譯出來,很可惜。很多人不知道這本書,實際上這本書是專題研究西南聯大的,日本人做學問是很講究資料的,全部都是有史有據,很嚴謹。
還有一個人,早稻田大學的名譽教授安藤彥太郎,對西南聯大也非常關注,早稻田大學退休之后,到日中學院當院長(中國和日本在日本合辦的最高的語言學校,里面還有會館,中國好多學校外訪團之后住的就是日中學院,我就在里面住了好幾年)。他當院長的時候,出了一本雜志,從1996年4月份開始一直到2003年5月,在日中學院學報上連載了65篇“抗日戰爭與中國大學—西南聯大物語”。他本來準備編一本書出版,可他后來得尿毒癥去世了。他的學生小林,把文章搜到一起,印了120冊,送給了我一本,我轉送給了云南師大圖書館。
這幾個國外的學者,對西南聯大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我們應該利用國外的成果,應該去思考:為什么這些學者要把目光對準西南聯大。
反觀國內的研究,對西南聯大研究是分階段性的。西南聯大的研究有兩種趨勢,一種渠道是以西南聯大為教育的研究參照物,進行一些教育的思想反思,以史寓今,比如廈門大學的謝泳教授,他的一些文章,社會影響很大,對中國的西南聯大的普及,起到了開拓作用。
再一種就是按照學術研究的方法,在歷史書中發現西南聯大的價值,按照史學方法進行專題考察,然后進行綜合研究。比如我,寫歷史研究的文章要比謝泳早,但是我的文章發表在專業的學術刊物上,沒有什么社會影響,讀者大眾不會看你的學術文章。
在國內真正為西南聯大學術研究做鋪墊工作的是西南聯大校友會。1984年,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編輯發行了《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剪輯》,每年兩期,一直持續到現在。1996年,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策劃出版了第一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2006年修訂版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北大、清華、南開、云南師大合編了六卷本的西南聯大史料。

借助電視劇、文旅線路,還有作家們的精彩文章的傳播和影響,西南聯大這段歷史,它的精神價值,能夠進一步地深入人心,得到充分的學術研究,被全世界發現和看見。
上述的著作和現在這些資料,是我們現在研究西南聯大最直接的基礎。這些東西是歷史研究,而不是故事。我們現在好多作家認識西南聯大,是看那些故事書,一些東拼西湊的資料,其實有很多問題,不夠真實。那些書作為文學作品可以讀,作為史學作品不行。
由于這些出版物,以及后來陸陸續續出版的西南聯大校友的日記,包括鄭天挺先生的日記,以及各種媒體對校友的訪談、報道,推動了西南聯大的專題研究。
就大眾層面來說,對西南聯大的了解,還相當大的程度上受一些作家創作的影響,停留在一些片段的敘事、人物的命運等方面。而對西南聯大的歷史地位,西南聯大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代表性的價值,特別是對今天具有哪些啟迪的意義,研究宣傳得都不夠。
重走西南聯大西遷之路
我相信隨著《戰火中的青春》(注:由云南省委宣傳部、騰訊影業、潤禾傳媒、優酷聯手打造的電視劇,依托西南聯大這段真實的歷史而改編)的播出,包括疫情結束以后“西南聯大文旅線路”的重啟,借助電視劇、文旅線路,還有作家們的精彩文章的傳播和影響,西南聯大這段歷史,它的精神價值,能夠進一步地深入人心,得到充分的學術研究,被全世界發現和看見。
作為《戰火中的青春》和“西南聯大影旅線路”的學術顧問,我很高興參加這次“重走西南聯大之路”的文化考察活動,也很高興參加電視劇《戰火中的青春》的學術研討會。
我是在醫院的床上,把整個電視劇都看完了。電視劇里的那些畫面和場景,作為一輩子研究西南聯大的學者,我太熟悉了,所以很感動。
在我眼里,《戰火中的青春》的價值追求,始終貫穿了“教育救國、讀書救國”這一個主線。我也很贊同劇中編導處理聞一多這個人物的辦法。聞一多的經歷,特別是他最后的演講,因為進入了中學課本,早已是人們熟悉的歷史事件。在《戰火中的青春》中,這個歷史情節的處理,非常有深度,真實歷史和歷史虛構結合得很合理。聞一多參加李公樸追悼會進場時,遇到他早年教過的一個學生,暗示他有危險,但聞一多根本不在乎,聞一多的整個精神狀態顯示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正氣。他的最后演講及被暗殺,劇中依據歷史真相,充分還原了當年的現實場景,讓觀眾感受到了黑暗中聞一多的大義凜然。
2020年10月底,我和國內一些著名的作家、媒體人,一起“重返西南聯大”,進行文化采風,沿著西南聯大當年的西遷之路,深入歷史現場,查閱史料,生產了許多動人的文章。
西南聯大主題旅游路線的1.0版本,是從昆明到蒙自建水,重走當年學子求學之路,串聯聯大師生的生活地點、影視劇核心取景地,包括西南聯大昆明及蒙自分校、碧色寨火車站等網紅打卡點,旅游體驗和歷史并重。
我對“西南聯大”旅游線路的規劃有過思考。但是,我不是從旅游的角度出發,我是從文化的角度和教育的角度來思考的。旅游是一種娛樂性的休閑旅游,我們現在這個旅游是愛國主義的紅色旅游。弘揚愛國主義和紅色旅游有各種各樣的版本,但屬于教育、屬于文化、屬于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旅游沒有,所以這一條西南聯大的歷史文旅線路是獨一份,是非常有社會價值和精神文明價值的。
回想這次的旅行,我覺得非常有意義,還是很震撼。雖然大部分景點我都去過,而且走過不止一遍。當年我走過貴陽到昆明這條路,那會兒還是土路,現在已經有高速公路了,部分線路還有了高鐵。想起我祖父聞一多和聯大師生,他們是冒著戰火的危險,兵荒馬亂的歲月,花那么漫長的時間,靠雙腳走全部的路程!雖然我們走的是同一條路,時空不同,隔著漫長的歲月,當路過一個熟悉的地名牌子,史書上的歷史記載與今天的現實,歷史老照片和我眼前的場景對照,這樣的對比,使我內心有無限感慨,憶古思今,特別激動。
我想對西南聯大這段歷史來說,文化旅游也應該有不同的版本,一個是像我們這樣的行走,從北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出發,搬遷到長沙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再到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從長沙搬遷到云南的昆明和自貢,這樣原汁原味的文旅完整版。
另外,也應該有區域版,比如云南的昆明、蒙自這條線,長沙的這條線,這樣的簡易版線路,可以作為愛國主義教育一部分,和當地的文旅局、文物局、教育局合作,納入到當地的中小學生的春游、秋游線路里。
比如說現在很流行考察研學,那我們要怎么做?首先要構建一個課程體系,這個體系不僅要針對中小學生,還有針對大學生、研究生的游學體系,它該如何設置,這都是需要考慮的。
不管完整版還是區域的簡易版的文旅線路,我們要把西南聯大的故事和愛國精神,通過學者和作家們的參與,生動地再現出來,把這些全程或者一段一段的線路,進行大眾化的傳播。

電視劇《戰火中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