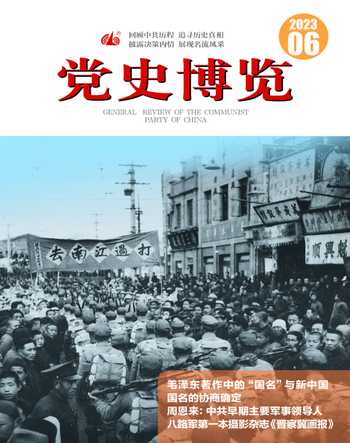毛澤東關心圖書撰寫和出版往事
曾珺

1940年9月5日,毛澤東寫給范文瀾的書信
毛澤東一生樂于書事。他愛書如命,手不釋卷。在人際交往中,但凡得知有關別人圖書撰寫或者出版的事情,他總是非常熱心,或協助審改書稿,或為其題寫序言,或幫助解決困難。本文選取幾則故事,以饗讀者。
關心《中國經學史的演變》的寫作:“倘能寫出來,必有大益”
在近現代歷史學家中,毛澤東和范文瀾的接觸是比較多的。范文瀾,字仲云,1893年11月15日生于浙江紹興一個書香門第,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文預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國學門,受業于著名學者黃侃、陳漢章和劉師培。畢業后,他先后執教于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大學、輔仁大學等。1940年夏,范文瀾到達延安,任延安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
1940年9月,范文瀾在延安新哲學年會上講授《中國經學史的演變》。毛澤東在百忙之中去聽了兩次課,并索要了范文瀾的演講提綱。第三次因病未到,毛澤東在事后給范文瀾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文瀾同志:
提綱讀了,十分高興,倘能寫出來,必有大益,因為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因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你的歷史學工作繼續下去,對這一斗爭必有大的影響。第三次講演因病沒有聽到,不知對康、梁、章、胡(指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胡適)的錯誤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吳虞、葉德輝等人否?越對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學術界發生影響。
我對歷史完全無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學得一點,深為幸事。致以敬禮!
毛澤東
九月五日
后來,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范文瀾又將提綱整理出來,以《中國經學史的演變》為題,于1941年發表在延安的《中國文化》雜志第二卷第二、三期上。
1941年初,毛澤東又委托范文瀾等人編寫一本《文化課本》,供工農干部提高文化素質之用。1942年初,這本書出版時,毛澤東題寫了序言。序言說:“一個革命干部,必須能看能寫,又有豐富的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以為從事工作的基礎與學習理論的基礎,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論也才有學好的希望。沒有這個基礎,就是說不識字,不能看,不能寫,其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限于直觀見聞的范圍,這樣的人,雖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雖然也能學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學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有大批精明忠實但缺乏文化基礎的干部,他們急切需要解決文化基礎問題,但課本問題遲遲沒有解決。現在文化課本出版了,這是一大勝利,這是凱豐、徐特立、范文瀾諸同志的功勞。不管課本內容還須隨時改正缺點,推陳出新,但有了這個課本,就打開了學習文化的大門。文化課本的出版,是廣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們大群的干部會以極大的熱忱來歡迎這個課本的。”
關心《中國大辭典》編撰工作:“所提大辭典處各點均可同意”
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有一位名叫黎錦熙的老師。黎錦熙,字邵西,又名鵬飛,1890年2月2日生于湖南省湘潭縣曉霧鎮石潭壩,早年執教于湖南長沙一些學校,后到北京任職。
黎錦熙長期從事文字研究和改革工作。1932年,他和錢玄同共任總編纂,開始編寫《中國大辭典》。黎錦熙等原本設想到1948年結束全部工作,但由于當時國內戰事頻繁,最終半途而廢。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大辭典》的編纂工作得以再續。時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的黎錦熙兼任了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總主任。1950年5月17日,他致信毛澤東,對自己一年來的工作進行了匯報,并對編纂工作存在的困難進行了客觀陳述。
毛澤東仔細閱讀了這封信,并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機構歸屬、人員編制以及辭書編輯事業合理發展的建議等重點部分做了標注。隨后,他將信中所提的意見反映給胡喬木。五天后,毛澤東復信黎錦熙。信中說:
邵西先生:
五月十七日惠書敬悉。所提大辭典處各點均可同意。并和胡喬木同志說了,他也同意。請用電話和胡同志接洽為荷。
順祝
健康
毛澤東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對黎錦熙的來信作出回復,足見他對《中國大辭典》編寫工作的重視。其實,不只是《中國大辭典》,包括對后來的《辭海》和《辭源》的編撰工作,毛澤東也是十分關心,多次作出批示。
為《瞿秋白文集》題詞并附信:“寫了幾句話,不知可用否”
瞿秋白是繼陳獨秀之后中國共產黨第二任最高領導人。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6月就義,年僅36歲。
在瞿秋白生平思想研究領域,學界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雖然中共中央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瞿秋白作出了“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的評價,但很多學者還是認為瞿秋白在獄中寫的《多余的話》和一些舊體詩證明了他當時有叛變之嫌。自瞿秋白犧牲后,他的妻子楊之華開始陸續撰寫一些紀念他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楊之華提供了大量有關瞿秋白生平思想的第一手資料,堅決捍衛瞿秋白的英名。
1950年10月,魯迅著作編刊社在上海成立,馮雪峰擔任總負責。不久,楊之華通過他將上海地下黨保留下來的瞿秋白手稿上交黨中央。馮雪峰覺得這批手稿非常有價值,經中央同意,準備編輯一套《瞿秋白文集》。楊之華非常贊同這種做法,隨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他能為文集寫幾句話。
12月31日,毛澤東為文集題了詞,并給楊之華回了信。信中說:
之華同志:
來信收到。瞿秋白同志文集出版,甚好。寫了幾句話,不知可用否?此復,順祝
健康
毛澤東
十二月卅一日
寫畢,毛澤東在信封上工整地寫了“中華全國總工會楊之華同志”,落款為“毛寄”。
毛澤東為文集的題詞是: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并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愿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遺集的出版,將有益于青年們,有益于人民的事業,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面。
毛澤東
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雖然毛澤東在題詞中對瞿秋白作出了重要評價,但中央覺得,在對瞿秋白評價爭論如此激烈的情況下,此篇序文以暫不發表為宜。另外,在編寫文集時,關于政治方面的文稿暫時不要出版。因此,在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四冊八卷的《瞿秋白文集》中,只收錄了他在文學方面的手稿,毛澤東的題詞也沒有刊發。后來,由于種種原因,《瞿秋白文集》全套的出版工作便中斷了。
粉碎“四人幫”后,中共中央作出了為瞿秋白平反的決定。在1980年召開的瞿秋白就義45周年紀念會上,中央決定,由溫濟澤和周揚負責,繼續整理和出版包括政治理論著作在內的《瞿秋白文集》。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的題詞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1985年3月8日,這幅題詞以《毛澤東同志為瞿秋白同志遺著出版的題辭》為名首次發表在雙月刊《人物》第二期上。題目下面還加寫了這樣一句話:“毛澤東的這個題辭,原存中央檔案館,現在已收入人民出版社正在排印的《瞿秋白選集》。”

1950年12月31日,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題詞
為李達審改《〈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希望你多多寫些文章”
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一位名叫李達的代表。李達,號鶴鳴,1890年10月2日生于湖南零陵,是黨內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新中國成立后,他把研究和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學術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來做。
研究和宣傳毛澤東思想,首先要從掌握毛澤東的相關著作開始。李達根據自己的學術特長,對毛澤東的重點著作進行了解讀,發表了大量文章和著作,為毛澤東思想在全國范圍內的宣傳作了理論準備和指導。在這些文章和著作中,以《〈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以下簡稱“兩論解說”)最具代表性。
《實踐論》和《矛盾論》(以下簡稱“兩論”)寫作于1937年,是抗戰初期毛澤東為紅軍大學(后更名為“抗日軍政大學”)講授哲學課的提綱《唯物辯證論(講授提綱)》中的兩部分。其中,《實踐論》為第二章第十一節,《矛盾論》(原名《矛盾統一法則》)為第三章第一節。新中國成立后,出于編輯《毛澤東選集》的需要,毛澤東先后對“兩論”作了重要修改,并提前在蘇聯《真理報》和《人民日報》上發表,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反響。
1950年底,毛澤東的《實踐論》重新發表。1951年3月,李達在寫完《〈實踐論〉解說》(第二部分)后,將書稿寄送毛澤東審讀。在書稿中,他不同意毛澤東把太平天國和義和團放在一起,將他們都看作排外主義的典型例子。李達的理由是:太平天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但并不一概反對外國人。為此,他專門致信毛澤東闡釋這種觀點。1951年3月27日,毛澤東回信說:
鶴鳴兄:
兩次來信及附來《〈實踐論〉解說》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謝謝您!《解說》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這個《解說》極好,對于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寫完并發表之后,應當出一單行本,以廣流傳。第二部分中論帝國主義和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那兩頁上有一點小的修改,請加斟酌。如已發表,則在印單行本時修改好了。
關于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寫些文章。順致
敬意!
毛澤東
三月二十七日
寫畢,毛澤東又補充了一句修改意見:“《實踐論》中將太平天國放在排外主義一起說不妥,出選集時擬加修改,此處暫仍照原。”可見,毛澤東在這里是贊同李達的觀點的。毛澤東在信中提到的修改部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在《解說》中談到中國人民對列強作排外主義的自發斗爭的地方,加寫了這樣一句話:“中國人民那時還不知道應當把外國的政府和人民、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和農民加以區別,我們應當反對侵略中國的外國地主資本家和政府官員,他們是帝國主義者,而在宣傳上爭取外國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國人都是壞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說》中談到孫中山當年所倡導的民族主義完全以清政府為對象,從未提起過反帝國主義的地方,加寫了這樣一句話:“雖然辛亥革命實際上起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作用,因為推翻了帝國主義的走狗——滿清政府,當然就帶著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國主義對于辛亥革命的不滿,不幫助孫中山而幫助袁世凱;但是當時的革命黨人的主觀上并沒有認識這一點。”(三)《解說》中談到“唯物論的‘唯理論是今日教條主義的來源,唯物論的‘經驗論是今日經驗主義的來源”。毛澤東把這句話修改為:“唯物論的‘唯理論與今日教條主義相像,唯物論的‘經驗論則與今日經驗主義相像。”
1952年4月,毛澤東的《矛盾論》重新發表。從這年7月開始,李達又以新的熱情投入到《〈矛盾論〉解說》的寫作中。9月17日,毛澤東再次復信李達,對為愛晚亭題寫亭名和寫作指導工作進行答復。信中說:
鶴鳴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幾信也都收到了。愛晚亭三字已照寫如另紙。
《矛盾論》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無論什么矛盾,也無論在什么時候,矛盾著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這里“也無論在什么時候”八字應刪,在選集第一卷第二版時,已將這八個字刪去。你寫解說時,請加注意為盼!
順候
教安
毛澤東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正是充分吸收了毛澤東提出的意見,“兩論解說”的寫作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需要重新對毛澤東思想進行歷史定位。“兩論解說”作為準確闡釋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代表作,于1978年4月后又歷經三次印刷。人民出版社還在1979年出版了合訂本,發行量達10萬冊。“兩論解說”采取對原著逐段解說的方式,運用歷史、哲學、自然科學和人類斗爭的經驗材料,以通俗易懂的語言詳細而準確地闡釋了毛澤東關于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哲學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理論方法,首開新中國系統宣傳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先河。
請人審看《六十年的變遷》:“請你指定一位水平較高同志看一看這部書”
《六十年的變遷》的作者是李六如。李六如,1887年7月11日生于湖南平江縣一個商人家庭,1908年到湖北參加新軍,加入同盟會。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進入日本東京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科。1918年回國變賣家產,創辦救貧工廠,進行實業救國嘗試。失敗后,又興辦平民學校,走教育救國之路。1921年秋,在毛澤東介紹下,李六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10月,李六如抵達延安,后任毛澤東主席辦公室秘書長。
1954年9月退休后,李六如著手寫作三卷巨著——《六十年的變遷》,反映從清末至新中國成立的歷史。在寫作過程中,李六如并不滿足于對這些歷史事件的所見所聞,還深入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同鄉親們親切交談,收集了大量關于毛澤東、毛澤民、何叔衡等人的革命史料,為創作提供了鮮活的素材。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六十年的變遷》第一卷脫稿。李六如打印了若干份,送請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審閱,還請范文瀾、呂振羽等歷史學家指正。
毛澤東認真閱看后,將書稿批轉給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林默涵審閱。林默涵看后,認為這是一部很好的歷史小說,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該卷。《六十年的變遷》實際上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小說主人公季交恕,是個滿懷救國救民理想的熱血青年。在歷盡種種磨難后,他最終認識到只有匯入人民解放事業的洪流中才能真正救中國的道理。這與李六如的人生經歷有異曲同工之處。小說發表后,一時間城鄉爭相購買,出版社不得已一版再版。此后,該書又被翻譯成英文、俄文、日文等幾種版本發行。
1959年初,李六如開始了第二卷的寫作。完成草稿后,他呈送給毛澤東審閱,并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茲將我所寫小說《六十年的變遷》第二卷草稿送請審閱,如若無暇,擬請指定一位秘書同志看看后半部和140—147、273—278這十來頁。并懇指示。”長篇歷史小說《六十年的變遷》第二卷從北洋軍閥統治開始寫到大革命失敗,信中請求審閱的,主要是該卷中有關毛澤東的部分內容。10月6日,毛澤東將草稿批轉給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審閱,同時寫下批語:
定一同志:
請你指定一位水平較高同志看一看這部書,如何?
毛澤東
十月六日
收到毛澤東的指示后,陸定一迅速組織人力審閱這部稿件,并將意見及時反饋給了李六如。李六如根據這些意見進行了認真的修改。1961年,第二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正當李六如滿懷信心開始第三卷的寫作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當年擔任毛主席辦公室秘書長時,李六如就因為不肯順從江青而得罪過她。江青等人利用這個機會,對這位時年已經70多歲高齡的老者進行了殘酷的批斗。1973年4月10日,僅完成第三卷8600字寫作任務的李六如帶著一生的遺憾離開了人世,終年86歲。
粉碎“四人幫”后,中共中央為李六如平反昭雪。他的《六十年的變遷》第一、二卷連同第三卷的部分手稿被列為當代文學經典叢書,于200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
關心《柳文指要》的寫作:“已經讀過一遍,還想讀一遍”
《柳文指要》的作者是我國現代著名學者、教育家、愛國人士章士釗。章士釗,字行嚴,1881年3月生于湖南善化。20世紀20年代初,在湖南長沙時,因與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是至交,故他也早與毛澤東相識,交情甚篤。新中國成立后,章士釗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等職。
章士釗酷愛唐代文學家柳宗元的文章,13歲時就開始讀柳文。1960年,章士釗開始著手撰寫《柳文指要》,至1965年初完成上、下部共近100萬字的初稿。毛澤東對章士釗寫作《柳文指要》一事頗為關心,多次索要書稿閱看,并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見。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派人給章士釗送去桃杏各5斤,并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行嚴先生:
大作收到,義正詞嚴,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納為盼!投報相反,尚乞諒解。含之(指章含之,章士釗的養女——引者注)同志身體如何?附此向她問好,望她努力奮斗,有所益進。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信中“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一句出自《詩經·衛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這是一首寫人們互贈禮物表達情意的詩。你贈給我果子,我回贈你美玉,很顯然,回報的東西要比受贈的東西價值大得多。這是人類高尚情感的一種體現,這種情感是人們精神上的契合、心靈上的共鳴,而不是一種等價交換。所以說“匪報也”。在信中,毛澤東把《柳文指要》比作“瓊瑤”,把自己送給章士釗的桃杏各五斤看作對章士釗不平等的交換,認為此舉是對《詩經》中“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的反解,“投報相反”之處,請他“尚乞諒解”。以桃杏各五斤換讀章士釗的《柳文指要》,也算一大趣事吧。
實際上,毛澤東對《柳文指要》的關注絕不是“投報相反”。就在這封信發出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毛澤東又讀完了書稿的下部,隨即又給章士釗寫了一封信:
行嚴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經讀過一遍,還想讀一遍。上部也還想再讀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讀。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斗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后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掘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來。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毛澤東的這封信,提出了他對《柳文指要》書稿的修改意見,給章士釗很大的啟迪。信中提到的“另有友人”,指的是當時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

毛澤東在寫作
康生曾明確反對出版《柳文指要》。早在1963年3月,章士釗曾將寫出的40多萬字書稿交付中華書局征求意見。總編輯不敢擅自做主,就打報告請示文化部和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又請示康生,康生批示說:“我認為中華書局不應該給章出此書。如同意,請告中華書局。”又說:“如章問,可直接告他,書中有許多錯誤觀點,并企圖為他過去的丑惡翻案,進而宣傳自己。我們的紙張不夠,為什么給他出這樣一部四十余萬言的書?即使沒有或刪去那些反動論點,也不必出。因為:(1)如果從哲學史思想史角度上研究柳文,沒有馬列主義觀點是不會得出正確結論的;(2)如當作材料來出,專家會去看原文。”
中華書局總編輯接到這個批件后,將稿件退給了章士釗。這件事情,毛澤東是知道的。事隔兩年之后,1965年8月5日,毛澤東想幫助老朋友再次出書時,便將書稿送給康生看,并寫了一封信與他溝通。信中說:“章士釗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兩部,二十二本,約百萬言,無事時可續續看去,頗有新義引人入勝之處。大抵揚柳抑韓,翻二王、八司馬之冤案,這是不錯的。又辟桐城而頌陽湖,譏帖括而尊古義,亦有可取之處。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觀,于文、史、哲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觀點解柳(此書可謂《解柳全書》),他日可能引起歷史學家用唯物史觀對此書作批判。如有此舉,亦是好事。此點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預作精神準備,也不要求八十五齡之老先生改變他的世界觀。”
看到毛澤東極力推崇《柳文指要》,康生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在12月5日給毛澤東的復信中說:“八十五歲的老先生,尚有精力做此百萬巨著,真非易事。我讀完之后,覺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對此書的評價,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確的。此書翻永貞政變之案,申二王八司馬之冤,揚柳子厚‘以民為主的思想,斥韓退之‘以民為仇的謬論,確有新義引人入勝之處。當然,正如主席信中所說,此書也有缺點,如著者不能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解釋柳文,對柳宗元這個歷史人物缺乏階級分析,對社會進化,以為‘承新仍返諸舊,‘新舊如環,因成進化必然之理等等,但這些對于一個沒有研究馬列主義的人,是可以理解的。”
1966年1月12日,毛澤東再次致信章士釗。信中說:
行嚴先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惠書及附件均已收讀,極為感謝!三國志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紀念,便時乞代致謝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讀完交來,茲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見,是否妥當,請酌定。
順頌
春安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寫畢,毛澤東又附注說:“附件兩紙,另康生同志來信一件,均附上。又及。”
正是由于毛澤東的關心和他與章士釗之間的特殊感情,《柳文指要》才得以在1971年9月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卻了章士釗多年的一樁心愿。他激動地買了上百冊,親筆題字送給毛澤東、周恩來和他的朋友們。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周恩來還送他一部《柳文指要》作為紀念,并特意解釋說,這本書是在毛澤東主席的關懷下才得以公開出版的。
支持完成《李自成》的寫作:“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
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是毛澤東非常喜歡的一位歷史人物。早在韶山讀私塾時,他愛看的“雜書”里面,就有關于李自成的書。對有關李自成的文學作品,毛澤東也非常關注。1930年,民間作家李健侯寫成了一部近35萬字的章回體歷史小說《永昌演義》。1944年,毛澤東讀后給李健侯的同鄉李鼎銘寫了一封信,稱贊該書,并將該書抄錄了一部以備后用。
從1957年開始,著名作家姚雪垠也開始著手寫作一部名為《李自成》的長篇小說。反右傾運動開始后,姚雪垠被劃為“右派”,發配到武漢東西湖農場種地。他克服了重重困難,到1958年8月,完成了《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一部分的寫作。1963年8月,第一卷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出于對毛澤東的崇敬之情,姚雪垠還寄送了一本簽名書給毛澤東。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白話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廣受好評。但“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對這本書的批判也隨之升級,有人批判這本書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攻擊姚雪垠和《李自成》的大字報更是鋪天蓋地。
毛澤東也認真地看了《李自成》,認為這是一部非常好的書。1966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委托中南局第二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轉達武漢市委,要對姚雪垠予以保護,讓他繼續寫下去。由于毛澤東的關心,姚雪垠得以免受批斗之苦,他的《李自成》原稿以及收藏的大量資料也幸免于難。后來,每當回憶起這件事情的時候,姚雪垠總是感慨地說,“我在最危險的時候得救了”,“這是毛主席的指示產生了巨大作用”。
1974年春夏之交,國內形勢變得更糟糕了。“四人幫”在全國范圍內大搞“批林批孔”,鬧得烏煙瘴氣。姚雪垠的創作權也被變相剝奪了。此時,湖北省委、武漢市委也被奪了權。姚雪垠覺得,要想將《李自成》繼續寫下去,只能致信毛澤東求助了。但他又擔心:信如何才能送到毛主席手中呢?
姚雪垠試探著給曾任武漢市委文教書記、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工作的宋一平寫了一封信,尋求幫助。收到信后,宋一平立即同胡喬木、鄧力群等人進行商討,并很快給姚雪垠回了信,同意姚雪垠給毛澤東寫信的想法,答應負責托人直接呈送到毛澤東手中。
接到信后的姚雪垠興奮不已,立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匯報了他的寫作情況,以及目前的困難。
宋一平接到信后,請胡喬木代為轉交。為示重視,胡喬木還專門就此事寫了一份報告,于1975年10月23日一并呈送給毛澤東。報告寫道:
主席:
送上長篇小說《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由武漢寫給您的一封信。姚在信里說,這部小說他擬寫成五卷約三百萬字,第一卷已改好,第二卷已寫成近兩年,但還沒有地方出版,請求您給予幫助。
姚的信是宋一平同志托我轉送的。宋現在哲學社會科學部工作,以前長期在武漢,所以姚把信寄給他。宋還把姚的兩封信給我看了。因為這兩封信可以幫助了解姚目前的具體困難,所以現在也一起附上,供您需要時參閱。
敬禮
胡喬木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此時,毛澤東已患病多日,特別是眼疾嚴重。盡管這樣,他還是認真地看了姚雪垠的信,旋即在胡喬木的報告上寫下批語:
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澤東
十一月二日
在毛澤東的親切關懷下,1975年12月21日,姚雪垠從武漢來到北京,專心于書稿的寫作和修改工作。后來,姚雪垠在回憶這件事時說:“在我極端困難的環境下,毛主席第二次保護了我。”正是由于毛澤東的關心,姚雪垠終于有了獨立的寫作時間。粉碎“四人幫”后,姚雪垠的寫作進入了最后沖刺期。從1977年開始,《李自成》第二卷至第五卷陸續出版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