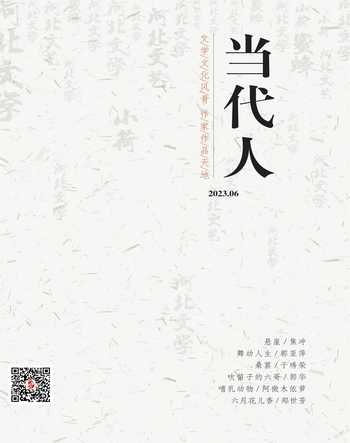短篇小說的隱喻性和爆發(fā)力
短篇小說在小說譜系中的獨(dú)特存在在于對(duì)單個(gè)場(chǎng)景的精準(zhǔn)復(fù)現(xiàn),相對(duì)于長(zhǎng)篇小說人物命運(yùn)的史詩(shī)感以及中篇小說的結(jié)構(gòu)復(fù)雜的故事性,短篇小說以“短”為標(biāo)志的主要審美特征使它在敘事中呈現(xiàn)了與其他小說截然不同的面貌,很多在長(zhǎng)篇小說或中篇小說中值得被稱道的特征,比如游離、散漫、松弛、細(xì)碎,在短篇小說中往往是致命的缺陷。短篇需要更加高效、復(fù)調(diào)的表現(xiàn)形式來實(shí)現(xiàn)自我存在,故而隱喻、爆發(fā)作為“短”的必要表征,始終是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無法繞過的核心因素。相對(duì)于按照篇幅劃分的長(zhǎng)、中篇小說,短篇小說身上似乎有這樣一種特質(zhì),即它的標(biāo)簽是被刻意制作出來的,它身上“短篇”的特質(zhì)要始終高于“小說”的特質(zhì)。
《年三十》大致上體現(xiàn)了作者對(duì)“短篇”的具體理解和審美判斷。收拾桌擺、置辦年貨、走親訪友等諸多北方農(nóng)村年下的生活場(chǎng)景在作者的筆下一一呈現(xiàn),傳統(tǒng)婚姻觀念的異化、農(nóng)村青年男女的抗?fàn)帯⒚藉议L(zhǎng)情節(jié)的崩塌在作者細(xì)膩的講述中也逐漸浮出水面,作為敘事的主要意圖映射出來,在掃秋置辦年貨及婚事彩頭中頻繁出現(xiàn)的“紅”在其中構(gòu)成了重要的象征意義。紅色在中國(guó)文化的傳統(tǒng)語境中有著極高的辨識(shí)度,收集紅色、展示紅色、分享紅色,作為中國(guó)人在年關(guān)、在婚配中必備之事,在文中已然有了別具意義的特定所指,在傳統(tǒng)的紅色表意之下,另外一層隱喻也在悄然地呈現(xiàn)。掃秋購(gòu)買“棗紅色的呢大衣”、男人購(gòu)買“紅公雞”,都因價(jià)格問題產(chǎn)生心理波動(dòng);生男生女、買賣婚姻的題外討論也都在暗中指向了時(shí)下農(nóng)村婚嫁中存在的巨大問題。紅外套、紅公雞作為小說中的兩個(gè)重要意象,從備選、購(gòu)買、處理等諸多事端都產(chǎn)生了微妙的對(duì)應(yīng),作者設(shè)計(jì)的隱喻也在其中悄然達(dá)成。
此外,未來親家的紅大門、自家門口的紅燈籠以及被衣服映得通紅的屋子等文中前前后后出現(xiàn)的十幾個(gè)“紅”的意象,也都在或多或少地渲染“紅”的場(chǎng)景。而這種“紅”在傳統(tǒng)審美中本應(yīng)具備的屬性在掃秋兒子婚事告吹之后,卻呈現(xiàn)了截然不同的景觀。蕭瑟代替了喜慶、孤獨(dú)替代了歡樂,“紅”色意象及其所指在此時(shí)顯得諷刺可笑。掃秋借親家送禮之名行婚姻買賣之實(shí)的封建行為,與置辦年貨、拜訪親友的現(xiàn)代生活間形成了巨大的錯(cuò)落感,小說的深度和沉重感于內(nèi)在的隱喻中正式產(chǎn)生。
短篇小說寫作需要隱喻春風(fēng)化雨、舉重若輕的能力,也需要“寸勁兒”。這個(gè)寸勁兒指的就是敘事中瞬間爆發(fā)的能力。在《年三十》中,任艷苓展現(xiàn)了她在短篇小說狹小的敘事空間內(nèi),將身邊生活細(xì)節(jié)、人心善變的紋理褶皺舒展,并賦予深意的能力,在她的文本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短篇小說這個(gè)文學(xué)體裁的細(xì)膩和悠遠(yuǎn)。然而在短篇的爆發(fā)力上,《年三十》卻有點(diǎn)稍顯乏力。首先,選取的生活片段在現(xiàn)實(shí)時(shí)間維度中看似較短(一個(gè)自然日的從早到晚),而在情節(jié)時(shí)間維度的鋪陳中顯得較長(zhǎng)(有枝杈的完整的事件),作者講故事的能力在兩條齟齬的時(shí)間線中難以對(duì)齊,而平鋪直敘、少于回旋的敘事方式在短篇中也顯得難以適用。其次,作者在主線敘事中沒有保持足夠克制和遮掩,隱喻的表達(dá)難以遮蓋暴露的敘事,人物的行為語言都過于按部就班。第三,散文化的敘事方式給我們帶來了簡(jiǎn)單快樂的閱讀體驗(yàn),同時(shí)也消化了小說結(jié)尾最后的波折和懸念,難以為讀者提供回味想象的空間。克制和遮掩作為一種寫作能力,在小說敘事中——尤其在短篇小說敘事中——至關(guān)重要,它們可以非常直觀地拉伸小說的敘事內(nèi)長(zhǎng),增加小說的敘事層次,短篇小說借此得以用更小的篇幅換取更大的敘事空間,它的密度、質(zhì)地,它的震撼力、沖擊力正是在其之后得以成立。《年三十》的敘事方式過于平坦、少于遮掩,足夠細(xì)膩卻不夠筋道,沒有形成“心事浩然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的爆發(fā)力和震撼感,讀罷有一種無從著力的失落感。
長(zhǎng)篇小說之所以為長(zhǎng)篇,是一種必然。因?yàn)樗枰米銐虼蟮捏w量,系統(tǒng)地認(rèn)識(shí)世界、整體地關(guān)注命運(yùn)。然而這種丈量方式在短篇小說中似乎難以成立,短篇小說的“短”更像是一種必要不充分條件——長(zhǎng)篇小說的“長(zhǎng)”一定程度上定義了自身,而短篇小說的“短”卻往往只是某種稱呼它約定俗成的方式,“長(zhǎng)”“短”的區(qū)別,更多在于手法而不是篇幅。在短篇小說緊張的敘事節(jié)奏中,文字沒有緩沖和回轉(zhuǎn)的空間,對(duì)小說家來講,這既是一種利劍懸頂?shù)恼勰ィ质且环N充滿樂趣的挑戰(zhàn)。徐則臣說,“短篇小說……就要不停推敲、打磨、刪改,直到里面的字不是趴著、躺著、坐著,而是精神抖擻地站著,短篇小說就是讓每個(gè)字都站在紙上”,即是此意。而《年三十》的遺憾,大致也在于此。或許鋪展開來,它會(huì)是一篇優(yōu)秀的中篇小說,但作為一篇短篇,《年三十》不夠驚艷。作為一名青年作家,任艷苓的小說語言和敘事細(xì)節(jié)極為工整,她隱于筆下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象的個(gè)人思考與觀照姿態(tài)有著超越年齡的成熟。《年三十》節(jié)奏舒緩、敘事平淡,雖有遺憾,但也為我們展示了另一種小說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在這種可能中,我們看得到作者未來的創(chuàng)作道路將會(huì)越走越高,越走越遠(yuǎn)。
(于梟,1989年出生,河北清苑人。文學(xué)評(píng)論作品散見于《文藝報(bào)》《文匯報(bào)》《青年文學(xué)》《河北日?qǐng)?bào)》等。)
編輯:耿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