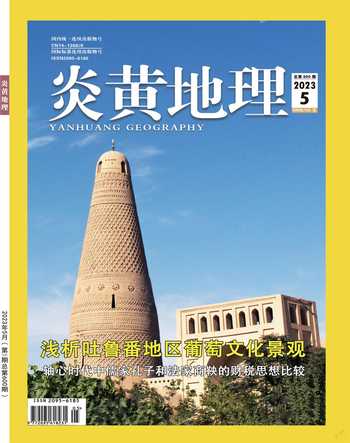南北之下:探討遼朝官制運維機制
吳怡萱
遼朝進入中原以后保留了中原官僚制度,并綜合考慮了契丹部族制度制定環節出現的各類因素,因此創新性地提出“因俗而治”的全新做法,構建了契丹部族制度和中原政治文化并行的運行模式,這種不同于以往的南北面官制度為后續民族之間的溝通與交流提供了全新的制度保障。現主要從南、北面官交流和維系的措施,南北面官的特點以及南北兩系統設置產生的效果和影響等方面對遼朝官制展開探討。
遼國是一個具有鮮明游牧民族特色的國家,同時其因包容并蓄的特點,受中原封建王朝的影響較深。為了更好地治理國家和各地區,遼朝實行了“因俗而治”的國策,采用了“藩漢分治”的南北面官制度。
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遼朝史料存留并不多,因此,學界對于遼朝職官管理制度的研究有待深入,有些成果具有開拓性,尤其是學界對遼朝選官制度的比較研究,對俸祿、致仕的探討,以及從宏觀層面探討遼朝職官管理制度等,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中古時期的職官管理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圍繞遼朝官制方面進行討論,邱靖嘉在《“超越北南”:從中樞體制看遼代官制的特性》中,從遼代宰輔群體的職銜構成及其排序,以及獨特的南北面官制度著手,側面反映出了遼朝的職官機制其實是南北政治文化的有機融合,如關鍵的中樞機制。因此,遼朝雖然提出了“因俗而治”,但南北實際體制仍然保持著一致的步伐。然而學界對于南北面官的研究常常處于割裂的狀態,在南北面官如何互相聯系和長時間地維持政權等方面未給予足夠的重視,且在機構的設置和官員選任的分析中尚未向縱深和動態平衡的方向發展,使得研究成果較少。因此,現重點研究遼朝官制運轉維系的方式,結合“因俗而治”的背景,分析南北面官的職能,探討南北面官交流和維系的措施,分析遼朝官制設置產生的效果和影響。
南北面官間的運轉
南北面官的職責與職能
考慮到受自然因素等多重發展因素的影響,中國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與漢族文化產生了較大的差異,有研究學者將少數民族的文化總結為“逐水草而居,四時遷徙”[1]。那么在特殊的民族背景下,遼朝的南北樞密院如何各司其職,妥善分工?各自的權力范圍有多大?這是學者分析研究遼朝南北面官制度的核心內容。筆者通過閱讀大量的文獻資料,整理了史料中有關遼朝樞密使職權的描述,其中,《遼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中說道[2]:
凡遼朝官,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北、南府宰相總之。
契丹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群牧之政,凡契丹軍馬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問所謂“北衙不理民”是也。
北院樞密使
知北院樞密使事
知樞密院事
北院樞密副使
知北院樞密副使事
同知北院樞密使事
簽書北樞密院事
契丹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衙不主兵”是也。
南院樞密使
知南院樞密使事
知南院樞密事
南院樞密副使
知南院樞密副使事
同知南院樞密事
簽書南樞密院事鋤
在南北面官制度下,北樞密院主要負責“兵機、武銓、群牧”之政,“兵機”是指與國家軍隊有關的各項工作;“武銓”指代朝廷選拔武職官員;“群牧”是九州治民的官長[3]。“兵民合一”很好地體現出了契丹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差異,在沒有戰亂時,契丹族仍然保持著狩獵放牧的民族習慣,原有的部落首領擔任管理民眾的行政長官;當有戰爭發生時,民眾就會拿起武器奔赴戰場,部落首領搖身一變成為軍事長官。而南樞密院主要負責“文銓、部族、丁賦”之政,主要負責管理遼朝行政機制下所有的民眾事務,“文銓”指文職官員的選拔與聘用;“部族”指代游牧的契丹等部落;“丁賦”指各個轄區內的人員及賦稅相關事務。遼朝全體民眾的稅收工作和文官的選拔任用直接由南樞密院的最高長官負責。
南北面官的合作與制衡
遼朝統治者在完善各項封建管理手段之后,漢族紳士的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是與遼朝貴族相比仍存在明顯差距,并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為南北面官制度在劃分權力時本就不平等,特別是南北面官制度的南、北樞密院,在皇權授意下成為遼朝的最高行政機關,分別實施軍事、民事的管理,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群牧之政,凡契丹軍馬皆屬焉”[4],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屬焉”[5],南北宰相府作為當時的權力中樞,一般都是在蕭氏后族和耶律皇族中篩選合適的人選;相比之下,南面官系統中的中樞職位其實并未掌握實權,只有南面京官中的三京東京、中京、南京宰相府、五京留守司、五京計司屬于實職,主要負責處理地方民政賦稅。在地方州縣職位方面,為了更好地維護地方的繁榮穩定,交由漢族士紳掌管[6]。因此從二者的合作關系方面來看,南北面官之間的合作是不平等的,雙方所擁有的職權范圍存在明顯的差異,從合作關系的視角來看,二者更像是上下級之間的關系。
耶律皇族和蕭氏后族同時參與處理朝政各項事務,形成了部落聯盟的聯合執政,打破了傳統意義上的皇權專政[7]。因為這一傳統,很多漢族官員也可以參與朝政事務。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實際爭奪權力的過程中常常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內斗和政變,而政治更多講究的是如何平衡,而非一家獨大,更不是將對手完全淘汰出局。由于漢族官員參與實際的管理,其手中的權力不斷增加,引起了契丹貴族的忌憚,所以契丹貴族采用各種手段打壓漢族官員。總而言之,南北面官之間的制衡機制無疑是成功的,一方面用漢人的立法對原部落首領進行約束,另一方面也借助漢官集團的勢力以平衡契丹貴族勢力,所以南北面官制度巧妙地借用了平衡思想,從根本上穩定了皇權。
南北面官的維系
南北面官的溝通協調
遼朝執行的南北面官制度需要南、北院樞密使為首的宰輔共同參與處理國家各項事務,這從國家的決策機制上打破了南北之間的桎梏,并最終構成了運轉流暢的領導圈層。如遼景宗時期,南院樞密使、知政事令高勛與北院樞密使蕭思溫“每朝,必命坐議國事”[8],高勛還被時人稱作“大丞相”,保寧八年《王守謙墓志》載“大丞相渤海高公保厘天邑,專總朝政”[9]。結合史料分析,在遼朝推崇的南北面官制度中,中書省與樞密院組成基本一致,領導人員及分工大致相當,可以說二者充當的角色有異曲同工之妙。中書省承襲唐代以來的中書門下之制,更多作為統治者的智囊團,不設置下屬單位,由樞密院下轄吏、兵、刑、戶、廳五房承擔各項行政管理的職能,職能分工類似于其他時期的尚書省,故《亡遼錄》稱“尚書省并入樞密院”。針對上述分析研究,學者已經達成一致的認知,在此不做贅述[10]。
南北面官的獎懲機制
南北面官制度同樣有著嚴格的獎懲機制。升遷主要是指當時的官員如果符合制度規定的升遷條件,或者是具備各類硬性要求,朝廷就可以根據貢獻的大小。升遷的種類決定是否給予升遷以及升遷幅度的大小,可以分為封爵加勛賜功臣號、晉升、減資考三種。減資考,就是結合實際情況縮短律法規定的官員考核時間,使官員在規定時限內完成升遷。統和十二年(994)六月,圣宗詔諭統一南北面官的減資考制度。重熙六年(1037),張績任燕京管內都商稅判官[11]。職官懲罰機制包括除名和免官兩種方式。所謂的除名,就是將官員從原有的名冊中刪除,類似如今的開除黨籍;免官,是指免去、奪去官職,但一般會保留爵位,罪行嚴重時才會削爵免官,如滌魯“以私取回鶻使者獺毛裘,及私取阻卜貢物,事覺,決大杖,削爵免官”[12]。大安十年(1094)六月,烏古敵烈統軍使蕭朽哥因為犯罪被除名。貶降包括降職、調任(由中央到地方)、左遷、削爵、降階等形式[13]。這幾種形式有時會兩種或多種同時使用。
綜上所述,遼朝獨創的南北面官制度本質上融合了少數民族與中原政治文化的精髓,最為明顯的體現就是南面漢族官員可兼任朝廷中樞機構官員,而這種做法在當時極富創新價值,有利于將南北兩院緊密結合,共同完成朝中大小事務。
南北面官的紀律管理
遼朝對于南北面官的紀律管理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遼朝在中央設立的考課機構有吏部和隸屬南樞密院的吏房;監察機構主要有御史臺、樞密院中丞司、殿中司等。遼朝吏部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等屬官[14]。吏部尚書一職,《遼史》中最早見載于《張礪傳》:“會同初,升翰林承旨,兼吏部尚書,從太宗伐晉。”[15]
樞密院中丞司主要負責監督朝廷官員的日常工作,為了實現高效率的分類管理,在主管部門下設置點檢中丞司事、總知中丞司事等部門,同時所有的官員必須按照朝廷規定的篩選機制進行選拔,這保證了官員來源的明確性[16]。清寧四年(1058),耶律弘世被“授守太尉、兼中書令、秦國王、判中丞司事”。在大康年間,蕭得里底“補祗候郎君,稍遷興圣宮副使,兼同知中丞司事”[17]。在對百官開展紀律管理的過程中,除了在中央全縣機構設置考課、監察機構以外,遼朝還在地方設立“司”級機構掌糾舉之任[18]。
由此可見,遼朝南北面官制度下對官員的紀律管理極為清晰,且明確了不同部門的權責范圍,設立了考核標準,對官員形成了良好的約束。
遼代南北面官特點與作用
南北面官制的特點
因俗而治——各民族生產、生活方式不變。南北面官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胡漢分治”,而是在當時社會背景影響下,考慮到國內各民族相對集中,且每個民族和地區的生產力水平處于不同的階段,因此為了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治國思想,很多少數民族均采用“胡漢分治”的方式[19],利用人為的方式割裂了與漢族之間的聯系。到了遼朝,除了部分契丹族和渤海人承擔著重要的軍事和政治要務,一般情況下不會出現強迫性的移民情況,當地的民族仍然可以居住在自己原來的生活領域,按照自己的生產生活方式開展勞作[20]。
上下一體——不僅是中央政權機構,也是地方行政體制[21]:遼朝統治者提出的南北面官制度,不僅是中央政權組織機構,還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有利于落實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行政制度,這一治國思想與其他朝代的羈縻制度存在本質上的區別。《營衛志》中描述為“遼朝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處”[22],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就是“契丹迭剌部霞瀨煙臺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23]。在遼圣宗耶律隆緒時期,隨著封建化制度的不斷發展,各個部落的首領逐漸由中央選拔,他們成為朝廷內部的重要官僚,但部落依然保留了原有的部族制度。
南北面官制度的作用
第一,遼朝皇帝針對不同類型的統治人群會展現不同的對外形象,在面對契丹族在內的各大游牧民族時,遼朝皇帝更多是以草原上的單于、可汗的形象出現;面對漢族老百姓時,他就是符合漢族儒家文化概念要求的皇帝,宣稱統治下的漢族百姓并非異族,“南北皆是中國”[24],所以遼朝境內各個民族都對當時的統治有著極強的認同感,這維護了社會局面的穩定。
第二,是否“漢化”,是很多少數民族政權在進入中原以后不得不面臨的關鍵問題,也是決定王朝未來發展的重大決策。遼朝以南北面官的形式吸收了前代的治國思想,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傳統的草原部落文化精神。
遼朝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保留地方特色的同時,制定了符合國家發展的政治制度,其中南北面官制度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正是這一制度的產生,實現了在相同范圍內兩種經濟模式的同時存在。南北面官制背后是漢族士紳和契丹貴族之間的博弈,一部遼朝史體現了漢族官員和契丹貴族之間的歷史羈絆,因此采用積極的視角審視南北面官制度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
參考文獻
[1][2][9][13][22][23][24]脫脫.遼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4][10]葉隆禮.契丹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4.
[5]歐陽修.新五代史[M].徐無黨,注.北京:中華書局,1974.
[6][7]李強.大遼帝國 阿保機的耶律家族[M].北京:中國鐵路出版社,2018.
[8]楊樹森.遼史簡編[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
[11]李紅艷.關于十六國時期“胡漢分治”問題的思考[J].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8(01):47-50.
[12]劉樹友.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國兩制”——遼朝北、南面官制述評[J].理論導刊,2005(09):95-96.
[14]任愛君.遼朝史稿[M].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12.
[15][21]鄭毅.“因俗而治”與“胡漢一體”——試論遼朝“一元兩制”的政治特色[J].黑龍江民族叢刊,2013(06):76-83.
[16]王滔韜.遼朝南面宰相制度研究[J].社會科學輯刊,2002(04):100-106.
[17]王滔韜.遼朝南面朝官體制研究[J].重慶交通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03):37-46.
[18]李根,張曉松.羈縻制與少數民族政治行政制度[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2(01):42-46.
[19]肖愛民.遼朝政治中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0]陳正奇.“一國兩制”的歷史述略[J].西安教育學院學報,2000(01):13-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