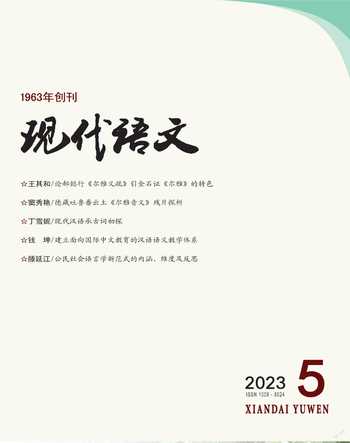現代漢語承古詞初探
丁雪妮



摘? 要:現代漢語承古詞是分歷史層次的,它們來自殷商、西周、東周等不同歷史時期。有些現代漢語承古詞自產生至今,語義一直未變;有些承古詞的語義則發生變化,這一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內部承古義與其相關的其他詞語的繁化與簡化。在現代漢語承古詞中,既有基本詞匯,也有一般詞匯。雖然基本詞匯比較穩定,但是也會出現新舊交替,有些基本詞匯還能轉化為一般詞匯,與此同時,一般詞匯也有可能會轉化為基本詞匯。
關鍵詞:承古詞;承古義;現代漢語;先秦時期;基本詞匯;一般詞匯
一、引言
王云路指出:“任何一段歷史時期的語匯不外乎兩種主要來源:一是繼承前代的語詞,一是當代的新造語詞。”[1](P72)楊端志認為:“現代漢語‘承古詞,指從古代漢語繼承來,現代漢語仍然使用的詞。換句話說,古代漢語的詞傳到現代,沒有消亡。”[2](P294)現代漢語承古詞數量龐大,學者們在詞匯研究中多有提及,但很少展開專門研究。本文擬以先秦時期產生的承古詞為例,探索現代漢語承古詞的演變規律與主要特點。楊端志指出:“我國現有文獻中,就研究漢語詞匯史來說,《漢語大詞典》是最方便最有效的一部書。《漢語大詞典》選用從先秦到現代‘反映口語的文獻三千多種,《四庫全書》所收文獻約四千種,《漢語大詞典》所用來反映漢語詞匯史的文獻,就代表性說,也夠多了。”[2](P272)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引例詞大多出自《漢語大詞典》。《漢語大詞典·凡例》云:“同一單字之下的多字條目,凡第一字讀音不同的,在右下角以阿拉伯數字標注相應單字字頭的序號。隸屬于第一字頭的不標。”[3]本文對隸屬于第一字頭的也進行標注,并在括號中注明讀音,如“乖戾1(lì)”。
總的來看,現代漢語的承古詞、承古義分別來自殷商、西周、東周等不同歷史時期。雖然很多承古詞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殷商時期,但是承古詞的產生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隨著社會和語言自身的發展,不斷補充,持續更新。也就是說,承古詞是分歷史層次的。游汝杰指出:“語言的歷史層次現象是人類語言的共性之一,并不限于漢語,不過歷史層次積壓現象的表現形式會因語言不同而有差異。”[4](P30)如果把對承古詞、承古義的研究視為考古挖掘的話,地面以上的部分是現代漢語詞語的面貌,依次一層一層往下挖掘,每一層都是不同歷史時期共時層面上詞語的面貌,最后最深的一層就是最早產生這些承古詞的那個歷史時期的詞語面貌。有些承古詞自產生起便出現在之后的每一層;有些承古詞在產生之后,緊接著又出現在幾個歷史層次,之后消亡;有些承古詞在產生之后,緊接著出現在后面的歷史層次,接下來不是消亡,而是發生演變。以目前出土可考的文字來看,殷商時期產生的承古詞是最早的,這部分承古詞在之后又產生新的承古詞、承古義,有的承古詞、承古義一直沿用到現代漢語中。
承古詞大致可以分為兩類:語義完全不變的承古詞;語義發展變化的承古詞。有的承古詞自產生至今語義完全未變,如“雞”“鵝”“羊”“豹”“棗”“杏”“麥”
“酒肉”“耋”“侄”“夫妻”“湖”“雹”“萬1(wàn)”“西南1(nán)”“西北1(běi)”“冬”“仲春”“仲夏”“仲秋”“仲冬”“立春”“春分1(fēn)”“立夏”“夏至”“立秋”“秋分1”“立冬”“冬至”“小腸”“大1(dà)腸”“匕首”等。有的承古詞的語義則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而發生了變化。承古詞語義的發展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承古詞內部承古義以及與其相關的其他詞語的豐富與繁化;一是承古詞及其內部承古義的簡化。除了承古詞的語義發生變化以外,承古詞的類型(基本詞匯、一般詞匯)也會發生變化。
二、現代漢語承古詞的語義變化
現代漢語承古詞的發展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承古詞內部承古義以及與其相關的其他詞語的豐富與繁化;一是承古詞及其內部承古義的簡化。下面,我們就對這兩種類型分別展開論述。
(一)承古詞的豐富與繁化
總的來說,承古詞的豐富與繁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就一個承古詞而言,這個承古詞內部承古義的豐富與繁化;就整個詞匯系統而言,這個承古詞與其相關的其他詞語的豐富與繁化。
1.承古詞內部承古義的豐富與繁化
一個詞產生之后,在使用過程中,相關的意義也逐漸用它來表達,它的義項就日漸增多,變成了多義詞。如“水”“天”等。
“水”的甲骨文為“”,本義為“河流”。例如:
(1)己亥卜,貞:王至于今水……(《甲骨文合集》14380)
還可以指無色無味的液體。例如:
(2)辛巳卜:其告水入于上甲,祝大乙牛?(《甲骨文合集》33347)
西周時期,產生了“浸泡,潤澤”義。例如:
(3)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周禮·秋官·柞氏》)
春秋時期,產生“大水,水災”義。例如:
(4)[襄公]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春秋戰國時期,泛指一切水域。例如:
(5)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尚書·
微子》)
戰國至秦時期,則產生出“水攻,放水淹沒對方”義,如例(6)所示;亦產生出“泅水”義,如例(7)所示。
(6)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沖、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辒、軒車。(《墨子·備城門》)
(7)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荀子·勸學》)
“天”的甲骨文為“”,其本義是“人的頭頂,頭部”。例如:
(8)庚辰卜,王弗疾朕天。(《甲骨文合集》20975)
古人以天為萬物主宰者。例如:
(9)辛丑卜:乙巳歲于天庚。(《甲骨文合集》22094)
春秋時期產生“天空”義。例如:
(10)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詩經·唐風·綢繆》)
戰國至秦時期,則產生出“日月星辰運行、四時寒暑交替、萬物受其覆育的自然之體”義,如例(11)所示;“命運,天意”義,如例(12)所示;“天然,天生”義,如例(13)所示;“天性與生命”義,如例(14)所示;“天時,指天氣、季節等”義,如例(15)所示。
(11)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莊子·大宗師》)
(12)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孟子·梁惠王下》)
(13)牛馬四足,是謂天。(《莊子·秋水》)
(14)故圣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呂氏春秋·本生》)
(15)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孫子·始計篇》)
以一個承古詞來表示多個意義,是符合語言的經濟原則的。多義詞最初的意義稱作“本義”,由本義衍生出的意義則稱為“派生義”。本義強調的是起源,不代表它一直居于中心地位;隨著語言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某一個派生義也可能會占據中心地位,本義則退居次要地位。如“元”的本義為“頭部”,在西周時期,其他義項的使用頻率已經高于本義的使用頻率,“頭部”不再占據中心地位。
承古詞新義項的產生往往是通過引申而實現的,引申大致分為兩種:隱喻(metaphor)和轉喻(metonymy)[5]。其中,隱喻建立在兩個義項所反映的概念之間存在相似之處的基礎上。如“天”的本義是“人的頭頂”,“天空”與“人的頭頂”的相似之處是都高高在上,“萬物主宰者”與“人的頭頂”的相似之處是都具有決定權。
轉喻產生的基礎是兩類現象之間存在著某種密切聯系,這種聯系在人們心理中已經相當穩固,穩固到可以用指稱A的詞來指稱B。古代墨刑的位置處于額頭上,因此,表“人的頭頂”的“天”增加了“墨刑”這一義項。“萬物主宰者”具有難以違背的力量,在它面前,人是無能為力的,唯有順應服從,因此,“天”又增加了“命運、天意”“天生”“天性與生命”這些義項。而“日月星辰運行、四時寒暑交替”“天氣、季節”等,多是依靠古人觀察“天空”中日月星辰等變化總結出來的,因此,“天”還增加了這兩個義項。
值得注意的是,“轉化”也是產生新承古義的途徑之一。蔣紹愚指出:“‘轉化則是通過語法變化的手段產生新義,即:使一個詞具有某種新的語法功能,使它改屬另一個詞類,從而也就使它的詞義發生改變。由轉化所產生的新義,其詞性一定是與舊義不同的。”[6](P223)
比如,“冠1(ɡuān)”是帽子的總稱。例如:
(16)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禮記·曲禮上》)
“冠2(ɡuàn)”則是指戴帽子、戴。例如:
(17)“許子冠乎?”曰:“冠。”(《孟子·滕文公上》)
又如,“雨1(yǔ)”是指從云層中降向地面的水滴。例如:
(18)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周易·說卦》)
“雨2(yù)”則是指降雨。例如:
(19)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經·小雅·大田》)
再如,“火1(huǒ)”是指物體燃燒時所發出的光焰。例如:
(20)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邇。(《尚書·盤庚上》)
“火1(huǒ)”還可以表“焚燒,焚毀”義。例如:
(21)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左傳·宣公十六年》)
以上名詞義素均進入動詞的語義結構中,作為動作的賓語、工具等。這時,有的讀音會發生變化,有的讀音則不發生變化。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說詞性改變了,就是通過轉化產生出的新承古義。例如:
(22)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韓非子·難三》)
這里的“冠”的意思是超出眾人,居于首位。古人早就意識到頭在整個人體中的重要地位,而帽子就戴在人的頭部,于是戴在頭上的帽子的地位也水漲船高,因此,“冠2”引申出“超出眾人,居于首位”義。該義是由轉喻產生的新承古義,而不是通過轉化而產生的新義。
2.承古詞與其相關詞語的豐富與繁化
有的承古詞與近義詞共存,共同發展;有的承古詞在與近義詞的共同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競爭,最終被替代。這里不妨以兩組詞為例進行說明:“嫁、妻2(qì)、女2(nǜ)、室、入”“止(趾)、足1(zú)、腳1
(jiǎo)、指”。
首先看第一組詞。“嫁”的本義是女子結婚,出嫁。例如:
(23)來嫁于周。(《詩經·大雅·大明》)
現代漢語中,大家所熟知的“出嫁”一詞,是戰國至秦時期產生的,不過,此時“出嫁”指的是“遣放宮女出宮嫁人”。例如:
(24)桓公曰:“善。”令于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自唐代開始,“出嫁”產生了“女子離開父母與丈夫成婚”義,并沿用至今。例如:
(25)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唐代韓愈《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妻2”的意思是嫁給。例如:
(26)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左傳·桓公六年》)
“妻2”也可以表“娶為配偶”義。例如:
(27)好色,人之所欲也,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孟子·萬章上》)
“女2”的意思是將女子嫁人。清代以后則不見該義用例。例如:
(28)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室”的意思是娶妻,成家。宋代以后則不見該義用例。例如:
(29)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左傳·昭公十九年》)
春秋時期,“室”還產生“以女嫁人”義。春秋之后則不見該義用例。例如:
(30)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左傳·宣公十四年》)
西漢時期,“入”產生“嫁”義。西漢以后則不見該義用例。例如:
(31)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于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西漢劉向《列女傳·晉趙衰妻》)
(32)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于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于朝。(西漢劉向《列女傳·晉羊叔姬》)
“嫁”“入”有時還會在文中共現,例如:
(33)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西漢劉向《列女傳·宋恭伯姬》)
(34)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西漢劉向《列女傳·衛寡夫人》)
在“出嫁,嫁給”義上,“妻2+某男子”是固定結構,而“嫁”不受此限制;在“娶為配偶,成家”義上,“妻2+某女子”是固定結構;“室”則單用,其后不加賓語。“妻2”“女2”在“嫁給”義上可以看作是近義詞,其中,“女2”的“嫁給”義清代以后不見用例;“妻2”在上一世紀30年代文學作品中仍有用例,現代漢語中已不再使用。在現代漢語中,“女子結婚,出嫁”義大多用“嫁”“出嫁”二詞表示。“女2”
與“妻2”之“嫁給”義的消亡,可能是因為“女2”
與“女1(nǚ)”、“妻2”與“妻1(qī)”字形一樣,讀音也只是聲調有區別,而“女1”“妻1”的語義早已深入人心,為了減少歧義產生,使表達更加準確,
“女2”“妻2”遂不再使用。
然后看第二組詞。“止”的甲骨文為“”,本義是“足,腳”,后通作“趾”。例如:
(35)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詩經·豳風·七月》)
西周時期,“趾”又產生了“支撐器物的腳”義。例如:
(36)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周易·鼎》)
春秋時期,進一步產生了“基礎部分,底腳”義。例如:
(37)議遠邇,略基趾。(《左傳·宣公十一年》)
戰國至秦時期,則出現“腳指頭”義。例如:
(38)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于目,目張則氣上行于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趾之端……其散者,別于目銳眥,下足少陽,注小趾次趾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于頷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趾之間。(《黃帝內經·靈樞》)
“足1”的甲骨文為“”,本義是“腳”。例如:
(39)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尚書·說命上》)
西周時期,引申出“器物下部形狀像腿的支撐部分”義。例如:
(40)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兇。(《周易·鼎》)
西周以后,產生“富裕,富足”義。例如:
(41)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尚書·旅獒》)
腳1,《說文解字·肉部》:“腳,脛也。從肉卻聲。”例如:
(42)詈侮捽搏,捶笞臏腳,斬斷枯磔,藉靡后縛,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荀子·正論》)
后來,“腳1”由“脛”轉指“踝下”,并沿用至今。例如:
(43)甚則肌肉萎,足痿不收,行善瘈,腳下痛,飲發中滿食減,四支不舉。(《黃帝內經·素問》)
自產生起直到民國時期,“止(趾)”“足1”一直都有“足,腳”義;民國之后,則很少單用。“腳1”自語義縮小為“足,腳”義后,直到現代漢語仍在使用。
“指”可表“腳指”義。例如:
(44)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左傳·定公十四年》)
“指”還可表“手指”義。例如:
(45)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墨子·大取》)
西漢時期,還出現了“手指”一詞。例如:
(46)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史記·貨殖列傳》)
西漢時期出現“手指”,唐代開始出現“腳指”。筆者檢索了北京語言大學BCC語料庫古代漢語庫,共檢索到881例“腳指”,212例“腳趾”,135例“腳指頭”,24例“腳趾頭”。
“腳指”用例如:
(47)菡苰竹,大如腳指,腹中白幕闌隔,狀如濕面。(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八)
“腳趾”用例如:
(48)唯露出腳趾,覺冷即續添沸漿,以盡為度,密蓋復忌風,漸淋至膝,候湯冷,收腳撲米粉。(北宋趙佶敕編《圣濟總錄》卷八十四)
“腳指頭”用例如:
(49)婦人髻堆腦后,四腕都是金鐲頭,手指頭、腳指頭都是渾金戒指。(明代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第七十二回)
“腳趾頭”用例如:
(50)不然,也要斷她的腳跟,撕掉她幾個腳趾頭。(清代頤瑣《黃繡球》第二回)
筆者檢索了北京語言大學BCC語料庫現代漢語報刊庫,共檢索到122例“腳指”,690例“腳趾”,53例“腳指頭”,102例“腳趾頭”。
“腳指”用例如:
(51)她每天去給病人作穴位按摩。從手指捏到腳指,全身一百多個穴位,按摩一次要一個多小時。(《人民日報》,1981-06-26)
“腳趾”用例如:
(52)親人為遺體更衣時發現他滿身的傷,還有那唯一的腳趾——失去的9根腳趾是在北大荒踏察時被凍掉的。(《人民日報》,2010-09-03)
“腳指頭”用例如:
(53)腳指頭一天到晚在鞋里,舒服不舒服,自己先知道。(《人民日報·海外版》,2003-11-10)
“腳趾頭”用例如:
(54)蔡萍發現他時,他腳趾頭全部潰爛了,疼得直咧嘴。(《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04-03)
雖然“腳指”“腳指頭”“腳趾”“腳趾頭”一直共存,但唐宋以來,“腳指”“腳指頭”的數量占據優勢;進入現代漢語之后,“腳趾”“腳趾頭”則明顯反超,在數量上占了上風。之所以會發生這種變化,可能是因為漢字簡化以后,帶“扌”的字主要是表示與手有關的意義,帶“?”的字則主要表示與腳有關的意義。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承古詞詞義的演變往往是相關詞語互相影響共同完成的。
從詞匯史的角度來看,先秦時期所產生的詞語有部分傳承到后世,其中,有些詞語一直沿用至現代漢語,或者作為構詞語素沿用至現代漢語。當然,承古詞的發展不一定都是完全照搬傳承,有的會發展出新的義項,并且發展出的新義項還不止一項;有的在發展過程中也會出現更替。在共時層面上,承古詞有多個義項,但是從歷時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些義項產生的時間不同,分屬于不同的歷史層次。這些承古詞的發展看似是獨立進行的,但以詞匯史的眼光來看,個體承古詞的發展也遵循著承古詞發展的共性。
(二)承古詞及其內部承古義的簡化
可以說,先秦時期所產生的承古義反映了詞語的多義化發展趨勢。需要指出的是,詞語的多義化發展雖然符合經濟原則,但是一旦義項過多則容易產生歧義,因此,伴隨承古義豐富與繁化的是承古詞及其內部承古義的簡化。總的來看,承古詞及其內部承古義的簡化,主要是通過承古詞的分化和承古義之間的競爭來實現的。
1.承古詞的分化
馬真指出:“通過詞義的引申,造成多義詞,再由多義詞分化出新的同音詞。”[7]在一定意義上說,詞的分化確實能夠有效避免產生歧義。這里不妨以“獸”“田”“禽”為例加以說明。
關于“獸”字,楊樹達指出:“蓋古文只有會意之獸字,形聲字之狩乃后起字也。今狩獵之義為后起之狩字所獨占,初形之獸卻只具后起禽獸之義矣。”[8](P306)例如:
(55)庚戌卜,辛亥王出獸。(《甲骨文合集》33381)
“田”具有“打獵”義,例如:
(56)乙卯卜,王往田,不雨。(《甲骨文合集》33412)
春秋時期,又產生“獵”字以表示“打獵”。例如:
(57)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詩經·魏風·伐檀》)
還產生“田獵”一詞,表示“打獵”。例如:
(58)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詩經·齊風·還序》)
戰國晚期,“獵”已經取代“田”而成為“打獵”義的常用詞了[9]。總之,“獸”的“打獵”義后來由“狩”表示,“獸”主要保留“四足、全身生毛的哺乳動物”義。“田”的“打獵”義由“獵”取代,主要保留“耕種用的土地”義。
再如“禽”,甲骨文作“”,有“獸的總名”義。例如:
(59)初六,井泥不食,舊井無禽。(《周易·井》)
又有“擒獲”義。例如:
(60)禽隹百卅八……(《甲骨文合集》37367)
還產生出“俘獲,被俘,制服”義。例如:
(61)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左傳·哀公二十三年》)
上述“擒獲”“俘獲,被俘,制服”義后來分化為“擒”。例如:
(62)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孫子兵法·謀攻篇》)
詞的多義化與詞的分化,這看似矛盾的兩個現象在詞匯發展過程中卻同步進行。歸結起來說,詞出現多義化主要是經濟原則起作用的結果,詞的分化則反映出人類表達對準確性、清晰性的不懈追求。
2.承古義之間的競爭
隨著社會的變遷和語言自身的發展,承古詞內部各義項之間也出現了相互競爭。承古義之間之所以會產生競爭,主要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各承古義意義相近或相關,但是色彩義并不一致,甚至相反;有的承古詞的各承古義意義不同,語音卻相同;語法的發展變化對詞語結構、用法等產生影響。
第一,因色彩義不一而導致的承古義變化。漢語詞匯追求表達準確、生動的另一個表現是:當意義相近或者相關的承古義感情色彩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時,其中一個或數個相關義項會逐漸走向消亡;當構詞語素的語義發生變化時,也可能會對承古義產生一定影響。這里不妨以“爪牙”為例加以說明。
先秦時期,“爪牙”有“動物的尖爪和利牙”義。例如:
(63)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荀子·勸學》)
該義沿用至今。例如:
(64)看見過力士搏獅么?當他屏息負隅,張空拳于猙獰的爪牙之下的時候,他雖有震恐,雖有狂傲,但他決不暇有蕭瑟與悲哀。(冰心《寄小讀者》二七)
有“人的指甲和牙齒”義。例如:
(65)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呂氏春秋·恃君》)
有“勇士,衛士”義。例如:
(66)祈父!予王之爪牙。(《詩經·小雅·祈父》)
還可以形容“勇武”。例如:
(67)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國語·越語上》)
西漢時期,產生“黨羽,幫兇”義,該義沿用至今。例如:
(68)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于文學之士。(《史記·酷吏列傳》)
“爪牙”表“勇士,衛士”“勇武”義,清代以后不見用例,“黨羽,幫兇”義則沿用至今。這大概是因為褒義的“勇士,衛士”“勇武”義,與貶義的“黨羽,幫兇”義感情色彩相互矛盾,影響了表達的準確、生動。同時,“人的指甲和牙齒”義消亡,“動物的尖爪和利牙”義則沿用至今,這應該與“爪”的語義變化密切相關。“爪”既有“鳥獸的趾端有尖甲的腳,亦指其尖利趾甲”義,又有“人的指甲,亦指手指或手”義,“爪”的這兩個義項都沿用至今。例如:
(69)攻堅戰更不能麻了爪(編后)(《人民日報》,2017-08-13)
不過,“爪”表“人的指甲,亦指手指或手”義的使用頻次已經很低。先秦時期所產生的“手”、西漢時期所產生的“手指”、宋代所產生的“指甲”等,均能將人區別于鳥獸,表達也更為精準。
第二,因語音相同而導致的承古義變化。在有些情況下,語音相同也會造成歧義。這里不妨以“指”為例加以說明。
先秦時期,“指”有“腳趾”義。例如:
(70)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左傳·定公十四年》)
“指”也有“手指”義,例如:
(71)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孟子·告子上》)
可以說,“手指”“腳趾”都用“指”來表示,很容易形成歧義。先秦時期,“趾”亦產生“腳趾”義。就字形而言,“指”與“趾”明顯不同,在書面語中容易區分,不過,兩字的發音完全相同,口語中則難以區別。西漢時期出現“手指”,唐代開始出現“腳指”。“手指”“腳指”的陸續出現,有效解決了表達的準確性問題。
第三,因語法發展而引起的承古義變化。王力指出:“漢語語法的發展,是朝著嚴密、充實、完全方面發展的。這是社會文化發展的一個方面,所以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總結出一些發展的規律來。”[10](P3)何樂士曾對《左傳》與《史記》的語法特點進行了比較:“《左傳》的句子常常省略主語或賓語,有時讀起來比較費解。隨著語言的發展,《史記》在敘述與《左傳》相同的史實時,常將主語或賓語補出,使句子成分更加完備。”[11](P2)漢語語法的主要特點是:詞、短語、句子的結構基本一致。因此,朝著嚴密、充實方向發展的不止是句子,也包括詞、短語。如“冠2,戴帽子”
“雨2,降雨”,后世則用“動作+對象”結構來表示;“火1,焚燒,焚毀”,后世則以“用火燒”來表示;“妻2,嫁給”,后世則用“女子嫁給男子”來表示;“妻2,娶為配偶”,后世則用“男子娶女子為配偶”來表示。通常情況下,后世的結構往往將對象、工具、主語、賓語等補齊,表達較前代更為精準。
三、現代漢語承古詞的類型變化
王力指出:“漢語的歷史很長,它的基本詞匯可以追溯到幾千年以前。在奴隸時代以前的遠古時期,基本詞匯和一般詞匯幾乎可以說是沒有差別的。在甲骨文時代,這二者之間的界限也還是不大的。”[10](P561)
王先生還指出:“漢語的基本詞匯是富于穩定性的;多數的基本詞有了幾千年(或者)幾百年的壽命。”[10](P585)
如“雞”“羊”“大1(dà)”“少1(shǎo)”“出”“入”“我”“一”等。這里不妨以“瓜分”“述職”為例加以說明。
“瓜分”一詞產生于戰國時期,意思是“如同切瓜一樣地分割或分配”,這一語義直到現代漢語仍在使用。例如:
(72)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戰國策·趙策三》)
(73)按照這個模式,“上線”瓜分“下線”的錢,“下線”不但得不到“高額回報”,到頭來只能是血本無歸。(《人民日報》,2001-10-13)
(74)全國體育大會各項比賽從27日到今天奪金高潮迭起,截至今天晚上,已有73枚金牌各歸其主,其中金牌大戶之一的健美和技巧項目各17枚金牌今天已被全部“瓜分”。(《人民日報》,2002-05-29)
在古代漢語中,與“瓜分”搭配的伙伴域大多是國土等;到了現代漢語,“瓜分”的伙伴域已大大拓展。需要說明的是,“瓜分”自產生至今始終是一般詞匯。
戰國至秦時期,“述職”專指諸侯向天子陳述其職守。例如:
(75)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孟子·梁惠王下》)
唐代,還產生了“外任官員向朝廷陳述守職”義。例如:
(76)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唐代柳宗元《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到了現代漢語,“述職”是指向主管部門領導或有關人員報告履行職務的情況。例如:
(77)近年來,浙江省德清縣、舟山市普陀區開展代表向選民述職、接受選民評議活動。(《人民日報》,2001-02-28)
(78)鄉人大堅持把聯系選民、向選民述職作為代表工作的重要內容,做好區代表每年向選民述職、代表組年終向選民匯報等工作,鄉代表在任期之內至少向選民述職一次。(《人民日報》,2003-02-12)
可以看出,與“述職”搭配的伙伴域發生了很大變化。“天子”“諸侯”已經隨著分封制度的結束而不復存在;至唐代,“述職”的主體成為“外任官員”,“述職”的對象成為“朝廷”;到了現代漢語中,“述職”的對象則變成了“主管部門領導或者有關人員”。需要說明的是,“述職”自產生至今也始終是一般詞匯。
隨著社會的發展,基本詞匯有可能會變成一般詞匯,甚至消亡;與之同時,一般詞匯也可能會轉變成基本詞匯。這里不妨以“領”“頭1(tóu)”“叔1(shū)”等為例加以說明。
“領”有“脖子”義。例如:
(79)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詩經·衛風·碩人》)
胡明指出:“戰國末期,‘領的詞義發生轉移,由‘脖子轉指‘衣領。”[12](P121)隨著“領”之語義的轉移,“領”亦由基本詞匯轉變為一般詞匯。
“元”的甲骨文為“”,是一個側立的人形,頭部突出。其本義為人的頭部。例如:
(80)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元”表“頭部”雖然起源很早,但是在先秦兩漢文獻中,用例并不多見。先秦表“頭部”義時,多使用“首”。“首”的甲骨文作“”,像一個羊頭,本義為“頭”。例如:
(81)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詩經·邶風·靜女》)
“頭1”可以表示人體的最上部分或動物的最前部分,通常長著口、鼻、眼等器官。例如:
(82)荀偃癉疽,生瘍于頭。(《左傳·襄公十九年》)
吳寶安認為,“頭部”義“首”先秦文獻出現146次,“頭”僅47例,“首”占絕對優勢;兩漢時期,“頭”“首”競爭激烈,“頭”漸占優勢;魏晉時期,“首”成為文言詞,完全被“頭”取代[13]。也就是說,先秦時期,“元”“首”為基本詞;兩漢以后則發生改變,“頭1”為基本詞。
“叔1”的本義是“拾取”,也通“菽1(shū)”,指豆類植物。“菽1”的甲骨文作“”[14]。例如:
(83)弗其受菽年?(《甲骨文合集》10047)
“豆”可以表示豆類植物的總稱。例如:
(84)韓地險惡,山居,五谷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戰國策·韓策一》)
陳榮杰指出,至西漢文景時期,在當時人們日常生活中,“豆”已經基本替代“叔”“菽”,作者認為:“‘豆替代‘叔‘菽的原因可能和古禮制的消亡、器物‘豆的消失及語言中詞匯的發展變化有關”[15](P334)。先秦時期,“叔1”“菽1”為基本詞,表“豆類植物”;西漢之后,“豆”取而代之,成為基本詞,“菽1”變為一般詞,而“叔1”作為“父親的弟弟,或者與父親平輩、年齡比父親小的人”,依然是基本詞匯。
西周時期,“屨”表示“鞋”。春秋時期,還產生了“葛屨”“屝屨”。例如:
(85)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周禮·天官·屨人》)
“履”的甲骨文作“”,本為動詞,表“踩踏”義。例如:
(86)初六,履霜,堅冰至。(《周易·坤》)
“履”還有“行走”義。例如:
(87)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周易·履》)
戰國時期,“履”產生“鞋”義。例如:
(88)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系履而過魏王。(《莊子·山木》)
至漢代,“履”完成了對“屨”的替代。也就是說,先秦時期,“屨”為基本詞;西漢以后,“履”則成為基本詞,“屨”變成一般詞匯;當然,后世“鞋”又取代“履”而成為基本詞。
“我”的甲骨文作“”,代詞,泛指自己一方。例如:
(89)甲辰卜,爭貞:我伐馬方,帝受我又(祐)一月。(《甲骨文合集》6664)
這里的“我”是指“殷商民族”。“我”這種泛指自己一方的復數用法一直延續下來,今天仍在使用。例如:
(90)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左傳·隱公元年》)
(91)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魯問》)
(92)從日臻完善的立法,到措施得力的執法,我國保護未成年人的工作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人民日報》,1996-05-28)
(93)既然已經答應了人家,就不能隨便毀約,雖然責任不在我方。(《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03-05)
西周以后,“我”也可以稱自己,這一用法一直沿用到現代漢語。例如:
(94)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小雅·采薇》)
(95)人家騙了我,我不能騙顧客,他一戶一戶道歉、退款,共退款300多元。(《人民日報》,1994-03-04)
現代漢語中,主要是以“我們”表示復數。例如:
(96)社區里也有老年協會,會不定期舉辦活動,我們一幫老友在一起樂呵樂呵,感覺挺好。(《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01-19)
“朕”也是殷商時期產生的第一人稱代詞。例如:
(97)戊寅卜,朕出今夕?(《甲骨文合集》22478)
(98)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尚書·堯典》)
從秦始皇二十六年起,“朕”只能用于帝王自稱。
“吾1(wú)”作為第一人稱代詞,產生于西周時期。例如:
(99)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周易·中孚》)
與“我”不同的是,“吾1”單用表示單數,如果要表示復數,則可以在“吾1”后加數量短語,或者
在“吾1”后加“輩”“等”“儕”等。例如:
(100)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論語·季氏》)
(101)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左傳·昭公元年》)
“吾1”在現當代文學作品中仍偶有用例,主要是追求仿古效果。現代漢語中,它基本不再使用。例如:
(102)她也哼哼唧唧自稱吾神長吾神短。(趙樹理《小二黑結婚》)
可見,基本詞匯總體是穩固的,如“雞”“羊” “出”“入”“我”“一”等。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基本詞匯內部也要進行新陳代謝,同樣會出現新舊交替的現象。不僅基本詞匯有可能會變成一般詞匯,甚至消亡;與之同時,一般詞匯也可能會轉變成基本詞匯。
四、結語
綜上所述,現代漢語承古詞是分歷史層次的,它們來自不同的歷史時期。就一個承古詞來看,其內部承古義的產生方式主要有三種:隱喻、轉喻和轉化。就多個承古詞來看,承古詞及其相關承古詞的發展演變,往往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相關詞語互相影響共同完成的。伴隨承古詞內部承古義不斷豐富與繁化的,是承古詞及其內部承古義的簡化。承古義的簡化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一是承古詞分化出新詞;二是承古詞內部承古義的更新。隨著承古詞義項的日漸豐富,承古詞內部的各承古義之間會出現競爭,并導致承古義的更新。產生競爭的原因主要有:各承古義意義相近或相關,但是色彩義不一,甚至相反;有的承古詞的承古義意義不同,語音卻相同;語法發展變化對詞語結構、用法等產生影響。這種內部的競爭更新保證了語言表達的精準生動。經濟原則促使承古詞內部承古義的豐富與繁化;表達準確生動的需求又促使承古詞內部的承古義不斷進行簡化。現代漢語中的承古詞數量較多,這些詞語中既有基本詞匯,也有一般詞匯。雖然基本詞匯比較穩定,但是它也會出現新舊更替,有的甚至轉變成一般詞匯。與此同時,一般詞匯也可能會轉化成基本詞匯。
參考文獻:
[1]王云路.中古漢語詞匯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2]楊端志.《漢語大詞典》對漢語詞匯發展演變史的價值與研究方法——《漢語大詞典》詞匯發展演變史研究條例[A].楊端志.漢語史論集[C].濟南:齊魯書社,2008.
[3]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漢語大詞典[Z].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3.
[4]游汝杰.吳語語法的歷史層次疊置[A].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語言研究集刊(第二輯)[C].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5]沈家煊.語用原則、語用推理和語義演變[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4,(4).
[6]蔣紹愚.古漢語詞匯綱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7]馬真.先秦復音詞初探(續完)[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1).
[8]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9]胡波.先秦兩漢“打獵”義動詞更替考——基于出土文獻、傳世文獻與異文材料的綜合考察[J].語文研究, 2022,(2).
[10]王力.漢語語法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11]何樂士.《史記》語法特點研究——從《左傳》與《史記》的比較看《史記》語法的若干特點[A].程湘清主編.兩漢漢語研究[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12]胡明.基于《漢語大詞典》的戰國——秦新詞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
[13]吳寶安.小議“頭”與“首”的詞義演變[J].語言研究,2011,(4).
[14]于省吾.商代的谷類作物[J].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7,(1).
[15]陳榮杰.試論“尗”“叔”“菽”到“豆”的歷時演替[A].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勵耕語言學刊(總第27輯)[C].北京:中華書局,2018.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Inheritance Words
——Taking the Inheritance Words Produced in the Pre-Qin Dynasty as an Example
Ding Xueni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Modern Chinese inheritance words are divided into historical levels, and they came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such as the Shang dynasty,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Some Modern Chinese inheritance words have remained unchanged in meaning since their emergence; Some semantics have undergone change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 complexity and simplification of ancient meanings. The ways in which the meaning of inheritance came into being include metaphor, metonymy, and trans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inheritance words are often influenced and completed together with relat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there are both basic vocabulary and general vocabulary in ancient Chinese. Although the basic vocabulary is stable, there may be alternations between old and new vocabulary, and some of them may even be converted into general vocabulary.
Key words:Modern Chinese inheritance words;meanings of Modern Chinese inheritance words;Modern Chinese;Pre-Qin period;basic vocabulary;general vocabul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