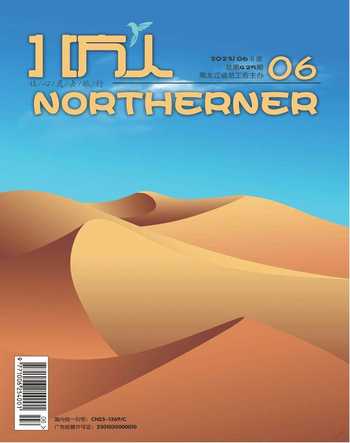把時間絆了一跤
劉亮程

我看見早晨的陽光,穿過村子時變慢了。時光在等一頭老牛。它讓一匹朝東跑的馬先奔走了,進入一匹馬的遙遙路途,在那里,塵土不會揚起,馬的嘶叫不會傳過來。而在這里,時光耐心地把最緩慢的東西都等齊了,連跑得最慢的蝸牛,都沒有落在時光后面。
劉二爺說,有些東西跑得快,我們放狗出去把它追回來。有些東西走得比我們慢,我們叫墻立著等它們,叫樹長著等它們。我們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讓跑得快的、走得慢的都和我們待在一起。
我在這里看見時光對人和事物的耐心等候。
四十歲那年我回到村里,看見我五歲時沒抱動的一截木頭還躺在墻根。我那時多想把它從東墻根挪到房檐下。仿佛我為移動這根木頭又回到村里。我二十歲時就能搬動這根木頭,可我顧不上這些小事。我在遠處。三十歲時我又在干什么呢?我長大后做的哪件事是那個五歲孩子夢想過的?幸虧還有一根沒挪窩的木頭。
我五十歲時,比我大一輪的王五瞎了眼,韓三瘸了一條腿,馮七的腰折了。就是我們這些人在拖延時間。我們年輕時被時間拖著跑,老了我們用跑瘸的一條腿拖住時間,用望瞎的一雙眼拖住時間。在我們拖延的時間里,兒孫們慢慢長大,我們希望他們慢慢長大,我們有的是時間讓他們慢慢長大。
時間在往后移動,所以我們看見的全是過去。我們離未來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近。時光讓我們留下來。許多時光沒有到來。好日子都在遠路上,一天天朝這里走來。我們只有在時光中等候時光,沒有別的辦法。你看,時間還沒來得及在一根刮磨一新的锨把上留下痕跡,時間還沒有磨皺那個孩子遠眺的雙眼,但時光確實已經慢了下來。
每天一早一晚,站在村頭清點人數的張望,可能看出些時光的動靜。當勞累一天的韓瘸子牽牛回到家,最后一縷夕陽也走失在西邊荒野。一年年走掉的那些歲月都到哪兒去了?夜晚透進陣陣寒風的那道門縫,也讓最早的一束陽光照在我們身上。那頭傍晚干活回來的老牛,一捆青草吃飽肚子。太陽落山后,黃昏星亮在晚歸人頭頂。在有人的曠野上,星光低垂。那些天上的燈籠,護送每個晚歸人。一方小窗里的燈光在黑暗深處接應。當我終于知道時間讓我做些什么,走還是停時,我已經沒有時間了。
每年春天,村東的樹長出一片半葉子時,村西的樹才開始發芽。可以看出陽光在很費力地穿過村子。
劉二爺說,如果從很高處看——夢里這一村莊人一個比一個飛得高——向西流淌的時間汪洋,在虛土莊這一塊形成一個渦流。時間之流被擋了一下。誰擋的,不清楚。我們村子里有一些時間嚼不動的硬東西,在抵擋時間。或許是一只貓、一個不起眼的人、一把插在地上的鐵锨,還是房子、樹,反正時間被絆了一跤,撲倒在虛土里。它再爬起來往前走時,已經多少年過去,我們把好多事都干完了,覺也睡夠了。別處的時光已經走得沒影,我們這一塊遠遠落在后面。
時間在丟失時間。
我們在時間丟失的那部分時間里,過著不被別人也不被自己知道的漫長日子。劉二爺說。
鳥是否真的飛到了時間上面?有一種鷹,愛往高遠飛,飛到紛亂的鳥群上面,飛過落葉和塵土到達的高度,一直飛到人看不見。鳥飛翔時,把不太好看的肚皮和爪子亮給我們,就像我們走路時,不知道該把手放在什么位置。鳥飛在天上,對自己的爪子也不知所措,有的鳥把爪子向后并攏,有的在空中亂蹬,有的爪子閑吊著,被風刮得晃悠。還有的鳥,一只爪子吊下來,一只蜷著,過一會兒又調換一下。
鳥在天上,真不知該怎樣處置那對沒用的爪子,把地上的人看得著急。不過,鳥不是飛給人看的,這一點小孩都知道。鳥把最美的羽毛亮給天空,好像天上有一雙看它的眼睛。鳥從來不在乎我們人怎么看它。
那些陽光,穿過裊裊炊煙和逐漸黃透的樹葉,到達墻根門檻時,就已經老了。像我們老了一樣,那些秋草般發黃的傍晚陽光,垛滿了村莊。每天這個時候,坐在門口衲鞋的馮二奶,最知道陽光怎樣離開村莊:絲線般細密的陽光,從樹枝、墻根、人的臉上絲絲縷縷抽走時,滿世界的聲響,天塌下來一樣。
我們把時間都熬老了。劉二爺說。
當我們老得啃不動骨頭,時間也已老得啃不動我們。
(摘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我的孤獨在人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