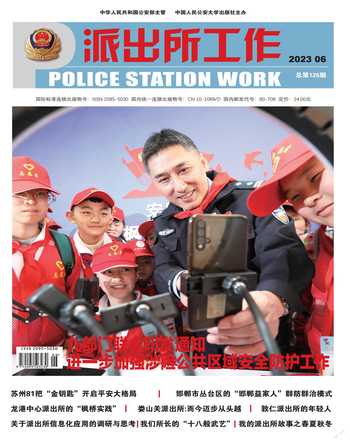現場調解后被害人可能構成輕傷該怎么處理
李值
李某與王某是某商場的同事,因為工作瑣事發生爭執繼而升級為肢體沖突。在撕扯中,王某踹了李某肋部一腳,李某報警。民警接警后將雙方帶至警務室,固定了相關證據。其間,王某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并愿意為此承擔責任,主動提出賠償李某500元。李某稱未感身體異常不需要去醫院治療,表示原諒王某的錯誤行為。雙方均提出要求,希望派出所民警現場調解處理此事。
民警認為,李某與王某的上述行為,因糾紛引起,情節較輕,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條“對于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打架斗毆或者損毀他人財物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情節較輕的,公安機關可以調解處理”與《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七十八條“情節輕微、事實清楚、因果關系明確,不涉及醫療費用、物品損失或者雙方當事人對醫療費用和物品損失的賠付無爭議,符合治安調解條件,雙方當事人同意當場調解并當場履行的治安案件,可以當場調解,并制作調解協議書。當事人基本情況、主要違法事實和協議內容在現場錄音錄像中明確記錄的,不再制作調解協議書”之規定,并明確告知李某放棄傷勢鑒定的法律后果后,同意了雙方的請求,現場調解處理該起糾紛。之后,王某當場向李某道歉并賠償李某500元,雙方握手言和。執法記錄儀全程記錄了此案的處理過程。
然而,兩日后,李某肋部疼痛難忍,與現場調解時完全不同。李某再次報警,認為自己可能構成輕傷,要求公安機關追究犯罪嫌疑人王某的刑事責任。
這種情況該怎么辦?
筆者認為,在并未確定李某構成輕傷的情況下,公安機關可以根據《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六十五條“對發現或者受理的案件暫時無法確定為刑事案件或者行政案件的,可以按照行政案件的程序辦理”之規定,對該案以行政案件受理。調查取證后,存在以下幾種可能:
其一,李某的傷勢經鑒定構不成輕傷。由于李某與王某已經在現場達成了調解協議,公安機關應當以《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二百五十八條第二款“按照本規定第十章的規定達成調解、和解協議并已履行的”之規定,對該案予以結案。
其二,李某的傷勢經鑒定構成輕傷,但其在離開調解現場后,因時間間隔的原因導致其傷勢與王某的行為之間存在介入因素,若無法證明該輕傷結果與王某傷害行為存在因果關系,此時公安機關應當以《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二百五十八條第二款“按照本規定第十章的規定達成調解、和解協議并已履行的”之規定,對該案予以結案。之后,告知被害人李某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其三,李某的傷勢經鑒定構成輕傷,且公安機關結合相關證據對該案進行綜合判斷,能夠證明被害人李某的傷勢確系犯罪嫌疑人王某的行為所致,同時,證據達到《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確實、充分”之標準,則公安機關應以《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七十二條“違法行為涉嫌構成犯罪的,轉為刑事案件辦理”之規定,對該案轉換成刑事案件,待案件偵查終結后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其四,李某的傷勢經鑒定構成輕傷,但其在離開調解現場后,因時間間隔的原因導致其傷勢與犯罪嫌疑人王某的行為之間存在介入因素,公安機關收集的證據雖然有薄弱環節或爭議之處,但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王某的基本犯罪事實,公安機關仍應將該案轉換成刑事案件,待案件偵查終結后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然而,有人可能不認同最后兩種思路,認為李某在調解現場已與王某達成調解協議,并放棄了追究王某的責任,即使事后發現自己構成輕傷,且確為王某的行為所致,公安機關也喪失了追究犯罪嫌疑人責任的權力,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條第二款“經公安機關調解,當事人達成協議的,不予處罰”之規定,不能再受理該案。
對此,筆者持反對意見。其原因在于上述觀點誤將該刑事案件當成了治安案件處理。誠然,如果李某僅構成輕微傷,其與王某達成調解協議后,公安機關和李某均喪失了追究王某責任的權力或權利。但是,李某與王某達成協議的前提是其主觀上對自己的傷情存在認識錯誤,故其在協議中不再追究王某法律責任的內容是可以撤銷的;即使李某在現場已認識到自己的傷勢會構成輕傷,也沒有權利要求公安機關放棄追究王某的刑事責任。因此,當李某發現自己構成輕傷的時候,有權要求公安機關依據《公安機關辦理傷害案件規定》第二十八條“被害人傷情構成輕傷、重傷或者死亡,需要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的,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辦理”之規定重新處理。公安機關也應當及時受案處理,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