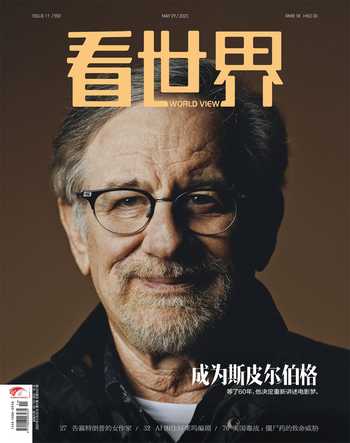34歲,我決定凍卵
姜雯

我一直沒想好,要不要當一個媽媽。
這件事與婚戀都無關,它只關乎:我自己,是否在心理和經濟上,準備好成為一個媽媽了。但目前這兩個條件都未滿足,而我也仍有許多想要去完成的事情。
但我已經34 歲了,不爭的事實是,女性的卵巢功能每年都在衰退,這讓我開始感到焦慮。所以我做了一個決定—去凍卵。
在決定凍卵之前,我與很多不同年齡層的朋友聊過。除了周圍的同齡人表示支持以外,絕大多數50 歲以上的友人都提出了類似的意見:你當務之急,應該是找個好男人嫁了,趁年輕趕緊生一個。這令我不禁疑惑:是我想多了,還是別人想少了?
“結婚、生子”固然在法律和傳統上是“配套的最優解”,但這似乎又與一個女性個體“想成為媽媽”“養育一個生命”沒有必然聯系。除了人類社會以外,自然界的動物們并沒有如此嚴格的“家庭概念”。而在父權社會,女性常常被當作“生育機器”,但是當代女性,已經逐漸從傳統窠臼中走出來,而當代醫學的發展,讓女性得以進一步在生育問題上獲得解放。
我并不“厭男”,就像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說的:“我從十幾歲開始,就對婚姻制度不感興趣,并不是不喜歡男人。”對我來說,我并不排斥和一個喜歡的人共同養育一個孩子,但如果上述條件沒有達成,而我在心理和經濟上都做好準備時,我也很樂意自己給自己生一個孩子。
于是凍卵對我來說,是當下最好的選擇。雖然費用昂貴,每年還要繳交保管費,但這相當于我為自己買了一份保險。待在“窮途末路”,我還是有機會要一個自己的孩子。當然,未來決定不生孩子是一種選擇,領養也是一種選擇,但這又是后話了。
我住在中國臺灣,在晚婚、少子化的臺灣社會,輔助生殖已然是一個龐大的產業。我的醫生朋友推薦了我一間不那么“商業化”的診所,我便前往咨詢和檢查。醫生告訴我,我的一切指數都正常,34 歲凍卵,相當于把34 歲的卵子保存下來,接下來就可以進入凍卵流程了。診所的護士也相當親切,她們鼓勵我:“為自己考慮,這是個很棒的決定。”
然而,在臺灣現行的法律下,輔助生殖只能用于已婚夫妻,單身女性并不能通過輔助生殖懷孕生子。也就是說,未來我還是要完成“結婚”這件事,才可以有一個孩子,所以“自己給自己生一個孩子”這件事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此外,根據臺灣2022 年的研究數據,凍卵使用率只有8%。
不過,對我來說,人生還很長,還有很多夢想、很多挑戰、很多有趣的事要去完成、要去體驗。因而我以一種“不執著”的心情,決定為自己買一份生育保險。我相信,這會是一筆“花得最值得”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