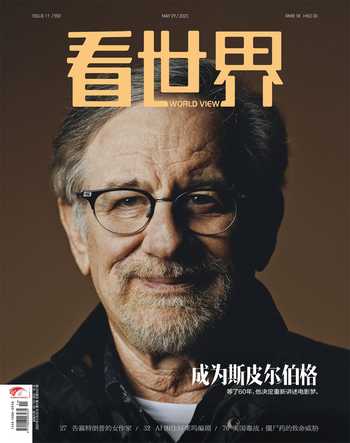有一天發現朋友們都死了
歐文·D. 亞隆

《生命的禮物:關于愛、死亡及存在的意義》
[ 美] 歐文·D. 亞隆 / 瑪麗蓮·亞隆 著
童慧琦 / 丁安睿 / 秦華 譯
機械工業出版社
2023 年4 月
過去幾年里,我的三位好友,赫伯·科茲、拉里·扎羅夫和奧斯卡·多德克,相繼去世了。他們是我高中和大學時代的朋友,在醫學院一年級時,我們曾是人體解剖課的搭檔,后來他們成為我一生的摯友。可現在他們三個都走了,獨剩我一人,保管著我們共同的記憶。
在我們的解剖學課程中,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真是太可怕了,當時我們正要把大腦移除出來開始解剖,掀開蓋在尸體上的黑色塑料布,我們看見尸體的眼窩子里趴著一只大蟑螂,大家都被惡心壞了,尤其是我,我從小就特別怕蟑螂,在我爸的雜貨店里和我家樓上的公寓地板上,到處都有爬來爬去的蟑螂,總能把我嚇得夠嗆。
那天,在迅速更換了黑色防水布后,我說服了其他人一起翹課去打橋牌。往常我們四個會在午餐時打橋牌,而在接下來的幾周里,我們一到解剖課就翹課去打橋牌。雖然后來我打得一手好牌,可我得慚愧地承認,作為一個畢生研究人類精神世界的工作者,我當年竟然翹掉了大腦解剖課。
然而真正讓人感到不安的是,我意識到,如此充滿了情感的生動往事,卻只存在于我一個人的腦海中。顯而易見,人人皆知“回憶只存在于腦海中”。然而問題是,我自己也未曾真正擁有那些記憶啊,那扇只有我能打開并通向回憶的門,我同樣也抓不住。
門是不存在的,解剖教室自然也不存在,記憶中忙碌的解剖課也并不存在。那一切的過往,豈非只存在于我嗡嗡作響的大腦神經元里?某一天,我,我們四人中僅存的一個,死了,“咻”的一下,一切都將湮滅,所有的記憶都將永遠消逝。一旦發現并承認這一點后,我感到腳下的大地不再堅實,如墜虛空。
只剩我一人
等等!當我再次檢視那個打橋牌的畫面時,突然發現有點不對勁。要知道,這可是65 年前的事了!當你要寫回憶錄時,你就會知道,記憶這個東西是有多么不可靠。我漸漸想起來,我們四人橋牌小組里的拉里·扎羅夫,是一位特別用功的好學生,早就決心當一名外科醫生,他是不可能翹掉解剖課來跟我們打橋牌的。
我用力閉上眼睛,努力湊近那段記憶,想要看個清楚。我突然意識到,跟我一起打橋牌的,除了赫伯、奧斯卡,確實還有一個拉里,但不是拉里·扎羅夫,是另外一個拉里,他姓埃內特,而不是扎羅夫。而且我還想起來,其實我們解剖學課的小組成員是六個人,當年出于種種原因,用于解剖教學的尸體緊缺,所以其實我們是六人一組,而不是四人一組。
我的朋友拉里·埃內特,我對他記憶猶新: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鋼琴家,在我們初高中所有的活動中演奏鋼琴,夢想成為一名音樂家。然而和我家一樣,他們也是移民家庭,他的爸爸媽媽非要他去念醫學院。拉里是個非常熱心的人,雖然我是個音盲,他卻一直努力嘗試喚醒我的音樂細胞,就在我們開始念醫學院不久,他帶我去了一家唱片店,幫我挑選了六張古典音樂唱片,說起來有點難堪,雖然我一遍一遍地聽,但一年以后,我還是聽不出哪首是哪首。
拉里選擇了皮膚病學,他覺得這個專業能讓他有最大的自由去追求音樂事業。若是能和拉里一起敘敘舊該多美妙啊!于是我決定聯系他,可在谷歌上一查卻發現,老天,他也在十年前離開了人世。
我們這個小組里,第六位同學是埃爾頓·赫爾曼,我在本科時就認識他了,這個小伙子聰明、友善、討人喜歡,常常穿著燈芯絨短褲去上課。埃爾頓后來怎樣了?他現在在哪兒呢?然而當我在網上搜索時才發現,他也去世了,八年前。
我們小組一共六個人,除了我,他們五個都死了!我開始覺得恍惚,閉起眼回想過往,有那么一瞬間,我看到我們在一起,摟著彼此的肩膀。那時的我們生機勃勃,充滿希望,渴望成功,聰明且各有成就,一起進了醫學院。我們所有人都曾如此勤奮學習,懷揣著各自的夢想。
然而除了我,他們都已化為枯骨,歸于塵土。六個人,如今只剩我一個人還在塵世間行走,想到這,我不禁心懷怵栗。為什么只有我活得更久?純粹是因為幸運吧!我還在呼吸,還能思考,能聞到氣味,還能牽著太太的手,我是何其幸運。但我也好孤獨,我想念他們。屬于我的“那個時刻”,也快降臨了吧!
請給我一個擁抱
這個故事還有下文。有兩次,我將這個故事講給病人聽,效果都很好。其中一位是女病人,在兩個月里先后失去了丈夫和父親—她生命中至親至愛的人。她告訴我,此前自己已經見過兩位治療師了,但他們顯得那么疏離,只是旁觀,她無法與其產生聯結。聽她這么說,我想很可能她也會這么看我。確實,在我們的咨詢過程里,她顯得冰冷、遲鈍、難以接近。我感覺我們之間有一個難以逾越的鴻溝,顯然她也有同感。有一次,在咨詢快結束時,她說: “幾個星期以來,我總覺得一切都不真實,我完全是孤獨的,就像獨自坐在一列火車上,所有座位都是空的,一個人都沒有。”
“我太能理解你的感受了,”我回應道,“最近我也有類似的體驗。”然后我把自己失去五位醫學院同學,以及我的真實感是如何崩塌的故事告訴了她。她身體前傾用心聽著,眼淚順著她的臉頰流下來。她說:“對,對,我理解,我完全理解,這正是我在經歷的。我的眼淚是因為感慨‘我所在的這列火車上,終究還是有別人在的。你知道我剛才想到了什么?我在想,當下的生活依然真切,我們都應該活在當下,感恩生活。”這番話震撼了我。我們沉浸于這份會心的喜悅中,靜坐良久,沉默不語。
幾周以后,我又把這個故事拿出來講述。這位病人我每周見一次,已經持續一年,這是最后一次咨詢。她住在千里之外,一直以來我們都是通過Zoom 約談。
由于這是最后一次咨詢,她決定親自飛來加州,首次和我面對面交流。在等著見她時,我還在琢磨透過網絡與見到真人,感覺一樣嗎?會不會見到真人后感覺迥異呢?在開始咨詢前我們握了握手,比通常握手的時間還要長一些,就好像我們需要通過這次握手,確信彼此的真實存在一樣。
我跟她完整地講述了我去世的五位同學的故事,以及我如何掙扎于她所提到的這個情境:“一切皆是虛幻。”我講完后,我們安靜地坐了很久,直到會談結束。然后,她說:“謝謝你,歐文,謝謝你跟我分享這個故事,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禮物,是一份巨大的饋贈。”工作結束了,我們站起身來,她說: “我想要一個擁抱,一個我可以長久帶在身邊的擁抱,一個實實在在的擁抱。”
(本文獲出版社授權,標題為編者所加)
責任編輯董可馨 dkx@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