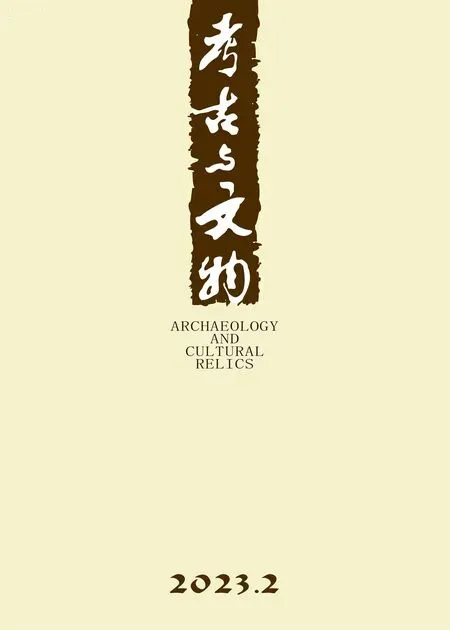咸陽坡劉村十六國墓M2 研究*
李雨生 耿慶剛
(1.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2.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陽坡劉村十六國墓M2因未被盜擾,故保存了完整的隨葬品組合及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1]。出土的銘文磚和印章有助于進一步框定墓主身份和墓葬年代,伎樂組合為認識漢晉以來俗樂演變提供了新資料,墓室中隨葬品的分布也別具一格。本文試從年代、墓主、伎樂組合和隨葬品分布等方面展開討論。
一、墓葬年代與墓主
墓室發現的印章、組佩、金片以及墓道填土中出土的銘文磚等,為判定墓葬年代和墓主人身份提供了新的線索,也提出了新的問題。
“西陵縣侯夫人”印章龜首昂起并明顯前傾至印臺之外,印文排置偏上,印面下部邊沿留有空間,這都是沿襲了西晉官印形制與文字的布局特征[2]。西晉官印制作規范,形制嚴謹,印面尺寸2.4厘米見方,與晉時一寸長度標準一致,少有誤差。而“西陵縣侯夫人”印章的印面為1.9厘米,尺寸變小,制作規格漸失標準;“西陵縣侯夫人”六字寫法簡率,文字大小參差,鑿刻尖細,筆勢平正中已見欹側,又與西晉官印在書法、刻鑄方面嚴謹有度的做派判然有別,反映出秦漢以來形成的規范正走向紊亂與荒疏,恰與晉末、十六國時期的官印風格相吻合[3]。不過基于現有研究成果還無法在此年代范圍內給出更為具體的斷代。
西陵縣侯本意為封于西陵的列侯。西陵是其食邑所在,檢諸文獻記載,可能為湖北宜昌、武漢、浙江杭州、江蘇南京等范圍內的古地名,但是由于其他信息匱乏,暫時無法明確其具體所指。縣侯作為封爵,秦漢以來是指食邑以縣為單位的列侯,秩次在諸王之下,封授對象多為功臣和宗室。東漢時,逐漸分為縣、鄉、侯亭三級,以詳細辨明功次等級,“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4]。曹魏以來,爵級與官品形成明確對應關系,縣侯為三品[5]。魏晉之際,官、爵合一的過程已經完成,文武功臣,莫不官爵兼備[6]。但遺憾的是,該墓中僅發現了屬于女性墓主的官印,除了能據之推測墓主丈夫曾封西陵縣侯之外,無從得知其擔任的具體官職。在僅知道墓主封爵的情況下,無法對其身份和仕宦經歷作出更加具體的推斷。因為漢唐之間的封爵制度有其復雜性,西陵縣侯是虛封還是實封、是就食本邑還是寄食他縣都無法確定。但在封授整體尚未泛濫的情況下,無論虛實,縣侯之爵級在魏晉時期仍然品秩較高,大致能反映出墓主生前的相應地位。
組佩和金飾片是墓主身份的重要標識物。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組玉佩不同于前代,據記載系由曹魏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舊佩”的基礎上重新創制。年代明確、時代較早且保存較為完整的考古發現包括山東聊城東阿曹植墓(233年)、湖南安鄉黃山頭西晉劉弘墓(306年)、江蘇南京仙鶴觀東晉高崧夫婦合葬墓(356年)。據這些發現并結合其他非紀年墓可以確認,王粲所創組玉佩是由三珩、二璜及垂珠構成的簡潔組合[7]。組玉佩通過玉色明尊卑,西晉時從天子、皇后、妃嬪、太子、諸王直至秩千石的尚書令,分別有白玉、于闐玉、采瓄玉、瑜玉、山玄玉、水蒼玉等不同的種類[8]。縣侯品秩第三,推測應該配水蒼玉。坡劉村十六國墓M2所出組佩在構成上跟前述發現相一致,特殊之處在于以銅鑄造組佩,佩體輕薄且表面粗糙,似乎流露出權宜、倉促的意味。
24件水滴形金片發現于女性頭骨周圍,可以確認是女性墓主的頭飾組成部分,一般認為應該是女性命婦步搖冠上的搖葉。類似發現在東漢晚期至東晉時期的墓葬中絡繹不絕,主要分為中原南方地區和遼西地區兩個系統。同為桃形金飾片,遼西地區花樹狀步搖葉片穿孔均在寬大一端,而中原南方地區金飾片的穿孔多在尖端[9],坡劉村十六國M2墓發現的金飾片顯然屬于后者。另外該墓沒有被盜,除金搖葉之外,沒有發現山題、枝干,再次證明中原南方地區的步搖跟遼西花樹狀步搖存在較大差異。
綜上所述,坡劉M2出土的印章、組佩和金飾片基本符合其墓主曾封授的縣侯夫人爵位。器物特征跟西晉時期同類發現相似又有新的變化,反映了該墓在年代上去晉未遠,同時還有稍晚時段動蕩、權宜的時代特色。該墓墓道填土中發現的殘磚上陰刻“天水姜沖……”,根據關中地區西晉、十六國時期墓葬中的類似發現可以認為,姜沖應該是墓主人之一[10]。同時,墓室棺中僅發現女性頭骨一例,保存狀況很好,但不知何故不見其余骨殖。隨出的“西陵縣侯夫人”印章,應該是女性墓主的生前遺物。問題是,西陵縣侯夫人是否就是墓道填土殘磚所提到的姜沖?抑或是姜沖為男性墓主的名字,但最終只有女性墓主入葬?綜合文獻記載以及這座墓觀察到的種種跡象,我們認為后者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檢諸史料,并沒有發現名為姜沖的西陵縣侯,但大致同時的文獻中有一條有關姜沖(兒)的記載。西晉末年,宗室司馬保部將陳安盤踞于秦隴地區,一度反復于司馬保和劉曜之間,最終趁劉曜患病而反叛。光初七年(324年),劉曜圍陳安于隴城(今甘肅天水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陳安率兵突圍后南下,留部將楊伯支、姜沖兒等守隴城。同年陳安兵敗被殺于陜中,“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余戶于長安”[11]。由此可見,姜沖兒是陳安屬將,后被一同守城的楊伯支斬殺于隴城。劉曜攻滅陳安勢力之后,將秦州(今甘肅天水)地區的楊、姜大族兩千余戶東遷并安置在長安地區。
坡劉M2隨葬品中的牛車、槅、樽、曲足案均可分為紅陶和灰陶兩種。紅、灰陶樽被分別放置在棺前,兩套陶質隨葬品形制差異不大,可以推定其時代大致同時。由此似乎可以合理推測:該墓在部分隨葬品的配置上應該是為兩人而準備,墓主姜沖曾任“西陵縣侯”,女性墓主也佩“西陵縣侯夫人”官印,不過由于種種原因,最終只有女性墓主入葬,男性墓主未能入葬。
為進一步確定墓葬的絕對年代,我們還對該墓出土的墨條殘塊和人牙進行了碳十四測年。數據顯示:墨條的碳十四測年結果經樹輪年代校正主要集中于65~135年(概率為61.99%),考慮到松煙墨有使用早期木料制作的可能,這一測年結果對確定墓葬的年代下限幫助不大;而人牙的碳十四測年結果經樹輪年代校正主要集中于352~404年(概率為61.14%),這一測年結論跟考古學研究所推定的年代范圍有重合之處。
該墓墓道中出土“天水姜沖……”磚志,所記郡望與文獻所見姜沖兒的活動地域相符;姜沖兒是割據一方的陳安屬將,同時也是秦州大族成員,完全有可能被封為西陵縣侯;坡劉M2規模適中,隨葬種類豐富的伎樂組合、罕見的金步搖搖葉、青瓷器、釉陶十二連枝燈和銅組佩(可能是戰亂時期的權宜之計),這些方面都跟墓主曾有的三品縣侯(夫人)封爵相符合。墓內沒有發現男性遺骸,可能跟姜沖兒被斬殺于隴城、亂軍之下尸骨無存有關。女性墓主僅余頭骨,是因為保存狀況不好還是非正常死亡,仍然不能確知。但人牙測年結果晚于姜沖兒死亡時間,且文獻提及姜沖兒死后其家族被遷置長安,因此推測女性墓主應當死于姜姓家族被遷置長安之后,最終被安葬在咸陽原上。
毋庸諱言,很多變數都會影響這一推斷的成立,尤其是考慮到女性墓主的死亡年齡和人牙測年結果均有誤差,缺乏進一步校準。即便如此,坡劉M2所蘊含的種種信息也不能簡單用巧合來一筆帶過。在目前關中地區十六國墓葬雖有一定積累、斷代仍然不夠具體的情況下,不能完全排除這座墓是姜沖兒夫人墓的可能性,且墓室中也為姜沖兒準備了隨葬品。果真如此,似乎可以進一步認為,坡劉M2的時代應該在前秦初年或稍早時期。
二、伎樂組合
墓室東壁下分布的伎樂俑是該墓隨葬俑群的一大特色。墓室東南角為釉陶十二連枝燈,燈前(西側)為1件體形較小、右肘彎處夾一束織物的女立俑(M2:39),燈后(東側)為陶雞、陶豬、捧陶盆女立俑(M2:46)、陶灶、小罐以及2件女立俑(M2:47、48)。其中M2:47手殘、M2:48雙手手掌向上平伸,這兩件女立俑跟M2:46高度相差無幾,發型、表情相近,右袖微拂,又都圍繞陶灶分布,似乎跟其北側沿東壁分布的伎樂俑無關,應當歸入反映日常居家的女侍俑行列。不過,根據朝鮮安岳冬壽墓(357年)后室東壁的樂舞壁畫[12],也不排除M2:47、48可能是樂隊中拍手、表演的角色。而M2:48以北包括8件坐樂俑在內的15件女俑則構成了一組別具特色的伎樂俑群。
這其中8件分別演奏不同樂器的坐樂俑是目前關中地區已刊布的十六國墓葬材料所僅見,接下來分別討論這些樂器所涉及的相關問題。M2:49雙手捧“笙”,此處之“笙”僅有7管,顯然是只求形似的明器,并非精確復制,因為根據不同時期的文獻記載,再結合湖北、云南等地春秋戰國以來的考古發現,竽、笙類自由簧管氣鳴樂器的管苗數量雖有增減變化,但管數從來沒有低于10管[13]。M2:50懷抱1件角形豎箜篌。箜篌有臥、豎之分,臥箜篌平置演奏、箱形共鳴箱,是起源于中原本土、有品柱的琴瑟類樂器;而豎箜篌是典型的西來樂器,其源頭在美索不達米亞,在數千年間不同文明的交往中,經中亞、新疆最終傳入中原地區。據《后漢書》記載,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14],說明至遲在東漢晚期中原地區就已經開始流行豎箜篌。以往研究多認為,甘肅永靖炳靈寺西秦建弘元年(420年)第六龕佛背光飛天伎樂中的豎箜篌是中原地區所見最早的豎箜篌形象,而坡劉M2伎樂俑所抱豎箜篌可以將這一時間提早至公元四世紀中葉甚至更早。從開孔推測這件豎箜篌只有四弦,跟以往同時期或稍晚時段的發現相比弦數偏少,可能仍然屬于“備物而不可用”的明器范疇[15]。
M2:51是一件擊鼓俑,所扶之鼓在以往材料中多根據形狀稱之為“小鼓”“扁鼓”“扁圓鼓”。此類小鼓在戰國時期楚墓中即已發現,有的腔板中部有方榫,可能跟置鼓方式有關,專名為鼙,其功能為“裨助鼓節”。在很多墓例中作為配套樂器與大鼓共出,其中“為大鼓先引”的鼙被稱為朄、朔或朔鼙,用以應大鼓或朔鼙的專稱應、應鼙或應鼓[16],亦即樂隊中的小鼓和大鼓在演奏時有呼應關系。也有人依據文獻記載稱其為“節鼓”,“節”原本是《宋書·樂志》記載漢代相和歌表演時提到的樂器,“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同書又載:“八音四曰革。革,鼓也,鞉也,節也……節,不知誰所造”[17],明確將“節”歸入鼓類。但根據《通典》:節鼓,狀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也[18]。置放方式跟坐樂俑所持小鼓差異較大,因此不宜稱其為節鼓。不過此類樂器在樂隊中的功能可能大體相似,即制造并控制節奏[19]。
M2:52手持一件長管狀豎吹樂器,推測應該是豎笛(豎吹的長笛)。依據主要有兩點:首先是該樂器的口部并沒有明顯的管哨(簧),因此應該屬于笛、簫類邊棱氣鳴樂器,排除了是篳篥、胡笳之類的簧管氣鳴樂器的可能性;其次是該樂器器身長大,豎吹時雙臂自然下垂,與演奏者身體形成較小的夾角(30°或更小),這是外削斜切形吹口樂器特有的演奏姿態[20]。盡管該樂器的口部沒有明顯的外削斜切痕跡,但考慮其明器屬性,不可能做到精確描摹,這也是討論該墓伎樂所用樂器需要時時注意的問題。伎樂中吹奏豎笛的形象在東漢畫像石和陶俑中即已流行,在江蘇常州金壇唐王村東吳墓出土堆塑罐、嘉峪關西晉M6中室西壁奏樂畫像磚、酒泉丁家閘M5(不晚于前涼)前室西壁第二層宴居行樂壁畫等也有發現[21](圖一)。以往研究有的稱之為笛,更多稱之為簫,這可能跟笛簫發聲原理有共通性有關;另外,一直以來笛簫類樂器確實存在名實混淆的問題[22]。不過,文獻中的簫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指編管的排簫,用來指代豎吹單管樂器可能在宋元之后,因此稱其為豎笛可能更穩妥一些。

圖一 酒泉丁家閘M5前室西壁伎樂
M2:53、M2:54、M2:56三件陶俑身前各置一張“琴”類樂器,三張琴各有特點,彼此不同。其中M2:53首、尾呈圓弧狀,面板墨繪六根琴弦,一側用四處白色圓點表示徽位;M2:54為圓首、窄項、聳肩,尾部圓弧,琴面墨繪五根琴弦;M2:56則尖首圓尾,面板涂白,上面墨繪七根琴弦。制式和弦數對于鑒定琴類樂器的具體種類至關重要,但是發掘出土時受保存狀況的限制,三張琴上的墨繪都存在部分模糊或掉色的問題,為此我們約請西北大學彭進業團隊采用高光譜成像儀對陶俑分析處理,將處理后的特征波段結合實物辨認,暫時將M2:53、M2:54、M2:56的弦數分別確定為六、五和七。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即便有高光譜成像技術的輔助,三張琴的弦數仍然不能完全確定,所以將其公布于此以便將來繼續深入討論(圖二)。

圖二 坡劉M2撫琴俑琴高光譜成像照片(由上至下分別為M2:53、54、56)
琴是中國本土起源的彈撥樂器,早期實物包括戰國至西漢時期兩湖地區的數例考古發現。這些琴的弦數有七、九、十弦之分,都是半箱體共鳴箱,不設徽位[23]。古琴形制在漢魏六朝時期逐漸定型,以往討論較多的有故宮博物院藏宋摹傳顧愷之作《斫琴圖》以及南京宮山西善橋大墓竹林七賢拼鑲磚畫中的嵇康和榮啟期彈琴形象,反映出東晉南朝時期的古琴已經由無徽半箱分體琴轉變為有徽全箱整體琴[24]。值得關注的還有敦煌佛爺廟灣M37和M133(西晉早期)照墻上的“伯牙撫琴”畫像磚[25](圖三)、南昌火車站東晉墓M3(352年)宴樂漆盤[26],前者琴體均呈長方形,沒有明顯的部位區分,面板上分別墨繪七根和四根琴弦,并且標記了徽位[27];后者頭寬尾窄,略呈長三角形,琴面上標出了八個徽位。

圖三 敦煌佛爺廟灣M37伯牙撫琴畫像磚
坡劉M2坐樂俑所演奏的三張琴都是全箱式琴體,雙岳山,尾岳繼續存在,但尾岳后的琴尾縮小呈圓弧狀(或尖狀),這種縮減更有利于琴體的震動與發音[28]。有的琴如M2:54已經有了項、肩等部位的區分,但三張琴整體平面仍然呈長方形,還不是東晉之后寬肩細尾的造型。三張琴的弦數各不相同,有的琴如M2:53已經標注了徽位,鑒于其明器性質,徽位和弦數的具體數量可能無法準確反映當時古琴的構造細節,三張琴的琴底平整無其他結構也可以作為佐證。同時期的其他類似發現,例如西安南郊草廠坡村十六國墓出土兩件撫琴俑,其中之一面板上可能陰刻八根琴弦[29];西安北郊頂益制面廠十六國墓出土撫琴俑,面板上陰刻四根琴弦;咸陽平陵M1撫琴俑,面板上陰刻八根琴弦[30];2009年咸陽機場二期工程發掘的十六國時期墓葬M298中出土了兩件撫琴俑,面板上分別陰刻五根和四根琴弦[31],都表明此類明器在表現上的隨意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古琴在尚未定型階段琴式、弦數的多樣化特征。
M2:55正持撥彈奏一把直柄圓盤的四弦琵琶,其形制跟西晉傅玄《琵琶賦》里的記載相符合[32]。此類樂器從唐代開始被稱為阮咸,在之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琵琶似乎是多種彈弦類樂器的統稱,包括長柄、短柄、圓形、梨形(共鳴箱)、弦多、弦少等不同類型[33]。不同類型的琵琶有不同淵源,至今仍然聚訟紛紜,具體到阮咸更是如此[34]。從考古發現來看,時代較早的琵琶形象見于四川樂山麻浩虎頭灣崖墓M22墓門上方琵琶樂伎(東漢晚期)、故宮博物院藏1939年出土于浙江紹興下窯陳村東吳墓的堆塑罐(260年)等[35],兩者都是阮咸琵琶(秦琵琶)。河西地區是早期琵琶圖像的另一集中發現區,例如嘉峪關M3和M6、酒泉西溝M7等魏晉十六國畫像磚墓,表現的也都是阮咸形象[36]。
大致同時期的關中十六國墓中的類似發現包括:咸陽平陵M1一件(圖四)、西安鳳棲原M9一件和咸陽機場二期M298兩件,均可確定為四弦。坡劉M2坐樂俑所演奏的阮咸制作稍顯精細,可以初步確定為十柱,跟傅玄《琵琶賦》里提到的十二柱有所不同,可能依然跟其明器性質有關。咸陽平陵M1、西安鳳棲原M9都持撥彈奏,咸陽機場二期M298則是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扣成環狀彈奏。以往有研究認為阮咸在關中的出現以及是否持撥彈奏具有斷代意義[37]。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古龜茲地區石窟寺的分期研究中,絕對年代問題至今仍然困擾著研究者[38],在此前提下洞窟壁畫中樂器圖像的絕對年代則有較大不確定性;咸陽機場二期M298出土的兩件彈琵琶坐樂俑仍然采用指彈,該墓目前沒有完全公布材料[39],但有研究認為其年代接近十六國后期(前秦)[40]。因此,在目前關中地區十六國墓葬斷代研究仍需深入的情況下,無法排除當時指彈和撥彈兩種彈奏方式同時流行的可能性。

圖四 咸陽平陵M1出土彈阮咸女坐樂俑
坐樂俑以北的M2:57至M2:63共計7件女立俑也應該是伎樂組合的構成部分。這七件女立俑高度接近,彼此間相差不超過0.5厘米;M2:58和M2:63手勢相同,后者左前方地面有一面鼓,因此兩者都應該是擊鼓俑。類似的鼓在草場坡十六國墓和洪慶梁猛墓中均有發現[41],區別在于坡劉M2的陶鼓無法立于地面,演奏時可能系掛于身前,演奏方式可能跟寧夏彭陽新集十六國墓出土的陶鼓相似[42]。由于位于隊列尾端的M2:63仍然是伎樂俑,這意味著她之前包括兩件擊鼓俑之間和身旁的女立俑是伎樂俑的可能性更大。這其中M2:60長臉豐頤,貌偏年長,可能是這組伎樂的主唱,M2:57、M2:61、M2:62攏袖侍立,未見演奏樂器,可能是樂隊中負責伴唱、表演的角色。
行文至此,坡劉M2墓室東壁下的這組伎樂俑的構成與性質已經基本明確:從樂器使用情況來看,除了兩種鼓之外,其余都是絲竹樂器,沒有鐘磬之類的金石樂器,絲竹樂器中又以本土樂器為主,也加入了像箜篌這樣的外來樂器;從表演形式來看,采用的可能是一人唱,馀人和,輔以絲竹聲的方式,這都跟文獻記載中曹魏、西晉宮廷流行的相和歌和清商三調相契合。一般認為清商樂源自漢代相和歌,興起于曹魏,流行并雅化于西晉,之后傳入南方與吳聲、西曲相結合,形成清商新聲,隨后一直盛行至唐代始見衰亡[43]。根據北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中相和六引部分轉引的南朝《古今樂錄》,不管是相和歌還是清商三調,所使用的樂器都是七到八種。其中各樂類共用的樂器有笙、笛、琴、瑟、琵琶、箏,相和歌跟清商三調中的清調及瑟調都有節或節歌[44],如果不糾結樂器的具體名稱而將琴、瑟、箏視為同類樂器,就會發現這跟坡劉M2的樂器配置非常接近,因為該墓伎樂也同樣有三種琴類樂器,其獨特之處在于還增加了箜篌。
總體而言,十六國時期是魏晉以來清商舊樂流散、衰落的時段。《魏書·樂志》對此有簡略記載,反映出在五十余年間魏晉清商舊樂至少輾轉流傳于劉漢、前趙、后趙、冉魏、前燕、前秦等六個北方政權的情況[45]。《隋書·音樂志》還記載了苻堅滅前涼而得清樂一事[46]。不過這些文獻更多反映的應該是樂府官署下轄的官伎流傳情況,而兩漢以來權貴豪門還流行蓄養家伎以自娛和自夸,廣蓄伎樂是世家大族權勢財富的重要象征[47]。坡劉M2墓主生前曾獲封西陵縣侯,又是秦州姜姓大族成員,應該具備蓄養家伎的實力。墓中隨葬的伎樂演奏的是曹魏、西晉以來流行的、源自漢代相和歌的清商三調。至于這組伎樂是否得自宮廷(或官方),目前還缺乏直接有力的證據。
三、隨葬品特征與分布
目前關中地區十六國墓的墓室數量有前中后三室、前后兩室和單室之分[48]。坡劉M2為單室土洞墓,墓室3米見方,不論是墓道規模、墓葬形制還是墓室尺寸都不突出。尤其是考慮到墓主曾經封授的縣侯(夫人)是三品爵位,在中古時期已經步入高級官員行列。在關中地區目前身份明確的十六國時期墓葬中,西安香積寺M5出土一枚“奉車都尉”銅印。該官職在西漢始置之時多由皇帝親信充任,秩比兩千石,以示格外優寵;魏晉時是資格較低的加官,有可能是虛號[49]。然而在沒有多人祔葬的情況下,這座墓葬卻是前后雙室土洞墓,前室尺寸與坡劉M2的墓室規模相仿[50]。考慮到坡劉M2最終只有“西陵縣侯夫人”單人入葬,依據本文第一部分的推測,這是形勢變化所造成的人生境遇的轉變。在這種情況下,該墓營造的首要動機仍然是藏尸與安魂,隨葬品的數量和分布跟墓室空間互相匹配。在當時戰亂頻仍以及目前可比對材料并不豐富的情況下,不宜從等級角度進一步引申。
與形制方面的簡約相比,坡劉M2的隨葬品更加豐富且高級,這當然跟該墓葬沒有被盜擾直接相關,但跟其他墓葬出土同類器作比較還是能發現一些問題。例如關中地區十六國墓的隨葬品多以陶器為主,釉陶器少見,瓷器更是罕見。而坡劉M2出土了一件青瓷壺,這件瓷壺出土時頸部已殘,下腹部未施釉且有灼燒痕跡。此外,釉陶十二連枝燈也非常重要。這組燈具由燈座、雙層燈盤和頂枝四部分組合而成,頂部燈盞口沿有灼燒痕跡。盡管跟漢代同類發現相比談不上有多精致,但在之前關中地區十六國墓葬中還沒有發現過如此復雜考究的同類器。這一時期墓室中發現的燈具以陶燈為主,燈盞數不多。即便是以西安少陵原焦村M25、M26和中兆村M100為代表的三座大型十六國墓葬,也不過都是九盤連枝燈而已。另外該墓發現的2件曲足案在關中地區十六國墓葬中也不常見[51]。由此可見,墓葬形制相對簡約,隨葬品級別較高是坡劉M2的特色。
坡劉M2的部分隨葬品可以分為紅陶和灰陶兩套。在以往發掘的十六國墓葬中,同類遺物例如牛車也有發現不止一套的情況。但坡劉M2的特殊之處在于多次出現分別用紅陶和灰陶制作同類器物的現象,包括陶槅、陶樽、牛車和曲足案,這很可能是有意而為之。同時,該墓葬沒有發現鞍馬、具裝鎧馬和騎馬鼓吹,除了2件牛車車夫之外,也沒有其他男性俑。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即同樣是牛車,西壁下靠北的M2:27(灰陶牛車)除了一件男立俑(M2:28)之外,北側緊靠牛車還放置了4件女立俑(M2:29、31、30、32),而西壁下靠南的M2:24(紅陶牛車)僅放置了1件男立俑(M2:25),這或許能反映出2套隨葬品中可能蘊含的性別信息。結合該墓發現的“西陵縣侯夫人”印章,似可推測墓中隨葬品仍然主要圍繞女性墓主設置,其中灰陶的那一套可能是為女性墓主而準備。
坡劉M2是一座單室土洞墓,僅在墓底的北半部分鋪設方磚,用來安放木棺,最前(南)排居中的兩塊方磚上放置一組灰陶樽和陶勺,暗示出以供奉為核心的墓內祭祀活動的存在。事實上前排方磚已經距離甬道不遠,在墓門封閉之前,這部分空間得以保留而沒有放置隨葬品,可能跟推棺入室以及開展墓內祭祀的需要息息相關,這也是隨葬品最終被安放在墓室前(南)半部東、西兩壁下的直接原因。在隨葬品分布方面與坡劉M2類似的是附近發掘的平陵M1,該墓同樣未被盜擾,墓室規模稍小,隨葬品更加豐富。人骨雖然腐朽不可辨認,但俑群中有鎧馬、騎馬鼓吹,還發現了鐵矛和釉陶虎子,墓主為男性的可能性更大。該墓同樣木棺居北,隨葬品在墓室前半部東西兩側分布,東側隨葬品種類相對簡單,包括騎馬鼓吹、鎧馬等。西側隨葬品種類更多,包括坐樂俑、女侍俑、牛車及軺車、日用器模型、家畜俑以及實用器,觀察不到清楚的分布規律與邏輯關系,更像是東側隨葬品擺放完畢之后,將剩下的隨葬品統一放置在西側。
綜合目前已刊布的關中地區十六國墓葬,木棺在墓室中的位置并沒有形成固定規律,祔葬墓則更加復雜。而隨葬品在墓室中的分布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包括木棺在墓室中的位置、墓室中可能進行的入葬活動和祭祀儀式、隨葬品本身的象征意義以及當時社會流行的喪葬觀念等。在多數墓葬被盜擾、年代框架尚未完全確立、可供對比分析的個案較少且沒有充分評估各項影響因素的情況下,對隨葬品的分布及其意蘊的討論仍然只能局限于個別保存較好的案例之間。
四、結語
坡劉M2出土的印章顯示墓主曾獲封“西陵縣侯夫人”,這是該地區罕見的墓主身份明確的高等級墓葬。首先,以印章、組佩和金飾片為代表的隨葬品基本能夠對應墓主的縣侯夫人身份,其隨葬品的時代特征源于漢晉又去晉未遠。綜合文獻記載和觀察到的考古現象,初步推測“西陵縣侯”很有可能是晉末在隴城被斬殺的姜沖兒,而“西陵縣侯夫人”應該是姜沖兒的夫人,平隴城之后被遷置長安,最終安葬在咸陽原上。因此,可以進一步推定坡劉M2的時代為前秦初年或更早。其次,逐一分析墓室東壁下的伎樂組合,根據樂器名實和樂工身份,推測這套伎樂更有可能是世家大族蓄養的家伎,其組合配置跟漢晉以來流行的清商三調相契合。最后分析了墓葬的規模、特征與隨葬品分布,認為墓內祭祀活動及其對應空間的存在最終決定了該墓隨葬品的分布格局。
21世紀初咸陽十六國墓葬陸續公布之后,關中地區十六國墓葬一反20世紀長期沉寂的局面,進入迅速積累階段。新材料持續刊布,更多重要材料尚在系統整理中。坡劉M2跟平陵M1情況類似,是關中地區目前少見的未被盜擾的十六國時期墓葬,同時墓主身份相對明確、伎樂組合更加豐富。相信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這座墓所蘊含的豐富歷史信息會得到更加全面的解讀。
[1]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咸陽坡劉村十六國墓M2 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23(2).
[2]孫慰祖.西晉官印考述[C]//上海博物館集刊(第7 期).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53-70.
[3]孫慰祖.中國璽印篆刻通史[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137-163.
[4]范曄.后漢書:百官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5:3630.
[5]杜佑.通典:職官(第36、37 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8:991,1003-1004.
[6]楊光輝.漢唐封爵制度[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15 9-166.
[7]褚馨.漢唐之間組玉佩的傳承與變革[J].考古與文物,2012(6).
[8]a.左駿,等.中國玉器通史(三國兩晉南北朝卷)[M].深圳:海天出版社,2014:59-60,表1.b.房玄齡,等.晉書:職官志(第24 卷)[M].北京:中華書局,1974:730.“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納言幘,五時朝服,配水蒼玉。”
[9]韋正.金珰與步搖—漢晉命婦冠飾試探[J].文物,20 13(5).
[10]李朝陽.陜西關中出土的西晉十六國時期磚志考述[J].文博,2012(6).
[11]崔鴻,等.十六國春秋輯補:劉曜(第8 卷)[M].北京:中華書局,2020:91-92.
[12]洪晴玉.關于冬壽墓的發現和研究[J].考古,1959(1).
[13]a.張振濤.和、巢、竽、笙辨:關于簧管類樂器發展史的若干思考(上)[J].武漢音樂學院學報,1996(4).b.張振濤.和、巢、竽、笙辨:關于簧管類樂器發展史的若干思考(下)[J].武漢音樂學院學報,1997(1).
[14]同[4]:3272.
[15]賀志凌.箜篌考[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9:14-2 1,248-274.
[16]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6-23.
[17]沈約.宋書:樂志(第21、19 卷)[M].北京:中華書局,1974:603,555.
[18]同[4]:3667.
[19]有關“節”的更詳細討論參見:王志清.東晉南朝音樂文化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118-126.
[20]王金旋.絲綢之路考察中發現的問題—古代豎笛出現年代新論[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4(1).
[21]a.《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總編輯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上海卷江蘇卷)[M].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272,圖2·2·6b.b.《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總編輯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甘肅卷)[M].鄭州:大象出版社,1998:245,圖2·7·4;256,圖2·8·1b.
[22]萬博.中國古代笛簫類樂器名實問題研究中的歧義與焦點[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2017(2).
[23]同[16]:448-455.
[24]全箱整體式琴是否一定由半箱分體式琴演變而來尚有爭議,此處僅是根據考古發現(主要是圖像材料)表達這種形制上的變化已經發生,具體參見:王子初.馬王堆七弦琴和早期琴史問題[J].上海文博論叢,2005(4).
[2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佛爺廟灣西晉畫像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五三1,圖版五四.
[2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火車站東晉墓葬群發掘簡報[J].文物,2001(2).
[27]方笑天分析了琴的形制、徽位及演奏方法,認為河西地區彈琴聽琴圖中對琴樂演奏的刻畫是錯誤的,可能是由于畫工對琴樂演奏本身缺乏理解。參見:方笑天.似與不似之間—河西魏晉壁畫墓中的“伯牙彈琴”與“李廣射虎”[J].美術觀察,2018(1).
[28]丁承運.漢代琴制革故鼎新考—出土樂俑鑒證的滄桑巨變[J].紫禁城,2013(10).
[29]中國國家博物館.中華文明:古代中國陳列文物精萃[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453.
[30]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陽十六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94,彩版141.報告中稱其為撫箏俑,圖像資料尤其局限,琴箏不好區分,但根據文獻記載及江西貴溪、江蘇吳橋等地春秋戰國時期的實物發現,箏整體呈船形,箏面微弧拱,箏首下弧,箏尾上翹,箏的弦數更多,為十二或十三弦,且弦下有柱碼。西安頂益制面廠、咸陽平陵M1 以及咸陽機場M298,其坐樂俑所奏之樂器跟這些特征無一符合,因此本文統稱其為撫琴俑。具體可參見王子初.中國音樂考古學[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242-246.
[31]孫偉剛,等.大音希聲:陜西古代音樂文物[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16:132-134.
[32]同[5]:3679.
[33]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冊)[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129.
[34]趙志安.漢代阮咸類琵琶起源考[J].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01(4).
[35]a.《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總編輯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四川卷)[M].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182,圖2·3·19.b.《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總編輯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北京卷)[M].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172,圖2·1·8b。
[36]同[21]b.
[37]周楊.關中地區十六國墓葬出土坐樂俑的時代與來源—十六國時期墓葬制度重建之管窺[C]//西部考古(第14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119-124.
[38]魏正中.區段與組合—龜茲石窟寺院遺址的考古學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64-65,172-178.
[39]劉呆運,等.陜西咸陽底張十六國至唐代墓葬[C]//2010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36-139.
[40]韋正,等.民族交融視野下的十六國墓葬[J].中原文物,2022(4).
[41]a.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南郊草場坡村北朝墓的發掘[J].考古,1959(6).b.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陜西西安洪慶原十六國梁猛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8(4).
[42]a.寧夏固原博物館.彭陽新集北魏墓[J].文物,1988(9).b.韋正.關中地區十六國墓葬研究的幾個問題[J].考古,2007(10).
[43]相和歌和清商樂是漢魏六朝音樂史研究中的焦點之一,相關研究成果極多,本文僅取其一般性結論,參見a.王運熙.樂府詩述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b.黎國韜.清商樂與清商曲辭論集[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8.
[44]相關討論參見[19]:112-113.
[45]魏收.魏書:樂志(第109 卷)[M].北京:中華書局,197 4:2827.
[46]魏征,等.隋書:音樂志(第15 卷)[M].北京:中華書局,1973:377.
[47]a.張承宗.三國兩晉倡伎考[J].襄樊學院學報,2007(3).b.張承宗.六朝倡伎考[J].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c.張承宗.北朝倡伎考[C]//北朝研究(第六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164-169.
[48]三室墓和規模較大的雙室墓參見師念.西安少陵原十六國大墓:撥開歷史的厚土 揭秘民族融合的故事[N].陜西日報,2021-4-14(8).
[49]董劭偉.西晉加官制度考述[J].晉陽學刊,2006(6).
[50]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香積寺村十六國墓地發掘簡報[J].中原文物,2021(1).
[51]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曲足案(包括圖像資料)的研究,參見班琳,等.淺析大同地區北魏墓葬中所見曲足案形象[J].云岡研究.2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