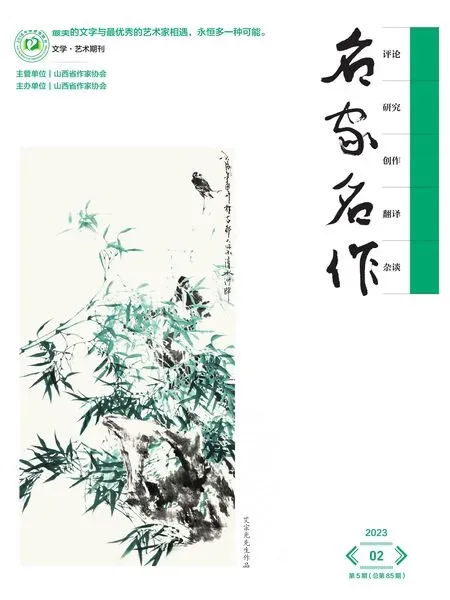全球視野下中國唐代美術史重構的可能性
——以唐代康善達墓中的《胡人馴馬圖》為切入點
趙翊方
唐代是中國古代藝術史上的一個高峰,不僅在繪畫、雕塑、建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審美觀念。然而,在中國文化史的長河中,對唐代美術史的研究一直存在著種種問題和爭議。首先,傳統的唐代美術史研究大多以中心城市為研究對象,忽視了在唐代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影響的邊疆地區的藝術遺產;其次,唐代美術作品的傳世數量有限,許多珍貴的作品已經失傳或毀于戰火;最后,唐代美術的創作和發展受多種文化因素影響,需要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和視野。
近年來,隨著考古學和文物保護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唐代藝術遺存被發掘和重新評價,這也為我們重新審視唐代美術史提供了機會。本文以2020 年陜西西咸新區空港新城發掘的康善達墓墓道西壁壁畫《胡人馴馬圖》為切入點,探討全球視野下中國唐代美術史重構的可能性。
一、唐代壁畫的特點和西域文化的影響
唐代是中國藝術發展的高峰時期,其壁畫藝術也融合了多種不同的藝術風格。其中,墓室壁畫是中國古代壁畫的重要代表,其具有色彩鮮艷、構圖豐富、造型優美、融合多種藝術風格和主題豐富等特點,是中國古代壁畫藝術的珍貴遺產之一。唐代壁畫體現了中國古代藝術的高度成就,展現了當時社會和文化的多樣性,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也在文化交流和藝術互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程度最高的朝代之一,其與西域地區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頻繁。唐代時的西域地區包括今天的新疆、甘肅、青海等地,這些地方曾經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在這些地方得以交流和融合。因此,唐代墓室壁畫中也不乏西域文化元素,如西域人物形象、題材內容、藝術風格等。唐代墓室壁畫中的西域文化元素不僅豐富了唐代壁畫的內容和形式,體現了唐代文化的多元性,還反映了當時唐朝和西域文化之間的交流和融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二、康善達墓《胡人馴馬圖》的歷史背景、藝術價值及對唐代美術史的意義
2021 年1 月,陜西省考古院在陜西省西咸新區空港新城底張街道布里村發掘了兩座唐代墓葬。其中一座,根據墓志可知墓主為康善達,墓道西壁的《胡人馴馬圖》(見圖1)描繪了一位深目高鼻絡腮胡、頭戴帽的胡人馴馬的場景,畫面中白馬形象有很強的線條勾勒感,掙扎姿態栩栩如生,胡人左手牽韁、右手揮鞭、身體后傾的馴馬姿勢很是生動。這幅壁畫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不僅技法精湛、構圖新穎,而且鮮活地表現了當時胡人對馬的馴養技術和文化生活的場景,具有很高的歷史和人文價值。康善達墓所處的時代是初唐時代,眾所周知,唐代文化和藝術發展的高峰時期以及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時期是唐朝中晚期,因此如此精美的唐代初期墓葬壁畫的發現就顯得很是珍貴。

圖1 康善達墓墓道壁畫《胡人馴馬圖》(圖片來源: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康善達墓的墓室結構完整。據考古工作人員初步估判,墓主人康善達籍貫為原州(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之粟特人,生前擔任過左驍衛親衛、東宮烏城監丞、咸陽監等職,在初唐時代從事馬政事務。馬政在唐代有著特殊的地位,唐王朝將養馬業完全納入了政府的行政體制管轄之中,有著完備的管理運營機構。在中央一級,太仆寺、駕部、司乘局、閑廄使四大部門專事馬政各項全國性的行政管理,而在地方政府,則有著相當嚴密的監牧體制對養馬業進行專項行政管理。比如,監牧以馬的多寡來確定其等級,五千匹馬是上監,三千匹馬是中監,三千匹以下則為下監。而根據墓志所載,康善達以及他的父親皆任職監牧,為地方政府之馬政官員。監牧的品秩為從五品下至六品下之間,屬唐政府中的中下級官員。
康善達及其父親因均有任職于帝國政府中養馬官員的經歷,所以在死后,遵《荀子·禮論》中“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視死如生,視亡如存”的葬制。
根據業已公布的部分考古信息,康善達墓內的大部分明器已不復存在。其中在西面墻壁的出行圖《胡人馴馬圖》中可以看到,不論是畫者捕捉到的馬之瞬間形態,還是馴馬人的剎那間的定格,通過明快、爽勁的線條和細部大膽、簡潔的刻畫,融匯成了一種靈動而極富韻律感的繪畫語言,也由此賦予了馬與人之間巨大的視覺張力,其生動傳神之態咄咄逼人,足以穿越時空,將唐帝國時期視覺藝術表達所能抵達的高度淋漓盡致地體現了出來。
中國繪畫史中對馬的描繪與再現到了唐朝已經形成了獨立的畫科,是為“鞍馬”科。曹霸、韓干、陳閎、韋偃、韓滉、戴嵩六人俱聲名顯赫于有唐一代。之后,跨越一千三百余年至今,他們亦始終存在于中國藝術史的敘事之中。但非常遺憾的是,這六位藝術大師的作品于今日已因時間的淘洗而鮮有存世,無學術異議的恐怕也就是韓干絹本《照夜白圖》(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牧馬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神駿圖》(遼寧博物館藏)、《呈馬圖》(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藏)了。在僅有的四幅有關馬的絹本視覺文獻中,正因為出自一位藝術家之手,馬的形象風格,馬與人的形象風格,以及對馬的姿態的捕捉,從本質上來說有著同一性,或者叫作同趨性。那么言及至此,在中國藝術史的繪畫敘事中,唐代“鞍馬科”的呈現似乎有一定的單調性,即使杜甫詩歌中曹霸所繪的馬令人心馳神往,但也從本質上可以看到,在探討唐朝時期的藝術史時,更多的關于作品與藝術家的敘事多為文字文獻的一次次編輯與組合,這一點顯然在藝術史敘事中存在著某種因具體圖像的缺失而顯現出來的悖論。
綜上所述,康善達墓《胡人馴馬圖》對研究唐代美術史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它豐富了唐代壁畫的題材和內容,呈現了唐代文化和西域文化之間的交流和融合,擴展了我們對唐代藝術的認識和理解。其次,它揭示了唐代胡人對馬的馴養技術和文化生活的場景,反映了唐代社會的多元面貌和文化風貌,為我們了解唐代社會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最后,它表現了唐代壁畫藝術的高度成就和創新精神,為我們探討唐代藝術史的演變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和參考。
三、全球視野下唐代美術史重構的思路
唐代美術史是中國古代美術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對于推動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和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自20 世紀以來,中國學者對唐代美術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不僅詳細闡述了唐代繪畫的藝術風格、內容、技法等,而且為后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但這些研究也有些許的不足之處,其中一點是往往缺乏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和對比,缺乏全球視野的宏觀把握。
唐康善達墓《胡人馴馬圖》的考古發掘,從全球視野來看,除了對唐朝時期鞍馬畫科的重要補充的意義探討之外,也可以探討藝術考古學與藝術史的敘事的關系。藝術考古學與藝術史敘事的關系,或者稱作進入范式,往往止于對藝術史中文字文獻的佐證,及對圖像文獻的豐富,它們對藝術史的敘事框架所起到的修正作用是更有力的。
那么,為什么要談到藝術史敘事框架的修正問題呢?簡而言之,隨著西學東漸,中國的藝術史敘事框架基本上都是沿著西方藝術史的理路在發展,從一開始的傅抱石的《中國繪畫變遷史綱》、潘天壽的《中國繪畫史》到現在汗牛充棟的諸多藝術史學家的著作,其內在核心的敘事邏輯,正如羅杰·弗萊(Roger Fry)在《論英國繪畫》(Reflections on British Painting,1934)一書中所言:“從某種角度來看,整個藝術史可以歸結為一部不斷發現外觀的歷史……自喬托(Giotto)時代起,歐洲藝術便不斷地沿此方向發展著。”
羅杰·弗萊的這一觀點,可以理解為藝術史在層累地以“新發現”文獻(文字/圖像)為主旨,不斷地更新,重新進行敘事。將羅杰·弗萊的觀點轉換成中國傳統史學的敘述,本質上其實就是“史識”的不斷擴充。而20 世紀80 年代以來,諸多中國藝術史敘事的寫作,也恰恰與羅杰·弗萊對藝術史的理解認知形成了一種從內到外的自洽與閉環狀態,特別是在20 世紀80 年代以降的四十年來,在基礎建設蓬勃發展的前提下,地下文物與過往相比更多地被發掘出來,以及隨著考古學專業的細分,藝術考古學學科建設的不斷完善,為這種寫作提供了巨大且客觀的可能性。然而,在這種“可能性”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兩個問題:第一,考古文物與藝術考古的終極目標是否就只是新文獻(文字/圖像)的發現呢?第二,藝術史的敘事是不是只能單向地接受這種“新發現”,并不斷地隨著更多的“新發現”而進行補充修正甚至重寫?
其實,從學理出發,藝術史學家貢布里希對羅杰·弗萊的“新發現”很早就委婉地提出了某種質疑,他認為藝術史學家“只能去‘發現’那些一直存在的東西”。貢布里希的言下之意是,在藝術史學家面對“新發現”之外,應該還有另外的可能性存在,這些“新發現”除了為已成規制的藝術史敘事提供重寫(更新)的動力之外,是不是還可以作為某種獨立的存在,并與藝術史中已有的文獻進行某種有效的分離,以此來重構藝術史呢?換而言之,文物發掘、藝術考古的作用、意義、目的將得到擴展,成為某種藝術史敘事的主體。
貢布里希對羅杰·弗萊委婉地提出質疑,是針對約翰·康斯泰勃爾的作品《埃塞克斯的威文霍公園》而言,他從現代知覺心理學的角度,陳述了約翰·康斯泰勃爾的藝術表達的實質——我們生來就有能力從空間和光線的角度去闡釋視覺印象,藝術語言的真正奇妙之處實際上并不在于它能夠使藝術家創造出現實的幻象……藝術家還會向我們呈現隱匿的內心世界的幻象。那么順著貢布里希之于藝術表達的陳述的思路,完全有理由以藝術考古學為起始點,在面對那些挖掘出的文物(藝術品)時,從藝術表達的意義、目的來進行敘述,進而使得藝術考古學本身成了去重構某個時代藝術史的內在動力,將藝術考古學從較為單一的文獻式意義中抽離出來,賦予其更為多元化的內涵。
以康善達墓中的《胡人馴馬圖》為切入點,從藝術表達的意義、目的的角度去看,唐代藝術史敘事除了具有補充擴展了唐代鞍馬畫科的圖像文獻意義、美學精神和神學(石窟佛寺壁畫)意義之外,還具有獨特的世俗化表達,這在與唐朝同時期的拜占庭藝術以及希臘羅馬化的中亞、南亞藝術中都較為少見。但這種世俗化的藝術表達在唐朝的藝術史敘事中所占比例還是較大的,本身的鞍馬畫科所留存的絹本作品就是世俗化的藝術表達。而那些近世以來出土的唐代壁畫,比起絹本作品的數量要多幾千倍,足以和唐代具有神學意味的宮觀石窟壁畫等量齊觀了。
在以往的中國藝術史敘事范式里,唐代繪畫的美學精神闡釋和神學宗教意義的敘述是主流,有關世俗化的藝術表達意義鮮有牽涉。而以全球化的視野來看,藝術史中的美學精神意義和神學宗教意義,在同一個時期不同的地域都會有所重合,尤其是拜占庭藝術、唐朝藝術、中亞南亞藝術在藝術表達的目的與意義方面多有相似之處,都是為了神所服務。唐朝時期的藝術史敘事與同時代的拜占庭藝術、中亞南亞藝術的真正的分野,恰恰就在于藝術考古學針對墓葬壁畫藝術表達的世俗化敘述——視死如生,視亡如存。更深入地進行思考亦可以清晰地看到,唐朝時期墓葬壁畫的藝術表達世俗化的最高目的,不是美學精神的追求,更不是神學意義的呈現,而是超越了二者,以社會倫理性藝術表達為目標的藝術史敘事策略。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應該以跨文化交流和多元視角為基礎,重新審視和研究中國唐代美術史。首先,我們需要正確看待外部文化對中國唐代藝術的影響,比如西域文化、印度文化等,同樣也要關注唐代藝術對外部文化的影響,如唐代壁畫對日本藝術的影響等。其次,我們應該突出唐代藝術的地域差異和多元性,注意各地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特點,比如唐代長安、洛陽、揚州等地的藝術風格和特點,以及唐代中原文化、南方文化、西北文化等的交流和融合。最后,我們需要借助現代科技手段,如數字化技術、虛擬現實技術等,將唐代藝術進行數字化重構和再現,為我們深入了解唐代藝術提供更多的途徑和手段。
四、結語
康善達墓發掘的《胡人馴馬圖》是一幅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的唐代壁畫。它展現了唐代文化和西域文化之間的交流和融合,揭示了唐代胡人對馬的馴養技術和文化生活的場景,反映了唐代社會的多元面貌和文化風貌,表現了唐代壁畫藝術的高度成就和創新精神。以康善達墓《胡人馴馬圖》作為切入點,以整個唐朝墓葬壁畫為主體,以藝術表達方式為主線,將社會倫理性作為核心敘述源的藝術斷代史,以此重構的藝術史必然跳脫出了西方藝術史的敘事框架與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