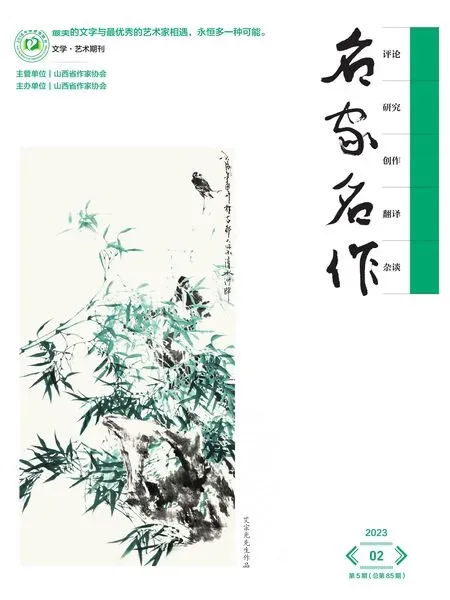“純靜”之界
——品鄭波的繪畫藝術
胡書靈
藝術家的自我應該是完整、穩定、獨一無二的,由這種自我來統一內心,引導行動和意向,并將豐富的思緒貫穿于完整的藝術創作。他們的藝術作品將形式的表達與自身的氣質還原到最本真的層面,糅合為一個獨立的精神世界。
一、藝術家鄭波的生平簡介
藝術家鄭波是沈陽魯迅美術學院油畫專業“黃金一代”的藝術家之一。他成名于1993 年受邀創作的芝加哥機場壁畫《芝加哥印象》(見圖1),這幅應邀為芝加哥繪制的大型壁畫被美國政府永久收藏。如同喬治·修拉的《大碗島的星期天下午》,藝術家在作品中展現了一座城市的浪漫閑逸,形色各異的人們被朝氣蓬勃的油綠色所襯托,代表著特殊含義的和平鴿以散點的形式貫穿于畫面的其他重要空間。

圖1 《芝加哥印象》(1993 年) 鄭波/作
二、鄭波作品的形式語言與藝術特質
優秀的藝術家筆下的世界比我們所見的更豐富、有趣,而這一切是基于其獨特的藝術感知和個人經歷,并將其對世界的理解融合在這一方畫布之中。在鄭波20 世紀90 年代的創作中,很多作品都圍繞“西藏”這一主題。《佛事慶典》《她們從山那邊走來》《藏北風情》這些早期畫作充溢著質樸的人文氣質和純凈的地方特色,體現出淳樸民俗洗滌的印痕,他在1985 年至1986 年的藏區考察中儲備了能量,不斷地醞釀和探索著自己的藝術風格。著名藝術家、評論家許榮初先生評論道:“從黃河考察歸來的鄭波謹慎地找尋著能表現他心態的油畫語言,找尋著屬于他自己所特有的造型意識和色彩情緒。”他將鄭波的作品形容為一方純凈的土地,并指出正是多次的西藏之行淬煉了這位青年藝術家。
鄭波在自己的藝術世界中不斷前行,他的作品愈發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美感。在畫面的構圖上,水平線分割畫面的手法多次出現于他的作品之中:廣袤戈壁之上的地平線、遠景起伏山巒的水平輪廓、直線分割的構圖語言出現在他的多幅作品中。這種構圖給觀者帶來心靈上平靜的安撫,令作品充滿神圣的審視感,觀者能從畫面中感受到畫家對自然和精神信仰的強烈敬畏。在形態的處理上,鄭波一直習慣于將人與物的輪廓清晰化,運用歸納手法去處理各個形象,這種方式有一種干凈利落、純粹又獨特的裝飾味道。他對光下事物的處理是帶有極強目的性的,有時為的就是削弱光影對物象的影響,形體明明存在于光之中卻不依賴光影來塑造,便形成了純靜、唯美的視覺效果。在作品《牧羊女》(見圖2)中,依舊是神秘沉靜的水平線構圖,加以垂直的人物造型,從視覺上強化了神圣感,被均勻打散的光影關系呈現出沉穩柔和的色調。作品中的女孩不卑不亢,遠處的羊群和風景和諧且溫潤,有一種靜謐的美感。筆觸與色彩在不斷的交相輝映中凝結為風格,這種“純和靜”利萬物而不爭,成為畫家獨有的自我表達。

圖2 《牧羊女》(2005 年) 鄭波/作
也許在平面中將三維事物轉化為二維并不費力,但能把對三維事物質感的主觀感受通過筆觸展現于二維畫面之中便是極為高級的了。鄭波對自然中真實肌理的處理方式非常有趣,他將由視覺得來的觀察記憶進行轉化和處理,從中抽離出最理想的色彩分子,并用細化到了極致的筆觸進行表述。被歸納的形象絲毫沒有脫離自然本身的真實,這不難讓人聯想到塞尚“為追求視覺的真實感受,而弱化細節,減化光影效果”的表現手法。他用消失了邊界的筆觸和弱化了光影的形態表現著他主觀中的自然,含蓄穩重的色彩讓畫面沉靜下來,展現出純靜的境界。整個畫面運用了極其細膩的寫實手法來表達,而這里的寫實,并非簡單的寫實、普通意義的寫實,因為它同時也擁有超現實的簡潔和概括。在第十一屆全國美展“提名獎”作品《哈薩克族的一家》(見圖3)中,鄭波用他細膩的筆觸“寫實”著畫面中呈現的一切,準確的形體塑造、質樸的色彩表現、標志性的水平線構圖,都是他的獨特風格。被凈化的光影既是技術又是目的,畫家在觀看了一個場景之后,會自然鏡像出一個更加清晰、寂靜的主觀世界,再將這種靜傳遞給觀者。《哈薩克族的一家》中僅有的動態要素是緩緩升騰的熱氣和哈薩克婦女正在熬制的羊奶,看著這幅作品,我們會不自覺地安靜下來,安靜得仿佛聽到了羊奶從大勺里傾倒而出的聲響。當然,在這樣靜美的畫面中,所有動態都出自觀者自己的想象,這與觀看大衛·霍克尼《大水花》的感受如出一轍,那種激烈升騰的動勢更加襯托了周遭環境的靜謐。

圖3 《哈薩克族的一家》(2006 年) 鄭波/作
三、精神之美與哲學之美
表現力量的美也曾經出現在他的西藏系列作品中。全國美展入選作品《摔跤》中,他將摔跤這一藏族傳統競技做了凝結一瞬的定格,他曾說希望營造出一種即將消失又永久存在的記憶,讓一瞬間的精神之美在畫面中成為永恒。近些年,鄭波的創作仍保持著心無旁騖的沉靜,但在作品題材和表現形式上發生了改變,這種變化與嘗試使得作品在沉穩之中越來越多地呈現出精神的意象。2017 年,他多次與藝術家好友前往東北的山林景區和村縣,秋季的楓林山谷山色裊裊,玉米收割,秸稈燃燒,在一片灰棕中蘊含無數的細節與色彩。他這一時期的作品都圍繞著“純樸自然”這一母題。
《春意》和《大地原生態西紅柿即興一號》(見圖4)這兩幅作品的主題都是植物。我們看到的依舊是細膩的筆觸、舒適的灰調,與之前清晰表達的場景的不同之處在于畫面紛繁模糊的形象展現了一種無法言表的生命之美,它代替了藝術家對場景既定記憶的刻畫。木心說:“藝術家可以寫實,可以寫虛,最好以自己的氣質而選擇。”在這兩幅作品中,鄭波準確地找到了東方寫意與當代油畫的巧妙結合,散發出獨特的氣質。在《大地原生態西紅柿即興一號》中,以往常見的水平線構圖同所有光影一并消失,紛亂復雜的線條交錯形成了眾多視覺細節和層次,春天在紛繁中綻放,顯露出無限的生命之美。而在畫面構成中,多個植物枝葉形成的力被趨向于中心的力抵消,并最終融入了清涼的色彩之中,這些仿佛從中國畫中走出的淡彩,明亮、愉悅,讓本應波濤洶涌的生命贊歌在觀賞者的心底安靜地流淌。

圖4 《大地原生態西紅柿即興一號》(2018 年) 鄭波/作
鄭波一直在不停地探索,他近幾年的創作逐漸向抽象表達轉變,試圖通過畫面的“純粹感”體現強烈的精神性和崇高感。蒙德里安曾說:“生命的機械自動化是引領藝術家從具象走向抽象的動因。”鄭波的創作探索從形式和構思上都在印證著這一觀點。比如2020 年的作品《向自然致敬!》(見圖5)。藝術家將辯證的世界觀貫穿這幅畫作,這不僅源于創作中的哲學思考,也體現在作品的觀看之道中。這幅作品在觀看時可以橫置也可以豎置,在橫與豎的狀態轉換中,直覺性地反映了自然世界與人造世界之間的沖突與和諧。當作品被橫置時,這是一幅用抽象手法表現的風景畫,群山與它在水中的倒影交相輝映,一個用構成語言表達的自然世界在靜謐的藍綠色調下熠熠生輝。而當作品被豎置時,山巒消失,一組新物像出現,由于它的直線語言和極致的對稱,我們可把它理解為機械一般的人造產物,或一朵仿造自然的美麗花朵,平衡與對等的力量是對普遍及和諧的最純粹的描述,這些生命最基本的固有特質在被抽象的自然中,呈現出“自我宇宙合一”的內涵。

圖5 《向自然致敬!》(2020 年) 鄭波/作
當我們靜心凝神去觀看它,橫置的畫面讓我們感覺靜如止水,豎置的畫面又呈現出令人崇敬的神圣。“空中有物,物中有聲”,這幅作品所迸發出的視覺感染力,連同作品形式所呈現的語義內涵引發觀者的無盡思考。不僅因為作品的形式賦予作品感染力,也因不同的觀看形式而喚起觀者的審美感受,這種存在于觀看之中的玄機,亦可以被當作一種對當代藝術實踐精神的反饋。
四、“純靜”之美
王國維說 :“無我之境,人惟于靜中得之。”這里的“靜”是創作形式與自我內在精神實現和諧統一的產物,鄭波創作中的靜正是他主觀精神的轉化和闡釋。在新的創作中,他的畫作逐漸體現出理性哲學的高度,又彰顯出“無我之境”與“有我之境”的融通。這種自我氣質與作品氣質統一的境界來自生活中的安靜與樸實。就是這樣的一位藝術家,從不追逐潮流,只是沉浸在旁若無人的世界中積淀著至靜至美的藝術。這“純靜”之美,正是來自他對藝術的單純熱愛及一份安守崇高精神之地的執著,而這種境界也深深地植入了他的繪畫藝術之中,不斷地帶給觀者與眾不同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