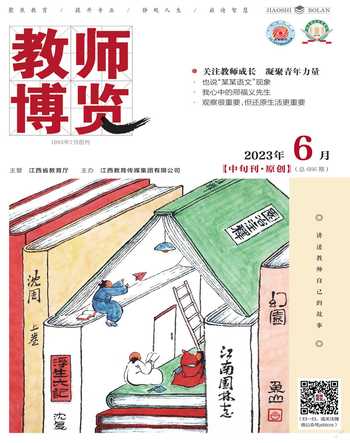《狂飆》:是“掃黑”的故事,更是“人”的故事
沈魯


2023年初,一部名為《狂飆》的電視劇“狂開飆走”,社交媒體上許多人都在熱議著“高啟強”與“張頌文”、“安欣”與“張譯”、“強盛集團”與“刀哥”,甚至劇中警察安欣曾經推薦高啟強閱讀的《孫子兵法》與《紅樓夢》也跟著“沾光”被討論。該劇以2000年至2021年間的中國經濟社會變遷為敘事背景,以新時代“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為基本題材,講述了一個名叫“高啟強”的卑微小人物如何成了掌控“京海市”諸多經濟資源、官場資源甚至他人榮辱與生死的所謂“大佬”的故事。而同樣普通平凡的警察“安欣”,與“高啟強”展開了長達20年的“對手戲”。“高啟強”是現實主義的“紅與黑”,“安欣”是理想主義的“善與圣”。本劇劇情環環相扣,細節豐富生動,折射出在經濟社會劇烈變遷的“最好與最壞”的時代里,人性撕扯酣斗的當代“浮世繪”。
《狂飆》之所以好看,主要還是因為全劇在形式上展現了包括“警匪”“黑幫”“動作”等在內的類型化元素本身的敘事魅力,同時也結合自身的創作環境與傳播環境,將文藝氣息貫穿始終。在“掃黑除惡”的陰郁悲壯氣氛之中,總有人性的無奈與抗爭,也還有令人糾結、難以釋懷的另類英雄。《狂飆》在故事的原創性上并不強,基本上依然是“文藝為掃黑除惡常態化服務”的“主旋律套路”。劇中不乏一個個精心構造又好似無心介入的兇案現場,也不缺少機警、冷靜、老練的公安干警。從這個意義上說,《狂飆》夠冷靜、夠老道、夠類型化,形式上至少具備了一般消費意義上的“賣相”,有收視率的基本保障。不過《狂飆》也并不是最好的反黑刑偵劇,之前我們已經有過《黑洞》與《黑冰》。而且與這兩部以往同類題材的電視劇相比,《狂飆》在反思與批判上顯然不如前兩作。但《狂飆》依舊好看、耐看,而最好看、最耐看的與其說是全部劇情,不如說是我們全程最聚焦、最牽掛、最不解也是最矛盾的一個關注對象“高啟強”。
張頌文飾演的這個“高啟強”究竟是個怎樣的人?他可能是一個尊重生活慣性的人。無論是作為“成功商人”時,還是在扮演“黑老大”玩弄權謀與實施犯罪時,他總認為在慣性的流程里,你要做的就是果敢地下決斷,不要考慮該不該做、怎樣做,因為人的一生中做決定的時間并不多。這基本就是高啟強的人生觀,當然這也是為什么他最終犯下一個又一個令人扼腕而又深感不安的罪案的原因。高啟強的堅毅、冷靜與自信源于他對慣性的堅定執著,當然他的冷酷與自私也源于此,他不希望任何一件事情脫離他的設計與掌控。因而可以說,高啟強在劇中是所有“男人”的心性代言符號——主流價值觀里,男人通常都是這樣,目標明確、策略簡潔、執行果敢,當然很多時候這些特質又會轉變為目標單一、邏輯嚴苛、膽大自負、一根筋等等。可以說,“高啟強”這個人物形象作為一種頗具“精神分析”意味的隱喻,折射出的是“男人”身份的無限焦慮,有關尊嚴,有關認同。
《狂飆》幾乎是一部由張頌文的表演撐起來的電視劇,我覺得今日的張頌文很像中國話劇史與電影史上的“一代名伶”石揮。張頌文與石揮對表演并無太多學識與學歷的標榜,有的都是從生活中來、到藝術中去的表演哲學。他們對生活有自己切膚的體驗與理解,對人性有深刻的省思與警醒,對情感有敏銳的感悟與表達。張頌文塑造的“高啟強”與當年《黑洞》《黑冰》里分別由陳道明和王志文塑造的“壞人”形象又有所不同,“高啟強”更加“草根化”。因此,我覺得高啟強也可能是一個“壞”到“深情”的“壞人”。所謂“深情”,是指高啟強代表了一類毫無背景卻試圖堅持自己做人原則與底線的人,可是“這樣的人”在現實生活里卻常常少有人會向他們投去“理解”與“贊賞”的目光。用高啟強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他從來沒有過尊嚴”。
劇中的高啟強曾經認為,他拜的干爹“泰叔”買下一家夜總會送給他,是他有尊嚴的開始。其實這個時候的高啟強已經在徹底“黑化”的道路上完成了自己的心理建設,所以他把自己與“泰叔”的第一次利益交換視為自己找到“尊嚴”的起點。然而我覺得,2000年除夕夜,安欣給高啟強的那盤餃子才是高啟強感受尊嚴的開始。安欣的這個舉動,讓高啟強即便在“黑化”之后都認為是值得拿出來偷偷溫暖自己的最美好的回憶。《狂飆》的故事,從這盤安欣給出的餃子開始,也以安欣20年后在看守所給出的另一盤餃子結束。而縈繞在高啟強內心最不安的疑問恰恰就是“如果我還是舊廠街那個賣魚的阿強,你會不會跟我做朋友”。我們絕不寬恕十惡不赦的壞人高啟強,但我們在各自的生活現場里卻總能看見很多“賣魚的阿強”。高啟強被飾演者張頌文拿捏均衡,這種豐富內斂的表演感,賦予這個角色無盡的余味,任人品咂,也讓我們反省各自的人生現場。
值得討論的,或許還應該有關于“自尊”的話題。我相信,人,生而有自尊。自尊并不復雜,它就是一個人把自己當成獨立的人來尊重。只有懂得尊重自己,才能進一步發現自己與理解自己,并且最終與自己和解。與自我和解是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表現。《狂飆》劇中的好人與壞人都是人,都各自有著對自尊的不同認識與執著。當然,受制于題材與創作空間的局限,《狂飆》的重點當然不是在探討“自尊”這個話題,但是我總覺得對觀眾而言,當我們品味“舊廠街”的人們對“生活之網”的無奈承受與掙扎的時候,“自尊”可能是他們最后保護自己的方式,當然也可能是最后毀滅他們的方式。
我也尤其欣賞《狂飆》對底層人物面對窘迫生存環境的藝術表現。“舊廠街”的生存環境是逼仄的,《狂飆》在有限的篇幅中完成了對都市平民“生活碎片”的展示。很多“壞人”似乎根本無力做出任何選擇,只能被一種無形的力量牽制著、引導著,因為這就是他們的生活。諸多“形而下”的生活所求與煩惱淹沒了人物幾乎一切對人生的希冀與追求,而所有這些生活的碎片都被一種力量控制著,那就是物質的力量。身處在由強大物質力量支配著的“生活之網”中的“高啟強們”,似乎是純粹的“被動存在物”。這種生存狀態的實質在于將生活的全部意義歸結為生活本身——生活不再是理想,不再是“形而上”的追求;生活不再有詩意,不再有終極的價值。現代社會某種基于身份與資本的社會流動,容易導致個人作為生活的主體逐漸喪失鮮明的主體性,主體人格的不健全導致人物在“生活之網”中的走失。《狂飆》中的大多數反面人物基本上都是走失了“自尊”的不知所措者,他們獲得尊嚴的方式其實常常具有最深的遺憾和最大的痛苦。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生活與人性能夠對“賣魚的阿強們”報以更大的、善意的尊重與撫慰,可能高啟強與安欣就能坦然而大方地成為朋友。
(作者單位:南昌大學)